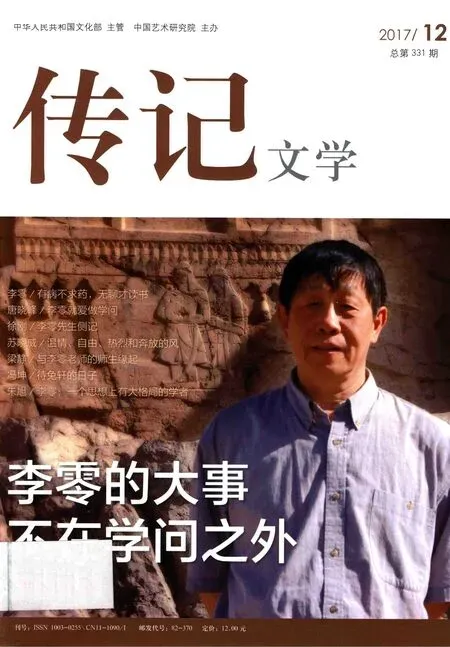李零先生侧记
徐 刚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
李零先生侧记
徐 刚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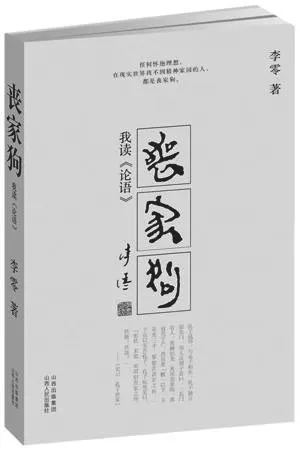
李零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书影
李零先生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不过,我认识先生的时候,他虽然已小有名气,但还不像今天这样明明赫赫。也许可以说,我是目睹了先生从一名普通的北大老师,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学者的艰辛历程。
我于199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读本科。当时的古文献专业,负担着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就是整理全宋诗。在化学北楼的西侧,有一个半独立的小楼,小楼的一层有一个古文献研究所,就是整理全宋诗的主要办公地点。那时候,古文献专业的老师如果来学校,基本上不去五院的中文系,因为五院只是系行政办公的地方,每个教研室只有一个小房间,老师是不可能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的。因此,这个面积并不大的古文献研究所,就成了我们专业的师生们经常出没的“据点”。
今天中文系的师生们说起全宋诗的整理工作,很少有正面肯定的。不过,我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情形,却又别是一番滋味。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觉得这话有失偏颇。大学可以没有大楼,但决不能没有一个供师生们经常交流、聚会的地方。由于古文献的老师们无论是否直接参与全宋诗的整理工作,来学校时,都会在这里歇脚,喝茶,因而这个小小的地方,很自然地成为凝聚师生共同体的一个精神家园。推开歪歪斜斜的门,右手是古文献的“大管家”崔老师的屋子,这个屋子很小,实际上是专业主任倪其心教授和崔老师共享的。每次去那里,几乎都能见到两人坐在那里喝茶,聊天。屋子的主体是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四周都是书架,中间是好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书桌和书架上堆满了书,过道上也到处都是,东一堆西一摊的。记得右手边有一间办公室,孙钦善老师经常在那里,还有管资料室的刘老师,好像也常驻那里。整个屋子拥挤不堪,但是有一种温暖的气氛。我们不但在那里跟老师见面、上实习课,还可以随时借阅专业书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向那里的老师以及师兄师姐们请教。对于一个刚入学的大一学生来说,这真是一个理想的求学之地。
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李零先生的。
先生并不参与全宋诗的整理工作。那时的古文献专业分两个研究室,一个是古文献,一个是古文字。先生是属于古文字研究室的。那时候,北大中文系的古文字学是全国最好的学科,裘锡圭教授是带头人,下面有李零先生和李家浩先生两位中青年学术骨干,还有沈培先生,他刚刚留校,是年轻的后起之秀。虽然只有四个人,却足以令任何一个兄弟院校艳羡不已。他们也是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最有荣誉感和骄傲感的几位学者。
不过,那时候的古文字学,还远远不是什么显学,虽然我们有最值得尊敬的学者,但真正想要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却并不多。我至今还记得南门口的教材部,有一个卖书的地方,上面有一排一排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大概是两毛钱一本,就是没人买。我买了几本,后来不知道都去了哪里。这批书中的大部分后来流入了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5毛钱一本,我至今还藏着两本。这虽然是个细节,但是可以知道那时的学者,虽然学问很好,但是要出名,却是很难的。
先生那时住在蓟门里小区,骑自行车来学校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所以每次来学校,就很自然地会到所里来休息。那应该是2月份刚刚开学的某一天。当时中文系要求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每人要写一篇学年论文。我那时对古代神话很有兴趣,班主任李更老师就向先生推荐了我,希望他做我的指导老师。我那天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去所里找他。到了附近,看到有两位年轻的老师在门口的空地上打羽毛球(先生说,他不记得有打球的事,但是我却记忆很深,不过,细节也许有出入,也可能是在聊天)。一位是刘英老师,还有一位就是先生。天气很冷,但是户外有太阳,而且阳光很好,空气也还是很清新的年代。在冬天的气息里,这一幕非常亲切。只是当时我们还并不认识,所以我一个人进了屋。屋里除了书的香味,还有一股浓浓的茶味,几个老师在看书。先生很快就进屋了,我才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人,而且马上要给我们讲授《孙子兵法》专书课。
北大的学生对老师的要求是很挑剔的,不仅要求讲的内容有学术水平,还要讲得生动,有趣。但是说老实话,我们这个年代的青年学生,读过几本古书,研究过几个问题,对于学术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呢?所以一个学者能否被欣赏,往往并不是取决于他的学术水平,而是他的“名声”。名声往往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平高,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资源网,这个网络就好像是一个放大镜,能把一个火柴棍放大成为一根顶梁柱,让你觉得好像一个学科的学术都是由他一根大柱子撑起来的。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前,一般人看到的只是这些放大了的火柴棍,要经过多少对比,浪费多少时间,才能看清楚火柴棍和顶梁柱之间的区别呢?因此,那些真正了不起的学者,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坚忍和努力,才能从中脱颖而出。
《孙子兵法》这门课,给过先生深刻的“教训”。1985年,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就是讲《孙子》。他自己说:“人太嫩,名太小,地位一点没有。”1986年,备课一年,开始给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讲课,“人很少,大概只有十人左右。当时,出于对北大的敬畏,我想学术一点。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讲《孙子》中的疑难点,但效果不理想。第二堂课,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叫韩振宇,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他来,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韩说,同学们反映,您的课太深,听不懂,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委托我跟您讲一声,我们都很忙,以后就不来了。”这是先生来了北大后头一回开课,“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幸好还有另外一个法国学生,叫魏立德,后来成了真正的专家。
先生后来陆续出版了《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等著作,这是讲授和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
我对这门课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还记得当年跟他去所里领取《武经七书》,发给同学们的情景。他的这门课的确不如他现在讲课这么幽默生动,但却非常朴实、扎实,只要认真听他讲课,就会觉察到他深厚的学术功底。比起当时很多通论性的课,这门课要实在得多,视野也开阔得多。我想,后来顾青、张大超、田天都跟他做《尉缭子》《六韬》等兵书研究,肯定是受他的课的影响。我当时就得出一个很粗略的印象,觉得李先生在研究古典的学者中属于那种既有深度,又不迂腐的难得的专家。
古文献专业的老师大多和蔼可亲,但是像裘锡圭先生那样的风格,不怒而威,俨然令人望而生畏。我那时非常崇拜裘先生,但如果没有学术上的问题,是不敢轻易接近裘先生的。而李零先生的风格,就温和多了,跟他谈话,有如沐春风之感。可能很多同学跟我有同样的感觉。1996年我们本科毕业的那年,古文献专业照例有一个“谢师宴”,老师们都会参加。散席之时,我就到先生面前,想跟他多聊一会儿天,没想到同学们都围上来,围成了一个圈儿,我反倒说不上几句话。本科时代与先生的缘分就这么尽了,直到2002年跟先生攻读出土文献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先生讲课风格的改变(我认为他的讲课风格是发生过非常大的变化的,不知道先生自己是否会同意这一点),我印象中是跟他研究方术有关。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古代的方术,不久就开设了“中国古代方术研究”的课程。方术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因为这是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但又罕有人涉足的领域。先生的方术课,我听过不止一次。那时也经常有考古系的学生来听课,其中有一位叫沈睿文的学生,我们当时不熟,但后来成为好朋友。先生研究任何问题,不管前人是否已经涉足过,他总能找到一个非常独到的切入点,而且能提炼出极其新颖的思想。我猜想,研究方术,不仅开拓了先生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增加了他的学术自信,使得他开始以一种非常轻松和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古代中国的各种问题。一个证据就是他的讲课风格也开始变得生动、新颖,开始将深刻的学术和生动的话语风格结合起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先生的杂文大体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闻名于世的。199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放虎归山》。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出版了《花间一壶酒》《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回家》《大刀阔斧绣花针》等多部杂文集。他也是书评杂志《读书》的重要撰稿人。他的杂文,学识渊博,思想深刻,角度独到,尤其是生动的文笔,举重若轻,摇曳生姿,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先生没有给《读书》杂志投稿,当时的很多读者评论说:“《读书》没有了李零的文章,已经没什么可看了。”其影响可见一斑。
《方术考》这部著作(还有稍后的《方术续考》)和“方术考”这门课,仅仅是个开始。1996年,先生从古文字研究室转到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出土文献。当时,古文献专业的主任倪其心先生建议他开设一门“出土文献与学术史”课,这对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有莫大影响的。2004年,先生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就是他在北大多年讲义的基础上整理的著作,这部著作对中国源头时期的学术史做了非常新颖而深刻的阐述,梳理了早期中国的书籍、知识、思想的源流及其特点,提出了很多富于思想性的创见,体现了他把握学术研究总体框架的能力。这是真正可以代表先生研究水平的著作。

李零在伊朗古尔城
我个人觉得,先生的“出土文献与学术史”课,已经真正展现了他丰富的思想和生动的语言相结合的特点。听他的这门课,是前所未有的享受,好像晒着日光浴,徜徉在学术的大海里。之后他开设的“《论语》选读”等课程,生动性时有过之,但是博大精深方面,却明显不如。《论语》课的讲义,后来也出版了,就是备受争议的《丧家狗》一书。
2007年,《丧家狗——我读〈论语〉》出版。这部著作的书名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可惜的是,反对这部著作的人大都只是反感书的名字,他们并没有理解“丧家狗”的含义,更没有耐心去理解书的内容。因此,反对基本上是一种情绪的谩骂。先生自己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其实是对孔子一生处境的准确概括。虽然颇受误解,但这部著作仍然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这部著作出版前夕,我和他曾一起跟出版社工作人员见了一面。我建议他不要用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担心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先生说,这部著作,就是要给当时盲目的传统文化热降降温的。要热爱传统,首先要了解传统,实事求是地评价传统,而不能像当时社会上的很多“名流”一样,书都没有读懂,就到处当导师,开学院,让幼儿读经书,以弘扬传统文化自居,本质上却是吃祖宗卖祖宗的有意无意的骗子。“丧家狗”这个词,也许可以引发很多人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早在两年前,先生就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作过一个《说话要说大实话》的演讲。《丧家狗》出版前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一次《传统为什么这样红》的演讲,都是一以贯之的意思。
也正是痛感流俗对于传统文化的误解,先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写了“我们的经典”系列,整理了古代中国的“四大经典”:《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这四部著作,解释简明准确,论述生动有趣,是他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纠正流俗的错误观念而撰写的著作。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聆听先生的授课了,好在他的讲义,总是能以各种方式发表和出版。近些年来,先生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他已经可以自由地出入“三古”领域,即他所说的古文献、古文字和考古。先生很早就在古文字学上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早年的《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就获得过吕叔湘语言学奖。他还曾经为了调查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专程去美国调查。他研究楚帛书的一系列著作,已经于2013年底,结集为《楚帛书研究(十一种)》,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2017年,又出版了《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这是他目前研读楚帛书的最新成果。先生在考古方面的贡献可能更为人称道,他的两部论文集《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和《万变》(三联书店,2016)可以作为代表。2006年在香港出版的《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从复古思想的角度研究考古艺术,也提供了非常有启发的艺术史研究思路。
先生最近的代表作,应该是四卷本的“我们的中国”系列。读这几本书,我有一种“迷糊”的感觉,时而觉得自己站在学术之巅,时而又觉得自己漂流在思想之海。有思想的学术,应该是很多学者毕生的追求,但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只是在用一种具体的材料重复别人的思想而已。而先生现在的思考,已经将对古代学术的研究与对当代国家命运的思考融为一体,已经进入了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他的写作风格,也已经将严谨的学术讨论与摇曳生姿的杂文笔法结合得越发天衣无缝,圆融无碍。
先生自述其主要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但更准确的概括,也许应该说,他是当今少数几位能够熟练地将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化的全方位研究的学者之一;而先生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独到的切入点,在当今学者中罕有其匹,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加上他多年勤奋的耕耘,使得他不但硕果累累,而且每一部学术著作总是能给人以思想和方法的启迪。我认为,这是先生在学术上最值得肯定的一点,也是他能够获得今天荣誉的最重要的原因。
先生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人。他的杂文《学校不是养鸡场》,蜚声知识界,脍炙人口。这是一篇对错误的改革直接说“不”的檄文,充分显示了先生的智慧和胆识。前些年北大沸沸扬扬的燕京学堂事件,先生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话,参加反对活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公平的事件,他也常常挺身而出。出版了《战国文字通论》的何琳仪先生,在古文字学界很有影响,但是却长期评不上教授职称,先生就在自己的杂文中为他抱不平。北大蓝旗营的住房,由于劣质施工,给老师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先生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很奇怪很多教授不敢说话,息事宁人,甚至自己不出头,却想趁着别人的努力,坐顺风船,让他大跌眼镜。先生曾跟我们几个学生说,如果你们看到不公平的事件,应该努力站出来说话,尤其是为弱势群体。如果你受到压力,保持沉默,那也可以,但是说话就要说大实话。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李零和学生们在一起,后排左四为本文作者
2013年,先生已到退休年龄,他接受了北大中文系的返聘,继续任教和研究。但是先生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他的手抖,我一直以为他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先生说他祖父、父亲都有祖传震颤。最近一些年来,胃、膝盖、眼睛也出现问题。北京又是看病极其困难的地方。先生跟我说过,医疗是个大麻烦,北大医院,他基本不去,因为有些大夫,看比不看更危险,比如今年春节骑自行车摔过后,外科只管让他不断核磁共振,没有任何建议和治疗,直到现在都没好。他的医疗问题,当时是孟繁之先生提醒我跟系里说说,系里告知我学校马上要聘先生为人文讲习教授,医疗问题就可以解决了。2016年4月,先生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不过,先生自己,却一直对美国颇有微词。
我读博士的时候,他曾经托我校对一部小说,是高沐鸿的《少年先锋》。高沐鸿是狂飙社的成员,与先生的父亲是同乡。《少年先锋》的主人公,其原型是先生的父亲。那时我才略略知道先生的一点家世。后来觉得先生对于国家民族的很多思考,可能跟他的这种出身有密切关系。先生早年在“文革”时参加过学生运动,跟我们几个学生描述过当时目睹的一些红卫兵的事情。在插队时还学习《资本论》等马列著作,不仅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也是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使然。他的有些朋友,是跟他一样“在大院中长大的”,比较能相互理解。在“我们的中国”这个系列丛书每一本书扉页上,他用闻一多的诗《一句话》作为主 题引子。在他的《鸟儿歌唱》等杂文集中,都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和态度。当然,我这种血统论的解释,是非常浅薄的看法,未必正确。
先生如今誉满天下。他的朋友可以说是遍布世界。他的学生中,也有一些已经成为优秀的学者,而我算不上是他的得意门生,只是忝列门墙而已。他的学问,既广且深,我想我未必能懂得他的全部,尤其是他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他的朋友张木生先生曾经写过一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的专著,不过李零先生自己是否认为这本书能够代表他的观点,我不知道。而且,那本书是2009年出版的,如今的李零先生,我想,他的思想可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且看他自己的新作吧。
2017年11月11日夜
写于九龙寓所
责任编辑/崔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