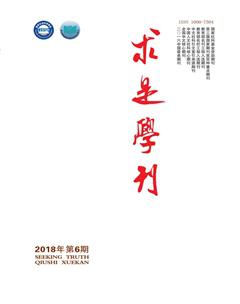公民与私人: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的双重向度及其辩证关系
景剑峰 赵东海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现实的人;公民;私人
作者简介:景剑峰,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呼和浩特 010021);赵东海,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呼和浩特 010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东正教人学思想演变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7BZJ02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6.002
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对于马克思人学思想史的梳理和挖掘并不均衡,尤其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的人学思想的研究展开得还不够充分,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1841—1843年的思想蜕变界定为青年黑格尔派阶段,其实,马克思早已悄然扬弃和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在政治人学方面提出许多原创性的思想表述,这些宝贵思想非常值得重新咀嚼。聚焦于马克思的1843年,会发现这一年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年份,在这一年马克思做了两件大事——与燕妮结婚和创办《德法年鉴》,因此,这一年也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思想的德法年鉴时期,期间他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多篇重要理论文本。其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而《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发表在次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初步探讨了人的解放问题,并勾勒出从宗教解放到政治解放再到市民社会解放这样一条线索。解放的结局是犹太人从精神中解放出来,德国公民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但是,马克思的表述并不像一般政治学家那样给出一个肤浅的结论,而是反复强调“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政治解放最终是要回归人的本质、实现人的本质。所以说,1843年马克思思想表现出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不断的逻辑递进,然其内在里却隐含着一种坚定的人学立场。
一、从抽象人格到现实的人
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就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思路,集中火力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可以说,1843年马克思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唯物史观,他还在吸收前辈又批判前辈的哲学营养的基础上毅然前行,但是敏锐的他已经渐渐发现了前辈尤其是自己精神导师黑格尔哲学的症候所在,他认为黑格尔法哲学的命门就在于立足于一种抽象人格,所以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重点就是黑格尔的抽象人格。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由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部分组成的,这分别是自在自为的自由的意志运行的三个阶段。其中,自由的意志的直接的概念体现就是人格,而人格的定在就是外在的抽象法领域。黑格尔在这里特别强调他所说的人格的人不是自然意义上的Mensch,而是法的意义上的Person。1“Person”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古罗马时期拉丁文原文是“Persona”,其本义是面具,后引申为容貌、身份、个性等,在中世纪哲学中“Person”主要指三位一体中的位格,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本主义的兴起,“Person”也指人格、个性、个体。现代英文学术文献中“person”既表示人也可表意人格,后来英文中又演变出“personality”来专门表意人格。黑格尔本人明确指出:“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毕竟我全然是纯自我相关系;因此我是在有限性中知道自己是某种无限的、普遍的、自由的东西。”2显然,黑格尔是在抽象意义上凸显了人格之人的个体性、独立性和自我反身的特征,尽管他补充说在有限性中有无限的东西,但是毕竟是一种抽象的表达。黑格尔所谓的人格的致命失误就在于只看到了抽象的人格,而没有看到具象的人本身。所以马克思敏锐地指出:“人格脱离了人,自然只是一个抽象,但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的理念。”3
此时,马克思目光如炬地发现,黑格尔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人格”脱离了“人”,前一个人是抽象的人,后一个人是具象的人。当然,马克思这里沿用的是黑格尔的术语,“人格”是用拉丁文“Person”表示,“人”用“Mensch”表示,相应的俄文译本中是“Личность”和“Лицо”, 4前者是抽象的人,后者是具体的人。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人格”只有“作为人们”的时候才有现实意义,才是现实的观念。当然,这个作为人们的人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社会的人,但此时马克思更多运用的是“类存在”这一费尔巴哈式的概念,以期表达社会存在意义的人。另外,黑格尔将抽象人格作为抽象法的主体还只是其法哲学体系的开端,他最终的目标是抽象法和道德相结合的伦理,尤其是伦理的最高阶段——国家,而在国家中君主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对于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马克思认为这种观念化身的神人似的君主并不能承载全部的自我意识,因为“主权,国家理想主义,作为人、作为‘主体而存在,自然是作为许多人、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因为任何单个的人都不能把人格的整个领域容纳到自身”。5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这个人格还是一种“实在的存在”,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体”(υποκειμενον)。1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υποκειμενον”其实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哲学范畴,在古希腊文中是充当主词的,而不是充当谓词的,该词有“载体”和“主体”的双重意蕴。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是υποκειμενον,才能成为现实的人。当然,馬克思这个时候所认为的“现实的人”还远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个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的人,而是指构成国家本质的“人们”。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将君主这个肉体存在物视为先天必然的规定这一思想,反讽黑格尔是将不合乎理性的东西论证成为合乎理性的东西。那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着力强调的作为现实的人的“人们”到底是谁呢?在此,马克思所作出的回答依然沿用的是黑格尔的术语——市民和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cellschaft),并认为:“‘等级要素就是市民社会向国家派出的代表团,市民社会作为‘众人是同国家相对立的。这些‘众人时时刻刻都应该有意识地把普遍事务作为自己本身的事物、作为公众意识的对象来对待,而这种公众意识在黑格尔看来,只不过是‘众人的观点和思想的经验普遍性。”2黑格尔的基本态度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公民高于市民,为了补救市民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促进民众的普遍利益,国家可以干预市民社会。3相应地,黑格尔对于市民之人民持鄙视的态度,他认为所谓的市民不过是利己主义的私人。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恰恰要弘扬市民这一现实的人,认为市民不是群氓,而是一种共同体。当然,这个共同体能否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为状态的关键还要看这群人能否完成思想的变革,能否成为一个有思想的阶级。只有思想和阶级、理论和群众结合起来,这样的阶级和这样的群众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很少用市民来说明现实的人,而是用思想改造后的无产阶级来说明现实的人,这样的表述在文章中比比皆是。同时,这个人是市民和公民的复合,是感性的法人,是自在又自为的人。对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做出了全面的解答:“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的人,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予以承认。”4 承认人的利己性才是扬弃抽象人格还原真正人的第一步,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也就此展开。
马克思早期政治人学的逻辑起点恰恰在于批判了黑格尔作为抽象人格的國家君主,而且是目光向下聚焦于作为“众人”的市民,而市民一旦经过哲学的思想改造就会实现升华,扬弃了自身的自利特征,变成了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者,变成了手持批判武器的进行武器批判的无产阶级,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完整的人、现实的人、从自在到自为的人。
二、人解放的双重向度:公民和私人
1843年间,马克思探讨人的解放的路径设计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1843年,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等文章,文章中提到的犹太人解放的基本思路是放弃犹太教,改宗基督教,然后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合法公民,这样就获得了犹太人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这样的解放模式幼稚可笑,更为关键的是鲍威尔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总是将现实的批判归咎于观念路线,依然是在唯心主义的老路上打转转,总是把宗教问题置于国家问题视域内考虑,而没有找到真正的批判着力点。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哲学以及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于人的解放的基本思路。概括起来,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有三个阶段的区分,分别是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市民社会的解放,而三个阶段表征出来的恰恰是公民与私人双重向度的内在变奏。
马克思所谈的宗教解放主要是针对鲍威尔的。鲍威尔认为,从犹太教信徒转变成基督教国家的公民就可以实现宗教解放,而马克思认为这还只是在宗教范围内打转转,宗教不是国家的前提,而是国家的表象,所以不是通过宗教解放来达到政治解放,而是通过政治解放来实现宗教解放。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是将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关系本末倒置了,更没有深入到对国家、政治和法本身的人学批判上来。“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质,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了。”1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缺陷只能在宗教国家本身的本质中去寻求,因为宗教不是世俗国家的原因,而是其现象。所以,犹太人解放的方法论就不再是世俗问题神学化,而是神学问题世俗化。一旦如此,国家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国家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只信奉自身,国家就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本质。所以到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2当批判的矛头从宗教批判转向法的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时候,马克思发现政治批判并不能建立终极真理,所以他要不断寻找政治前提的前提,不断推进政治人学的前提批判。黑格尔将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有限性,而马克思则反复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都是颠倒的。”3
马克思在此强调市民社会的前提性意义,这一观点又非常接近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式传统的政治哲学观,因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市民就是以经济为主导的利己主义者,所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强调的“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4而这个现实的人其实是国家公民和市民社会之私人的结合物,并不是片面的任何一方,因为单纯的国家公民则具有过多抽象性,单纯的私人则过多工具性。如此看来,“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且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5马克思这一大段表述所要实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综合,即将国家主义传统与资产阶级私人产权传统综合起来,并扬弃各自的弱点,综合为一个崭新的现实的人的复合体。国家的公民具有公共性和类的特性,但是这种公共性过于抽象而脱离现实,并且还不是终极前提,甚至容易堕落为简单的君主主权;市民社会的私人凸显了私人性和个体性,但是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容易将他人以及自己降低为私利的工具。马克思将“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两个词着重指出是别有深意的。在马克思看来,解放后的人是公民和私人的结合,但是私人和公民之间也是有区分的,私人是公民的前提和基础,是在市民的私人人权确认的基础上的共同体建构。既然如此,那么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政治解放和市民社会解放的双重结合。马克思反对单纯的政治解放,而是要将政治解放与其基础的市民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并让市民社会中的那个特殊阶级肩负起革命实践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个特殊阶级就是市民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并且是要经过理论武装和精神洗礼的无产阶级。
三、“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在1843年的著述中谈到人的解放问题时,马克思有这样的表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但是在行文中马克思又没有紧接着作出具体解释,如什么是人的最高本质,什么是人回到人自身。然而,通过对这一时期文本的综合考量,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正是强调人要克服人身上的非人性,然后回到人本身,实现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市民社会中人的对象化和异化特征:“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既然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具有异化特征,那么市民社会中的人权也是如此,总是一种私人的利益和任意。马克思所谈到的人的异化特征一般可以归为市民社会的异化、国家主权的异化和宗教的异化。当然,马克思这一时期所表述的宗教异化思想更多的是来源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而异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己的本质的疏离和分化,这也是过分强调私人的内在病灶,当然这一问题的批判主要集中于1844年及其后。
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是从批判黑格尔的人格范畴出发的,而人格范畴要从自在进入自为状态,最终的目标是自由。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有对历史上法权社会的追溯,并指出,中世纪时国家和市民社会没有很好的区分,人民生活和国家生活是直接同一的,而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了,并且人格在其中也分裂了,而在更高形态的社会中,国家和市民社会达到新的统一,人格的公民权和私人权也成为一体,人的最高本质,也即人的自由得以实现,人也就進入解放状态。当然,马克思这时候的历史观还没有得以清晰系统的总结,但是我们从其文本可以归纳出一条线索:当中世纪人民生活和国家生活直接同一时,人是一种自在状态;而当现代文明(资产阶级社会)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时,人是一种自为状态;只有到了更高形态的社会中,市民社会和国家才能重新同一,人才能进入自由状态。马克思在1843年所进行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市民社会批判,都是反对宗教、政治和市民社会对人本质的背离或者异化,这些与人本质疏离所导致的共同结果就是人进入了不自由状态。马克思这一时期所谓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实是指复归人的自由本质,而这种自由本质又不是单纯的西方文艺复兴语境中的个体自由,而是一种保障私人权利基础上的共同体自由。因为马克思在1843年的著作中分外强调“众人”“人民”“阶级”,用这些概念来克服市民社会中私人所带来的工具性异化。当然,这一时期对共同体自由的表述还并不成熟,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中才有了清晰的表述,如“代表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马克思在这里同样强调的是从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共同体的自由,这同样是公民和私人的结合。所以,只有实现了人的集体自由,人才算回复到了自身,回复到了人的最高本质。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一生著述的隐含线索就是对人的本质的探究,并做出了科学系统的自我回答。“马克思伴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生,对人的本质问题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积淀,成为哲学史上科学地阐释人的本质的第一人。”3
四、公民与私人双重向度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早期政治人学从抽象人格到现实人格以及公民与私人的双重变奏,最终是人的解放的完成。对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中公民与私人的辩证关系可以做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解。
首先,公民到私人、抽象人格到现实人格是潜能与现实(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的关系。抽象人格是潜能状态,是未有而能有;现实人格是实现状态,是“现有”而“永有”。抽象人格虽然是潜在状态,但是已然包含了现实人格的内在规定性,但是在没有实现时则永远属于潜在状态,而不具有其现实性。所以,当人只具有抽象的政治人格时还不能称为人,还要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展开其具体生命形式,拥有其私有产权才算完成了其现实性。工人以及无产阶级虽然拥有政治人格的一般属性,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并不真正具有私有产权,所以还不具有人的现实性,不能说是人的完成。人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扬弃虚伪的私有产权,使得工人以及无产阶级真正和全体占有生产资料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马克思1843年之后一直到《哥达纲领批判》中都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次,公民与私人从形上学来讲是本体与位格的关系。公民尽管是抽象人格,但是若置之不顾,只是蝇营狗苟,那么私人和市民的异化性对抗结果同样是沉重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私人是利己的,从而也是非人的”,1这个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出了详尽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公民与私人不能二分,而是要统一在一起的,但是这种统一绝不是两个人的统一,而是本身就是一个人。在公民意义上是其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和实体性,在其私人意义上是具体性、特殊性、个别性和主体性。公民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但是私人就是指这个人或那个人,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成为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现实性。中世纪哲学把这种关系称为本体(Substance)与位格(Person)的关系,本体规定了人之为人的一般性,而位格是指成为那个人或那种人,不能生成位格的本体是空洞的,同样,没有本体则位格无以依靠。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关系被表述为实体(Substanz;Substance)与主体(Subjekt)概念的内在张力。公民是实体性存在,支撑了人的存在意义,而私人或市民是人的主体性的具体展开。
再次,最初私人扬弃了公民的抽象性,然而私人并不是逻辑终点,而是扬弃的新起点,共产主义最终恰恰是扬弃各自的片面性,回归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政治人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一个基本人学假设,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天然是政治的动物”,即作为一个人政治状态是其潜在的本然状态,当然亚里士多德这里的政治主要指城邦属性。但是在古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中,人只有获得财产权,成为私人,才能实现其自身的现实规定性,这是近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基础。黑格尔重视公民,而资产阶级学者看重私人,马克思认为二者本是一人,只是个体的不同面相和角色。公民是人之为人,私人是人之为那个人。梳理马克思1843年著述,我们可以体会出其早期人学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以及对于公民与私人向度辩证关系的深刻阐发,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人要扬弃抽象人格之公民进展到现实人格之私人,另一方面又迫切地感受到私人过分的欲望使其再度丧失掉人的本质,所以后来马克思反复强调要回归“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当然,对私人特征而造成的异化劳动则是集中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批判的,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资本论》等著作,大致都是沿着经济批判路径展开的。所以说,1843年已经埋下了政治解放向市民社会解放的伏笔,至于市民社会解放的具体方略则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进行了详尽阐述。可是市民社会解放的最终目标反过来还是要依靠政治解放这一手段才能实现,同时经济解放最终要获得更普遍意义上的政治人格,这是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的。政治批判与政治人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文献中都做出了完整的说明。所以,在理解1844年后的经济批判和市民社会解放时,就不能简单地抛弃政治批判和政治解放的维度,马克思一生对这两种批判和解放都是互为表里地统一处理的,不能单向度地认为后者扬弃前者。最终,马克思所扬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和私有产权,而“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2
马克思早期的人学思想是马克思全部人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考察的是政治、法、市民社会的人学基础,挖掘出现实的人得以解放的基本逻辑,即通过公民和私人双重向度变奏,成就一个自在自为的“感性的法人”,最终回归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不仅有鲜明的理论特色,而且对于理解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命题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