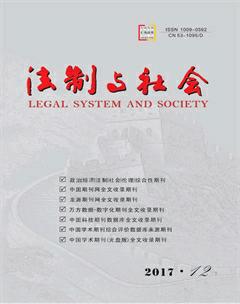我国行政规定研究之评述与展望
黄玉寅++司建明
摘 要 以往围绕行政规定的学术成果在研究立场上呈现出积极防御的进路,体现为聚焦行政法源地位的讨论、对行政规定种类的探究、困于效力的内外区别、偏重于监控模式的拟制四个板块的研究内容同时存在。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与行政法治模式的转变,通过行政规定回应真实世界的新的行政法学研究进路已然兴起。
关键词 行政规定 新行政法 研究立场
基金项目:本文是宁波市2015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行政规范后评估的宁波模式(G15-ZX3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玉寅,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政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司建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2.305
长久以来,公法学界有关行政规定 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大板块,对此四个板块进行依次探析可得知,迄今为止,行政法学界业已在学理上编制了一个巨大的防控网,意图将行政规定严密地覆盖起来。可见,行政法学界以往并不信任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彰显出对行政规定进行防御的研究偏好。
一、围绕法源地位的讨论
受行政法解释学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公法学者曾习惯于将行政法的基本理论与制度看作“一个预设的常量” ,习惯并善于对行政法的概念范畴进行定性分析。围绕行政规定的研究成果,对其稍加关注,就能看出上述法解释学的明显痕迹。如学者们过去总是纠结在行政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这一点。
在讨论法律渊源时,国内权威行政法著作呈现出两个规律,第一,通常将行政法源等同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第二,认为行政规定不是法的表现形式。权威著作中对行政规定“不姓法”的定性,虽然在晚近遭到了不同方式与程度的质疑,但该“通说”至今仍屹立不倒,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颁布,赋予了“行政规定不是法”的通说一个坚实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还道出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要想成为“法”,必须在制定主体、表现形式、制定程序甚至称谓上均符合一定条件。看来,《立法法》认为行政规定不是法或许是因为行政规定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表现形式上还不够格。
要理解这两点并不难。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罗豪才与姜明安两位教授就曾说过:“法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如果每个行政机关,以至于乡镇一级政府都能制定行政法,那就无普遍性和统一性可言,国家法制的统一就无法保障。” 应松年教授也指出,“把法的制定者限于高层级机关,表明了对法的合法性问题的关注,对‘法出多门的忧虑和抗拒。” 而刘莘教授基于行政立法应当具有固定形式的缘由主张,行政规定不是行政立法是因为其形式上的丰富与灵活性,故需警惕行政规定带来的副作用。 综上,国内权威行政法著作关于行政规定不是法源的定性,或者说认为行政规定够不上“法”之标准的主要原因,包含着学者对行政规定制定主体的多层级性与其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担忧,这某种程度上说明,权威著作对行政规定是持防范态度的。
此外,有一些著作倾向于从司法审判维度探究什么是行政法源。例如,有观点认为,“法律渊源涉及到的并非普遍公民的行为受什么样的规则管辖,而是法院在解决具体纠纷时应该适用哪些法律的问题。” 该种著作未将行政规定定性为行政法之渊源,理由或取决于行政规定不能作为审判依据或参照, 或基于行政规定对法院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总之,因为法院尚需进一步对行政规定的“合法有效合理适当”进行评判后才可适用,故行政规定不是法源。笔者认为,暂不论前述观点的适切与否,从需要法院审核、检测“合格”之后方可适用的逻辑不难看出,这些学者对行政规定仍然是不太信任——对法院来说,行政规定至少不像法律一样有着绝对约束力。我们认为,学界对行政规定的前述警惕、排斥心理与偏好是耐心寻味的。
二、关于行政规定种类的探究
行政规定的分类历来是有关行政规定基本理论研究的重镇之一。但迄今为止,学者们的分类标准仍存在着个体间的巨大差异。 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学界中曾经通行的分类标准还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流变性。例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行政法学者往往依照效力之对内和对外的不同,将行政规定划分为内部行政规定和外部行政规定。本世纪开端至今,“法律效果标准”逐渐演化、确立为行政规定分类的通行标准。按照“法律效果标准”,行政规定大致可分为解释性行政规定、创制性行政规定与指导性行政规定。目前,以“法律效果”作为分类的一种主导标准诚然可以接受,但将指导性行政规定与解释性、创制性行政规定视作平行的概念范畴却有商榷余地,因为在笔者看来,指导性行政规定乃是解释性或创制性行政规定的下位概念。据此,如果一定要接受“法律效果说”的通行分类标准,则行政规定仅有解释性规定与创制性规定两种。
一般来说,解释性规定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施法律、法規和规章,或者为了统一各个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理解及执行活动,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解释而形成的行政规范。” 既然是对上位法进行的解释,那么“这些行政规定的内容的规范性应该归结于其上位的法律规范”, 由此行政规定是法的组成部分。
创制性行政规定与解释性行政规定有所不同,它并非作为上位法的具体化,而是特指行政机关自主制定的,为公民创设了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 在这个意义上,创制性行政规定又称为“自主性行政规定”。在创制性行政规定缘何可以设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上,学界尚存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规定得创设公民权利义务的权力依据来自于宪法与组织法的规定; 另一种观点主张,除了应当具有宪法与组织法的依据外,前种权力仍“必须来自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某一具体法律条文,否则,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定不具有合法性。” 尽管存在两种分歧,但绝大多行政法学人还是保留着一条底线——包括创制性行政规定在内的所有行政规定均不得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
两种行政规定的分类表明:首先,解释性行政规定的精髓主要在于揭示——行政权乃是作为一种执行法律法规的权力(exe cutive power),是作为将法律予以具体化、精密化的权力;其次,创制性行政规定之制定权能源于上位法的授权,并且,创制性行政规定不得与既存之上位法相抵触。上述内容与法律优先原则之“上位法具有优越地位,其他规范性文件应遵照之” 的要求和立场如出一辙,符合法治国原则中有关公民与国家之关系应由法律加以规定的精神意涵。 正是从该分类之中,笔者深刻感受到公法学人对行政规定的防范情绪。由此观之,当前学界关于行政规定分类的学理探讨自觉地滑向了“法律之外无行政”的“控权论”领地,相关探讨折射出学者对行政机关“自我造法”的普遍担忧。
三、困于效力的内外区别
行政规定的效力问题也是以往理论研究的重镇,在行政规定之外部效力的有关理论中,“行政规定无权直接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或者说与相对人不发生关系,由此不具有外部效果”并非个别学者的零星观点。 诸多学者阐释行政规定不具有外部效果的理由往往是:行政规定在授权依据、制定程序、是否公布以及外在的具体表现等方面与法律规范存在差别,亦即行政规定作为非法律规范,其制定无需法律的授权,在形式上并不固定且不需要对外公布。 不难看出,前述学者乃是基于行政规定的种种“不规范”才忽视甚至否定行政规定具有外部效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政规定具有内部效力这一点,学人之间并没有太多分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部分学者据此主张行政规定是具有外部效力的。近年来,行政规定内部效力之外部化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此外,一些实务部门也开始承认行政规定内部效力的外部化。然而,这绝非表明学者对行政规定的存在不再担惊害怕,相反,鉴于“行政规定外部化现象”的势不可挡,行政法学人在理论上承认行政规定具有外部效力的同时,又开始对行政的外部效力进行缩限。如章志远教授认为行政规定的外部效力乃是事实拘束力而非法定拘束力,事实上的拘束力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通过严格说理机制逸脱出行政规定的效力染指。 王天华教授甚至认为,上级行政机关无权代替立法者消减下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的裁量权,由此,下级行政机关违反上级行政机关的以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裁量标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必然违法。 在他看来,没有说理机制似乎也是可以的。笔者以为,公法学人在行政规定是否具有效力、是事实拘束力还是法定拘束力上表露的纠结和彷徨,正是其对行政规定作出的学理抵抗。
四、偏重于监控模式的拟制
尽管从时间上看,我国行政法学对行政规定应当如何被监控的研究要晚于行政规定监控的制度实践,但目前,相比于实践中的制度推演,监控模式的理论拟制之进展更为迅速。
纵观已有行政规定之监控模式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其彰显出了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社会组织等作为核心监督主体,并以合法性标准、合理性标准、效益性标准等作为主要监督标准的研究样态;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还紧紧围绕着行政规定制定前、制定中、制定后这一连贯过程,发展出了诸如附带审查、直接审查、备案审查等多元化的监督模式,以及违法制定行政规定后“三足鼎立“的责任承担方式。总之,作为行政规定理论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长久以来堆积的有关行政规定之监控模式的理论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下时间节点,仍有很多学人继续辛勤耕耘在行政规定监控模式之拟定这片领地,试图继续编织一张巨大的防控网。因为,在实践中,行政规定被大量制定确实诱发了不良后果——“消弱了自身的稳定性、协调性与连续性,由原来的政出多门恶化为当今的法出多门,既增加了立法成本,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又人为地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和障碍。” 笔者认为,有关行政规定监控模式之研究成果上的丰硕,源自于学人对行政机关涉嫌“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的积极防备。“没有这样的权力(行政规定),行政机关就不能有效地完成它们所担负的各种任务” 的现实虽然被人们接受,但通过各种监控模式对其进行制约仍是一条公认的底线。
“每一種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 当前,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在原有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新的任务——即更为高效地实现民众的社会福祉,提升其生活品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应当适时进行创新转换,故今后在聚焦行政规定之时,行政法学者应展现出更多的宽容和睿智——研究如何通过行政规定达成给付任务、怎样经由行政规定分配公共资源,如何通过行政规定的实施,实现软法之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承认以往围绕行政规定的传统研究偏好,过多地折射出了学人心态上的片面和视角的单一,那么在今后,前述传统研究偏好就应当得到纠正。
注释:
本文所说的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的,除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之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
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构建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5).4.
沈岿教授精致地发现,《立法法》的对法范围的框定是在既有通说的影响下制定的,并不是立法者的首创。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218.
罗豪才、姜明安.我国行政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法源.法学研究.1987(4).
应松年、何海波.我国行政法的渊源:反思与重述.公法研究.2004(第二辑).6.
刘莘.行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11-12.
[美]格伦顿著.米健,等译.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54.
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2.
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6.
行政规定之分类所依据的标准,目前至少有:制定主体标准、制定目的标准、调整对象标准、公务性质标准、法律效果标准、制定权来源标准等。叶必丰、周佑勇.行政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69-77;陈丽芳.非立法性行政规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21-23.
周佑勇主编.行政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6.
朱芒.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中国法学.2003(1).44.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63.
例如,湛中乐教授在他发表在1992年《中国法学》第2期的论文之中,将行政规定界定为:“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的规定,或者依据自身的法定职权,为了行政的目的,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对不特定的事项作出一般性规定的决定、决议、命令和措施。”其中,根据自身法定职权即本文所指的来自于宪法、组织法的职权。湛中乐.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国法学.1992(2).109.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192.
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9.
此种要求的原因源自于:“我国的行政立法与法律相抵触的现象极为严重,而行政机关往往都乐于依据这些大量‘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造成了事实上的行政权由行政权自我规定。”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4.
在此意义上,日本学界普遍认为:行政规定(行政规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例外。室井力主编.吴薇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69.
孟鸿志.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4;张宝羊、时进刚.行政规则及其效力外部化初探.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12).52;值得注意的是,周佑勇教授尽管留意到了行政规定有时会发生一些效力,但他认为,这源于行政规则(行政规定)所确立的行政惯例和所体现的法律原则的效力。可见,他将行政规定本身当作效力的外部物质载体。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法律出版社.2008.70-71.日本著名行政法学者盐野宏教授也认为,行政规定(行政规则),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但与国民的权利、義务不直接发生关系,即不具有外部效果的规定。[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4.
日本行政法学者室井力教授基于行政规则与法规范存在的差异,认为行政规定构成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体系内部的“依法行政原理”的例外。室井力主编.吴薇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69.
章志远.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2).158.
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6).127.
袁明圣.行政立法权扩张的现实之批判.法商研究.2006(2).49.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82.156.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29.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著.杨伟东,等译.法律与行政.商务印书馆.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