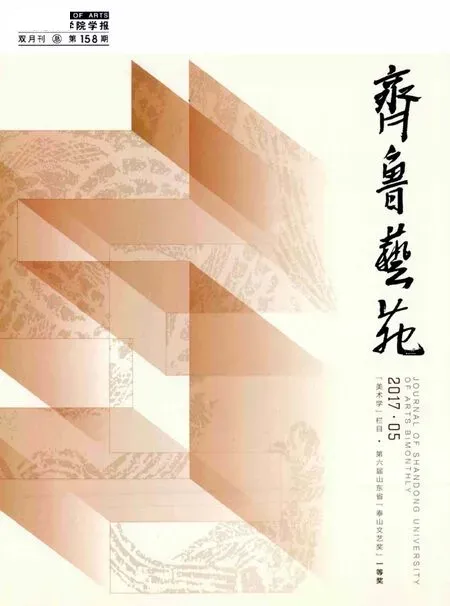千年风雨,斯韵犹存
——《写生蛱蝶图》流转考述
叶 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写生蛱蝶图》卷,槠纸本,设色,纵27.7厘米,横91厘米。*该数据为故宫博物院官方所公布的《写》卷尺寸,来源址:http//www.dpm.org.cn/shtml/ 117/@/6765.htm。《石渠宝笈》记《写生蛱蝶图》卷尺寸为高八寸六分、广二尺八寸三分。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三十二“宋赵昌蛱蝶图”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25册,第283页。该卷绘有秋花枯芦随风摇曳、蛱蝶轻灵起舞、蚱蜢昂头呼应,把秋日原野高旷简远、清新宜人的景色,描绘得十分动人。该卷整体设色清雅、用笔精微、造型传神、构图巧妙、变化自然,是传世至今的宋画精品,弥足珍贵。该卷并无作者款,赵昌仅“姓名见跋中”,*此跋文即为董其昌所题跋文:“赵昌写生曾入御府,元时赐大长公主者,屡见冯海粟跋,此其一也。”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三十二“宋赵昌蛱蝶图”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25册,第283页。因而是否确乎其人,历来众说纷纭。*《写生蛱蝶图》卷无作者款印,其后元冯、赵二人题诗亦未说明是何人所作,至明董其昌时始鉴题为赵昌所作,沿为成说。但徐邦达先生将该卷于传世的《粉花图》卷进行艺术风格对比,认为该图与史籍所载赵昌的艺术风格很不一致,且《写生蛱蝶图》卷仅在《石渠宝笈》卷三十二有所著录,因而认定该图并非出自赵昌而可能是出自徐熙传派之手。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辩》上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85-187页。天秀则著文指出:现代难以找到一副确定为赵昌的传世作品,因而难以通过艺术风格的对比来确定《写生蛱蝶图》卷是否为赵昌所作。该卷自董其昌以后一直确信为赵昌所作,这与相关史料的记载基本吻合,因而此说并非毫无根据。天秀:《宋赵昌(传)〈写生蛱蝶图〉》[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本文所采为董氏成说。但无论其说如何,此卷为艺术水准上乘之宋画精品、国之瑰宝则为古今共识,如《石渠宝笈》著录该画时即将其列在“列朝人画卷上等”之中。[1]
根据《石渠宝笈》等史料的相关记载及一众前贤的研究成果,《写生蛱蝶图》卷的流转虽称有序,*为便行文,以下简称“《写》卷”。2009年11月17日,该卷高仿真复制品曾被故宫博物院方面赠送给到访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该卷的关注。但对其流转细节及时代背景并未见有详细探讨,未免缺憾。今结合图中历代题识、相关书画著录和各种文献记载尝试勾勒其前后流转轨迹,透示历代藏家珍藏转让该图的复杂过程,期能为进一步赏鉴这一艺术珍品增加一些背景材料。
传为该图作者的赵昌(生卒年不详),字昌之,广汉人,工画花果,其在世时便颇有画名,号称“写生赵昌”。其画作不惟因年代久远,兼因“昌家富,晚年复自购己画”,在当时已为难得,传世至今者更是凤毛麟角。[2](P547)
欲知《写》卷流转,先应明晰卷中钤印及题跋情况,《石渠宝笈》记载详实:
……卷前有“皇姊图书”一印,又半印“存子孙永保之”五字,又半印三,俱漫患不可识。卷后有“魏国公印”、“秋壑”二印,卷中幅押缝有“汝明父”一印,前隔水有卷字十号,四字俱作半字,上钤之印半印,又“蕉林梁氏书画之印”、“家在北澶”二印,押缝有“新宇”一印,后隔水有“棠村审定”、“蕉林居士”、“张宇钧”诸印,押缝有“棠村”、“吴新宇珍藏印”、“安定”、“新宇”、“吴希元印”诸印。拖尾冯子振题云:“……命题。”下有“邗上张鏐黄美拜观”一印……董其昌观后有“苍岩子”、“蕉林鉴定”二印,最后有“松云居士”一印。诸跋中押缝有“冶溪渔隐”、“张伟鉴定”二印,又“汝明父”印三。卷高八寸六分、广二尺八寸三分……下有“乾隆辰翰”、“几暇临池”二玺 御笔题签,签上有“乾隆辰翰”一玺。[3](P282-283)
而《写》卷今存印鉴41处,题跋4处。其中朱文印32处,白文印9处;全印36处,半印5处;其中三方半印漫漶不辨,“新宇”及“女明父”二印各重复一次。总体情况与《石渠宝笈》相关记载基本吻合,*《石渠宝笈》将“张镠”一印误作“张宇钧”,另该书所载“松云居士”一印今卷佚去。具体情形详见表一。
表一《写》卷今存钤印情况一览表

②一作“女明父”,《四库全书艺术类分类索引》一书载有该印,但亦未载其所属何人。《四库全书艺术类分类索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册,第3592页。
由表中所列该卷所钤“魏国公印”、“秋壑”二印可知,该卷初为南宋权相贾似道收藏。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秋壑,台州人,为制置使贾涉之子,宋理宗贾妃之弟。理宗一朝,似道深得宠信,屡蒙超擢,仕途亨通。度宗感念其拥立之功,对其亦颇为优礼“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朝臣则“皆称其为周公”,可谓权势煊赫。[4](P13783)
两宋时期帝室对书画艺术颇为倾心,在五代各国所设画院的基础上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和书艺局。“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5](P505)的徽宗打破了“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6](P550)的旧制,亲身参与画事,“故一时作者,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7](P507)南宋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扰攘之余,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万机之暇,展玩摹搨不少怠”,因此“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此外“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间御府所藏图书,不亚于宣政时”。[8](P218)
北宋时,汴京城内书画经营活动就已颇为发达,如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相国寺,其“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十分热闹。[9](P138)城内西大街北的都亭驿“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10](P132);东角楼街巷一处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营销衣物书画珍玩犀玉”。[11](P133)南宋虽偏安一隅,但时人对书画之钟情较之北宋亦不遑多让。除前述高宗通过榷场搜集前朝流散字画扩充内府事例外,彼时临安城御街应市时“有三百余人设肆”,其中便有“做画”者,此外城中还设有专门的“纸画儿”行。[12](P19)北宋“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13](P7)南宋临安城内则不惟酒楼,甚至某些茶铺为了吸引顾客也开始张挂名人字画以装点门面、史载:“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14](P130)
这种时代背景下,贾似道也热衷收藏书画。其人不仅“酷嗜宝玩”,[15](P13780)且鉴赏能力颇强,时人评论他“收蓄书画妙绝古今,不特搜访详备,尤是目力过人,盖其相业虽误国,而鉴赏则称独步矣”。[16](P118)其当国之日,搜罗书画珍宝不遗余力,搜罗所得则筑半闲堂、多宝阁庋藏。似道当权之时,南宋朝廷已然积弊丛生、吏治腐败、贿赂盛行,“吏争纳贿求美职,其为求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似道私德不佳,对贿赂往往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贿,“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更有甚者 “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17](P13780)景定五年(1264年),似道加官太师,进封魏国公。从“魏国公印”一印可知贾氏得到《写》卷的时间应在其加官之后。至于该卷是其门客为其罗致而来、还是受贿所得,亦或是从何人手中以势相劫,则不得而知。
《写》卷中时间稍晚于“魏国公印”和“秋壑”两收藏印的是卷首的“台州市房务抵当库印”半印。所谓抵当库是指宋代的一种官营借贷机构,又称抵挡所、抵质库等,不一而足。其为太府寺“所隶官司二十有五”之一,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18](P3906)熙宁五年市易法推行,市务抵当库亦随之出现,业务为 “市易抵当”。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获罪被抄家,藏品皆没入官。龚子敬跋黄山谷书《庞居士诗卷》描述该印“卷首官印,德祐末籍其家(按指贾似道),凡入宫者皆有“台州抵当库印”。[19](P187)根据这一史料,徐邦达先生指出:贾似道是天台人(今浙江台州),其被抄家之时蛱蝶图可能藏于其台州老家而非临安,故所钤印为“台州抵当库印”。[20](P187)
该图被台州官府抄没之后,理应解送临安内府,但今图却并未见有南宋内府钤印。笔者认为:该卷于台州被抄没之后确被解送临安内府,但因为所抄没贾氏书画甚多、国家多事加之即位的恭帝年幼等原因,所以该卷虽入内府但未被品玩,故无钤印。
德佑二年(1276年),蒙古军攻陷临安,史载“(德佑二年)二月……辛丑……大元使者入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21](P938)当年十二月,南宋内府库藏法书名画被运往大都,并许京朝士借阅。元王恢《书画目录自序》就记载:
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图书、礼器悉送京师,敕平章太原张公兼领监事,仍以故左垂相忠式史公子杠为之贰。寻诏许京朝士假观。予适调官都下,日饱食无事,遂与左山商台符叩阁,披阅者竟日,凡得二百余幅。书字一百四十七幅 画八十一幅。[22](P534)
需要指出的是王恽《书画目录》一卷中并未著录《写》卷,这是否说明《写》卷佚入民间?笔者认为彼时《写》卷应仍在元内府,并未佚入民间。原因在于相对后世而言,元初去古未远,历朝翰墨名迹遗存甚多,佚名《写》卷虽称精品但在当时恐非出类拔萃,*该书著录阎立本、顾恺之、吴道子、王维、李思训、张萱、黄鉴、李公麟、赵估等历代书画名家作品共228幅,对不同藏品记载虽有详有略,但未见有如《写》卷这样既无年代又无作者款识的藏品 。因而王恽未将《写》卷著录于《书画目录》,甚至于王恽根本就没见过《写》卷也很有可能。
元内府之后,《写》卷由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喇吉(约1284-1331)[23]收藏,故钤有其“皇姊图书”印。祥哥喇吉为元顺宗答剌麻八剌之女、武宗海山之妹、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姊、文宗图帖睦尔之姑,其女又为文宗图帖睦尔皇后,地位尊贵,屡受厚赐,元史对此多有记载如“(至大四年)丁巳,奉太后旨,以永平路岁入,除经费外,悉赐鲁国大长公主”、 “(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朔,赐皇姊大长公主钞五锭,币帛二百匹”、“(天历二年)戊戌,以淮、浙、山东、河间四转运司盐引六万,为鲁国大长公主汤沐之资。”[24](P547)此外由于大长公主对汉文化及书画艺术颇为钟意,好收藏历代字画名迹,因而这些赏赐中除钱钞外还包含了大量的内府书画作品。通过研读元代侍讲学士袁桷为记录公主收藏所撰编《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可以发现其收藏品确实多为内府藏品,可为佐证。因而基本可以断定,《写》卷乃是通过赏赐的形式由元内府转移到大长公主手中。
大长公主好与文士交游,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甲寅,她在天庆寺召集魏必复、李泂、张珪、王约、冯子振、孛朮鲁翀、赵岩、袁桷、邓文原等诸多文士一同品鉴其所藏书画,是为著名的“天庆寺雅集”。前述《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对这次集会有详细记载: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鲁国大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钧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监丞李某为之主,其王府之寮悉以佐执事。豆静嘉,尊洁清,酒不强饮,簪佩杂错,水陆毕。各执礼尽欢以承,饮赐而莫敢自恣。酒阑,出图画若干卷,命随其所能,俾识于后。礼成,复命能文词者,叙其岁月,以昭示来世。[25](P600)
也正是在这次集会上,出现了与会的魏必复、李泂、张珪、王约、冯子振、赵岩等十四人在大长公主所藏宋黄庭坚《松风阁诗》卷上共同题跋的盛况。其中冯子振诗题为:“大苏门下士,真不愧涪翁。前日长风阁,依然谓诬风。前集贤待制冯子振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赵岩题诗为:“凉风高阁响钟笙,老墨犹思翠翁横。寄语分宁黄太史,何如紫极听秋声。赵岩。”[26](P152)通过将冯、赵二人《松风阁诗》卷题跋与《写生蛱蝶图》卷题跋的对比可以发现,二卷中的赵跋的书法结体、气韵、布局、所落名款颇为一致,冯跋亦基本一致,由此笔者认为《写》卷跋文与《松风阁诗》卷跋文极有可能同在“天庆寺雅集”这一日写成。而通过局部对比也可以发现:冯跋与赵跋字迹都是《写》卷工而《松》卷草,《写》卷藏锋用笔稍多于《松》卷。因而笔者推测当时名气更大的《松》卷应该次于《写》卷出现在集会上。*历代字画收藏,多重书轻画。北宋米芾就曾称:“余家收古画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幅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论赀用及他犀玉琉璃宝玩,无虑十轴名画。”米芾:《画史》[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13册,第14页。另结合题跋数量、作者名望等因素综合考量可知,在时人眼中,《写》卷地位逊于《松》卷当无疑议。当时的状况可是能是冯、赵二人题跋于《写》卷时,宴会进行未久,二人行笔较为谨慎工整。而随着宴会的进行,及至《松》卷出现时,宴会氛围已更为活跃,因而二人行笔也更为大胆飘逸。
《写》卷中在时间上次于“皇姊图书”印出现的是明内府“典礼纪察司印”半印。明典礼纪察司创设于洪武六年(1373年),《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六年)又考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置内正司,设司正一人,正七品,司副一人,从七品,专纠内官失仪及不法者。旋改为典礼司,又改为典礼纪察司,升其品秩”。[27](P1823-1824)对于该印为何只存半印一事,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称:“明洪武‘典礼纪察司印’,手卷中横钤在右下方边缘,大都只见末行‘司印’二字,亦偶见中间‘纪察’之半者 ;大约另外一半印文,是钤在执掌簿子上的。”[28](P37)《写》卷从大长公主手中如何辗转进入明内府已难详考。但从现有资料可以确知的是明太祖本人对于字画名迹并无特别兴趣,因而明初存于民间的字画珍玩并未大量的流入内府。洪武元年,明太祖定都金陵,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平定中原。徐达攻陷大都,并查封元内府书画典籍,将其运送至南京,史载:“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29](P2343)因而这一时期这批被接收的元代内府旧藏就构成了明代内府字画收藏的主体。以此反推可知,大长公主死后,《写》卷仍在大都而不是全宁路的鲁王府,可能为大长公主长居大都的后人所持有,也可能由于种种缘由再次回流到元朝内府,可以确定的是不太可能流落民间。不论为前述何种情况,最后都随着大都的陷落而成为明军的战利品,从而成为新王朝的内府藏品。
明朝中叶,四海宴安。在江南等文化经济发达的地区逐渐掀起了一股古玩收藏热潮,“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27](P654)其中字画尤受追捧,嘉靖时人何良俊(1506-1573)曾形容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31](P269-270)
而《写》卷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流转至徽州巨富鉴赏吴希元处的。吴希元(1551-1606),字汝明,号新宇,歙县人。吴氏好风雅,平时“屏处斋中,扫地焚香,储古法书名画、琴剑彝鼎诸物与名流雅土鉴赏为乐”。[32](P453)吴氏资财雄厚,收藏颇丰,王献之《鸭头丸帖》、阎立本《步辇图》和颜真卿《祭侄稿》等名迹皆曾为其所藏。那么《写》卷是如何为吴氏所得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应先明晰《写》卷以何种方式从明内府流出。其一,皇帝赏赐给臣下。如朱元璋就曾赏赐给晋王朱棡和黔宁王沐英家族大量书画。宣宗朱基瞻也常以书画赏赐臣下。其二,太监盗出宫外。史载:“成化末,太监钱能、王赐在南都,每五日舁书画二柜,循环互玩”。[33](P883)彼时南京留都尚有大量字画,太监钱能、王赐之流便监守自盗,造成大量字画珍品外流。其三,朝廷以内府字画折俸发给官员。嘉、万时期,由于库帑不足,就曾将抄没的严嵩旧藏字画折俸发放给武官。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34](P211)造成了内府字画的一次大规模外流。董其昌所藏郭忠恕《越王宫殿》即为外流字画珍品之一,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记载:“郭忠恕《越王宫殿》,向为严分宜物,后籍没。朱节庵国公以折俸得之,流传至余处。”[35](P121)由此可知,《写》卷因为类似前述的某种缘故从内府流出,其后辗转由徽商吴希元购得。
从图中题跋可知,约略在吴希元拥有《写》卷的同时,一代文宗董其昌(1555-1636)曾得见该卷。因而延伸出两个问题:一是是否二人都曾是该卷主人?假如二人都是该卷主人,那又是谁先得到该卷后转手另一人?董其昌与溪南吴氏过从甚密,[36]吴、董二人相识当无疑议。笔者认为该卷不太可能是由董氏转手吴氏,而极有可能是吴氏得到该卷之后请董氏品鉴,才使得卷中有董氏题跋。细读董氏跋文可以发现,董跋意在为《写》卷正名,倘若此卷彼时正为董氏本人所有,则无疑有自抬《写》卷身价之嫌,要价自然会比无款《写》卷高出甚多。若说身为书画商人的吴希元不了解个中曲直,反而高价接手此画则于理不通。此外,吴希元二印中,一印钤在后隔水与画面接缝处、一印钤在后隔水与元跋的接缝处,而董跋则接纸续在元跋后,由此可知吴印在前而董跋在后。因而推断很有可能是吴氏得到该卷之后,请董氏题跋以正其名,从而达到以增其值得目的。
继吴希元之后拥有《写》卷的是大鉴藏家梁清标。《写》卷所钤印中也以梁清标印鉴为最多,总计有“蕉林梁氏书画之印”、“仓岩子”、“冶溪渔隐”等9印。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一字苍岩,号棠村、蕉林,直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名宦梁梦龙曾孙,曾任清朝兵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要职,为明末清初鉴藏大家。史称梁清标“雍容闲雅,宏奖风流,一时贤士大夫皆游其门。每退直,日抱芸编,黄阁青灯,互相酬唱。搜藏金石文字书画鼎彝之属甲海内”。[37](P6)明清之际时局动荡,明内府及原明旧臣的大量书画珍玩流落,这为继承了大量家族藏品且已入仕清朝的梁氏提供了扩大其字画收藏的绝佳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梁氏一生主要的活动地域是在北方,那么当时尚在江南的《写》卷为何又能跨越地域阻隔而辗转至梁氏手中呢?这与当时书画收藏界“南画北渡”的风潮有关。彼时江南文风鼎盛,艺术品相对集中,鉴藏中心转移到南方,颇具慧眼的梁氏等北方收藏大家早已不失时机地将触角伸到了的江南,让一些书画商、裱画师等代为搜罗书画,充当眼目。[38]而这些书画经纪人当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张镠。张镠,字黄美,康熙间扬州人,吴其贞《书画记》称其“善于裱背,幼为通判王公装潢,书画目力日隆。近日,游艺都门,得遇大司农梁公见爱,便为佳士”。[27](P443)由此可知张镠曾是鉴赏能力颇高的装潢匠人,后因“游艺都门”而结识梁氏并受其赏识。梁氏对张镠助力已之收藏颇为赞赏,其《送张黄美至广陵》诗即可为证:“离亭飞木叶,归及广陵春。手泽存先志,功勋在古人。鸿鸣村月晓,霜迹野桥新。别馆今悬榻,君无厌路尘。”[40](P91)此外,从梁氏所作《丰城道中喜广陵张黄美至》等诗亦可见二人交清匪浅。*《丰城道中喜广陵张黄美至》诗,其一:“三日风涛阻,春寒拔尽灰。客随疏雨到,樽为故人开。夜话思千绪,乡书首屡回。感君存古道,冒险沂江来。”其二:“数上胜王阁,迎来剑水边。虚声惊羽檄,远道念风烟。袂接人情外,颜开图画前。何期归客棹,翻似米家船”。梁清标:《丰城道中喜广陵张黄美至》,《蕉林诗集·五言律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4册,第103页。张镠曾搜罗宋徽宗《雪江归棹图》、顾恺之《女史箴图》等多幅名迹转手梁氏,故今存梁氏旧藏中有许多都遗存有张镠收藏印鉴。而今本《写》卷中也钤有其“张镠(白)”、“邗上张镠黄美拜观”二印。因此是否可以断定《写》卷也与《女史箴图》等一样,是由张镠从江南罗致,其后转手于梁氏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因为从印文内容上看“邗上张镠黄美拜观”一印显然为鉴赏印而非强调物主的收藏印,因而更可能的情况是梁氏先得《写》卷,而后以物主身份请张镠品鉴赏玩,张氏因而钤印为记。
所谓“物有聚散理所必然”,[41](P324)梁氏死后,子孙不能守,数十年间其收藏流散殆尽。然而物又必聚于所好,喜好法书图籍的乾隆帝在全国着意搜求书画名迹,这一时期散落民间的书画名帖、珍宝古玩汇集于内府,其中就有唐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北宋祁序《江山放牧图》、元王冕《梅花图》等大量梁氏旧藏,《写》卷亦在其中。乾隆对《写》卷颇为喜爱,不仅在该卷中钤上了所谓的乾隆五玺,*即“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乾隆御赏”、“宜子孙”五玺。还在卷中题跋,并钤盖“乾隆宸翰”、“幾暇临池”等印。此后编修《石渠宝笈》一书,即将此图收入,前已述及。此后,该卷一直存于清廷内府,为后世诸帝赏玩。
清末,末代皇帝溥仪从宫里盗运出大批书画名迹,《写生蛱蝶图》也包括在内,伪满时期存放在长春伪满皇宫的小白楼内。1945年8月,溥仪携部分法书名帖随日本关东军仓皇逃离伪满皇宫。溥仪溃逃后,执勤的士兵蜂涌进入书画楼抢夺剩余珍宝。[42]《写》卷与其他十余件文物俱为伪满国兵朱国恩抢得,并于1952年东北文化部组织工作组清查清宫散佚文物时由其上缴,由当时的东北博物馆保存,后经文物局拨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
综上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昌(传)《写生蛱蝶图》卷,是传世至今的宋画精品,弥足珍贵,该卷数次进入皇室内府,又几度在民间辗转流转,近千年间不知经受了多少飘摇风雨。虽然该图在有些时段如元代末年至明初如何流转,明初至嘉、万时如何播迁,又如何进入清内府等情形,尚待考索,但是其流转轮廓,似可勾勒。该图最初为南宋权相贾似道所收藏。似道获罪之后,该卷入官。其后南宋灭亡,转入元内府,但彼时该卷声名未著,故不为王恽《书画目录》所著录。旋即赏赐给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喇吉,至治三年(1323)三月天庆寺雅集时为冯子振、赵岩所品鉴。四十余年后,又辗转成为明军战利品进入内府。此后流落民间,为徽商吴希元所得,吴氏又求得文宗董其昌题跋,从而得以为《写》卷正名。其后该卷易手大鉴赏家梁清标,梁氏为其钤印多处,其间又为梁氏好友张镠所鉴赏。梁氏死后,子孙不能保,该卷辗转进入乾隆内府,直至清末为溥仪从宫中盗出,伪满时期存放在长春伪皇宫的小白楼内。后又为伪满国兵朱国恩所得,存放于吉林长春的家中。1952年,东北文化部组织工作组清查清宫散佚文物时,收到此画,由当时的东北博物馆保存,后经文物局拨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乃为国家所有,从而结束了不断播迁的旅程,找到了永久的归宿。
[1]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三十二)[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25册.
[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赵昌”条[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12册.
[3]张照等.石渠宝笈(卷三十二)“宋赵昌蛱蝶图”条[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
[4]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点校本.
[5]邓椿.画继(卷一)圣艺[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13册.
[6]邓椿.画继(卷十)《杂说》[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
[7]邓椿.画继》卷一《圣艺》[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
[8]郑兴裔.跋高宗皇帝赐世父手札,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140册.
[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万姓交易”条[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89册.
[1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条[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
[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
[12]西湖老人.西湖繁盛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13]佚名.都城纪胜“茶坊”条[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14]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条[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15]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M].
[16]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四上)[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17册.
[17]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M].
[18]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M].
[19]胡敬.胡氏书画三种之西清札记(卷二)“二十三日丁未”条[M].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第463册.
[20]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21]宋史卷四十七灜国公本纪[M].
[22]王恽.书画目录序[M].秋涧集(卷四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200册.
[23]云峰.论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喇吉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1).
[24]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25]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203册.
[26]吴升.大观录(卷六)宋名贤法书“黄山谷松风阁诗卷”条[M].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丛刊,北京:全国图书关文献缩微中心,2001年影印本.
[27]明史卷七四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28]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29]明史卷九十四艺文志[M].
[3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何良俊.四有斋丛说(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2]李维帧.中书舍人吴君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二)[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集部,第152册.
[33]汪砢玉.珊瑚网(卷四十七)名画题跋二十三“明内监所藏”条[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18册.
[3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古玩”条[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5]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36]范金民.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1).
[37]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上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
[38]李虹霖.鉴藏大家梁清标与历代名迹[N].中国文化报,2015-8-24.
[39]吴其贞.书画记(卷五)“赵松雪写生水草鸳鸯图纸画一小幅”条[M].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343册.
[40]梁清标.送张黄美归广陵,蕉林诗集·五言律二[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204册.
[41]吴其贞.书画录(卷二)“黄山谷行草残缺诗一卷”条[M].故宫珍本丛刊,第343册.
[42]李莉.伪满皇宫小白楼所藏清宫散佚字画[J].溥仪研究,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