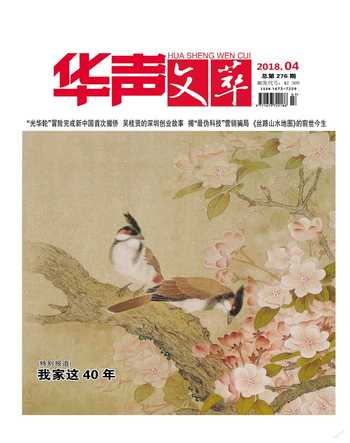小家巨变
1998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出版了70万字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如今,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时候,这本书又在重印之中。当年,我满怀激情写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是因为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切身的感受。
我收到了第一笔稿费
在“文革”中,虽然我出版了10本著作,每次出书只是收到出版社寄来的50本样书,并无稿酬。那时候“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我“上有老,下有小”,仅靠菲薄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
“文革”结束之后,稿酬制度的恢复,使我走出了多年来经济拮据的窘境。记得当时我收到的第一笔稿费,是《化学与农业》一书的增补稿费。
《化学与农业》是一本科普读物,从1963年5月初版时的6万字,到1975年2月再版扩充到8万字,以及后来扩充至16万字。“文革”结束,这本书的新版本在1977年2月印出,我以为仍然没有稿费。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收到出版社通知,说是恢复稿费制。由于新版本比第二版增加了8万字,按照当时每干字4元人民币的稿费标准,人民出版社寄来320元稿费。这笔稿费解决了我家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我一收到,第一件事就是给两个儿子买了新书包,给妻子买了一套新衣服。
此后,随着我的一大批新著问世,我家在经济上翻了身。
分了一套房
1979年6月,我所在的上海科教电影厂通知我,上海市政府特意分配一套4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新房子给我,以改善我的居住条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我才知道,上海市政府是根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1979年1月6日的批示,给我分配新居的。方毅批示说:“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
方毅副总理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条件很差呢?原来,那是《光明日报》记者谢军到我家采访之后,曾写了一份内参(后来在1979年2月1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头版),内中写道:“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大孩12岁,小孩8岁)挤在12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竹片编墙,夏热冬凉,门口对着一家茶馆,喧闹嘈杂。每年酷暑季节,他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挥汗写作”。
拿到房门钥匙之后,妻先把一本出版不久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放进了新居。她说,“我们家第一个住进新房子的是小灵通!”《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我在1961年写的。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像这样描写美好未来世界的书理所当然遭到退稿。“文革”中,我被抄家时,《小灵通漫游未来》手稿差一点毁于劫难。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春风吹拂下,这颗被遗弃的种子发芽了,一下子印了300万册,成了超级畅销书。这本书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印刷。
如今我的家不仅拥有私家游泳池,而且拥有50平方米的客厅,与当年的小屋有着天壤之别了。
第一次在家接待外国记者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门。我在上海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美国、日本、英国作家。最初,国门开而家门闭。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谈话总是在科学会堂的外宾接待室里进行,宴请也都是“公宴”。位于上海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原本是法租界的法国总会,典雅而华丽。
1982年,英国记者房义安要求采訪我。按照“惯例”,请他到上海科学会堂。但他却说:“何必在办公室谈话?我希望看一看中国作家的家。”我赶紧请示领导,“家门”能否开放?领导指示折中一下,于是我在上海和平饭店会见了那位英国记者。
不料,在与他会面之后,他又提出上我家采访。我不得不向领导再次请示。“好吧,就让他上你家。”领导同意了,关照我把家里的内部文件收好,打扫一下,干干净净接待外宾。这样,我的家门头一回对外“开放”。那位英国记者来了。当他拿出录音机时,我在旁边也放了我的录音机——因为第一次在家里接待外宾,万一这位大胡子记者对外乱写报道,我有录音带作证,以免“麻烦”。经历过“文革”苦难的我,不得不多加小心。
后来才知道,那位英国记者非要上我家不可,纯属好奇之心。因为他听我说出过好多书,尤其是《十万个为什么》印了近亿册,很想来我家看个究竟。进门之后他哈哈大笑:“我以为你家有私人飞机呢。原来,中国作家的家,也普普通通!”
自从那位英国记者来了之后,我家也就对外开放了。日本作家来了,美国作家来了,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和夫人来了,我也都在家里接待并设宴款待……一位日本朋友来过多次,熟了,甚至像老朋友似的,敲敲门就进来了,事先连招呼也不打(那时候我家只有传呼公用电话,没有“宅电”)。
苏联作家博布洛夫也来我家作客
不过,那时候我跟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却一直没有交往。只有捷克的一家杂志刊载了我的小说之后,来过信,说是来华时定前来拜访,但没有成行。
中苏关系的冰河终于渐渐解冻。于是,我家迎来了稀客——苏联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的作家博布洛夫·阿里克萨德尔·阿里克萨德洛维奇。
那天下午2时,我家门铃响了。我用俄语说:“您好,博布洛夫同志!”他呢,也称我和妻为“同志”。我发觉,跟苏联同行聊天,共同的话题比西方同行更多。谈斯大林的功过,谈赫鲁晓夫的是非……他很有兴趣地翻阅着我的书架上的《戈尔巴乔夫传》以及戈氏《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
在家里,我们用上海菜招待远方的来客。有上海茭白、炒鳝丝,还有螃蟹。博布洛夫学着我们的样子,掰开螃蟹,犹犹豫豫地咬了一口,马上笑起来说:“味道好极了!”
吃罢,他若有所思地进行了一番比较:“苏联人跟上海人的不同是,苏联人第一道菜是汤,而上海人则最后一道菜是汤。不过,这只是个顺序问题,我们的共同点是都爱喝汤!”说完,他又欢快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使我想起那位英国记者头一回来我家访问时我们的拘谨、紧张。过去了,都过去了。国运盛而家运昌,我小小的家门,是在国门开放的年代里逐渐打开的……
两个儿子都赴美国留学
中国敞开了国门,出国成了潮流,人称“出国潮”。“出国潮”也冲击着我的家。
学好英语,考好“托福”,成为当时中国年轻人前往美国留学的必经之路。我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考“托福”的队伍。长子白天在大学里读专业课程,入夜则到夜校进修英语,啃“托福”课本。啃完“托福”,接着又啃“GK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他买了张美国地图,贴在他的书桌前天天看,对美国的五十个州了若指掌。
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国营企业里工作。那家企业里有许多外国专家,领导得知他的英语很好,就让他担任英语翻译。不过,就在他担任英语翻译的时候,人事科科长调侃地对他说:“哦,你是我们厂的第八任英语翻译。前面七任都已经到美国去了,我看你很快也会去美国!”人事科科长的话没错。经过“托福”考试,我的长子收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时候,在上海乌鲁木齐路,飘着星条旗的美国驻沪领事馆门前,入夜便排起签证长队。我的长子也加入了这支队伍。上午8时多,这支队伍开始蠕动。从大门里出来的人,只消看一下脸色,便知道“晴雨”。我的长子板着面孔走了出来,不言而喻,被美国人拒签了——原因是他虽然被美国大学录取了研究生,但没有获得奖学金。那时候,光是被美国大学录取却没有奖学金,通常是会被拒签的。好在长子是个很开朗的小伙子。他不在乎,再考“托福”和"GKE"。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又收到一封美国来信时,忽地欢呼雀跃起来——美国一所大学给了他全额奖学金。
身边的榜样最有力量。老二见哥哥去了美国,也加紧学习英语。两年之后,他也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我和妻子首牵手,游全球
緊接着,1993年11月30日,我和妻子开始第一次美国之行。我刚刚抵达洛杉矶,连东南西北都还没弄清楚,就被美国联邦影视集团电视台接去,在那里接受专访。圣诞节前夕,我和妻从洛杉矶飞往匹兹堡,长子开着他在美国买的的二手车,驾车带领我们去他弟弟那里,我们全家终于在美国团聚。
从那以后,我和妻10次去美国,两个儿子都在美国成了家。我和妻“手牵手,游全球”。我游历一个个国家,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在我看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历史是人类的脚印。只有以文化和历史这“双筒望远镜”观察世界,才能撩开瑰丽多彩的表象轻纱,深层次地揭示丰富深邃的内涵。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记、所思凝聚笔端,写出一部又一部“行走文学”作品。我还拍摄了大量精美的照片,作为书的插图。如今,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看世界”丛书,已达22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以小见大。我的小家巨变,见证了4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