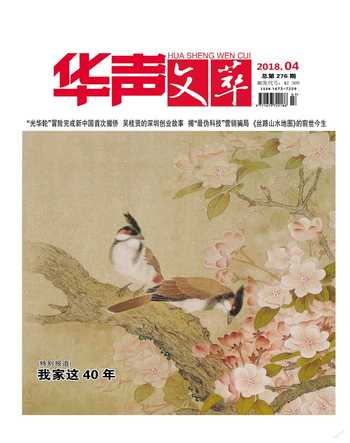开枝散叶 四处皆家园
母亲说,这辈子注定要看四个地方的天气预报:成都、北京、广州和乌鲁木齐,这是我们一家人各自的住地,几乎分散在中国的四方。传统中国人安土重迁,家人聚族而居。进入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像我们家五口竟分成四处的情况开始越来越多了。
离家的路从父亲说起。父母都是四川成都人。父亲1963年大学毕业,他学的电子专业在当时还是新兴的学科,那时候毕业生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父亲被分到北京电子管厂。
为解决夫妻分居父母调动到乌鲁木齐
1969年,我的出生之年,父亲调动到乌鲁木齐的一家电子企业,目的是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在四川当老师的母亲也一起调动到了这个冬季非常漫长寒冷的地方。两个地道的南方人开始学习在西北地区生活。冬天,母亲学会了做棉衣棉裤、织毛衣,父亲学会了生炉子,保持夜里取暖。乌鲁木齐附近就是煤矿,父母的同事们互相帮助:大家去煤矿买一大卡车的煤回来,几家人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加快了,一幢幢楼房迅速地拔地而起。我们家上世纪80年代初搬进了楼房,用上了煤气,这份买煤、烧煤的辛苦才免去了。
气候之外,饮食习惯是另一个难题。四川人习惯吃大米,北方人习惯吃面食。当时的粮食是国家供应,乌鲁木齐的职工每人每月只有一公斤大米。大米贵、面粉便宜、玉米面更便宜。父母会想方设法跟不爱吃大米的同事换,两公斤玉米面或一公斤白面换半公斤大米。他们还会从四川老家带米回来。70年代回乡,行李箱里经常装着大米等食物。记得姐姐1976年跟随母亲回老家,就背回来一书包的大米。
2005年电影《孔雀》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据说触发了70后的普遍回忆。电影中的父母做煤球、腌咸菜等等生活细节是中国上世纪70年代的真实生活写照。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社会都充满希望的、欣欣向荣的时期,父母积极地投入工作。国家开始給技术人员评定职称。父亲当时参评高级工程师,需要考英语。他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才学的英语,已经十几年没有用了。为了考试,四十多岁的父亲开始勤学苦读。每天早上他带着我和上中学的姐姐去附近的公园晨读,我们三人分散在三个方向,各自读着自己的英语书。
姐弟三人考上大学成为同龄人中的幸运儿
1985年姐姐考上了大学,那时候能上大学的人很少,姐姐是父母单位同事的孩子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女生。她毕业后成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定居乌鲁木齐。
1988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乌鲁木齐到北京3770多公里,那时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整整72小时,三天的火车坐下来,腿都肿了。但到北京上大学是我此生最为重要的收获。那是一个各种思想观念、潮流都蜂拥至中国的时期,学校里有各种讲座、辩论,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西方的文学、哲学著作被大量翻译引进。至今记得大二那年某个春天的下午,在图书馆的书架旁,翻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带来的精神震动。大学毕业后我继续深造,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先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随后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后来还曾赴爱尔兰从事过几年汉语教学。
我的弟弟比我小三岁,1990年考上了厦门大学财会专业,那一年我上大三,姐姐刚刚开始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俩去帮他置办上学需要的行李箱、衣服等物品,路上遇到母亲的同事朋友,都很羡慕地问:儿子也考上大学了?母亲以一种看似不经意却又充满自豪的语气回答道:是啊,考上了。
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的人比较少。据有关资料,1990年前后,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比)大约是3~4%。我们姐弟是同龄人中比较幸运的。弟弟大学毕业时,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之际,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与机会。因此,他选择了当时全国的经济重镇、南方大都市广州。如今他是一家大型国企的华南公司的财务部部长,还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
便捷的交通和更多的选择
回想四十年的变迁,交通上愈来愈便捷对于我们一家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父母在乌鲁木齐工作的时候,很多年才能回四川老家一次。当时的假期很少,收入又有限,父亲离家之后,再回去探望祖母已经过了十年之久。我的记忆中,少年时代最辛苦的就是坐火车。乌鲁木齐到成都要60多个小时,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夜里有座位的人坐着睡;没座位的人白天站在过道里,晚上就坐在地上睡。那时最好的位置是座位底下,人们会在长条座位底下铺上报纸或床单,钻进去就可以躺着睡觉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父母退休后回到故乡四川成都定居。成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生活悠闲,很适合养老。不过,一家人天南海北,相距遥远,加之各自的假期有限,见面的机会很少。当然,交通成本很高也是一大原因。2003年我博士毕业刚工作的时候,北京到成都的单程飞机票相当于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二;而乌鲁木齐至成都的单程飞机票钱更比姐姐一个月的收入还高。火车票又非常难买,特别是春节期间,全中国大迁徙之际。弟弟工作繁忙,每年只有春节才有假期可回成都去探望父母;而姐姐常常在暑假火车票不太紧张的时候去成都探望父母。因此,他们俩竟然有十年时间没有见过面。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而交通成本也越来越低,高铁通行,机票价格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大大降低,大家见面的次数自然多了起来。我的父母如今已是八十高龄,依然身体健康,我们都尽可能地多去探望他们。
总的来说,父母那一代,工作、住房甚至粮食等物品都是国家分配,他们会在一个岗位上干一辈子,从来不担心自己不合格或可能被开除。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物质匮乏,夫妻俩必须胼手胝足地应对生存。我们这一代,工作的压力陡然大增。姐姐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国家分配工作,她因为在新疆上大学,户口在那里,就只能被安排在那里工作。到我和弟弟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我因为从事文化教育行业,自然选择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弟弟从事经济行业,就选择了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南方。他的工作也不断转换,从国企到民企,到港资私企,再到央企,做得不好就只能走人,因而我们必须努力工作。
当然,我们这一代物质上比父母好了很多。四十年前,北京的大街上汽车很少,除非高级领导人才有可能坐小汽车;二十年前,中国有私家车的人也绝少。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个人财富积累获利的一代。90年代刚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住宿舍,慢慢的有了单位分配的小房子;2000年前后开始买房,随后添置汽车。因此,现在很多人家都有一到两套房子和一辆车,我弟甚至买了5房子。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当时他与兄弟姊妹分隔在五个地方,望月思乡怀人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见主题。作为教授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师,我每每读到这些典雅的诗句,都会感叹,古典的感受方式与情绪已经漫漶邈远之极,如今的中国人出外求学、工作,不断迁徙。至于我的家庭,一夜乡心,分隔四处,但几个小时的高铁或者两个小时的飞机就能相聚,自然无须垂泪了。姐姐的女儿今年大学毕业,正在准备考硕士研究生,还计划将来出国留学。他们这一代,应该会走得更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