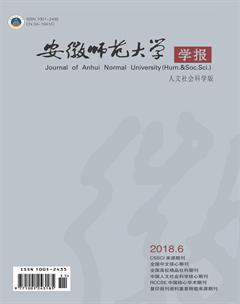《周易》“王用三驱”阐说的学术史考察
摘要: 前人对《周易》“王用三驱”的释说,大致可分政务说、道德论两类。前者以王弼、孔颖达为代表,主要从狩猎文化的角度,用“三驱之道”喻比王者“唯贤是与”的用人之道。这一释说与曹魏、唐初的政治背景及其人才政策有关。由于《周易》王注、孔疏影响甚大,此后注、解《周易》者大都沿袭此说,进而附会以如军事等行政或政治事务,从而成为传、注“王用三驱”的传统。而从马王堆出土帛书、传世文献等记载看,以儒家一贯强调的“仁义”之德阐说“王用三驱”,早在上古即已出现。唯因政务说流行颇广,道德论始终未为儒者瞩目。直至北宋程颐传注《周易》时,“王用三驱”的释说才回归儒家说《易》传统。尽管两类阐说都是针对狩猎活动而发的,但“王用三驱”的道德性阐释更契合《周易》原旨。
关键词: 政务说;道德论;王用三驱;《周易》
中图分类号: K207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8)06000910
Abstract: 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predecessors of the sentence, “the king used the Rite of San Qu”, can be divided into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moral theory. From the angle of hunting culture, Wang Bi and Kong Yingda who supported the former one thought the sentence referred to the strategy of hiring the qualified people,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talent policy during WeiCao period and the EarlyTang Dynasty. Under their influence of annotations by Wang Zhu and Kong Shu for the Zhou Yi,this interpretation added with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or political affairs led to be a convention. However, on the basis of records such as the silk manuscripts and handeddown documents from Mawangdui Han Tomb, the moral conduct of kindness and justice emphasized by the Confucianists,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times, could also expound that sentence. Because the political one was so popular, the latter one did not draw the Confucianists attention until Chen Yi in the NorthernSong Dynasty made annotations for the Zhou Yi. Although these two are both based on hunting activities, the explanation of moral theory to the sentence of “the king used the Rite of San Qu” still corresponds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Zhou Yi.
《周易》之《比》卦九五爻辞有“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一语,①对其“三驱”何谓与“王用三驱”何义,古今学界有较多的阐释。今人论著重要者有李亚农:《大蒐解》,《学术月刊》1957年第1期;杨宽:《“大蒐礼”新探》,《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等。另外,周国瑞:《“三驱”小议》,《殷都学刊》1984年第1期;李建国:《“三驱”“三田”辨》,《辞书研究》1984年第2期;党积生:《“三驱”一词发微,《青海師专学报》1993年第1期;董秋成:《“三驱”的另一种解释》,《语文建设》2005年第1期;杨名:《如何理解〈谏太宗十思疏〉的“三驱”》,《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4期等对此亦曾作过一定的探讨。笔者曾撰文对“三驱”何谓以及汉唐时期的“三驱”礼衍变分别进行了考释和梳理,认为“三驱”礼源于殷商狩猎文化。西周将殷商狩猎活动礼乐化,成就蒐狩礼,蒐狩礼融“阅兵之制”“田猎之仪”于一体。“阅兵”乃讲武即军事训练;“田猎”即狩猎,则是为检验讲武的效果。“三驱”乃指讲武活动中参加演习的战车、士兵(徒)在特定区域(防)内三次前进及“表”的行为,古人因而称“三驱教人战”。讲武结束后,即行狩猎,在车、徒襄助下,天子率先射杀,猎物以其上、中、下杀而各用于祭祀、招待宾客与日常食用。诸侯、大夫随后依次而猎,所获之物,大者归公,小者属己。祀祭诸神、宗庙后,蒐狩礼即完毕。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西周礼乐渐遭争霸诸侯遗弃;军事方面,由于兵种、战争形式的变化,原以车战为内容的军事训练方式也发生变易。蒐狩礼因“阅兵之制”淡出而仅存“田猎之仪”,且其田猎亦逐渐衍变为游逸活动。秦汉以降,受“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卷37,1530思想影响,各朝无不重视蒐狩礼建设。然因历史条件差异,后世所谓蒐狩礼,已与西周蒐礼大有不同。两汉蒐礼仅限专门的讲武礼(貙刘),田猎活动基本上是奢靡的游乐行为;魏晋也大体如是;南北朝时代,如北齐、北周等试图恢复传统礼制,为踵承西周蒐礼而做了许多努力,但因年代久远和形势差异,其蒐礼虽具集讲武、狩猎于一之形式,而内容却大有不同,西周“教人战”的“三驱”礼从寄诸“阅兵之制”转移到“田猎之仪”中,“三驱”尽失“教人战”的性质和作用;隋唐因袭魏晋之制。“三驱”礼本源因而尽遭湮没,完全成为“田猎之仪”的一部分。因此,后世关于“三驱”礼的诸多说法,基本上是就“田猎之仪”而言的。具体参见陈业新:《〈周易〉“三驱”礼考释》,《周易研究》2016年第2期;《“成礼三驱”:汉唐时期“三驱”礼衍变述论——以蒐狩礼的建设为线索》,《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由于历史上的“三驱”礼多有变易,复以坟册载记不甚详明,因而学术史上对《周易》“王用三驱”的阐说多有歧义。查慎行的《周易玩辞集解》卷2称:“三驱之礼,经传无明文……先儒之解,纷纷不同。”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页。(下引《四库全书》皆为此本,简称《四库》)本文以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帛书载记为据,在笔者此前“三驱”礼考释及其变迁研究的基础上,对学术史中有关“王用三驱”的阐说进行简要的梳理,希冀有益于整体了解、把握《周易》“三驱”礼仪文化。通过对有关《周易》传注、疏解文献的爬梳,我们发现,前人对“王用三驱”之义的释说,大致可分为以王弼、孔颖达为代表的政务说和儒家一贯强调的“仁义”道德论两大类。
一、“王用三驱”政务说
《周易》“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究竟有何深意,其《象》传未做具体解释,而仅云:“‘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那么,了解“王用三驱”之义,只能求诸后世的阐说。传世文献中有关《周易》的解说,今之所见,较早且系统者自然为魏晋学者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朱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宽)、孟(喜)、京(房)、田(何),东都则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宋本周易注疏·周易正义·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页)可知,两汉学者在传述《周易》上,或多限于“祖述”,缺乏系统释说传诸后世。王注《周易》“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曰:
为比之主而有应在二,“显比”者也。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2]181
王弼“‘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一语,说明在王氏看来,“三驱”发生在“蒐狩礼”的“田猎之仪”即狩猎活动中。但具体是什么,则未曾明言。不过,将其言和孔疏《比》卦所引南齐褚澄“诸儒皆以为‘三面着人驱禽,必知三面者,禽唯有背己、向己、趣己,故左右及于后皆有驱之”一文相对照,大概可知王弼所谓的“三驱”,指的就是狩猎活动中车、徒三面围驱禽兽而射之的行为。此其一;其二,王弼以“无私于物,唯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阐释“王用三驱”,用“三驱之道”喻比王者“唯贤是与”的用人之道。
如众周知,王弼注《易》,一扫汉儒笺注繁琐之风,且摈弃汉《易》象数灾谴之论,开后世以义理说《易》之先河,对后世《易》学研究有极大的影响。纪昀等:《〈周易注〉提要》《〈周易正义〉提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7页;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8、6985页。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即稱:“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唐初孔氏等奉命正义《五经》,即以王注《周易》为本。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云:“今既奉勅删定,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为之正义,凡十有四卷。”(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宋本周易注疏·周易正义·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14页)孔疏云:
“王用三驱,失前禽”者,此假田猎之道,以喻“显比”之事。凡“三驱”之礼,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是失于前禽也。“显比”之道,与己相应者则亲之,与己不相应者则疏之,与三驱田猎爱来恶去相似,故云“王用三驱,失前禽”也……“去之与来,皆无失”者,若“比”道弘阔,不偏私于物,唯贤是亲,则背己去者与来向己者皆悉亲附,无所失也,言去亦不失,来亦不失。“夫‘三驱之礼者”,先儒皆云“三度驱禽而射之”也,三度则已,今亦从之。去则射之。褚氏诸儒皆以为“三面着人驱禽”,必知三面者,禽唯有背己、向己、趣己,故左右及于后皆有驱之。“爱于来而恶于去”者,来则舍之,是爱于来也;去则射之,是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者,言独“比”所应,则所比为失,如三驱所施,爱来憎去,则失在前禽也。[2]182184
与王注相比,孔疏的价值在于:首先,孔疏讲明了“假田猎之道,以喻‘显比之事”的根据。按孔氏之说,就是“‘显比之道,与己相应者则亲之,与己不相应者则疏之,与三驱田猎爱来恶去相似”;其次,孔疏援引先人之说,解释了何谓“三驱”:一则为先儒皆云的“三度驱禽而射之”,二则为说明“去则射之”而带出的南齐褚澄等所持的“三面着人驱禽”之说;最后,孔疏对“以喻‘显比之事”进行了反复的阐说,强调用人应“‘比道弘阔,不偏私于物,唯贤是亲”,如此“则背己去者与来向己者皆悉亲附,无所失也”。但由于孔氏“正义”“以辅嗣(王弼)为本”,故而总体来说,孔疏关于“王用三驱”的释义没有突破王弼的注论,只是对王注作了进一步的申说。王、孔对《周易》“显比”的注疏,其“比而显之”之事,俱为“唯贤是与”的用人之道。这一释说,当与王、孔二氏各处的曹魏时期和唐初之政治背景及其人才政策有关。
孔氏《周易正义》为官方定本,成书后,作为《五经正义》之一者颁行于学校,成为士子读经科举的官方教材,流传全国,影响深远。以致唐、宋诸多学者注《易》、解《易》著述,在解说“王用三驱”时,大都按依王注、孔疏之说,强调“王用三驱”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之意,并附会以如用人等行政或政治事务,从而成为传、注“王用三驱”的传统。如唐代史徵《周易口诀义·上经一》:“‘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者,处比之时,居得尊位,固当心无偏党,来者比亲,而乃独应于二,显明亲比之道,是用心偏拘,故曰‘显比也。夫不能普及于物,而乃亲于二,亦如‘王用三驱田猎相似。凡三驱之礼,爱来恶去,故逆来趣己者舍之,背己而走者射之,故‘失前禽也。”又如宋代司马光《易说·上经》:“‘王用三驱,失前禽,‘前禽者何?背去之禽也;‘失者何?求与之相亲而不可得者也。”载《四库》第8册,第17、582页。且后来一些学者还将“王用三驱”与其时的国家形势等相联系,从而表达其政治主张。如南宋学者张浚《紫岩易传·上经》即曰:
“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圣人之仁德也。古者,天子蒐田,讲三驱礼,失前禽,则违而去之者弗之取,仁之至也。圣人以中正比天下,其道既显,而荒逖之俗犹有不化,圣人增修德政而已,不胁以武力,曰“失前禽”,宁失之宽也。“失前禽”,正所以兼爱华夏之人。成汤祝三面之网,诸侯闻之,相率以朝,得“比”之吉……读《易》至《比》九五,知圣人缓于治外、急于治内也……“失前禽”,则遐裔犹有未宾附者,抚之以宽而遂其生,仁德益大,合是二美,获“显比”之吉,圣人于天下既比,后不肯邀功生事于夷狄不毛地也。后世若汉武、唐宗,穷兵极武,于“显比”失之。然“显比”而用“三驱”之礼,是圣人亦不以天下比而忘武备也。吁,孰谓天下未比而备可遽忘乎?[3] 卷1,31
张浚是南宋抗金名将,亦是一代名相,其读《易》注经,多与时务相联系。上引传文,主要讲述边疆民族事务,强调治理荒逖疆务既要增修德政,但也不可遽忘武备。并在传《易》之《豫》卦时,再次以时务附会“王用三驱”,且专谈兵备:
“豫”惟顺动,故治可兴,害可去,而“豫”治益大……《比》九五曰:“王用三驱,失前禽”。盖阳动而复,天威已行,至“比”则威德益著,而生物之功至大。圣人生物之功在兵,兵以德胜,圣人复其心,以复其德,复其政事,然后可以行《师》之众正,可以举《谦》之征伐,可以体《豫》之行师,可以讲《比》之三驱,此一阳用事之序也。夫天下顺比而不忘“三驱”礼焉,圣人仁爱天下,惟恐一朝备弛而害加于百姓。后世天下始定,儒者急急偃兵息民之说,以从事夫礼乐之文,导君骄奢纵逸之地,卒至败人之国,岂不陋哉!若夫天下未定而曰“我无事于复”,玩岁乐身,以兵为讳,吾不知危亡之日矣。戒之哉![3]卷2,54、55
二、“王用三驱”道德论
就相关文献来看,以儒家一贯强调的“仁义”之德阐说“王用三驱”,當为《易》说的另一传统。讨论这一问题,有几条文献值得关注。
首先看19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则帛书——《昭力》《缪和》,其中均载有与《周易》“王用三驱”相关的文字和解释。《昭力》第2章载:
昭力问曰:“《易》又国君之义乎?”子曰:“《师》之‘王参赐命与《比》之‘王参殴、与《柰》(《泰》)之‘自邑告命者,三者国君之义也。”……又问:“《比》之‘王参殴,何胃也?”子曰:“□□□□□人以察(或释作宪、法),教之以义,付之以刑,杀当罪而人服,君乃服小节以无人曰义。为上且犹又不能,人为下何无过之又?夫失之前,将戒诸后,此之胃教而戒之。《易》□□[曰:《比》]之‘王参欧,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若为人君殴省亓(其)人,孙(逊)戒在前,何不吉之又?”马王堆出土帛书第36页:“与比之王参殴与柰之自邑告命者三者国君之义也(8行)……又问比之王参殴何胃也子(10行)为上且犹又不能人为下何无过之又夫失之前将戒诸后此之胃教而戒之易□□之王参欧失(11行)”;第37页:“昭力问曰易又国君之义乎子曰师之王参赐命(9行)曰昔□□□□□人以察教之以义付之以刑杀当罪而人服君乃服小节以无人曰义(12行)前禽邑人不戒吉若为人君殴省亓人孙戒在前何不吉之又(13行下)”。参见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帛书》(一),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8384页。所引整理文本以邓球柏的《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为主(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42543页),同时参照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377页;廖名春:《帛书〈昭力〉释文》,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丁四新:《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390页;《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等释文,其中部分句读,笔者引用时略有变动。
研究者认为,文中之“子”即为儒家创始人孔子,郭沂:《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重新检讨〈易传〉成书问题》,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3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丁四新:《帛书〈缪和〉、〈昭力〉“子曰”辨》,《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宋立林:《帛书〈缪和〉〈昭力〉中“子”为孔子考》,《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昭力》乃以昭力、孔子之间问答的形式而解《易》的儒家研《易》之作。《帛书〈缪和〉、〈昭力〉“子曰”辨》。该章通过对“王参赐命”“王参驱”“自邑告命”的解释,阐明了“国君之义”的内涵:其一,“以爱人为德”;其二,教人以德,君主统治,重在德化,为上者身教以德,人有过则劝戒于后,就能达到德化下民的目的;其三,人君要以亲贤为重。这一点,和王注、孔疏“王用三驱”阐发的君王“唯贤是与”用人之道基本一致。而《昭力》对“王参驱”教化行为、突显人君宽容大度高尚德性的阐述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丁四新:《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缪和〉〈昭力〉二篇之义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则不为王注、孔疏《周易》“王用三驱”所具备。
另外,帛书《缪和》第15章载云:
汤出巡守东北,又火。曰:“彼何火也?”又司对曰:“渔者也。”汤遂□□□□子之祝[曰:“古者蛛]蝥作网,今之人缘序。左者右者,尚者下者,卫突乎土者,皆来吾网。”汤曰:“不可。我教子祝之。曰:‘古者蛛蝥作网,今之缘序。左者使左,右者使右,尚者使上,下者使下,吾取亓犯命者。。”诸侯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鱼鳖矣……《易》卦亓义曰:‘显比,王用参驱,失前禽,邑人不戒,吉。此之胃也。”马王堆出土帛书第34页:“汤出巡守东北又火曰彼何火也又司对曰渔者也汤遂□□□□子之祝(6行)曰不可我教子祝之曰古者蛛蝥作网今之缘序左者使左右者使右尚者使上□□弗乡□(7行)余国易卦亓义曰显比王用参驱失前禽邑人不戒吉此之胃也(8行)”;第35页:“卦亓□蝥作网今之人缘序左者右者尚者下者卫突乎土者皆来吾网汤(7行)也是知晋□□□□诸侯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鱼鳖矣(8行)”。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第8081页。所引整理文本以《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第157、524页)为主,同时参照《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释文》、廖名春《帛书〈缪和〉释文》、《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等释文,其中部分句读,笔者引用时略有变动。
该段文字记述的是“汤之德及禽兽鱼鳖”的典故,并以此释说《周易》“王用三驱,失前禽”。刘大钧视这一记载为以史释《易》或以《易》释史研究方法的最早记录,认为它用以《易》阐史或以史证《易》的方式,向我们透露出很多汉初今文《易》义。强调这些可贵的资料,对于我们正确解读《彖》《象》《文言》等《易传》之文,提供了先儒从未得见的依据和旁证[4]。这条史料对于解读“王用三驱”之义的价值可见一斑。
《缪和》对“王用三驱”的解说,与《昭力》对国君“德”义的阐释基本一致:不仅要以德教化人民,而且还要“德及禽兽鱼鳖”等万物。目前,学界基本认为马王堆帛书《昭力》《缪和》乃战国中晚期作品,证之以《吕氏春秋·异用》“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的记载。我们认为,至少在战国中晚期,学界就赋予了“王用三驱”以彰显君王“德”性的内涵。然而,传世《周易》之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关于“王用三驱”的解释,则与之有所不同,其注、疏基本上限于“爱于来而恶于去”,并生发出王者“唯贤是与”的用人之道。有论者曾将王注、孔疏《周易》“王用三驱”与《缪和》记载进行比较,称王、孔氏之“传世的解说与《缪和》的解释虽有差别,但都是以‘显比为弘阔之道。《缪和》以‘显比为弘阔大道,德及禽兽鱼鳖,不求皆来吾网,但咎其犯命者。真可谓帝王之道,汤武之德者也。”[5]157而在笔者看来,虽同为“显比”之道,但王注、孔疏“显比之事”为政治或行政层面的具体事务,而《昭力》《缪和》喻比之事则主要为道德意义上者,彼此的区别因此显而易见。
《缪和》“汤之德及禽兽鱼鳖”的故事,在先秦秦汉哲学如《吕氏春秋》载:“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螯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吕不韦撰、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10《孟冬纪·异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5页)、史学如《史记》曰:“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页)、文学如经刘向整编的贾谊政论文集《新书》云:“汤见设网者四面张,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罗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网,今之人循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士民闻之,曰:‘汤之德及于禽兽矣,而况我乎?于是下亲其上。”(贾谊,卢文弨校:《新书》卷7《谕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475页)传世著述中也较为常见,后世在传注早期儒家典籍时亦经常援用这一典故。如西魏、北周时期卢辩注《大戴礼记·保傅》“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二垂至”即云:“汤尝出田,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噫!尽之矣。乃去其三面,而祝曰:‘欲左欲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乃及禽兽。于是朝商者三十国。二垂,谓天地之际,言感通之远。《淮南子》云:‘文王砥德修政,二垂至。”(戴德撰、王聘珍解诂,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3《保傅》,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页)将这些文献记载与《缪和》文字进行比较,我们认为:其一,撰述某一“圣人”的故事,并附会以儒家强调的美德,是先秦文献书写常用的手法,商汤“网开三面”即为其例;其二,同样为商汤至德的故事,和帛书《缪和》所录相比,传世文献描述中增加了汤“收(去)其(网)三面”等内容;其三,《缪和》在记载汤之至德行为时,不仅援引《易》之“王用参驱”文字,而且其“此之胃”即明确地指出,汤之举就是《周易》比卦“王用参驱,失前禽”“显比”之义。但《吕览》等传世文献中,只是书写了汤的行为及其道德价值而没有将商汤“德及禽兽鱼鳖”之举与“王用三驱”相联系。
其实,以君王的狩猎事例而彰明其美德,在早期文献中并不罕见。《诗·驺虞》是一首描述周文王行“蒐田”礼之诗,诗中有“彼茁者葭,一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句。关于“驺虞”学界从不同角度,对驺虞有一定的研究。具体可参见陈士林:《〈驺虞〉注释中反映出来的几个训诂学问题》,《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严国荣等:《“驺虞”考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王春阳等:《“驺虞”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1期;尹荣方:《〈诗经·驺虞〉与上古“迎虎之礼”》,《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冬之卷;刘毓庆:《〈诗经·召南·驺虞〉研究》,《晋阳学刊》2017年第2期;等等。,毛傳云:“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三国陆玑、唐陆德明、宋陆佃均持是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于嗟乎驺虞》,陆佃:《埤雅》卷5《释兽五·驺虞》,分别载《四库》第70、222册,第15、100页;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页。郑笺将“君射一发而翼五豝者”解释为君王“仁心之至”的结果,孔颖达据此疏曰:“国君于此草生之时出田猎,一发矢而射五豝。兽五豝唯一发者,不忍尽杀,仁心如是”。把君王“一发五豝”的蒐田行为和义兽(驺虞)出现的现象,都作为君王“仁心”的表现和反映。因此,毛传《驺虞》“序”云:“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6]卷1,294可知《驺虞》乃歌颂文王教化之诗。对此,宋人罗愿进一步释云:“夫驺虞之马,工于逐禽,如此而《诗》言其仁,何也?盖一发而得五,则庶类蕃殖矣。当葭蓬茁茁之时,则蒐田以时矣。有以见文王于平时不妄杀如此,此其一时之义仁。如此,《诗》则王道成矣。”[7] 卷18,402成书于西汉的《榖梁传》释《春秋》昭公八年(前534年)“秋蒐于红”云:“过防弗逐……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晋范宁注:“射以不争为仁,揖让为义”;唐初杨士勋疏:“‘古之贵仁义者,谓田猎之时,务在得禽,不升降,是‘勇力也;射宫之内,有揖让周旋,是‘仁义也。田虽不得禽,射中则得禽,是‘贵仁义而‘贱勇力也。”[8]昭公八年,2435由上述注疏家对儒家经典《诗》、《春秋》及其传有关蒐田记载的注解可以看出:早在西汉初年,儒者就以“仁义”之德解说蒐田,此后经东汉、三国、晋乃至唐宋,无不如此。
如上所述,在先秦秦汉史学等典籍中,尽管对商汤德及禽兽鱼鳖之事有诸多的记载,但传世文献在载记此事并颂扬商汤行为时,并没有将商汤的行为与“王用三驱”相关联。而到东汉初年,赋家张衡在其《东京赋》中,不仅将蒐田与“成礼三驱”联系起来,且援用商汤“教祝”于民而“昭仁”的事例以喻之:
三农之隙,曜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成礼三驱,解罘放麟。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怀民。
赋中天乙为成汤名,“天乙之弛罟”即商汤“网开三面”之典事。张衡将“三驱”礼与狩猎时放逐野兽、网开三面、“昭仁”相联系,按照唐代薛综注,其意在说明“成礼三驱”乃“言杀禽兽不尽,即昭明人君行仁之道”[9] 卷3,7576。张衡的书写和薛综之注,与帛书《昭力》《缪和》阐释的精神基本一致,我们或可将之一并视为“王用三驱”的经典释说。
而稍晚于张衡的东汉经学家郑玄亦曾“以仁恩养威之道”论“王用三驱”。据《隋书·经籍志一》记载,后汉郑玄有《周易注》9卷传之于世。但王弼注《易》,“扫空一切旧说”[10] 296。隋时,王弼注《周易》盛行,“郑学浸微”;唐代孔颖达等奉诏作疏,“专崇王注”,郑注遂于此间“殆绝”,纪昀等:《〈周易郑康成注〉提要》、《〈周易正义〉提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6页。因而郑注《周易》今多不详。不过,透过前人有关经传注疏或辑本,我们仍可窥见郑注《周易》的一些情况。
关于郑注“王用三驱”,传世文献中有三则记载值得关注。一是孔颖达疏《左传》“(桓公)四年(前682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引郑玄注《易》“王用三驱,失前禽”语其语云:“王者习兵于蒐狩,驱禽而射之,三则已,法军礼也。‘失前禽者,谓禽在前来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顺而射之,不中则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杀,奔者不御,皆为敌不敌己,加以仁恩养威之道。是说三驱之事也。”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桓公四年,载《十三经注疏》,第1747页。;二为唐代贾公彦疏《周礼·士师》“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三曰禁用诸田役”引郑玄语;其语云:“王因天下显,习兵于蒐狩焉。驱禽而射之,三发则已。‘失前禽者,谓禽在前来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顺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习军礼。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杀,奔者不禁,背敌不杀,以仁恩养威之道。”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5《士师》,载《十三经注疏》,第875页。三则南宋王应麟辑《周易》郑注而成《周易郑康成注》一书有关郑注“王用三驱”语其语云:“王因天下显,习兵于蒐狩焉。驱禽而射之,三则已,发军礼也……以仁恩养威之道。”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比》,载《四库》第7册,第132页。。三者文中所引郑注“王用三驱”,均言“三驱”为军礼,而“王用三驱”则“以仁恩养威之道”。可知,郑注《周易》亦以“王用三驱”为“仁恩”之道。但是,唐代郑注彻底湮绝,王注盛行,治《易》者于是承王氏之说而传焉。
由于此前人们一再申说“王用三驱”之“贵仁义”“昭仁”寓意,于是东晋殷仲文《解尚书表》便有“申三驱于大信”之说。所谓“大信”,唐代刘良根据前人所云,曰:“三驱之礼,去三面网而留一面者,言宽仁也”,以“王用三驱”为“宽仁”。[9]卷38,709因“三驱”有申“仁义”之功效,到南朝时,正史中就有了“冬大阅……礼成而义举。三驱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的记载。[11]卷22,654唐代房玄龄等撰修《晋书》时,也援用《宋书》“三驱以崇仁”之说,并书之于《晋书·乐志》中。由于“王用三驱”昭显“仁”德说在历史上影响甚大,一些儒士因此常藉此上疏言政,成为其抒发政论的理论依据,如袁宏《后汉纪》卷6载光武建武十二年(36年),光禄勋杜林奏曰:“汤去三面之网,《易》著三驱之义,所以德刑参用,而示民有耻”。援用“三驱”礼典,疏谏刘秀“法令轻重,宜遵旧典”。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后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4页。更是一些臣僚规劝君王节制狩猎行为的思想工具。这一点在唐代表现得较突出。如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上疏谏劝太宗“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元人戈直注云:“三驱者……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驱,失前禽。盖犹成汤祝网之义”;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张玄素以太子李承乾游畋废学,上书谏曰:“古三驱之礼,非欲教杀,将为百姓除害,故汤罗一面,天下归仁”。均以彰显“仁义”的“三驱”礼劝谏君王恪守礼仪,不可妄为滥杀。吴兢:《贞观政要》卷1《君道》、卷4《规谏太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142页;《旧唐书》卷71《魏徵传》、卷75《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52、2641页。
但是,上述关于“王用三驱”彰显君王德仁之心的阐释,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众多修治《周易》学者的关注,以致汉魏以降的易学家对“王用三驱”的注解大都顺承王弼“爱于来而恶于去”之说。即使北宋初,经学家基本上也没有将“王用三驱”与“仁”相联系。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尽管其《周易口义》曾引用《史记》等文献表彰商汤至“德”的“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网”之典型狩猎事例来释解“田猎之礼”,但他仍未明确地以“仁”释“王用三驱”,依旧用“就事论事”的形式论说“王用三驱,失前禽”之缘由。胡瑗《周易口义》卷2《上经》:“田猎之时,禽有逆之而去者,则弃而杀之;其有顺而来者,则爱而活之。田猎之礼,常失前往之禽也。”(载《四库》第8册,第229230页)不过,而后的程颐在传注《周易》时,其解说开始与此前的阐释有所不同:他不仅释传经意,而且更注重探索经文之微言大义,以人君“好生之仁”的品德释说“王用三驱”。其《伊川易传·比》云:
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泽,是人君亲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亲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违道干誉,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狭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圣人以九五尽比道之正,取三驱为喻。曰:“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先王以四时之畋不可废也,故推其仁心为三驱之礼,乃《礼》所谓“天子不合围”也,“成汤祝网”是其义也。天子之畋,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兽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12]卷1,189190
程氏在将“三驱”释为捕猎之三面围而不合的基础上,明确地以“仁”比“王用三驱”之“道”,认为“三驱之礼”是先王“推其仁心”的产物,而“王用三驱”则是王者“不忍尽物,好生之仁”的表现。因此,程颐用“仁义”释“王用三驱”,深合《周易》之旨。“王用三驱”的释说自此回归儒家说《易》传统。朱熹等肯定了程颐的解说,[13] 卷8,649并将“三驱”和商汤“网开三面”(而非“网开一面”)的行为并论,以之为“仁义并用”[14] 卷2,423之举。后来《周易》传注者大多秉承其说,将“王用三驱”与儒家一贯提倡的“仁义”等美德紧密联系,并成为儒者释说“王用三驱”的主流。如宋代林栗《周易经传集解·比》(载《四库》第12册,第66页):“‘王用三驱,即《礼》所谓‘天子不合围是也,三面而驱,阙其一面,顺而来者取之,逆而去者舍之,古之道也。夫三面而驱,禽之逸者固多矣。圣人以为外物任其去来,而不强取之也。故曰‘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成汤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网,圣人之仁盖如此也。或曰:汤以一面,而王用三驱,何也?曰:三驱,礼也。汤之一面,代虐以宽,矫枉过正,非常道也。原其设心则同矣”;明代胡广等《周易传义大全》卷4(载《四库》第28册,第158159页):“先王以四时之畋不可废也,故推其仁心为三驱之礼,乃《礼》所谓‘天子不合围也,成汤祝网是其义也。天子之畋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兽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其他如元代赵采《周易程朱传义折衷》、胡震《周易衍义》(载《四库》第23册,第7576、505506页)等等,都以“仁义”之德阐说“王用三驱”。清代沈起元《周易孔义集说·上经》(载《四库》第50册,第5657页)对此有系统的条列,可参见。
三、政务说与道德论之辨
“三驱”礼为西周蒐狩礼的重要内容。就考古发现的战国中晚期帛书《缪和》等和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周易》记载“王用三驱”,意在“昭明人君行仁之道”。然而,受《周易》王弼注、孔颖达等正义的影响,长期以来,有关《周易》“王用三驱”的注说均顺承王、孔二氏关于“王用三驱”“爱于来而恶于去”之意,其“显比之事”亦基本限于“唯贤是与”的用人之道,属政治或行政事务的范畴,和《缪和》等强调的王者“仁恩”道德品质说具有显著的差异。由于王弼注的盛行,加之孔颖达正义的作用,“王用三驱”的仁德释说在“十三经”注疏系统中未能得到继承与发扬,而在史学、文学有关释说中,“王用三驱”的道德论则得以弘扬,且始终赓续不断。
但是,无论是王弼注《周易》“王用三驱”,还是帛书《缪和》等以“王用三驱”附说汤之“网开三面”,其“王用三驱”的阐说皆是就狩猎而言的。究其因,与历史时期的蒐狩礼变迁相关。西周蒐狩礼来自于殷商时期的狩猎,是西周将殷商狩猎活动礼乐化的结果。作为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仁义之德无疑被渗透到西周礼仪及其文化要素的各个环节中,蒐狩礼因此也留有浓郁的道德印记,其“阅兵之制”的“王用三驱”“田猎之仪”的“失前禽”,就分别从“以仁恩养威之道”“不忍盡物,好生之仁”的角度,彰显了王者之“仁”德。由于时事和征战形式的变化,春秋以后,传统“阅兵之制”淡出蒐狩礼,“三驱”礼为何也渐为人所忘?而蒐狩礼中仅有“田猎之仪”为世人所知。学术史上有关“三驱”之释、之议,因此基本上围绕田猎活动而展开。参见《〈周易〉“三驱”礼考释》《“成礼三驱”:汉唐时期“三驱”礼衍变述论——以蒐狩礼的建设为线索》。
尽管两类阐说都是针对狩猎活动而发的,但《缪和》等“王用三驱”的道德性阐释,更为契合儒家解《易》的传统。我们知道,儒学创始人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儒家一贯倡导的“仁”德,即源于西周礼仪制度。儒家之“仁”有诸多内涵,但基本点为人与人相爱,即“仁者爱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惟武是崇,诸侯征伐蜂起,兼并不休,民生维艰。然“王道以得民心为本”[15] 孟子集注·梁惠王上,204。为帮助民众摆脱锋镝之厄,儒家力吁争霸者注重民心之所向。如《孟子·离娄上》载孟子曾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开始,王公贵族的游逸性狩猎日趋严重。为有效节制贵族无度狩猎,儒者或借以孔子之口,或以商汤“网开三面”之事,将儒家反复申述的“仁”德,巧妙地和事关“祀与戎”国之大事《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载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页。的蒐狩礼相糅合。同时,儒家认为“仁”是天赋的,仁者不仅爱人,而且还要爱及大千世界的一草一木。儒家之“仁”爱因而又有圈层性,即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物是“仁术”表现之一,而在儒家看来,“仁术”就是“不忍”之心。《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云:“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乃仁术也”。“不忍”之心是儒家对待万物之“仁”的最基本原则和要求;“爱物”则是儒家“仁”的最高境界和追求,“天地万物一体之仁”[16] 卷2,81。这就是学界所谓的儒家“仁”的差异性和普遍性问题。[17] 911
关爱树木禽兽等自然生态要素,并将之与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相联系,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和做法。如《礼记·祭义》载孔子回答曾子“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云:“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1]卷48,1598;《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孔子曰:“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18]卷6,112。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道德规范结合起来,对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加以约束。另外,“生生之谓仁”[19] 卷39、53、929、1268。儒家认为人类还肩负有“生生”万物之道义,学界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粗列有如刘泽亮:《生生之道与中国哲学》,《周易研究》1996年第3期;干春松:《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儒家的构成和发展》,《东岳论坛》2005年第1期;向世陵:《易之“生”意与理学的生生之学》,《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王雅:《“生生”、“感通”、“偕行”——《易传》的天人共生哲学》,《周易研究》2010年第3期;乔清举:《论“仁”的生态意义》,《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3期;蒙培元:《〈周易〉哲学的生命意义》,《周易研究》2014年第4期;陈来:《仁学本体论》,《文史哲》2014年第4期;窦晨光:《儒家“生生”义考》,《孔子研究》2017年第3期;等等。《周易》“元亨利贞”和万物的生长遂成、人之仁礼义智乃三位一体,《伊川易传·上经·乾》(载《四库》第9册,第157页):“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周易本义·上经·乾》:“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上经·乾》,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页)元是万物之始,“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不当或过度地利用万物,就是“尽物”,违背“生生”之仁。因此,对自然万物的道德关怀是人之“仁”的本能表现和基本要求,“爱物”为“仁”的内在规定,这就是所谓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20]卷2上,65。儒家之“仁”因此具有生态伦理的意义,从而被后世力加申述,并用来诠释于“三驱”之中。如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宋祁注《汉书·扬雄传上》载扬雄《校猎赋》“三驱之意”即曰“不忍尽物,盖先王之仁心”;南宋董楷也完全接受程颐之论,赋予“三驱”以“推其(王)仁心为三驱之礼……不忍尽物,好生之仁”[21] 卷3上,167大义;清代内阁学士徐乾学等注魏徵劝谏太宗“思三驱以为度”时,同样云“三驱者……不忍尽物,好生之德也”。[22]卷30,626后世的进一步阐述和申说,不仅丰富了“王用三驱”的内容,而且使“三驱”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些学者在其研究成果中,即对“三驱”在生态资源保护方面的价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这方面成果很多,粗列者如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杨文衡:《易学与生态环境》,中国书店2003年版;张云飞等:《中国传统伦理的生态文明意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彦民:《由商汤“网开三面”说到商代鸟类保护观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常春雨等:《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郑玄.礼记正义[M]∥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2]王弼,韩康伯.宋本周易注疏:卷3[M].孔颖达.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8.
[3]张浚.紫岩易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刘大钧.再读帛书《缪和》篇[J].周易研究,2007(5):310.
[5]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6]毛亨传,郑玄.毛诗正义[M]∥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7]罗愿.尔雅翼[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9]萧统.六臣注文选[M].李善,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程颐.伊川易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张京华,辑校.长沙:岳麓书社,2009.
[14]郑刚中.周易窥余[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7]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1]董楷.周易传义:附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2]徐乾学,等.御选古文渊鉴[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