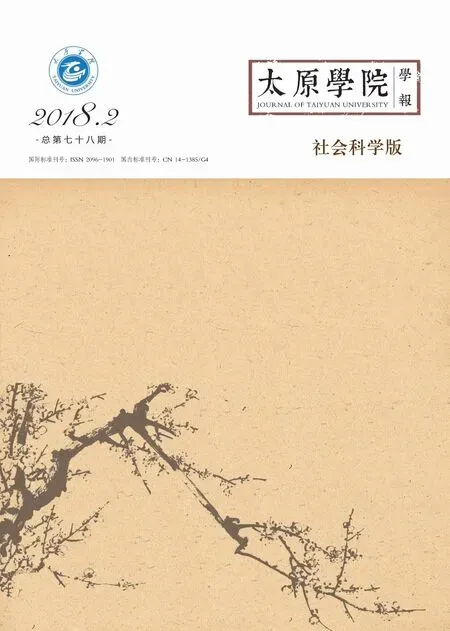地理·情感·时事曾懿的行旅经历与女性成长
范 婷 婷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研究明清妇女史及女性文化的学者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从17世纪起,为数众多的才女闺媛将写诗作为自我再现的一种手段”[1]21,即她们以诗歌记录生活,展现自己的成长经历、内心世界和人生感悟。曾懿作为晚清闺阁女性,亦是其中的一员。
曾懿,字伯渊,又名朗秋,四川华阳人(今属成都),清末著名的女中医与女诗人。其父曾咏,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于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初二日巳时,因积劳成疾殁于太平军次。而后,其母左锡嘉扶柩归葬,曾懿亦随母归川。归川后,居于成都浣花溪侧。因生活困顿,其母左锡嘉以卖字画为生。在成都的闺阁时光,对于年幼丧父的曾懿而言,可以说是生活困顿而精神富足。在其母左锡嘉的主持下,曾懿、曾彦、曾鸾芷姐妹与赵韵卿等友人结浣花诗社。诗社成立之际,左锡嘉与曾懿均作有《浣花诗社歌》。
婚姻使女性社会身份发生转变,并为女性的远距离出游提供可能,不少女性在结婚之后便随夫宦游。光绪元年(1875),时年二十三的曾懿,适江苏武进袁绩懋之子袁学昌(字幼安),“幼安赘于蜀”[2]5262,即婚后二人居于蜀地。光绪三年(1877)年,即婚后第二年,曾懿随袁学昌归闽中,开启了她一生的行旅之途*在《辛卯秋赴太和阻雨六安,正白云在天,苍波无极,回忆故乡骨肉,大半天涯死别生离,不胜悲感因和杜陵秋兴八首以寄兄弟姐妹·其四》一诗中,曾懿注云:“丁丑,余归闽中,叔俊四妹归铜梁。同时分手,幸将来皖,心窃慰之”。。她先后随夫旅居于福建、安徽各地,在领略各地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同时,亦感知社会百态、国家现状。晚年的曾懿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作《医学篇》与《女学篇》,倡导强国保种、男女平权。可以说行旅经历对她产生重大影响,她的眼界与心境在行旅中不断开阔,并以作诗的方式将这些感受与变化记录下来。
曾懿的《古欢室诗词集》共四卷,包括《浣花集》《鸣鸾集》《飞鸿集》《浣月词》。正如其兄曾光煦所言,《古欢室诗词集》中的《浣花集》是曾懿在草堂闺中所作;《鸣鸾集》是其“由川入闽,由闽之皖”期间所作;《飞鸿集》是其“随宦皖江”期间所作,而《浣月词》虽未点明何时所作,考察其内容亦有不少是随宦期间所作。故本文以《浣花集》《飞鸿集》《浣月词》三卷为文本对象,以时间为序,在梳理曾懿行旅路线的基础上,探讨她在行旅过程中内心世界及关注点的变化,进而展现其成长历程。
一、行旅路线与阶段
行旅是一种漂泊的人生状态,从此地到彼地,而行旅书写则能够“成为沟通与调节不同场域的管道”,透过那些沉淀下来的符号,相关的场域、相关的历史都不断地被诠释着与理解着[3]。行旅诗属于行旅书写的一种,它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记录着作者在行旅中所途径或生活过的地方,以及路途中的情感变化。在中国古代,男性出行较为方便,而身处闺阁的女性,除少部分因生计逼迫不得不自己出行外,更多的女性是随着父亲或者丈夫进行远距离的出游活动。同大多数闺阁女性一样,曾懿的行旅亦是随夫宦游。
曾懿与袁学昌的结合属于家族联姻,袁学昌之母左锡璇与曾懿之母左锡嘉为姐妹。光绪元年(1875),曾懿与袁学昌结为连理,因二人结婚后仍居住在四川,故将四川华阳(成都)视为曾懿的故居之地。以曾懿的诗歌为基础,兼及其他资料,可推知曾懿大致的行旅路线:
第一阶段:由川入闽。光绪三年(1877)年,结婚第二年的曾懿随袁学昌归闽中。这年秋天,曾懿好友赵佩云闻其将远行,特来叙别,曾懿以《赵佩云夫人闻余将有远行特来叙别时秋菊盛开》一诗纪之。远行之际,正值岁末寒冬,曾懿另作诗《旋闽别亲》一诗以抒发内心情感。曾懿随丈夫袁学昌乘船前往福建,夫妻二人一路写诗唱和,其间经过大佛岩(重庆武隆)、巫峡、夔州(重庆奉节地区)、归峡、巫山(湖北、重庆、湖南交界)、彝陵(亦称夷陵)等地。
第二阶段:由闽入皖。由川入闽之后,袁学昌因举业之事奔波外地,曾懿留在闽地,期间她创作了具有闽地特色的诗歌,如《闽南竹枝词》;亦有传达相思之情的诗歌,如《闺中意别呈外子》。据史料记载,光绪五年(1879),袁学昌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袁学昌以知县发安徽,曾懿亦携子由闽入皖。其诗歌中对这部分的记录较少,但透过零星的作品,亦可知在这一时期,曾懿的诗歌中对情感的关注明显增加,包括思亲及思夫之情。
第三阶段:随宦皖江。光绪十一年(1885),袁学昌署英山;光绪十九年(1894),袁学昌时任太和知县;光绪二十四年(1989),袁学昌任全椒知县;光绪三十年(1900),任涡阳知县。曾懿诗歌中展现出的地点与之相对应:《英山官廨四面环山朝霭夕霏掩映几案时届仲冬朔气凝云冻痕积雪寒窗寂坐忆故乡忽奉母书感而赋此》《辛卯秋赴太和阻雨六安正白云在天苍波无极回忆故乡骨肉大半天涯死别生离不胜悲感因和杜陵秋兴八首以寄兄弟姐妹》《全椒官廨即事感赋》《南浦·春水用玉田韵寄幼安涡阳》等,诗歌中还有展现旅途过程的地点:潜山,六安,安庆等。随宦皖江的这一时段,曾懿的诗歌内容明显发生变化:在表达思亲时透露出自己的漂泊之感,更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二、诗歌内容
以诗歌记录随宦之旅的点点滴滴,曾懿似乎想以字句的形式将行旅中的见闻与感受固定下来,永恒化。考察曾懿的行旅诗不难发现,她以地理、情感与时事为书写对象,展现宦游途中自身的变化,从侧面展现出闺阁女性的成长历程。
(一)自然地理与人文风情
《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4]。刘勰在此处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江山之助”,即山川自然景物,能够触发人的情志,助人写作。曾懿随袁学昌宦游多年,颇得江山之助。对比曾懿初期《浣花集》中的作品,《鸣鸾集》与《飞鸿集》中的诗歌题材无疑是更为丰富的。曾懿在行旅诗的写作中以时间为序,记录空间的位移,而空间的位移是以自然地理的书写呈现的。以行旅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由川入闽中纯粹的自然地理书写最为集中,故以之为例:
八阵雄图馀垒蟠,卧龙遗庙枕狂澜。
断云压雨过鱼复,一舸洄旋飞过滩。[2]5277
(《由夔府溯流而下山峡险峻古迹甚多诗以纪之·其二》)
曾懿从四川经由重庆、湖北前往福建。在借道重庆的过程中,曾懿写下五首与地理位置有关的诗歌:《舟过大佛岩》《巫山高》《舟过巫峡见十二峰高插霄汉神女峰尤为纤丽俊俏神女庙在山之巅》《过归峡》及本诗。夔府指重庆奉节地区,曾懿在《由夔府溯流而下山峡险峻古迹甚多诗以纪之·其二》一诗中集中记录了鱼复、武侯庙、八阵图三个景点。诗中“八阵图”是诸葛亮用石头垒成的,位于鱼复(重庆奉节)。“卧龙遗庙”是指武侯庙(诸葛亮号卧龙)。关于二者的地理位置,曾懿做过说明:“八阵图在府南,垒石为之,武侯庙即在八阵图台下”[2]5277。该诗后两句记录下雨时乘舟过虎须滩的情形,水中有洄旋似乎使得行程艰难,然而自己的船竟然一下子就通过了,曾懿为此注云:“舟过虎须,幸遇风利,一旋即过”[2]5277。诗中的“滩”即虎须滩,《水经注释》云:“江水又径虎须滩,滩水广大,夏断行旅”[5]。显然,能一次就通过虎须滩是十分幸运的,也无怪曾懿加小注详记之。在本诗中,曾懿详细书写了八阵图、武侯庙、鱼复、虎须滩四个位置及其情形,一方面记录行旅所经过的路线,另一方面亦展现出行旅途中的艰辛。
曾懿行旅诗中除了有关自然地理的记录,亦有有关人文风情的记录。首次离家,初到闽地的曾懿接触到与四川很不相同的文化氛围,她对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充满好奇,将当地的习俗文化以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批语的形式进行详细说明,在此选取《闽南竹枝诗八首》中的有批语的部分加以说明:
纸鸢掩映碧天心,稚子欢呼闹隔林。
三月薰风春画静,市声高卷女儿音。
(其二)
窄袖织腰黑练裙,香花堆鬓髻如云。
压肩鲜果沿街卖,贸易归来日已曛。
(其三)
盘龙宝髻簇流苏,红袖买春携玉壶。
怪道冰肌甘耐冷,严冬犹自赤双趺。
(其八)[2]5279
正如迈克·克朗所言,“特定的空间与地理位置始终与文化的维持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内容不仅仅涉及表面的象征意义,而且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6]。从地理方位上而言,福建属于东南地区,而四川属于西南地区,二者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包括气候风貌、服饰装扮、风俗习惯等,都有很大差别。《闽南竹枝诗八首·其二》是有关清明时节儿童玩耍纸鸢的记录,曾懿称闽中这个地方夏天热得比较早,每年清明的时候儿童都“以纸鸢为戏,使得清灵之气,以免疾病”[2]5279。《其三》与《其八》都是有关女性的诗歌,前一首中曾懿从着装入手,加以描写。窄袖之便在于“袖窄弯时不碍肘”,练裙”指妇女所穿的裙子,此处的女性着窄袖之裙,系着腰带,她们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水果,等卖完回来天已经黑了。这显然是下层劳动妇女的形象,曾懿批注云:“闽中凡耕田、挑负贸易者,半是妇人”[2]5279。后一首中曾懿从发饰入手,“宝髻”指女子的发式,“流苏”指附在簪、钗之上的一种金玉装饰。穿着打扮漂亮的这些女性,一定十分耐寒,冬天出门竟然也不穿袜子,此处展现出的是妩媚的女子形象,曾懿批注云:“闽中女子妩媚者多,然虽至严冬不袜亦不觉其寒,奇矣”[2]5279。这三首诗歌的内容均是曾懿以外来客的视角,关注福建地区的文化。
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曾懿都以一种新奇的目光进行审视与记录,行旅无疑开阔了她的眼界,丰富了其诗歌内容。同时,展现出曾懿行旅的空间变化。
(二)行旅与情感
随宦在外,女性细腻的特质使得她们对周围的变化更为敏感。在曾懿的行旅诗中,以亲人家乡为书写对象的诗歌占据极大部分,且很明显地能看出情感的变化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深刻的。以时间为序,考察曾懿的行旅诗,大致按行旅路线,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由川入闽途中,曾懿透过诗歌展现给大众的是一个颇为矛盾的状态。正如上文所言,一方面在出发之后,她被大自然的神奇瑰丽所吸引,无比兴奋;而另一方面,在出发之前,由于是离开熟悉的地方前往他处,未来不可预知,这使得她充满不安,她不断表达出此次远行的无奈与感伤,以《旋闽别亲》为例:
(一)
生小依依骨肉亲,天涯忽已转雕轮。
明知久聚愁言别,故作欢言强对人。
燕寝何时承色笑,鹿车从此历风尘。
亲心更比儿心切,隔夕先看泪满巾。
(二)
一曲骊歌百虑攒,思亲容易侍亲难。
夔关雪冷魂先怯,巫峡云深梦亦寒。
雁影无端重聚散,鱼书从此望平安。
临岐无限伤心泪,忍到鸳舆细细弹。[2]5276
从空间转移的角度看,表达思乡怀人的行旅作品大致有三种写法:其一,离别之地的相送;其二,行旅途中外界诱发的相思;其三,抵达目的地之后写相思[7]。本诗属于第一种,即在离别之地写分离场景与心情。前四句指出诗人自小跟亲人生活在一起,出嫁之后也是如此,却突然要与在外谋官的丈夫离乡,一个“忽”字流露出无限的无奈与哀痛。久聚之下,离别显得更为伤感,为了不让亲人伤怀,她不得不强颜欢笑。随后两句描写了诗人对未来的想象,路途遥远,乘坐鹿车,不知几时能至。从前进的路途到目的地,一切都是不可知的,而恐惧往往诞生于未知。透过那一方濡湿的巾帕,诗人窥见了亲人比自己更深沉的离别之痛。后四句尽是诗人想象的场景,分别是诗人对离别情景、旅途与抵达目的地后境况的想象,充满了画面感。最后一句更是神来之笔,将诗人从想象的情景拉回现实,临别时无限伤心的泪水,却要忍到上车后才发泄出来,这既是怕亲人更加伤心,又是怕自己这样下去会更加不忍离别,但离别已是必然。无限感伤,无限心思,尽藏于诗。
在第二个阶段中,袁学昌到京中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曾懿留在福建,夫妻二人分别。如众多闺秀一样,曾懿不得不独自处理家庭的大小事,这样的情况下,她对家乡的思念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万里关山客路遥,征云漠漠水迢迢。
衰亲望眼今犹昔,游子含愁暮复朝。
远信欲催过岭雁,离怀怕听隔溪箫。
夜来幸有远乡梦,骨肉团圆慰寂寥。[2]5280
(《接不接家书作此解闷》)
在陌生的异乡,思亲念友之情似乎格外容易迸发出来。此处曾懿以家书为切入点,传达自己渴望接到家书,以解相思之情。四川与福建相隔千里,路途遥远,亲人之间相见实难,作为传递情感的家书怎么还不来呢。随宦远方,音讯难通,惟有梦中团聚。诗人有意采取梦中团聚的虚写,将现实中自己远离家乡、亲人分离的情况道出。
在第三个阶段中,曾懿“随宦皖江,萍踪靡定”。离家多年,漂泊亦多年,她不断以回忆往昔、梦游故园、寄诗亲友等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在描述该阶段行旅历程的《飞鸿集》中,曾懿记录了她与五妹曾彦的相聚:
嗟我同怀子,离居踰十年。十年积沉思,衷情何由宣。君今来吴越,皖江停双辙。相离苦郁纡,相见同愉悦。甘醴涤清尘,朱颜华灯列。方经十日欢,复作千里别。千里隔江都,送君登艟舻。临组心不畅,携手共踟踌。浮轮无返轨,长波飞辘轳。怅望不可见,泪下如连珠。山川修且阔,魂梦渺以邈。既伤心绪违,且感年华促。重会杳何极,忉怛业忧绩,安得乘风翔,高飞振六翮。
(《季硕五妹由川往苏皖垣小聚别后赋此》)
光绪十一年(1885),易佩绅移任苏州。张祥龄应其邀请,挈家前往苏州[8]。经过安徽时,曾彦与曾懿得以相见,曾懿姐妹二人在离别后作此诗。关于二人相见的时间,曾懿有言曰:“(辛卯,即1891年)去秋季硕五妹又卒于吴,忆曩时花萼连芳。欢乐无极,不意丁年一别,竟成永诀。”光绪时期与“丁”有关的年份有三个:丁丑(1877),丁亥(1887),丁酉(1897)。而在这三个年份中,处在1886年与1891年之间的只有丁亥年(1887),据此可知二人相见时间为光绪十三年(1887)。离家十年,相思之情多借家书慰藉。而此时,自己却能和妹妹相见,将一腔衷情倾诉,这无疑是让人兴奋的。相聚的时间似乎格外短,才十日曾彦就将乘船离去。姐妹二人心情抑郁,拉着手久久不愿离去,诗人自己也是泣不成声。
如果说这次的相见聊慰了曾懿的思乡思亲之情,那么亲人的不断离世,似乎让相见更具悲凉意味。在这个阶段中,曾懿的思乡怀人作品充满漂泊悲苦的意味,以《辛卯秋赴太和阻雨六安正白云在天苍波无极回忆故乡骨肉大半天涯死别生离,不胜悲感因和杜陵秋兴八首以寄兄弟姐妹》为例,这是典型的写于行旅途中的思乡怀人组诗。作此诗时,三妹曾玉(字仲仪)、五妹曾彦(字季硕)、六妹曾祉(字茝香)均已离世;大哥曾光禧、二哥曾光煦(字旭初)、三弟曾光岷(字蜀章)、四弟曾光文(字季章)各在一方。字里行间,曾懿的漂泊、无奈与凄苦全然呈现,以该组诗中的总结性篇章为例:
平畴雨润绿逶迤,疏柳含秋映泽陂。
衙古蟠松苍翠盖,庭间菊剩傲霜枝。
年年愁病风霜苦,夜夜乡心四海移。
珍重天涯诸弟妹,莫教两鬓雪丝垂。
(其八)
该诗借由太和署中之景,抒写自身宦游途中的凄苦。兄弟姐妹生离死别,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漂泊凄苦之感陡然上升。万般无奈,只可道一声珍重。
从第一阶段的不安与新奇的交织,到第二阶段的强烈思亲与思乡,再到最后一个阶段中与亲人生离死别,自身颠沛漂泊,使得该阶段的思乡与思亲更具凄苦意味。总体说来,在表达思亲怀人的作品中,曾懿传达出的情感是逐步深刻的,而深刻源于经历,源于长期的宦游之旅。
(三)行旅与时事
在记录行旅中的所见所闻中,诗人以特殊的具体的社会大事件为背景,表达了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传达忧世情怀。遭逢世乱,她以幽微的言语探索历史真相,抒发兴亡之感,展现出自身的历史关怀,更是体现了“诗史”的理想”[1]175。对女性来说,书写社会时事,发表自己观点,这一行为意味着她们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这半亩方田,而是扩展到社会。在行旅的第三个阶段,即随宦皖江期间,曾懿以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两件大事为背景,写下诗篇,表达自己的想法。曾懿行旅诗中有一诗是关于水患的:
翩翩者鹏,振翼云霄。之子于征,自彼荒郊。朝登山麓,宿夕江皋。灿星被野,零露盈条。阴霾暗晦,曜灵不骄。洪流浩淼,平陆腾蛟。彼黍既陨,彼禾云凋。哀鸿遍野,饥哺嗷嗷。肃肃君子,诚笃可钦。自夏徂秋,淹留至今。嗟我怀人,永啸长吟。瞻望靡路,离居同心。横琴不弹,旨酒停樽。游鱼潜渊,倦鸟林归。勉志修业,以隆德音。[2]5282
(《英霍患蛟外子赈饥诗以奉答》)
该诗是曾懿写给袁学昌的,作诗的起因乃是英霍之地患蛟,袁学昌赈灾。古人以为洪水是蛟所发,故称蛟水。该诗中“洪流浩淼,平陆腾蛟”一句亦表明本诗记载的乃是英霍之地的洪灾。在地方志中,有两条关于袁学昌赈灾的记录。其一,《霍山县志》有载:光绪八年(1882)夏,霍山地区“霉雨蛟水暴涨,没田庐不计”,时霍山县令李璜“慨然据灾形详请大府简名吏袁学昌,勘覆劝辦赈给明年,特恩免春夏税千金”[9]。其二,《沈丘县志》有载:光绪十九年(1893)旱涝虫灾,太和县知事袁学昌由颍州府借来一批人马到界首捕蝗[10]。从地点上看,曾懿诗中记载的显然是1882年霍山地区的洪灾。材料一中“大府”指上级官府,这则材料中表明洪灾发生时,袁学昌在霍山上级官府为官。光绪六年(1880),袁学昌以知县发安徽,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袁学昌任英山知县。故1882年的这场洪灾中袁学昌确在安徽为官,且参与赈灾。
该诗中,曾懿一方面以悲悯的情怀描绘洪灾肆虐后的场面:粮食歉收,灾民甚多,嗷嗷待哺。另一方面以颇为自豪的语言赞美丈夫袁学昌的赈灾之举,从她的叙述中可以得知赈灾之举已经持续很久了,夫妻二人亦许久未见面。曾懿以“游鱼”“倦鸟”两个意象传达自己期盼丈夫归来的心情。“勉志修业,以隆德音”一句中,“修业”指建功立业,实际上是曾懿对初出为官的丈夫的鼓励,希望他能有一番造业。随着时间的转变,时局的动荡,曾懿从最初勉励丈夫“修业”,逐步转变为希望自己能隐居:
丹心铭帝阙,骨肉阻关河。
冀北烽烟壮,江南感慨多。
连天悲鼓角,何日奏饶歌。
愿觅岩棲隐,结茅补薜萝。[2]5290
《全椒官廨即是感赋·其四》
诗人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在首句直接地抒发着自己的爱国之情和骨肉分离的伤痛。颈联中诗人将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娓娓道来,冀北之地发生了战乱,而江南之地还是相对安全的。颔联中诗人以连天的战场上的鼓角之声展现战乱的艰难,期待战争早日结束。尾句中“薜萝”是指隐者的住所,而隐者的住所往往充满祥和的意味,诗人借以表达对乱世的忧心及强烈的家国情怀。
关于该诗的内容,大致可以做上述解释。然而,进一步考察该诗创作的时代背景,发现它所展现出的意蕴更为深厚。该诗结束后,曾懿有一小句批语:“庚子遭拳匪之乱,时大、四儿均在京中,依蜀章三弟处”[2]5290。据此可推知,该诗约创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990)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期。曾光岷,字蜀章,曾懿三弟,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人,次年(1889)中进士,官刑部贵州司主事。曾懿大儿袁励祯与四儿袁励衡皆在北京依曾光岷。曾懿在该诗中以“骨肉阻关河”表达在战乱时期,一个母亲对出行在外的孩子的担忧。她以个人遭际展现社会动荡背景下骨肉分离等一系列状况。在批语中,曾懿将义和团运动定义为“拳匪之乱”,“拳匪”是一个含有明确的价值判断的词语。从该词在义和团事件描述中使用的普遍性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义和团之匪徒性质的普遍认同,很显然在曾懿眼中这是一场暴乱。她希望胜利的一方是朝廷,是清政府,这与她自身所属的社会阶级(士绅阶层)有关。
另外在这个阶段中,曾懿还在诗歌中记载曾旭初治理宿松水荒、袁学昌平叛涡阳之乱等历史事件。她用写诗的方式,叙述个人的经验和记忆,充当历史的见证者,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寻求自身的价值所在。从最初鼓励丈夫建功立业到渴望家国安稳太平,曾懿的思想情感发生重大变化,她的目光在投向家庭的同时更关注着时局。
三、行旅经历与个人成长
《现代汉语词典》中“行旅”作动词时与“旅行”同义,即“为了办事或游览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基于地理空间而言,行旅意味着空间位置的转移,即身为主体的人要借由船、马车、轿子等交通工具,从此处前往他处。而不同的地方拥有自身独特的地理文化,标志性的就是不同的风景,它是“身份(status)的附属物,是认同的缘起,是自我或集体意识的再现,经过意识形态再现的风景甚至可以起到更强的固化身份和强化自我或者集体意识的作用”[11]。
曾懿的行旅书写中,有大量的关于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的诗歌,并以极为详尽(做批注)的方式对所见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加以记录,她通过文字与陌生的地方发生关联,使其成为自己获得归属感和建构自我主体的场所。正如前文所言,曾懿的行旅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这意味着她所生活的地理空间是不断拓展的,她建构自我的过程是不断进行的。
从时间概念上而言,行旅的时间并非某个时间点,而是一个持续性时间段。随着行旅时间的深入,闺阁女性的情感体验与心理状态呈现出变化。曾懿行旅诗中对情感与心理的描写着墨较多,从行旅的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所呈现的情感是逐步深刻的,以思乡与思亲为例,第二阶段增加了思念的对象——丈夫;第三阶段又加入了自身的漂泊与无奈之感。这实际上呈现的是闺阁女性在长期宦游中的情感变化。如果说地理与情感的书写展现的诗人个人小我的情感体验,那么对于时事的书写无疑是展现大我的情怀。有关时事的诗歌集中在随宦的第三个阶段,这意味着经过时间的磨砺,她的目光逐步投射到社会现实,关注国家命运,而非局限在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明末清初出现了“巡游的女塾师”,她们独立于父亲与丈夫之外谋生,其“身体的流动性及其越出自己闺阁的能力……都颠覆了女性生存空间封闭性的理想”[12],王端淑、黄媛介都是其中的翘楚,她们不依从父亲或丈夫进行远游。但这只是少数人,对明清的闺阁女性来说,随父或者随夫宦游依然是其开展远距离行旅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指出,她们“通过在赴任途中或者在远任上服侍父亲或者丈夫”,彰显其恪守“三从”之德,即她们随宦远行的行为并不会被视为僭越之举,而“这种顺从转化成为了开阔眼界的机会,给行旅者带来了乐趣和新知识”[11]。换而言之,在男性亲人的支持之下,她们逐步走出家门,接触外部世界,对时世与时事加以关注,并以作诗的方式进行发声。
“诗歌是盛世教化的工具”[13],而晚清的时局风雨飘摇,盛世之景早已不复存在。行旅使得曾懿更为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到晚清的社会现实,即盛世不再,诗歌无益。故而,考察其诗歌内容,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她本人在对待诗歌的的问题上是有矛盾性的。一方面她认为“人生处世苦局促,唯有新诗可傲骨。摇笔长吟天地宽,放怀何必争荣辱”(《季硕五妹以诗见示题其卷后》),将诗歌视为书写个人情志、表达个人情绪的形式,认同“诗言志”的传统。另一方面,她又认为“恨我非男振厥声,文章无用博公卿。羡君晋皖勋猷著,天性融成一鉴清”(《再和二哥宿松留别原韵·其一》)。对于女性而言,“感怀家国背后是若隐若现的性别牢骚”[1]190。无论是幼时的“怅怅不食终日”,还是长大后的“恨我非男”,曾懿以书写性别牢骚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家国情怀。在她看来,文章之事对男性来说是关乎举业的大事,是他们介入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而对于女性来说,文章之事似乎只能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她们无法通过诗词歌赋获得功名,进而介入社会管理。对待诗歌问题的矛盾性实际上反映出曾懿本人的转变与成长,她渴望能在风云变化、民族危亡时刻尽自己的力量,这与她《女学篇》中倡导男女平权的思想是一致的。
行旅经历在曾懿的生命历程中留下重要的印记,透过她的诗集,可以发现她的目光已从小我转向大我,从关注相夫教子、主持中馈的家庭琐事迈入关注国家兴亡、社会现状的领域。这一过程,正是其成长历程。晚清的大多数闺阁女性同曾懿一样,她们不再沉溺于个人的人生悲叹之中,而是或以文本的形式,或以实学的方式,或以革命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与国家之中。她们对社会现实与家国命运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诗词歌赋之中,更是将之付于行动。
参考文献:
[1]方秀洁,魏爱莲.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曾懿.古欢室诗词集[M]//清代闺阁诗集萃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3]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第16辑[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78.
[4]刘勰.文心雕龙[M].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5.
[5]赵一清.水经注释[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564.
[6]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7]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M].北京:中华书局,2003:115-116.
[8]张远东,熊泽文.经学大师廖平[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59.
[9]秦达章,何国佑.霍山县志(影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3:474-475.
[10]沈丘县志编纂委员会.沈丘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631.
[11]苏锑平.风景叙事与民族性的塑造[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16-820.
[12]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3]杨彬彬.曾懿与晚清“疾病的隐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2):113-118.
——行旅图中的文人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