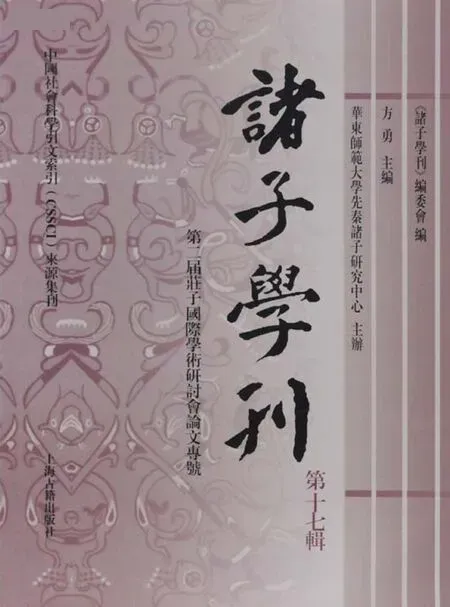莊子學派對老子無爲思想的拓展
李秀華
内容提要 以莊子爲核心的莊子學派,其思想仍然是以老子思想爲基石。這一點在他們闡述無爲思想時,體現得十分明顯。儘管莊子學派内部對於無爲的認識存在差異,但無疑都是從精神世界這個層面對老子無爲思想大力拓展。以莊子本人爲代表的一部分學者,他們沿着老子“致虚極,守静篤”這一理路下來,否定世俗一切行爲,甚至人的情感,提出了逍遥恬淡即無爲的觀點。還有一部分學者,他們立足於性命這個概念,沿着老子“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這一理路下來,激烈反對仁義智巧,提出了安性順命即無爲的觀點。另有一部分學者,他們則立足於天道這個概念,沿着老子“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這一理路下來,將無爲視爲帝王不能缺失的德性,演變成帝王自我修養和統治民衆的一種精神境界。莊子學派對老子無爲思想在精神層面的拓展,雖然一方面消泯了無爲之於世俗社會的能動作用,但另一方面又發現了無爲之於藝術創造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 莊子學派 老子 無爲 精神世界
前 言
莊子的生活年代,稍後於列子,與梁惠王(前400—前319)、齊宣王(前350—前301)、楚威王(前340—前329年在位)同時。這個時期正處於戰國中期,百家競流,精彩紛呈。莊子學派是其中較有特色的一派,它以老子思想爲根本,融合關尹喜、列子、楊朱等早期老學學者的觀點,創造性地發展和壯大了道家的思想力量,對後世産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莊子學派是對莊子及其弟子和再傳弟子所形成學術流派的總稱,《莊子》一書是該派思想主張的集合。關於《莊子》篇目的作者、年代及真僞問題,自北宋以來争議不斷,有很多學者試圖去分辨哪些篇目屬於莊子自著,哪些篇目屬於莊子後學,哪些篇目屬於僞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都不是一錘定音的結論。因爲《莊子》中的每一篇並非都是統一在一個思想主題下的論述,有的甚至自相矛盾,説明其中有些篇目仍是各種言論的匯録。因此,我們認爲用莊子學派這個稱呼來討論其無爲思想,是比較穩妥的做法。而學者在討論莊子的無爲思想時,大多忽視了莊子學派内部的觀點差異,而混作一談,故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梳理與研究。
莊子學派非常推崇老子,稱他爲“古之博大真人”,並對他的思想進行了總結:“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虚,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鋭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莊子·天下》)這段總結幾乎就是對老子無爲思想的精妙闡述,特别突出了老子無爲思想中不争不先、致虚守静、持弱守柔的主張。莊子學派也幾乎全盤接受了這些主張,其無爲思想除了吸取列子、楊朱的觀點外(1)列子御風而行,先要經過自我意志和情感的消融,由此進入神秘的精神體驗,這爲莊子學派所發揚光大。楊朱以無爲而全生的思想,也爲莊子學派所吸收。《莊子·讓王》云:“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又云:“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重生輕物,就不被天下、功名、利禄所束縛,就能做到無爲而全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對老子無爲思想的承襲和充實而已。但在這承襲和充實過程中,莊子學派由於自身觀點的不統一,實際上把老子無爲思想導向了不同的理論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改造了老子的無爲思想。
一、 摒棄世俗一切作爲,逍遥恬淡即無爲
莊子學派内部有一部分學者闡釋無爲,是沿着老子“致虚極,守静篤”(《老子》十六章)這個觀點下來的,再加以極致的發揮,將其完完全全引入到了人的精神層面。這部分學者以莊子本人爲代表。劉笑敢先生認爲,莊子的無爲與實際事務無關,這是老莊之間的一個很大不同之處。老子的無爲是一種方法,指向一定的目的,例如克服對立和逃避災禍等,而莊子的無爲則不考慮任何具體問題,只想超越日常世界(2)劉笑敢《無爲思想的發展——從〈老子〉到〈淮南子〉》,《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2期,第96頁。。與實際事務無關,不考慮具體問題,超越日常世界,説明這部分學者把無爲理解成了無所作爲。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突出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爲了實現精神上的無爲,他們必須首先排斥世俗社會中一切帶有目的性的作爲,治理天下則是首當其衝。《逍遥遊》虚構了一個居住在姑射之山的神人,這個神人不吃五穀雜糧,只是吸風飲露,卻能乘雲御龍,遨遊在四海之外。作者借連叔之口爲這個神人發出了感歎:“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即使堯舜,也不過是神人眼中的塵垢秕糠,神人根本用不着去理會治理天下、管理萬物這些世俗的事務。在《讓王》篇中,舜要把天下讓給善卷,善卷回答説:“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把個人的一切托付給天地,融入自然,根本不需要做什麽額外的事情,就能獲得逍遥自得的樂趣,那誰還在乎什麽天下國家呢?在這部分學者看來,把天下國家的世俗事務攬於自身,不僅會使自己徒增煩惱,可能還會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所以任自然、不治理要比人爲的治理好。《應帝王》虚構了天根和無名人的一段對話,當天根問無名人怎麽治理天下的時候,無名人大罵他是鄙俗之人,並説:“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意思是説,天下根本不需要什麽實際的治理工作,你只管讓你的精神遨遊,不起私心,順應萬物的自然天性,一切就會不治而治。天下國家不值得爲,也不需要爲,其主要原因是他們相信天地萬物本身就很完美,人爲的造作只會破壞這種完美。他們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説。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知北遊》)天地的大美、四時的明法和萬物的成理,都不是人爲的。要讓這些最美的東西呈現出來,最好的辦法就是無所作爲。
在摒棄治理天下的事務之後,莊子學派的這部分學者認爲還要摒棄個人的一些俗務。《應帝王》云:“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世俗的名位、謀略、事業、智巧,都不值得個人去主導和追求。得道的人對於世俗社會的用心就像一面鏡子,完全被動地去反應,不主動也不保留,以此來避免世俗社會所帶來的傷害。應該説,這也是這部分學者摒棄個人世俗事務的目的之一,他們稱之爲衛生之經。《庚桑楚》云:“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至人只與天地相往來,決不允許世俗的利害來干擾,不求立異,不作謀劃,不務俗事。生活在世間,卻要以出世的態度相對待,這主要是由於處世的艱難。《山木》篇的一則寓言故事最能説明這一點。木因爲不材而得以頤養天年,雁因爲不鳴而命喪農夫之手,莊子和他的弟子們對此都感到深深的困惑。莊子感歎説:“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世間俗事總是擺脱不了正反相隨的規律,合帶來離,成帶來毁,鋭帶來鈍,位尊而遭非議,有爲而遭虧損,賢能而遭算計,平庸而遭欺侮。那乾脆什麽事都不做,将自己托付於没有世俗傷害的“道德之鄉”。
這一“道德之鄉”,實際上只是一個被隔離、被净化的精神世界。它的形成不僅需要摒棄世俗的作爲,還需要不斷減損個人的感覺、情感、意志和思維。《在宥》篇中,廣成子在回答黄帝如何得以長生的問題時説:“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心静必清,無勞女形,無摇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内,閉女外,多知爲敗。”庚桑子亦説了相似的話:“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庚桑楚》)完全關閉個人的感覺器官和思維器官,使形體不勞,精神不疲,這是達到“抱神以静”狀態的必由之徑。
除了關閉感覺和思維外,莊子本人還提出了“無情”之説:“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從這段話看,他所主張的無情是指排除那些非自然的、過分的個人情感。《庚桑楚》的一段文字可以視爲莊子“無情”説的注脚:“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静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心中存有某種目的而去開展相應的行爲,這即是有爲。無心的、不得已之類的行爲,則可以看作是無爲。同樣的道理,排除那些非自然流露的、非不得已之類的情感,便是無情。但莊子後學主張的無情,則没有這樣細分,擴展至人類一般的情感。《刻意》篇云:“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静之至也;無所於忤,虚之至也;不與物交,惔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個人的喜怒悲樂好惡,只會破壞自己的道德天性。只有排除這些情感,與自然無所違,才能徹底斷絶與世俗的相接,才能復歸於純粹虚静的道德天性。《庚桑楚》説得更加徹底:“徹志之勃,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静,静則明,明則虚,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在這部分學者看來,幾乎個人所有的情感、意志和思維都應排除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外。只有這樣,内心才能中正清明,虚静無爲。
個人的情感、意志和思維都排除了,是不是就到了極致之境呢?這部分學者顯然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們在列子思想的影響下再進一步提出了“坐忘”、“心齋”,甚至把自我的存在也排除在外。消散形體,廢黜感覺,抛棄認知,像是精神離開了形體而融通於天地,又像是没有自我的存在,極盡於虚無。這就是“坐忘”、“心齋”的内涵(3)“坐忘”,《莊子·大宗師》:“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心齋”,《莊子·人間世》:“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通過“坐忘”、“心齋”,人似非人,與槁木無異。甚至動物也能被訓練成如此,呆若木雞(4)像這種人似非人、形若槁木的狀態,莊子學派有很多描述。《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又《莊子·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再如《莊子·達生》:“紀渻子爲王養鬥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可見,他們已把老子的無爲改造成了一種極端的無所作爲,轉向了一種絶對虚静的精神狀態。
極端的無所作爲,絶對的虚静狀態,對於世俗社會來説,它可能毫無意義。但對於精神世界而言,它卻是這部分學者養神和凝神的方式,是他們尋求人生至樂和進入純粹之美的途徑。養神是爲至樂,凝神是爲大美。《刻意》篇云:“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静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遺棄天下,排除個人的情感、意志和思維活動,虚静不動,不得已而行,順自然而爲,其目的就是使精神純粹不雜。在這部分學者的眼裏,由無爲而達到的精神純粹不雜才是人生真正的快樂,所謂神養而德全,所以他們説“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至樂》)。聖人是精神純粹不雜的典範,《刻意》篇云:“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虚無恬惔,乃合天德。”聖人的情感、意志和思維等幾乎所有行爲都是被動的,從不去思慮,去謀劃,其生死、動静皆出於自然,與天地相契合。因此他没有世俗是非禍福的侵擾,内心恬淡平静,精神純粹不勞,進入了不夢無憂的至樂境界。莊子學派把這種境界形象地稱爲“無何有之鄉”、“無何有之宫”、“塵垢之外”、“無爲之業”、“無事之業”(5)這幾個詞語意義相近,在《莊子》一書多次出現,不可輕視。據統計,“無何有之鄉”出現3次,“無何有之宫”1次,“塵垢之外”3次,“無爲之業”1次,“無事之業”1次。前面兩個詞語可以視作同義詞,核心在於“無何有”。“無何有”意謂空無所有,那麽這樣的地方就相當於虚無之境。如《知北遊》:“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宫,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調而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没有時空,更没有事物,這只能是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一直是作爲世俗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莊子也將其稱作“塵垢之外”。如《莊子·大宗師》:“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之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沖決了世俗關於生死、禮儀等一切樊籬,甚至自身肉體的存在感都没有了,這樣才能得到世俗世界所得不到的愉悦。“無爲之業”等同於“無事之業”,都是指逃離了俗事後的輕鬆狀態,如《莊子·達生》:“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莊子説:“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遊》)此處首次把無爲與逍遥聯繫起來。《天運》篇又説:“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這就進一步把兩者等同起來。這樣,無爲已不再僅是一種原則和方法,而成爲一種值得實現的價值。從這一方面看,逍遥便是無爲的價值體現,是人生至樂的代稱。此爲養神之效果。
除養神外,排除世俗功利的干擾和個人情感、意志及思維活動,可以達到的另一個效果便是凝神。《逍遥游》裏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被讚爲:“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達生》篇中,痀僂丈人爲孔子講述他的捕蟬之道:“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排除一切身内和身外的干擾後,自己的整個身體就像枯死在地裏的斷木,執竿的手臂就像枯槁的樹枝,進入到絶對虚静的狀態(6)成玄英説:“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見張繼禹《中華道藏》第十三册,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頁。,意識裏面只有蟬翼,這樣捕蟬就如同拾掇一般容易。孔子讚歎説:“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從這則寓言故事可以看出,凝神所産生的效果不僅僅停留在精神层面,還伸展到藝術创作层面,能够産生一些神秘的技藝或藝術品。《達生》篇中,梓慶削木爲鐻之前,必須要進行一個類似於“心齋”、“坐忘”的静心過程,用以排除慶賞爵禄、非譽巧拙的欲念,直至忘掉自身肢體的存在,完完全全隨順對象的自然屬性,“以天合天”(7)《莊子·達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静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以天合天,猶王國維的“無我之境”。。這样,具有純粹之美的藝術品就自然而然地被创造出來了。《莊子》書中所有的神秘技藝或藝術品,都不是以邀名贏利爲目的,而是径由無爲而至自然天成。劉笑敢先生説:“述莊派把莊子無爲概念的精神在藝術創作的領域大加發揮,在這一領域貫徹莊子無心無情的基本意旨,從而把無爲理論導入了美學領域。”(8)劉笑敢《“無爲”思想的發展——從〈老子〉到〈淮南子〉》,第96頁。顯然,這是對老子無爲思想在美學領域的一種拓展。
二、 激烈反對仁義智巧,安性順命即無爲
莊子學派還有一部分學者,主要從政治角度來闡述他們的無爲主張,是沿着老子“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六十四章)、“小國寡民”(八十章)這些觀點下來的。他們把“自然”理解成“性命之情”,這是老子無爲思想中不曾有過的元素。所有版本的《老子》都未見使用過“性”這個詞,王弼本“命”字也僅出現3次,更没有“性命”一詞。《達生》篇中,吕梁丈夫説:“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又説:“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從這兩段話來看,性是指自然形成的人性或物性,命是指無從瞭解卻又不得不如此的命運。性與命都是不可改易的,“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天運》),否則就是失性。《庚桑楚》云:“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9)郭象注:“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也。”成玄英疏:“率性而動,分内而爲,爲而無爲,非有爲也。”見《中華道藏》第十三册,第391頁。順性而動,爲亦無爲,但矯性而動,爲即有爲,有爲則僞。
因此,安於性命之情的人,也是不失性命之情的人,不做違背天性和抗拒命運的分外之事。《達生》篇説:“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秋水》篇又説:“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所表達的都是這個意思。但世間的人總不能明白這一點,常常失性憂命,不能安守性命的本來面貌。《則陽》篇云:“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情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徐無鬼》亦云:“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世人粗暴地忤逆和離散自己的天性,追逐性命之外的錢財、權勢,不能無爲,也就無法返樸歸真。
在這部分學者看來,導致世人失性憂命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個人本身,而在於統治者不合自然的有爲政治,他們所鼓吹的仁義智巧則是最直接的原因。這些學者説:“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正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馬蹄》)這裏的聖人已非他們心中理想人格的代表,而是世俗所稱道的傑出人物,如周公、孔子。這部分學者認爲,正是像周公、孔子這樣的聖人用禮樂、仁義相標榜,擾亂天下人之心,使他們失掉了性命之情。在他們看來,仁義禮樂是性命之外的東西,並不是個人天性所有。《駢拇》篇説:“彼正正者(10)俞樾曰:“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説,非是。”見《諸子平議》,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345頁。,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之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萬物皆有天性,不是人爲可以改易的。遭人爲改易之後,萬物將喪其天性。把仁義禮樂强加給個人,就像把鳧脛續長和鶴脛截短一樣,都是以人爲改易天性的做法,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他們進一步用伯樂治馬、陶者治埴、匠人治木來作喻:“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馬蹄》)馬自有天性,而伯樂無視這一點,按照人爲的方式和目的來整治,結果馬死亡大半。陶者治埴、匠人治木也是同樣的結果,都讓泥埴和樹木失去了原有的天性。同樣的道理,仁義禮樂非人之天性,以之治民則會造成民心大亂、淳樸盡失的後果。《繕性》篇説:“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在宥》篇又借老聃之口説:“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仁義禮樂即在所謂文、博之列,其惑亂人心,結果可想而知。
莊子學派的這部分學者改變了老子對於仁義禮樂温和的批評態度,顯得更加尖鋭激烈(11)傳世本《老子》十九章:“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似乎對仁義的態度並不温和,但楚簡甲本此文作:“絶智棄辯,民利百倍。絶巧棄利,盜賊亡有。絶僞棄慮,民復季子。”全然没有出現絶棄聖人和絶棄仁義的言論。傳世本“絶聖棄智”、“絶仁棄義”這種激烈尖鋭的反對態度,很有可能就是莊子學派加以修正的,非古本《老子》之有。《知北遊》篇借黄帝之口發揮老子的觀點説:“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也體現了反對仁義的鮮明態度。。除仁義禮樂外,智巧也是他們要堅決摒棄的。《胠篋》篇云:“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于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他們認爲,人類的智巧主要體現在工具器械的製造,以及人類自身的口舌之争和欺騙詐僞上,這足以使萬物(包括人類自己)喪失本性,導致天下大亂。反對智巧是貫通《胠篋》篇的一個根本主題,它把老子“不以智治國”的主張推向無以復加的地步(12)此篇還説:“故曰:‘魚不可脱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毁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鬥折衡,而民不争;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又説:“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内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明、聰、智、德原本就包含在人的天性之中,根本用不着人爲的智巧和仁義。。
這部分學者激烈反對以仁義智巧治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堅信人的天性是不需要被治理的,統治者只要無爲,讓民衆安守自己的性命之情,不破壞,不惑亂,社會自然就會不治而治。《在宥》篇説:“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在他們看來,不僅是夏商周三代以來,即使是三皇五帝時期,治理天下也徒以智巧賞罰爲事,使百姓不能安守性命之情(13)《莊子·在宥》説:“昔堯之治天下,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天運》篇又説:“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若百姓皆能安守其性命之情,那麽明、聰、仁、義、禮、樂、聖、知這八者就可有可無,否則將大亂天下。所以,最好的社會就是最原始的社會,是性命不失、淳樸不散的社會,是不需要治理的社會。
如果非要進行治理,那麽一定需要得道的人來實行,得道的人實行治理的最佳方式一定是無爲而治。無爲而治,就是要使百姓安性順命而非失性憂命,總括起來便是“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則陽》)。這部分學者非常推崇老子“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認爲這是最好的社會,並對其作了進一步推演。《胠篋》篇云:“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這裏把軒轅氏、伏犧氏、神農氏時期都看成是至德之世,顯然與《在宥》篇相衝突,説明莊子學派内部也是主張不一。這些學者把“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歷史化,並非老子本意。他們又説:“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馬蹄》)在老子“小國寡民”的社會裏,有什佰之器,有舟車,有甲兵,只是無所可用,但莊子學派的“至德之世”,不僅没有任何實用器械和軍事裝備,就連山間小路、河上橋樑也没有,純粹是一個排斥人類文明的原始社會。在這個“至德之世”裏,萬物皆安性順命,質樸無華,和諧共處,智無所用,無有强制,無有界限,無有夭折,百姓無爲而自然,即如《繕性》篇所説:“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静,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强調天性自得,抛棄治理(或者説淡化治理),這是莊子學派對老子“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小國寡民”思想朝着更理想化方向的進一步拓展。
三、 轉成帝王獨有之德,主張君無爲臣有爲
老子提出的無爲是一種普遍性的原則和方法,由形而上的道下落至聖人、天子、侯王,以至於庶人,並非帝王所獨有。至莊子學派提出逍遥即無爲、安性即無爲等主張之後,無爲又成爲一種美好的價值,擴展到宇宙萬物的身上。但莊子學派還提出了一種無爲主張,即把無爲看作是帝王獨有之德,將它轉化成帝王專有的治民用人之道,而非臣下和庶民所能擁有和運用。實際上,這仍然是沿着老子“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這一觀點而發展下來的。
《天道》篇云:“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説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對帝王來説,無爲是一種恒久存在和不能丢失的德性,原因就在於無爲能够讓帝王輕鬆自如地掌管天下。作爲無爲的對立面,有爲決不是帝王之道,而只能是臣下之道。其原因就在於有爲能够使臣下成爲具體事務的執行者,被天下所用。如果帝王無爲,臣下也無爲,那麽社會就會停止不前。同樣的道理,如果臣下有爲,帝王也有爲,那麽社會就會群龍無首。因此,君上必須無爲,臣下必須有爲。君臣異道,這是不能改變也不能顛倒的法則。《在宥》篇説:“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天道無爲,人道有爲;天道爲主,人道爲臣。此即君臣異道。君主的地位尊崇,故行無爲;臣屬的地位卑下,故行有爲。一個“用天下”,一個“爲天下用”,兩者的社會職責截然不同。從這一方面説,君上無爲是建立在臣下有爲的基礎之上,臣下有爲則是在君上無爲的前提之下,只有兩者相合有序,各司其職,整個社會才能正常運轉。
莊子學派對討論臣下如何有爲的問題没有興趣,而是極力去稱讚帝王的無爲之德,去頌揚它的好處。《天道》篇説:“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静者矣。聖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静也。水静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静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虚静、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虚,虚則實,實者倫矣。虚則静,静則動,動則得矣。静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虚静、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静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争美。”莊子學派的這部分學者將帝王的地位升格,放在了聖人的前面,所謂“明於天,通於聖”。這種做法,或許是爲了順應戰國時代的社會形勢。帝王無爲,最重要的是保持精神上的絶對虚静。只有這樣,帝王才能不被外在世界所干擾,才能對社會的一舉一動瞭然於心。帝王無爲,不操持具體事務,所以臣下就是實際工作的擔當者,責任自然就在他們身上。在他們看來,虚静、恬淡、寂漠、無爲(皆是無爲精神的代名詞)體現了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萬物的根本。明白這一點,踐行這一點,國可大治,名可大顯,居上位可成就帝王天子,處民間可成就玄聖素王,退隱歸田可爲山林之士拜服,就像握住了一把萬能鑰匙,無爲而無所不爲。這種極度理想化的描述,顯示了莊子學派對於君上無爲的急切心態。
他們相信,君上無爲的終極根據在於天道、天德。《天地》篇説:“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静而百姓定。”與前面激烈反對君主社會的那部分學者不同的是,這部分學者並不認爲君主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應該存在且一定存在的。“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地》),表明了君主存在的必要性;“君原于德而成於天”(同上),表明了君主存在的必然性。君主的存在就決定了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存在。但社會如此龐大,僅靠君主一人則無法完成統治。因此,所有實際的社會治理工作就必須需要臣下來分擔,此即“有爲而累”。在臣下擔當所有實際事務之後,君主就應該約束自己,淵静無欲,不與臣下同道,才能真正獲得“無爲而尊”的地位。就像天地贊育萬物一樣,天地不參與其具體的生長過程,萬物卻興盛不衰,折射出天地的大美。此即是莊子學派眼中的天道、天德。
君上無爲,臣下有爲,並不等於説兩者就是平行線,没有連接。實際上,兩者關係就像一棵樹,有本有末,樹根爲本,枝葉爲末,連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前面引文中“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14)郭象注曰:“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見《中華道藏》第十三册,第237頁。,所表達的正是這個道理。《天道》篇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君主執要固本,臣下處詳居末。兵甲、賞罰、禮法、樂器、喪服這些都只是國家治理方式中的末流,不應該成爲君主關注的對象。君主只要握住了本根,運用一些精神上的方法,末流亦可爲其所用。從這一點看,莊子學派的這部分學者又改變了前面那些學者極力排斥儒家、法家、名家的態度,對仁義、形名、賞罰等治理方式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認可,只是要確定好其本末次序。
《天道》篇又説:“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大平,治之至也。”由大道降至天,由天降至道德,由道德降至仁義,由仁義降至分守,由分守降至形名,由形名降至因任,由因任降至原省,由原省降至是非,由是非降至賞罰,其中每一步的次序都不能顛倒混亂。只有這樣,才能上通下達,本末俱暢。社會的每個成員,不管其智愚,都會因此而安守自己的本分,履行自己的職責,對最高的統治者來説,社會就能無爲而治了。可見,先秦後期的道家不再純粹守住自己的主張,對儒、法、名諸家不再一概排斥,而是站在自己的根基上有條件、有選擇地對其加以利用。所以,有學者將莊子學派的這部分學者稱作黄老派,並説:“黄老帛書不是典型的黄老派的典籍,因爲從内容來看,帛書雖然散發着道家的氣息,但法家的味很濃重。如果我們認爲黄老派是道家的分支而不是法家或其他家派的分支,那麽就可以説,作爲黄老派的文獻,帛書遠不如《莊子》書中的有關内容典型。”(15)劉笑敢《“無爲”思想的發展——從〈老子〉到〈淮南子〉》,第99頁。莊子學派的這部分學者雖然一定程度上認可儒、法、名諸家,但並未將它們的觀點真正轉化成自己的主張,筆者認爲這與黄老派仍有一定的距離。
結 語
莊子學派之前,老子的無爲思想即被老學早期學者所挖掘。例如,關尹、列子、楊朱等人是向内開掘,强調保持内心的澄明和精神的純一,於世俗社會采取被動的、消極的無爲;文子則是向外開掘,强調無爲對於聖王的重要,主張治理天下應“執一”、“守静”和“見小”。顯然,這些早期學者的觀點對莊子學派拓展老子的無爲思想産生了重要影響。但從本根上説,莊子學派的無爲思想並没有完全脱離《老子》所預設的軌迹。一部分學者是沿着“致虚極,守静篤”這一思路下來的,着重拓展無爲之于精神與心靈的内涵;另一部分學者是沿着“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小國寡民”這一思路下來的,着重拓展無爲之于萬物天性自然的内涵;還有一部分學者是沿着“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這一思路下來的,着重拓展無爲之於帝王獨有德性的内涵。拓展的方向,是向内、向外兼有。然而,歸根結底,莊子學派還是把老子的無爲從一種普遍性的原則、方法,完全導向了一種難以指實的精神狀態。這種拓展,雖然一方面消泯了無爲之於世俗社會的能動作用,但另一方面又發現了無爲之于藝術創造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