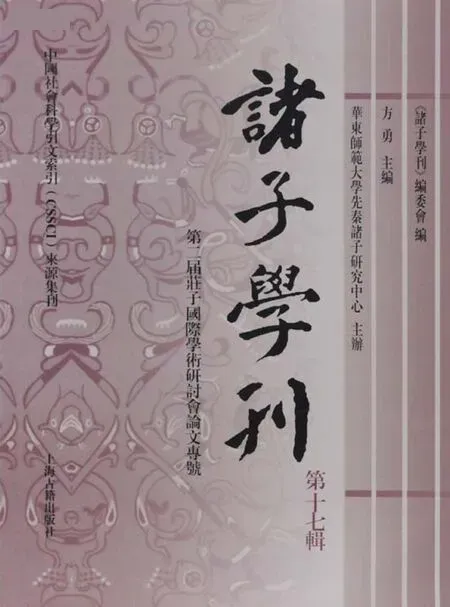道樞之應: 《莊子》經世要義初識
(澳門) 鄧國光
内容提要 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則《莊子》“三言”,精義所寄,所以存莊旨。“三言”本乎莊子之時代關懷,其中保存人性天德之義,以期後世之再復真心真性,而避免真性爲時代邪惡所異化而致斲喪殆盡,人性無存,則劫難無復祛除之幾。故《莊子》之經世在永恒而非一時,其關懷在人類整體而非一隅,此《莊子》之超越乃根本於是至深摯之時代關懷與同情。
[關鍵詞] 《莊子》 卮言 救世 復心 道樞
緒論: 聖人救世
先秦諸子之學,“關懷”乃重要之一面,如何處理時代問題即“經世”又是另一面,兩面相輔而顯示其淑世之心志。就《莊子》而言之,錢賓四先生嘗言“《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又綜言曰:
然則處衰世而具深識,必將有會於蒙叟之言,寧不然耶?此非沮、溺避世,曾滌生曾欲體《莊》用《墨》,亦《孟子》“禹、稷、顔回同道”之義耳!(1)錢穆《莊子纂箋·序目》,(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頁。
時世之衰,不避不逃,此其爲深可肯定之人文關懷;用心若孟子之撥亂反正,此爲其經世關懷,乃屬更寶貴之淑世“道術”精神。王先謙云: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群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内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説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捄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2)王先謙《莊子集解·序》,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頁。
云“意猶存乎捄世”,捄世者救世也,“經世”之謂,莊子自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張默生先生釋云:
春秋,指歷史言,非孔子所作之《春秋》;經世,猶云世紀編年也。志即古文“識”字,今俗作“志”。議而不辯者,言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也。(3)張默生《莊子新釋·齊物論》,張翰勛校補本,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118頁。此本成玄英《莊子疏》,詳郭慶藩《莊子集釋》及王先謙《莊子集解》。
按: 先秦《春秋》乃通名,專屬孔子自《孟子》始,莊子所言《春秋》,非必排除孔子《春秋》,蓋孔子《春秋》亦處其中,皆屬天子之事(4)詳參拙著《聖王之道: 先秦諸子經世的智慧》,中華書局2010年版。,故曰“先王之志”,則“《春秋》經世”,孔子王道義自然涵蓋在内,不必强别爲二。諸家注解皆刻意分别其非孔子之《春秋》,隔絶孔子,反致斷絶上下文理之自然脈絡,故不可取也。成《疏》復謂意義在“聖人議論,利益當時”者,究非通論;蓋聖人之道在萬世,使命自任,唯義所在,豈囿於當下利害之考量也哉!就文本上下文理,則可斷定莊子之關懷,心迹實情寄存之所在,非徒個人榮辱得失,斷可言也。故今探求其精世關懷之重旨,以見其“道術”之活潑與廣包之根本意義焉。
本論一: 莊語天德
《莊子》書中所體現之注意關懷者,陳鼓應先生稱之曰“人文關懷”,而當下之認知强調個體、社會、自然三向度言(5)陳立驤《論儒、道、釋“經典”中的“人文關懷”》,《哲學與文化》第412期(第35卷9期),2008年9月,第 9頁。,皆卓識通論。
進一步言,《莊子》關涉者,“衰世之代”所期盼之“全德之世”,則天人之間者,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存”(6)張默生《莊子新釋·齊物論》,第118頁。,六合之内外,“聖人”皆分别先後所存心,有所議論。“六合”者,《淮南子·時則訓》明謂“六合: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指春秋、夏冬之四時對配,乃天地之内四時運行之序。此屬天道之自然如此,不因人事而變易者,而其運行有律有度,天地萬物之衍育胥賴之以成。具體言之,天地爲兩儀,六合爲四象。《淮南子·道應訓》復言:“天地之間,六合之内,可陶冶而變化也。”六合處天地之下而成變化,其非四時之代序、三春配三秋與三夏配三冬而何?四時更替有節候規律,是爲“信”。故《吕氏春秋·貴信》言:“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虚言可以賞矣;虚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内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此《淮南子·本經訓》所謂“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而《本經訓》開宗明義謂“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此陰陽生四時之意,四時有信而“盡制”。
苟以時代先後,則《吕氏春秋》與《淮南子》較之唐人成玄英均更接近《莊子》成書時代,故六合之義,可以涵蓋成《疏》“四方上下”之静態實體義,而更接近原意者,乃天地四時之有序更替,其“合”字已足顯示動態之運行意。合者是爲會,氣會則生,氣散則亡,四時乃所以會陰陽之氣,會則盡制,神化不測,亦在六合之中,皆足成體,體足以見信,信者實也。
《莊子》之意,以爲聖人之於不必議論陰陽四時變化之外之不可測,蓋天體之變化無異乎生命體自身之衍育,不勞指説;是以其不可測者,蓋論難之談説之,究屬無謂而徒勞,但心存其意可也;與《孟子》存心養性之義,實在異曲同工。至於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表見四時定制,既有定制定體之客觀信實,則聖人用心,會歸之善美,推拓之時制之天德,落實客觀實存之“天道”,而以天道公平之本德衡量政事,故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志意雖隱微不可以形見,蓋自然而釋,非刻意作爲。而《春秋》之“經世”,聖人之本天道之公爲道德判斷,務“人道”之彰顯,而不在舌辯。若以“聖人”爲之全德之前提以解讀《莊子》,其與儒家精神之相通,瞭然可見,是以云《春秋》經世,則孔子之神髓自然處其中,根據文本義脈而可肯定。
故就《齊物論》文本義脈而言,莊子之關懷注意者,乃天人之道,而其中“天道”公平,不存軒輊,則“齊”之爲義,所以保其全;齊全無闕,整存有在,整全之爲實爲信,斯爲“天德”,故《天地》云“天地雖大,其化均也”,此真實長存不朽者。天德流行(7)方勇《莊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79頁)釋《天地》之“天德”云:“即天道之自然無爲之德。”是其 旨也。,運以四時,周行有度,制立德成。四時節候之更替,萬古而長新,乃天德之發揮之作用,不勞外作,自生自發而自成自美;聖王本天德神理治天下,皆實存於其心之純德;而此關注之主體,原非凡夫俗子,乃爲“聖人”。聖人之心所體現之天德,乃一無有差異分歧之整體生命關懷,是爲全德,乃稱“經世”。經者永存之謂,全德之意義體現於此,天德之所以流行,乃得周遍無私,此實《莊子》思想之根本大義。
本論二: 重言天殺
如此端視“天德”,實在對治時代之弊,尤其是在位者之種種違背天德之行徑,是稱“天殺”。聖人天德無有偏私,則莊子處於民不堪命之時,人間世種種情事,亦無由視而不見,或漠不關心。孫以昭先生揭示《莊子》之關懷所及之六項,皆出自在位者之偏頗不正,其“天殺”之一大者是謂屠戮天下百姓之大惡:
剛愎自用,窮兵黷武,不聽勸諫,人民大量死亡,“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焦)。”(8)孫以昭《試論莊子哲學的基本傾向及其積極因素》,《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編《莊子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頁。
此第一項實虐殺天下生命之無比大罪,《莊子》謂“其行獨”,指人君而言,則無異《孟子·梁惠王》所責“一夫紂”及《荀子·議兵》所痛斥之“獨夫紂”,以其罪大惡極,不配人君之名。
其二大者是謂窒善以縱惡:
第二、不容許别人在他面前講仁義,否則就認爲你是在炫耀自己,是在害他,他就必然要害你,“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此人主之極私,難容天下公議,故必盡傾其權力以鉗制人口,疾善揚惡,顛倒黑白。《尚書·秦誓》言:“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禍福,皆自取之。向來亡國破家相隨屬,害善而倒行逆施,天下亦盡荼毒,此罪不下屠民也。
其第三大頗行乃爲害賢,以至不擇手段:
第三、妬嫉臣下有好品德修養,愛護人民,一旦違逆了自己,就予以殺戮,“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此《人間世》所云“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桀、紂虐殺賢德,自作自受,結果乃致自招身死敗殃。
其第四類邪行是謂險詐:
第四、喜怒無常,自以爲是,不接受意見,“采色不定”,“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
“采色不定”者,陳鼓應先生亦釋曰“喜怒無常”(9)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人間世》,(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23頁。,而表裏不一,較之喜怒不形於色,更爲邪惡陰險。偏固之弊,復加上面善心狠,則朝政之壞,源自君心之險惡,臣民百姓,隨時罹殃。
其第五邪行在失信而延宕:
第五、處理外交事務,表面謹慎恭敬,實際卻拖延不辦,“待使者,蓋將甚敬”,而緩於應事。
不守承諾,禍害無窮,此戰國陰謀之常態,乃致戰禍連年。
其第六項乃嚴重之嗜殺:
第六、嗜殺成性,只知責人,不見己過,“其德天殺”,“其知適足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此典型暴君行徑,“其德天殺”,張默生先生謂“天性惡劣”(10)張默生《莊子新釋·人間世》,張翰勛校補本,第159頁。,其惡劣之地步,竟至自然行惡,莫知所爲。
按: 《人間世》借重孔子、蘧伯玉之聖賢之名,揭露當時人君暴行,直如一部《春秋》,足見其時代之淌血與痛苦,皆出於人爲,而人君失德敗行,甚至暴虐成性,乃致毒害天下蒼生。《莊子·人間世》全篇皆是重言,主爲人間之痛苦而發,而非教人避世,所以孫以昭先生認爲“其中寄寓了胸間無限的辛酸和憤慨”,並且説明莊子“絶不是甚麽‘滑頭主義’、‘混世主義’”。他更强調:“一個真正隨俗浮沉,毫無主見和是非的人能够如此尖刻地揭露、抨擊統治者麽?”(11)孫以昭《試論莊子哲學的基本傾向及其積極因素》,《莊子研究》,第151頁。是故《人間世》之末段,楚狂接輿遊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天下有道,乃聖人成化之時,堯舜是也。天下無道,民不知措手足,末世是也。而當其時之境況,則更不如天下無道,民“僅”免刑。“僅”者,陸永品與方勇先生引劉如瑛云:“僅,少。言今世很少有人能免於刑戮。”(12)方勇、陸永品合注《莊子詮解》(增訂新版),巴蜀書社2007年版,第162頁。方勇先生謂“很少”(13)方勇《莊子譯注·人間世》,第75頁。,是謂天下蒼生皆罹陷隨時死亡境地之中,無處可生如此狀況,莊子乃重言時代之悲慟者也。此莊生惻隱之關懷,同乎孟子、荀況,皆正視人間世之巨大痛苦,何曾避世哉!
本論三: 寓言成心
基於昏暴之君“其德天殺”而無惡不作,其根治之道,亦但能勸世以無有所爲。苟有所爲,則提供昏暴之君作虐之條件。蓋亂源所在,在於暴君之獸性與殘忍。面對如此對象,談説制度與道德,其結果必如上舉《人間世》所述之種種揚湯止沸之悲慘,以故方勇先生觀察到莊子之意向,乃“認爲當時所存在的政治制度、道德法度是完全多餘的”(14)方勇《莊子譯注·前言》,第15頁。。如此非謂制度與道德不足持,而是處較“天下無道”更爲荒誕殘酷之時代,非但無法發揮應有之作用,更反爲昏暴之君利用以爲殺人作惡之藉口,而自取禍害。《盜跖》以“寓言”盜跖云:
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15)方勇、陸永品合注《莊子詮解》(增訂新版),第965、966頁。
以上三類正面人物,皆“强反其性情”以求治,卒適得其反,非但難以遏制暴行,而自身已墮險境焉。聖君賢士之所以不足貴,乃因其沉處污世之中以求清致治,不能如願之餘,反而異化自我。《駢拇》又言: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16)方勇、陸永品合注《莊子詮解》(增訂新版),第278頁。
自莊子言之,暴君污吏所以難以制度與道德治理者,乃其人心之特質使之然。制度仁義非心之常,更難以對治心之變。心之常是爲天德,然此常心處變詐巧僞之時,形成心術,是爲“成心”。“成心”者,《齊物論》所强調者,謂此心之見成也。見成之心,則非本然天德之心。知識屬於成心,至於上所擧昏暴之君“其德天殺”亦屬於成心。《在宥》言:“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攖者擾亂之謂,非平定之意。以後出之制度仁義,救治成心所致之敗壞,非但未能安人心,更反而擾亂人心,則治絲而益棼。
人心之特質,説具於《列禦寇》篇,其引孔子云:
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17)方勇、陸永品合注《莊子詮解》(增訂新版),第1038頁。
此謂人心險惡,遠過山川,甚至理解人心難過知天。制度與道德,皆不能處理此至爲險惡之人心。況處壞透之時代,人心之壞已成,此成心更進一步吞噬一切之善良,轉善爲惡,就其輕者而言之,則謂之“機心”。“機心”傾向虐殺作惡之唯念,破壞力之强大,則“殺機”重重,無人可以幸免,則已非空言制度與倫理所可醇化者也。
結論: 卮言復心
《天下》篇云“以卮言爲曼衍”,“卮言”者,鍾泰先生謂自“真人”視之乃爲“妙道”之行(18)鍾泰《莊子發微·寓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方勇、陸永品合注《莊子詮解·寓言》,第907頁。,則“卮言”實在爲心事所在,以故楊柳橋先生曰:
《莊子》全書,“寓言”是它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是它的思想學説的具體内容,而“重言”乃是借以申明它的思想學説的一些往古佐證。(19)楊柳橋《莊子“三言”試論》,原載《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收入《莊子研究》,第 38頁。
莊子既不以“成心”爲可,則“卮言”所以“日出”而“漫衍”,不著任何邊際,“自己没有成見”(20)黄錦鈜《新譯莊子讀本·寓言》,(臺灣)三民書店1977年版,第321頁。,平平無奇,若生活之自然表達。言“卮言”之同時“和以天倪”,《寓言》釋“天倪”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謂成就萬物自成之天道,不存任何成心成見,“卮言”之爲“天均”者,出此言者自永恒之天德而流出,而非從後世代降之成心而來。張默生先生言:
卮是漏斗,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話。……漏斗之爲物,是空而無底的,你若向裏注水,它便立刻漏下。……幾時不注了,它也幾時不漏了,而且滴水不存。莊子卮言的取意,就是説,他説的話,都是無成見之言,正有似於漏斗。他是替大自然宣洩聲音的。(21)張默生《莊子新釋·莊子研究答問》,張翰勛校補本,第16頁。
“卮言”乃屬“替天行道”之方式,楊柳橋先生謂之爲《莊子》之“思想學説的具體内容”,則此具體之内容,其指向是爲天均、天倪,乃天道之所以爲施者也。其爲天道無私無偏之施用,非人世之“成心”所能支配,故其變化無端,是以鍾泰先生謂之“妙道”之行也。
經世者若天道之運,自然而施。是故,對治荒唐殘酷、曾“無道”之世不若之時,與其提出“堯舜之道”之人類文明至核心之道德標準,而反爲陰險奸邪之徒所利用,而“異化”爲其行惡之口實,《齊物論》所云“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22)方勇、陸永品合注《莊子詮解》(增訂新版),第87頁。,弔詭者,因正言而引出詭異之心,乃謂之異化,出乎意料之外者。人間代降衰變,不出乎弔詭之作用。如此則不若“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23)同上,第92頁。,是之謂寓言。以“卮言”爲本之寓言,無所起是非之心念,自無所爲作惡者之藉口。然如之何救治乎?《徐無鬼》云: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24)同上,第817頁。
錢賓四先生引王敔云:“視聽止於視聽,不以滑心,心自復其本定。”(25)錢穆《莊子纂箋·徐無鬼》,第207頁。此復其本心之自然,乃前乎“成心”之本然狀態也,此謂之“天德”。本天德以應物,則時代之治,亦含其中,《齊物論》概括言之曰“道樞”云“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26)方勇、陸永品合注《莊子詮解》(增訂新版),第56頁。。復心者,復活其天德真心。心之惡,治之以心,此爲相應之治,其效在久遠;若以道德之言、制度之設,其外存者而未能相應,非對症所下之方劑也。
於亂世中言天德,所以長保民性,以待無窮來日,再復其真而不失。夫孔、孟於不可教者則置之,蓋尚有可教者焉。莊生於亂世則置之,蓋亦有來世焉,其大仁大義所在也,豈筆鋒口舌争勝於一時者哉!此《莊子》非獨“衰世”而已,乃處“衰世”而求永恒真實意義之“道樞”,此道在萬世,是爲“道術”,不偏一隅,而與天道同其體,則其爲開萬世太平之書,是可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