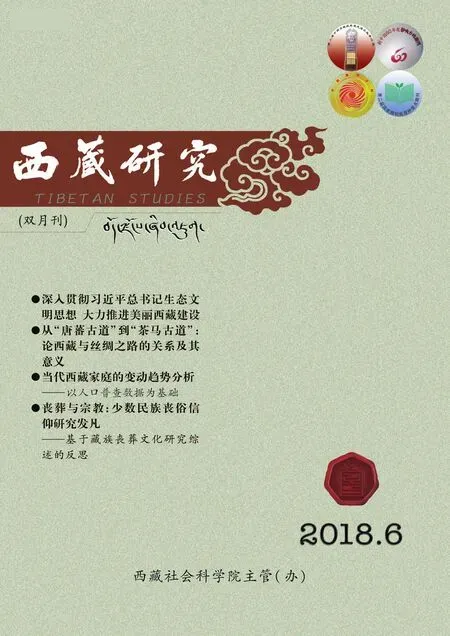丧葬与宗教:少数民族丧俗信仰研究发凡
——基于藏族丧葬文化研究综述的反思
叶远飘
(广东医科大学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湛江524000)
就目前我国各民族传承的丧葬风俗而言,藏族的丧葬风俗无疑类型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自意大利修士德里德西18世纪向西方宣告藏族存在天葬之始,西藏地区异常丰富的丧葬文化资源就备受学术界的青睐。根据人类学对文化的三分法,丧葬也包括三个层面的文化事项:一是丧葬的物质文化层面,即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物质文化面貌,甚至某些与之紧密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中以“物化”形式体现的丧葬内容,如葬所(包括坟地和墓穴)、葬具(棺、敛尸用具)、随葬器物等;其二是丧葬的制度文化层面,主要是指丧葬礼制风俗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依丧行俗”的不成文法等;其三是丧葬的精神文化层面,亦即通过上述两个层面所反映出来灵魂观念、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等当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状况[1]。故而,虽然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等学科都涉及对藏族丧葬文化的研究,但是研究的内容和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其中丧葬文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宗教学要关注的内容,也是丧葬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评述宗教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为宗教学的少数民族丧葬文化研究提供范式转换的同时拓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领域。
一、宗教学对藏族丧葬习俗的研究成果
尽管学术界对宗教的定义琳琅满目,但是要想把握宗教的本质,规定宗教的定义,核心还是在于承认以神灵观念为中心的主张,“把宗教确定为信仰和崇拜神的体系、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2]50因此,宗教学对丧葬(当然包括藏族的丧葬)的研究主要是把丧葬文化的精神层面从文化的有机体中解析出来,关注丧葬所体现出来的灵魂观念,概而言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
一是主张原始萨满教的灵魂观念支配藏族的丧葬习俗。德国最早研究西藏苯教的著名宗教学家霍夫曼曾指出,“苯”这个词具有“念念有词”之意,其特点表现为神秘性的咒语,实质是原始萨满教[3]。在萨满教看来,人有三个灵魂,即命魂、浮魂和真魂[4]。由于命魂与生命息息相关,所以藏族的丧葬大多是围绕着如何保护“命魂”举行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就指出,古藏族人有实施曝尸,待尸体腐烂以后捡骨埋葬的习俗[5]。这是因为萨满教认为人的命魂依附于毛发、石头、骨骼等坚硬的物质上,与肉体比起来不容易腐烂,灵魂在这些地方就意味着具备永生的能力[6]54。遵循这一思路,谢继胜重点研究了藏民族的两个灵魂观念:bla和bstan。他指出bla相当于“命魂”,而吐蕃时期的停柩习俗是期望灵魂bla回归尸体[7]。谢热则认为,藏民族将萨满教的命魂、浮魂和真魂分别表达为“恩摘”“南木西”与“拉”,其丧葬仪式是围绕后两个灵魂升天举行的[8]。汤惠生基于对青海化隆的卡约遗址和西藏昌都贡觉的香贝石棺墓中存在的剔尸现象的研究指出,西藏的天葬仪轨在精神内涵上是藏族人对萨满所谓“断骨后灵魂可获得重生”的表达,是人类头脑固有的二元对立和转化观念在尸体处理上的表现[9]。
二是主张苯教的灵魂观支配藏族的丧葬习俗。苯教是一个十分重视丧葬的教派,它专门设有一个葬辛兵器派,作用是“为生者除障,死者安葬,幻者驱鬼,上观天象,下降地魔”,有所谓“三百六十种送葬法”“四丧门法”,等等[10]。苯教对灵魂观的认识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灵魂外寄”——使用法术使灵魂离开人的身体,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寄存,以确保生命的安全。据此,挪威的帕·克瓦尔耐、德国华裔学者褚俊杰深入分析了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的古藏族人丧礼大量使用动物祭祀的现象,并认为这是苯教巫师使用的“灵魂迁移术”,与才让、冯智、周锡银等人关于“笨教的‘灵魂外寄’观念支配其古老的丧葬习俗”的论述一致[11]。现有的研究还表明,苯教夹杂着图腾崇拜、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12]。李家平就认为天葬体现的就是苯教的图腾崇拜观念,是来自人类不分种族从氏族时期就有的愿死者灵魂升天的共同心理的表现[13]。尕藏加考察天葬起源时认为这种葬式体现的是天神崇拜的观念[14]。相同的见解亦可参见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对历代赞普坟墓依次呈现出一个自高向低移动的解释[15]。孙林基于吐蕃王室的世系谱牒与藏族的灵魂观念的考察后指出藏族的丧仪受苯教祖先崇拜的影响很大[16]。
三是主张藏传佛教的教义支配其丧葬习俗。毫无疑问,佛教最初是不承认“灵魂”的,但佛教讲轮回又间接承认了死后世界的存在,在向西藏传播的过程中,它吸收了苯教的一些观念,显著的体现就是为自己的“轮回”注入了一个实体——“灵魂”。以王尧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藏族天葬的起源时主张“佛教教义”说,认为天葬不是藏区土生土长的丧葬类型,而是12世纪,僧人帕当巴桑杰从印度带入的[17],其核心内容是“布施”,是一种舍己利他的思想,这种葬式明显受到了佛教教义中“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佛经故事的影响[18]。有学者甚至指出西藏的天葬“只有从佛教的‘中观’论来理解最为透彻。”[19]不过,霍巍在列出西藏上古与中亚存在的许多考古学上的联系证据以后,反对天葬受佛教教义影响的说法,从而把这种葬式的源头指向了中亚的拜火教[20]。但总体而言,目前藏民族举行的各种丧葬仪式是为了让灵魂在佛教的“六道”中获得转世则是学术界的共识[21]74。当然,这种局面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些学者在支持此观点的同时注意到西藏的丧葬先后经历过图腾崇拜、苯教教义和佛教教义的影响[22],是苯教与佛教长期互动过程中,苯教仪轨向佛教转变的生动注解[23]。
以上研究成果固然有利于学术界认识藏族丧葬的精神体系,但是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成果中对藏族丧葬文化的精神体系的关注大多立足于具体的葬式,却缺乏对“丧”的关注。众所周知,丧葬应该包括两部分:即围绕着死去的人举行的各种仪式——“丧”以及对死者进行最后的掩埋——“葬”。而且从文献的记载来看,藏族自古以来的丧葬活动中“丧”的周期很长,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葬”。《隋书·附国传》言:“死家杀牛……死后一年而大葬……立其祖父神而事之。”[24]在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写卷P.T.1024“第20节乙(第81—86行)讲述‘mada’(大葬)这个动作所发生的时间——要在死后第三年进行。”[25]《汉藏史集》中亦有“止贡赞普之尸在铜棺中封闭了十三年”[26]的记录皆是有力证据。二是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将丧葬文化的精神层面作为丧葬文化物质与制度层面研究的一个“引子”出现,尚未将之独立出来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造成这样的局面可能与学科专业的分类目录有关——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分类目录中,宗教学学科下属的研究方向分别为“宗教学原理、无神论、原始宗教、古代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代宗教、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少数民族宗教”,倘若将前述三类研究成果和目前宗教学学科的研究分类对照起来,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三类研究成果分别是在原始宗教(萨满教)、少数民族宗教(苯教)和佛教(藏传佛教)的框架下进行的。换言之,这些研究有一个前提预设:认为藏族的丧葬文化受某种宗教教义的支配,于是形成了从宗教教义寻找所谓“证据”为丧葬文化做注脚的思维,无意识导致了藏族的丧葬文化成为了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拜火教等宗教的附属品。
然而,丧葬作为一个民族千年传承的风俗,并不总是被动地被宗教教义支配,而是在与各种宗教互动过程中对宗教的相关因子进行扬弃、吸纳和改造——“这些不同要素的结合体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新奇而又新鲜,其发展类似于大树的成长一样,从原来的宗教那里继承了一些显著特点,很快地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27]这时候再说某种丧葬文化受到什么宗教教义的支配肯定不合适了,欲弥补前述研究成果的两大缺陷,笔者在此提出“丧俗信仰”的概念。
二、“丧俗信仰”概念的必要性
“丧俗信仰”是指以血缘为主体、地缘和业缘为补充的群体基于灵魂信仰,在丧事期间,依托灵堂和墓地发展出的一套针对死者的灵魂崇拜行为,并通过民俗方式使其规范化的社会文化体系。我们之所以在研究少数民族丧葬的精神体系时摒弃所谓的宗教教义说而采用“丧俗信仰”的概念进行指导不仅是纠正前述研究成果中对“葬”的重视大于“丧”的需要,而且还因为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所举行的丧葬仪式并非仅仅只受一种宗教教义的影响,而是同时受到多重宗教(信仰)的影响。就西藏的丧葬风俗而言,它至少先后经历过苯教教义和佛教教义的洗礼,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它是苯教与佛教互动过程中佛“含括”苯的体现[28]。从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当两种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时会出现文化的“涵化”,它导致的结果不是两种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产生第三种文化。因此,笼统地说西藏的丧葬既受到苯教的影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表面上似乎也是事实,但远远没有说明本质。所以,在逻辑上我们不能把藏族某种丧葬习俗隐含的信仰视为某种宗教的附属品,而是给予它与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等宗教同等的地位,视其为一种特殊的从宗教独立出来的精神体系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丧俗信仰是否具备这一特点?不妨看看我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的一段论述。吕先生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曾经对我国的宗教学学科建设有巨大影响,他认为“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依次在逻辑的发展上呈现出递进关系,并说这是货真价实的宗教的充要条件[2]65。为此,他以考古发现距今1万8千年以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尸体丧葬为例做了说明: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尸体丧葬,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最原始的宗教迹象……在这最早的宗教“幼芽”中,也已出现了宗教四要素的“种子”。如果山顶洞人没有某种死后的观念,他们就不会把死人进行丧葬处理,并随葬装饰用品和生活用物……既然山顶洞人有了某种“死后生活”的遐想,就必然会伴生对“死灵”的“敬”“畏”感,没有这种感情和感受,就不会出现使用殉葬物的行动,此即是宗教的感情和宗教的行为。死者不会自己埋葬自己。在当时,葬他者只能是与他具有血缘关系的血缘集团中人,可以设想,埋葬时是同一血缘集团成员集体进行的。这是一种社会性、集体性的宗教行为,是以原始社会中的氏族血缘关系作为背景的。[2]65—66
上述论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原始丧葬是宗教的最早萌芽,但尚未发育成型为完整的宗教[2]65。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丧葬文化在代代传承中不断与各种宗教教义进行互动,其精神层面的灵魂观念也得到充实和升华,所含的丰富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原始时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少数民族的丧俗信仰而言,把它理解为一种宗教既是照顾现实研究的需要,也是遵从学科分类的传统。首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之所以特别把少数民族的丧俗信仰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它与汉族的丧俗信仰相比有本质区别——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汉族社会也存在丰富多彩的灵魂观念,但是自从西周宗法制确立,特别是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历代王朝推崇儒学治国的背景下,汉族民间的丧葬仪式已经不可避免向儒家紧密靠拢,甚至被儒家支配,逐渐走向了世俗的理性形态:虽然它还带有一定的鬼神观念,但儒家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对其有根本性的支配,导致其丧葬不以追求出世的灵魂归宿为主要目标,而是追求入世的政治伦理教化。但少数民族社会历来受宗教的影响比较大,甚至可以说,宗教是其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的核心手段[29]。这种情况导致其丧葬仍然以追求灵性为目标。其次,从学科分类的传统出发,学术界习惯把那些流行于民间而且得不到官方宗教认可的信仰形态称为民间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汉族的丧俗信仰可以称得上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形态,但“民间信仰”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去少数民族化的。对于少数民族社会而言,更真实的情景是,“民族传统信仰……就是其制度宗教……其民俗信仰和宗教信仰往往是相融合而共生的,难以言说何为宗教信仰,何为民俗信仰或民间信仰,民族宗教与其民间信仰有着根本的内在连续性,并表现为在民族生活中二者相融共存的实际状态。”[30]故而,现有的宗教学分类中已经把少数民族的宗教和信仰统称为“少数民族宗教”,这种分类实际上为我们把藏族的丧俗信仰视为宗教进行研究提供了启发。
三、“丧俗信仰”概念的重要性
那么,丧俗信仰这一概念可以为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具体带来哪些创新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前述学术界对藏族丧葬研究所取得的两个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首先,前述研究成果按宗教的分类把藏族的丧葬文化置于原始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和拜火教等教义的框架下讨论,从理论而言,是一种类型学的研究。对于类型而言,学术界目前普遍承认藏族的丧葬仪式主要受藏传佛教的“灵魂转世观”支配[21]74。但是,这一共识回避了藏传佛教与“地方性知识”整合后导致藏民族对灵魂认知形成的差异,因此,这一共识未必就一定符合藏区的实际情况。换句话说,即便同样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倘若他们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生活,两地的族源构成不同、所处的社会结构不一样,那么他们的灵魂观、宇宙观是否完全相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信徒既是宗教的信徒,又是当地社会文化的载体。任何宗教沉淀到民众社会生活层面的实践必然借助特殊的中介与原生型文化发生混融,形成不同的宗教文化复合体。”[31]这种宗教文化复合体还会被“地方性知识”[32]重新解释,我们可以举一些比较显著的例子做出说明,譬如佛教的核心思想是“业报轮回”,当佛教在传入西藏的过程中吸取了苯教的“灵魂外寄”思想以后,为“业报”找到了一个载体。佛教倡导的十善业包括: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恶口,五、不两舌,六、不妄语,七、不绮语,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此说来,凡偷盗、抢劫、打架、斗殴等行为都属于“恶业”,灵魂注定要下地狱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笔者的田野调查却发现,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族并不总是如此认识——在金沙江三岩地区的藏族,族源成分构成复杂,但主要成分是自上古以来沿横断山脉南下的古羌人,他们至今仍继承着古羌人“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荣,病终为不祥”[33]的尚武精神。换言之,他们即便信仰藏传佛教,但并不认为抢劫、斗殴是恶业,特别是为了本氏族的利益敢于和外氏族械斗致死的,被认为灵魂是不会下地狱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一点甚至当地的一些藏传佛教僧人也是认可的[6]151。因此,相比于某某宗教在其经典上记载的某种教义,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被当地人称为“传统”的东西。也就是说,当地居民真正关心的是他所举行丧葬仪式是不是符合所在社区代代传承的传统?然而,“传统”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是一个不断解构过去,被后代不断重构的过程。藏传佛教与地方传统整合后导致各区域(族群)丧葬形成差异,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恰好可以在丧俗信仰这个概念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运用这一概念在原有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类型细化,总结出若干区域(族群)的文化小模式,得出更具体的、更细微的接近于事实的认知,深化学术界对藏族丧葬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其次,类型学的研究固然可以将表面看起来紊乱的现象条理化,但是它只能告诉人们“是什么”,并不能帮助人们了解“为什么”,丧俗信仰的概念打破了我们所认知的宗教的边界,在对原有类型进一步细化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类型的界限,意味着可以把静态的类型学研究模式变为动态的研究模式——考察灵魂信仰的流动,关照那些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我们“在对待社会现象的时候,就如同印象派画家将空气和阳光看作是流动的一样,将社会现象看作是流动的、鲜活的、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的。”[34]我们的目标就是透过这些流动去捕捉种种隐秘,具体到丧俗信仰而言,就是寻求灵魂信仰流动的机制,建立起若干中层理论。诚如前述研究成果,藏族的丧葬经历过原始萨满教到苯教再到佛教的洗礼,其灵魂信仰的变迁相应是“灵魂不灭”——“灵魂外寄”(苯教的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山神崇拜、天神崇拜)——“灵魂转世”(藏传佛教)。那么,在丧俗信仰概念的指导下,以下两个方向的研究将会取得突破:一是关注宗教文化层在藏区的叠压,探讨“灵魂不灭”——“灵魂外寄”——“灵魂转世”演变的动力和原因;二是理解文化层的打破与共存,寻求灵魂信仰是如何与萨满教、苯教与藏传佛教等教义互动并整合的。对于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神圣”这个词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宗教起源于神圣与世俗最原初的分离,人类发展的历史无非是一方面随着物质能力的提升,其心灵从自然界中异化出来;另一方面,人类对精神的永恒追求又使异化出来的心灵采用宗教实现与神圣超越者的关联。与受儒学浸淫使其民俗或信仰缺乏神圣性的汉族社会相比,在少数民族地区,信仰、宗教与民俗往往呈现出三位一体格局,神圣性是贯穿少数民族信仰、宗教和民俗生活的主线。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和宗教并无本质的区别,宗教的源头和内核就是信仰,而不同信仰层次上的民俗,与其源头有亲疏远近的关系,若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分析,则存在一个由核心的原始意象逐步向外层泛化的形态[30]。又因为丧葬是宗教的最早萌芽,丧葬民俗自然处于这个信仰层次的核心,人们在丧事期间的民俗生活就是他们的宗教生活。换言之,当一个人死亡的那一天起,这个社区的人的生活自然转入了神圣的空间,丧葬毫无疑问成为神圣与世俗时空的边界,丧葬仪式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从世俗生活进入神圣生活以使那些早已从自然界异化出来的心灵超越世俗回归神圣所依赖的重要手段,而丧俗信仰的核心便是灵魂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丧葬观念中的灵魂信仰之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有的宗教在不断世俗化的过程中,其教义不能再满足人类从自然界异化出来心灵去实现与神圣超越者的和谐,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宗教,这种迫切必然导致人们寄希望于丧葬,因为从理论上说,丧葬具有发展成为一种全新宗教的潜力。少数民族丧俗信仰之所以是一种宗教,恰恰就是因为它与汉族相比,体现出了无可替代的“神圣性”,这也是该概念能够指导我们对少数民族丧葬进行动态研究,捕抓灵魂信仰流动与整合机制的原因。
四、方法论的支撑
对丧俗信仰的研究方法不是单一的,就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各学科的边界在不断被打破,那种把某某方法视为某学科独有而拒绝其他学科使用的做法已经不再适合学科的发展。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选择合适的方法,只要有利于解释研究主题的任何学科的方法都可以借用,对于丧俗信仰的研究也是如此。不过,“丧俗信仰”这一概念是我们基于宗教学对丧葬的客位研究之不足而提出的,因此,运用该概念进行指导研究时,我们应该坚持一些能体现该概念价值的基本的方法论。
首先就是主位视角,主位(emic)与客位(etic)本来是语音学的一对概念,后来人类学家将此概念引入对文化的研究,发展出两种研究方法:后者是以旁观者的角度,通过与对象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即所谓的客位研究;前者则是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即所谓的主位研究。总的来说,主位研究强调被研究对象的想法,而确保主位视角的手段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应该长期生活在一起,通过参与观察的方式收集资料。从调查的完整性来说,至少是一年以上,历经四季轮回感受。以藏区的丧葬为例,站在客位的角度,我们很容易发现,藏民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藏区各地藏民族举行的丧葬仪式中也主要交给藏传佛教的僧侣主持,但倘若以此认为他们的丧葬受藏传佛教教义支配至少并不完全是客观的。事实上,藏民族对所谓的某某宗教的某某教义是不甚了解的,而我们平常说的某些宗教的经典记载着某条教义,这些分类其实也不存在于当地居民的头脑当中。作为基层民众,大家实际上是分不清哪些观念属于苯教,哪些观念属于佛教的,而且事实上也不需要分清。因此,当我们说某种宗教教义支配某地的丧葬习俗时,本身就是以牺牲主人公自身的感受为代价的,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35]色彩,而“丧俗信仰”这一概念恰恰是对上述表达的纠正。“丧俗信仰”的存在说明了人们在举行丧事活动中应遵守的一套信仰、禁忌和规约,这无疑是基于主人公的主位表达。
顺着这条思路,要想使自己的理解更接近于神圣事物原有的本质,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基于现代科技和理性的发展,片面地对宗教进行化约式的理解,因为宗教本身最基本的也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而不是其他的最独特的要素是它的不可化约性——即神圣性,如伊利亚德所言:“‘宗教现象’唯一可被认识的方式就是从其本身的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把它当作宗教性的事物来研究。”[36]胡塞尔为此提出了现象学的方法,主张研究者在对宗教研究时应该“悬置(epoche)”一切价值判断,避免研究受“先验主观认识”的影响,最大程度让宗教的“神圣”本质如其自身所是呈现出来,倡导“把宗教经验引进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之中,并且以同情的态度来体验这些经验。”[37]如果一个人对宗教丝毫没有感受或者毫不认可的情况下去研究宗教,得出的结论或许可以说是现代理性逻辑下的客观,但未必就是事实。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学者倡导“灵性的认知科学”[38]、“学术神学”[39]以及“用‘文化亲证’的概念取代‘文化实证’”[40]的方法皆值得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丧俗信仰时借鉴。但是,我们也承认,宗教神圣性现象本身应该还存在一个“民族志的客体”,这提醒我们在研究丧俗信仰时,既要走进去,也要走出来,借助“深描”的方式对主位的解释进行再解释,从而实现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统一。
五、结语
少数民族丧俗信仰集民俗、信仰和宗教为一体,神圣性是其根本属性和生命力,如果无视这一点,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实现对其本质的理解,所以宗教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彻底抛弃那种视丧葬为宗教附属物的下意识,将丧葬的精神层面单独抽离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对待。在丧俗信仰概念的指导下,坚持运用田野调查的手段收集第一手材料,将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相结合,静态方面对类型的东西再进一步细化,总结出关于少数民族丧俗信仰的若干区域(族群)的文化小模式;动态方面则不断突破原有类型的界限,考察丧俗信仰的流动并探寻其机制,建立起若干中层理论,形成完备的丧俗信仰理论体系。这种做法不仅符合少数民族丧葬的现实,而且可以为学术界研究丧葬文化提供范式转换,同时拓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领域。当然,其现实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丧俗信仰也是一种“生命文化遗产”(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神圣),将其独立出来专门研究实际上也是迎合时代提出的“抢救、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迫切要求;其次,对丧俗信仰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探究“他者”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维方式,有益于为现代社会的生命教育提供参照;最后,深入理解丧俗信仰的社会功能,可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殡葬改革与社会稳定决策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