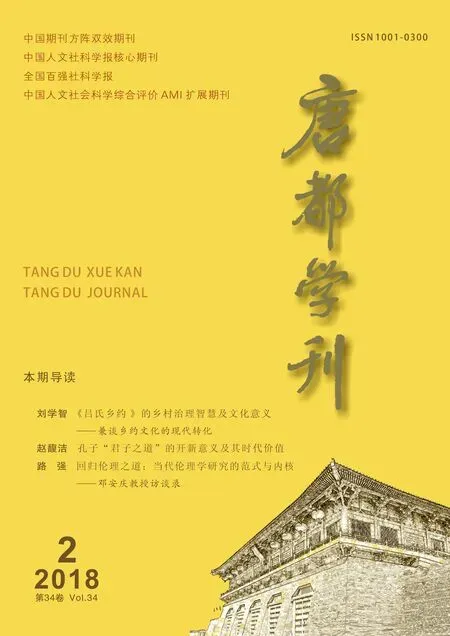简论杨毓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
岳 恒, 郝延军
(1.空军工程大学 军政基础系,西安 710051; 2.西安文理学院 评估与质量监控办公室,西安 710065)
郝延军,男,陕西延安人,西安文理学院评估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副教授,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在长沙岳麓、校经等书院读书,聪颖好学,思想活跃。“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1]面对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悲惨局面,他时刻都在思索,如何能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02年,他毅然负笈东去,前往日本留学,以探求救国之道。抵达东京不久,杨毓麟即撰写出《新湖南》等鼓吹革命的著作,其思想的光辉,激励了许多有志青年投身反清革命洪流。《新湖南》一书的出版发行是杨毓麟民主革命政治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杨毓麟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学术、交通等多个方面,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综述其主要政治思想。
一、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
清朝末年,封建统治尤为残酷,百姓民不聊生。以湖南为例,“中兴以后数十年来吾湖南人无日不在黑暗地狱中也,中兴诸公……徒足驱迫我湖南人,弱者为沟途之饿殍,强者为绿林之豪客而已”“郭门十里多为盗薮,如南门外之金盆林,如省河对岸之望城坡,白日行劫,入夜则篝火狐鸣相啸聚。由湘入粤,行宝庆一路,由湘入黔,行辰州一路,由湘至江岸,行澧州一路,行客不戒,则贸其首。附郭之县,若长沙、善化,闾里之间,日日闻愁痛声,岁穷腊近,烟火寂寥,春贴几至数百户无一新者”[2]39。严酷的现实与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驱使着杨毓麟积极倡导社会变革,以解决社会危机。在由日本返回国内后,杨毓麟积极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从事反清活动。他与友人一起“谋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震动天下人耳目。潜居京城数月,以无隙可乘,失意南归”[3]。这是他积极策划推翻清廷的最初尝试。
在近代中国,除内忧之外,外患也是威胁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自海禁既开,欧风紧急,亚云惨淡权利之断送,外人之骄横,史不绝书。”[2]34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无不在此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无一不是围绕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而展开。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指出:“强之谋我中国也,不遗余力矣。”而考察欧美各国所以强盛并积极对外扩张的原因,他认为其远因是“民族建国主义”,近因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
在杨毓麟看来,帝国主义的原动力之一是“国民生殖繁盛之力之所膨胀”,一是“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2]41。这种认识虽不很准确,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显然抓住了要害。他还进一步分析帝国主义的方针是“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万全之地”,“但使有所谓通商主义,而无殖民主义,其后一变而为殖民主义也”,“使所谓租界者,虽有治外法权之损失,尚无所谓土地所有权及先得权也,政略既变,则虽有租界之名,而实则土地所有权及先得权,俱已包含于其中矣”。长此以往,则“以工商势力圈限为其实,招牌未改,而数百年之老店已盘顶于他人,堂构依然,而数十世家之居,已重典于异姓矣”[2]43-44。
杨毓麟进一步揭示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间的依存关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卖国政府。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虎伥关系。在列强与清政府的勾结、镇压之下,“哀我生民,独奈何不痴不聋堕入罟护陷阱之中,无术以自脱也”[2]45,“六十四州县,该渲颜色之图,已于黄昏黑暗时,高挂于白人之壁矣”[2]56。倘若“能执一理论以图匡救之法,则彼民族者,尚未及牢钉而熟熨也,不然,则亦谓他人父而已矣,谓他人母而已”。他指出要想有效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首先推翻昏聩腐朽的清政府,“今日不暴动,不能禁他人之不破坏我也。与其他日见破坏于外人,何如发之自我,尚可以收拾之哉?”“改造旧社会者,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则必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暴动者乃开辟新局面之艾牟乾也”,暴力斗争的对象“即其坐堂皇而巍然具冠带者”及“日日坐大轿,掌纱灯,以出入于游戏征逐之地,称老师,拜大人以雄长于厮养仆御之间者”,“未来之湖南尤树也,溉之以顽官、劣绅、瘁士之血,而后生长焉”[2]56-59。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独立,必须推翻清政府。
不难看出,杨毓麟对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手段及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对清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利用,共同压榨中国劳苦大众的实际情况更是揭露得十分形象、透彻。他明确提出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这标志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的新觉醒。
二、以捍卫人权为核心的民族建国主义
杨毓麟十分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尤其是民族建国主义与个人权利主义。所谓民族建国主义,简言之,就是通过排满,恢复汉人对中国的主权,建立汉人主导下的民主宪政国家,进而团结全国各民族力量共同排外,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使中华民族巍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由于当时的激进派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出现了很多与该主题相关的言论。如吴樾以民族建国主义为唯一原理,认为扶满不足以救亡,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清政府行奴视汉人政策,立宪决不利于汉人[5]300。杨毓麟则进一步指出:“凡种族不同,习惯不同,宗教不同之民皆必有特别之性质。有特别之性质,则必有特别之思想,以特别之性质与特别之思想各适其自营之手段,则一种人的特别之权利者,必对他一种人生不平之妨害”,因此“异类之民集于一政府之下者实人类危辀仄轨也”。只有实行民族建国才能使“异者相离,同者相即”[2]50。针对当时的西方列强,杨毓麟认为“地球诸国,所为凌厉无前者,帝国主义也。而此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根底”。要想“扼此帝国主义之潮流”,只有针锋相对地使用民族主义以增强国家内部凝聚力及“与异种相冲突相抵抗之力”。他指出,只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力破万难,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桃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2]51经过以杨毓麟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宣扬,以民族建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风行一时,迅即扩散于晚清的知识阶层之间,更有力地唤醒了一般知识青年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6]。
同时,民族建国主义也需要个人权利主义相辅翼,所谓个人权利,即“天赋个人之自由权”,是“生人之公理也,天下之正义也”[7]633。杨毓麟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天赋人权说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发挥,他说:“此自由权,人与我皆平等,故不捐弃己之自由权,亦不侵害人之自由权”[2]51-52。杨毓麟指出,国家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于“国家以民约集合而成”,因此,“人生而欲保护其自由权,及增进其自由权,故不能无群,群之始成于所谓民约者,此国家所由成立之原理也”[7]632-633。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社会之初本没有什么国家和官长,人人都是一样的,后来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便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成立了国家,国家应该是“以集约诸人之希望为目的”,即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思想相对立。强调民权,强调个人权利,“人人为服从于国家之一人,亦为享有自由权之一人”,“放弃其自由权者,失人格者也”。既然国家是人民自由协议的结果,一旦契约被统治者撕毁,人民就不再受统治者摆布,有权夺回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既然国家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是公众意志的反映,那么国家就必须为民众服务,保证公民的权利,谋求公民的幸福[8]260。“惟国家以民约集合而成,故以集约诸人之希望为目的,而不得以一二人之希望为目的,以集约诸人之幸福为趋向,而不以一二人之幸福为趋向。”[7]633与杨毓麟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们虽也都积极向欧美“取经”,但他们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国家”“集体”上,而对个人的自由权利则较少关注。杨毓麟在强调“国家”的同时将个人的自由权利放到与国家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杨毓麟指出:“主权者,国民之所独掌也。政府者,承国民之意欲而奉行之委员也,国民者,股东也,政府者,股东之司事也。”[2]52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被大大提高,杨毓麟指出,“国家之土地,乃人民所根著之基址也,国家之政务,乃人民所共同之期向也,非政府之私职也,国家之区域,乃此民族与彼民族相别白之标识也,非政府之所得随意收缩割弃也;国家之政治机关,乃吾国民建设大社会之完全秩序,非政府所得薮逋逃而凭狐鼠也。于是以全国之观念为观念;以全国之感情为感情;以全国之思意为思意;以全国之运动为运动;人人知其身为国家之一份子,为公同社会一质点。”[2]52由是将传统的“政府的人民”一变而为“人民的政府”,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中,杨毓麟特别欣赏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他早期曾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参与维新变法,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理想是以英、日为代表的“君主立宪”,但维新的失败使他的立宪梦破碎。1903年杨毓麟追随黄兴等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将眼光转向了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国家,使他看到了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共和制度的优越性。杨毓麟批评“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知政府与国家之区别也”[2]53,他说:“西方之学说曰:国家有三权,三权不分立者,其秩序必不安宁,幸福必不增进,是故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不得不分部别居,使各在于独立之地。虽然,三权者,由国家之主权而生;主权者,以国民全体为体。而以三权分立为用。是故主张此三权者,国民全体之意识也,立法权者,由国民全体付之少数之部分,以达全体之意识者也。行法权(行政权)者,国民少数之一部分,受全体之委任而奉行主权之职务者也。司法权者,所以监督执法者与人民之奉法者也”,彻底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外,杨毓麟还指出,“宪法者,以国民之公意立之,亦以国民之公意废之;以国民之公意护持之,亦以国民之公意革除之。是故宪法者,国民公意之眉目,而政府与国民所同受之约束也。政府者在于国家为一部分,国家者,不独非一姓之政府所得私也”[7]635,国家与政府分立开来,由此则“有政府亡而国家不亡者,有国家亡而政府不亡者,明国家之存亡,系于全体主权之存亡,不系于政府之兴废”[2]53-54。
杨毓麟就此进而指出,要想建立这种“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将人民组织起来,这就需要建立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各种政治组织,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政党,他说:“今世立国于地球之上,不能无以党会为基础也。是故有国会,有地方议会,有私人所倡立之政党会。国会及地方议会者,立法之机关也,自治之零件也。私人所倡立之政党会者,于国会地方议会外,以特别之性质结特别之团体,主张一党派特别之议论,而欲施行一党派特别之方针者也。此特别会党者唯其各以公益为主,则其所执之方针目的不必尽同,而其维持公益则大同”[2]65,这就明确提出了“以公益为主”的政党学说,号召建立有自己的施政方针与目的的各种政党,通过议会竞选,争取多数来取得执政地位,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也是近代英、德、美、日诸国能成为世界强国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
三、推崇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
杨毓麟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先后留学于日本和英国,这对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崇无政府主义思想、极力推动国内暗杀活动的展开、寄望于“中等社会”起来革命是其表现形式。
(一)暗杀活动的策划者与“急先锋”
从20世纪初的远东局势来看,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不少影响,包括暗杀方法的传入。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于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者不少,留寓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不仅从他们那里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学到了制造炸弹的技术。
与时代背景相关,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暗杀风潮盛行。国内外暗杀团体的广泛组建,重大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如吴樾刺杀清廷赴欧考察五大臣等。革命党人暗杀活动的盛行与清末社会转型加剧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这些富于行动力的年轻革命者深受中国古代刺客、游侠精神的影响,以及当时舆论界对暗杀活动的大力宣传。当时创办的《苏报》《江苏》《浙江潮》等革命刊物,都先后发表了许多鼓吹暗杀的文章,大谈暗杀的好处,号召革命志士效仿中国古代和外国的刺客,进行“刺客的教育”,参与到实际的暗杀活动中[9]39。组织、策划、参与暗杀活动的年轻革命党人大都受到西方虚无主义(包括俄国的民粹主义和欧美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相信英雄的作用,以为杀死几个人便能解决问题,不需依靠群众。暗杀活动虽非疆场决胜,然以目标单纯,易于保密,费用无多,成功的机会较大。可以说,暗杀可用于阻吓,用于宣传,当起事一时未能发动时,作革命的火花,实与起事有相长相成之效[5]300。
说到清末革命党人发动的暗杀活动,便不能不提到杨毓麟,因为他是清末革命党组织暗杀团、密谋暗杀活动的重要人物。其在日留学期间写成的《新湖南》一书,字里行间都在强调暗杀是救亡图存的首要途径。其格外推崇俄国无政府党的暗杀活动。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近千年暗杀活动的统计研究,他得出结论:“暗杀事件出俄国为最多。除共和国若法、若美得数事以外,其他乃皆人民与专制政体君相之战争”[2]339。杨毓麟认为中国同俄国一样均为君主专制政体,所以暗杀活动是适于在中国进行的。
1903年,杨毓麟“力主暗杀,于横滨学制炸药,研究爆发物十余种,因拂案触药屑失慎,一眼失明。革命党人能自造炸药,当自杨守仁始”[5]308。在这之后,1904年夏,杨毓麟又与周来苏、苏鹏等人携带炸药北上,会同自湖南来的张继与何海樵,在天津各主要街道布置机关,意图炸毁内城宫殿和颐和园,但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到了第二年,杨毓麟又与吴樾策划,于是便发生了谋炸五大臣的事情。
杨毓麟狂热地讴歌、赞颂当时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精神,主张对清廷达官贵人采取极端的个人恐怖手段,鼓励年轻的革命志士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到暗杀活动中,以此推动反清革命。他由此大声疾呼:“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2]58这两句名言,无疑成为了清末革命党人从事政治暗杀活动的座右铭。而杨毓麟直到蹈海自尽前夕,还曾想买一把手枪,乘便船回国,寻找一两个独夫民贼同归于尽[2]389。由此不难看出他对暗杀活动始终如一的追求。
历史发展进程证明,最终推翻清政权的手段还是依靠军队发动的武装起义,这一革命策略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单纯依靠暗杀的激情,革命是不能够取得胜利的。武昌起义之前,两湖地区革命志士就已经得出“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的结论[9]223。
(二)“中等社会革命”论的倡导者
何谓中等社会?主要是指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认为,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上等社会”,对内镇压对外卖国,腐败不堪,已成为革命的对象;而由广大劳动者、士兵和会党组成的“下等社会”虽然幼稚无知,但身受压迫,有革命精神,因此是“革命事业的中坚”;“中等社会”则有一定的资产、文化知识和活动能力,是“革命事业的前列”,即革命的领导力量。也就是说,革命者应在“中等社会”中广泛地组织革命团体,建立革命的领导机关,提出统一的革命纲领,确定革命方针,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
杨毓麟在他的很多著述中都有提及或涉及“中等社会”,综观他的论述,都能看出他主张“中等社会”挺身而出,承担起推翻清政府、建设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其所谓的“中等社会”,实际上指的是当时一部分掌握了新知识、新思想的“新”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人士大多有着留洋背景,回国后在清廷担任要职、在民间兴办各类实业,还包括正在欧美、日本等国留学的莘莘学子。他们有别于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埋首于故纸堆中钻研八股文章的陈腐文人,而是一群思想活跃、有行动力的年轻人。杨毓麟认为他们是革命成功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也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群体。早在他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之时,就在《游学译编》等刊物上积极呼吁;后来前往英国,在阿伯丁大学就读期间也不断在欧美国家学生界阐述自己的观点。
杨毓麟在《新湖南》里对湖南的“中等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挚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同时,他又暗示这“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军”,可知其多半是针对学生社群而言[10]。
杨毓麟对知识界特别是对留学生这个群体寄予了很高希望,从其留学日本的第一天起,他就向留学界发出了“当以救国为第一义,个人之功名为第二义”的强劲呐喊,希望留学界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国之不保则个人之富贵将焉取之”的道理,希望留学生能够一心一意致力于“毋致中国之亡”的伟大事业。
(三)推崇“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理想
无政府主义是近代西方影响力较大的政治流派之一,他们认为权力和权威是屠杀人类智慧的工具,国家是万恶之源,因此否定一切国家权力,鼓吹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建立无政府社会[8]273。其之所以能被杨毓麟所接受,从他所留下来的著作来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团体组织不论是在物质方面或在道德方面,皆丝毫不复有强迫的权利存在于其间”[2]177。杨毓麟认为:“唯真理绝对,故自由与真理绝对不可离析。是故自由亦绝对,不绝对则非自由。人生最终之目的,当以真理为归宿;不能以真理为归宿,则吾人知识,感情,意志三项发达不圆满。吾人既应以真理为归宿,即不可不以绝对自由为归宿,不以绝对自由为归宿,则吾人所以发达知识,感情,意志三项,以蕲达于绝对自由者,不复丝毫可以受他力;丝毫受他力,则自由已非绝对。”[2]181-183而无政府主义者所奉行的“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思想与之不谋而合。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无政府革命呢?暗杀无疑是一个当时吸引着大批革命者进行实践活动的方式。
杨毓麟在留学日本期间撰写了大量介绍无政府主义、歌颂俄国民意党的文章。如其在《湖南之湖南人》中兴奋地说:“今世界各国中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无政府党有破坏之渊薮也。”他甚至宣称:“今日之言暴动者,立义也!”“今日之言暴动者,爱国也!”“今日之言暴动者,贞士也!”在《理想的虚无党绪言》中,杨毓麟激昂地呐喊:“虚无党,虚无党,我爱你,我崇拜你,你们所作的事业磊磊落落,能杀那混账王八蛋的皇帝,能搭救那一般受苦的兄弟姐妹,无一件事不惊天动地……我久想见见你们,和你们谈谈,我好领教一切,学学你们的手段方法,我好做个榜样。”[9]65
此外,杨毓麟认为无政府主义虽然“排斥国家,排斥爱国心”,但是“无政府党之所以趋向此意者,其目的全在建设万国无政府,四海兄弟之黄金世界。国家主义及爱国心为此绝大之障碍物,故诋斥特甚”。同时,“无政府教义中排斥国家为排斥蹂躏人权,刍狗国民自由之国家,排斥爱国心为排斥谬假政治学说迷乱生民之爱国心。苟其为恢复人权,力争自由,扫除旧政府,建设新国家以为建设四海兄弟黄金世界之过渡物,固当暂许为无政府党之发轫地。苟其人以恢复人权,力争自由,为爱国死,固当谓为无政府主义之佛种。故无政府与爱国心非不相容”[2]175。
但杨毓麟也清醒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绝对真理,绝对自由之“黄金世界”在短时间内由于受现实条件的限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改造绝非易事,杨毓麟又总结了改革建造过程中应遵循的“五义谛”。“第一义谛,凡欲得自由者,一切当以自立。以血得之,以铁得之以破坏力得之,而不以要求得之,此地球上无人能与我自由者,亦无人能吝我自由者。第二义谛,非以铁血种种自立活动改革,由国民自由良知上组成之政治,法律,权利,不成为政治,法律,权利。第三义谛,吾人当知人道只认自由,所有一切妨碍自由之恶魔恶法,吾人随时随地挺身决战之义务,人道者,吾人当以人道正义,完全享受自由。不然则当以苦战奋斗,完全恢复自由。舍此二事以外,皆非正当行为。第四义谛,吾人以自立恢复自由者,非一革新后,自由便完全存在。吾人一面对于本民族,本国民恢复自由,一面即当知吾人应为构造未来世界黄金时代之预备,吾人所以改造一新国家者,系对于铸造绝对真理世界为一过渡物。第五义谛,吾人当知恢复自由者,须是时时将过去思想,及过去事实革新。过去未久又有过去,革新未久又有革新。吾人对于此事,事后绝无成功可居。”[2]185-186
四、结语
杨毓麟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精华,如三权分立、人民主权以及政府责任论等,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相比,他有着彻底推翻旧制度的远见和勇气。而与一般革命派相比,他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实践的同时,又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政治理论上颇有建树,有其独特之处。以革命派代表孙中山为例,在孙中山早期(辛亥革命前),其政治思想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即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由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11],同时实行党治,“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12]。杨毓麟的政治主张与其是一致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补充,如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重要性。
但杨毓麟的政治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孙中山在提出政治构想的同时提出了实现构想的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的具体行动方案;而从现有资料来看,杨毓麟虽然提出了政治理论、设想,但是缺乏具体的行动方案。其次,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孙、杨虽都主张暴力革命,但是孙中山走的是军事(武装起义)路线,而杨毓麟则受其认识水平的局限,走的是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暗杀路线,并极力推崇俄国无政府主义,指望依靠“手枪”“炸弹”来实现革命目的,同时又错误地将革命的依靠力量定为“中等社会”。杨毓麟认为:“吾湖南而为埃及,必有人为亚拉斐;吾湖南而为菲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为杜兰斯哇,必有人为古鲁家。若而人者,必出与中等社会无疑也。”[2]47其认为,中等社会肩负着提携下等社会、改造上等社会的使命。这种狭隘的革命观使得杨毓麟在革命实践中屡屡碰壁,并最终在遭遇了一系列失败打击之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于1911年8月即武昌起义前夕投海自尽,这不能不说是杨毓麟个人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王兴国.杨昌济集(1)[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27.
[2] 饶怀民.杨毓麟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1.
[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7.
[4] 周接兵.挽救危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形势下的湘学[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6(2):72-79.
[5]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 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72.
[7] 杨笃生.新湖南[G]∥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8] 胡滨.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9] 左玉河.暗杀:义烈千秋的壮举[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0]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32.
[11]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9.
[12]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