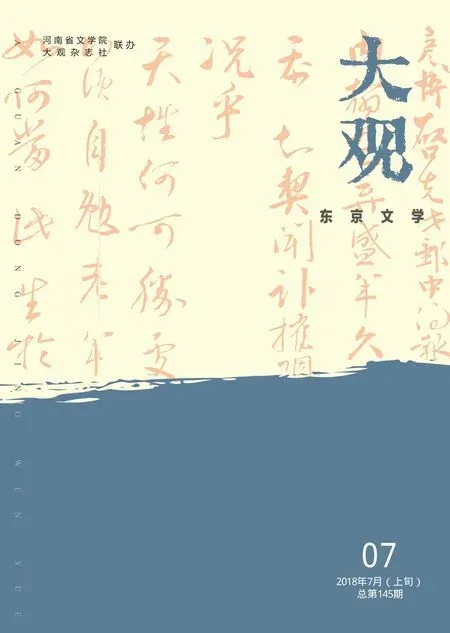话语诠释:酒、弃婴、血:层层反转中的移步换景
——评《圣保罗之夜》
康建伟
此文原名《并非所有午夜的人都已入眠,或:圣保罗之夜》,笔者不知道作家是写完全篇之后再拟定题目,还是先拟定题目再敷演出一篇荒诞人事。作家在命名自己作品时以“或”呈现出两种游移与可能,就让我们预感作家可能带领读者踏上“或然”的文字之旅。同作家的笔名“犹豫”一般,从题目出发,我们便能想象到各种彷徨徘徊与游移不定,而这一“或”字呈现的“游移”,我们却实实在在能在文中感受到。
顺着作者的叙述笔触,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勾勒出两个空间视域,一个是现实界,一个是想象界。按照文章的自然分节,在现实视域里,依次出现的事件是斗地主等待老湖、医院看望老湖父亲、寻找护士长丁楠、寻找道友、遇到弃婴、关于弃婴的议论与臆想以及最后“我”的意外受伤。现实场景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医院,圣保罗既是人名(使徒保罗),又是地名(巴西圣保罗州的首府、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初睹标题,“圣保罗”当指地名,但并非想当然的巴西或美国,而是指向了宗教信徒。从文中可知,豫东小城里的圣保罗教会医院,是1922年受加拿大教会委派来河南做医生、当地人都称之为饶大夫的故居,这本是一家带有宗教性质的医院,自然渗透着某种宗教隐喻。圣保罗医院既是现实界故事发生的场景,也是“我”昔日的恋人护士长丁楠工作的地方,是“我”一段情感纠葛的所在地。这也让笔者想起了1990年米家山导演拍摄的敌特片《圣保罗医院之谜》,惊悚恐怖,气氛阴森。本文中的圣保罗医院是“一座黑黢黢、爬满青藤的两层半的旧式小楼”,“巨兽般耸立”,“大楼数不清的窗口透出的灯光氤氲出一种迷离的神秘”,“整个二楼更像是一个阡陌交错的迷魂阵”。部分描写也有恐惧色彩,“他站在那里发呆,身体僵直,眼睛直直地望着地上的一堆缓慢蠕动着的黑影,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更为重要的是棒球帽、脚步迟疑的女人、弃婴、警察也构成了一起疑案。同名的圣保罗医院也出现悬疑剧情,还带有一丝恐惧的氛围,不知道作者是否看过《圣保罗医院之谜》,但单纯从读者的阅读经验来看,可以任意揣测为一种致敬?一种怀旧?还是一种戏谑性模仿?从茶舍到圣保罗医院之后,沿着“我”的足迹,地点也在不断循环转移:医院病房大楼重症监护室—病房大楼对面小花园—医院二楼医护人员专用通道—病房大楼对面小花园—医院二楼医护人员专用通道—病房大楼对面小花园—圣保罗医院急救中心。随着空间的转移,文中人物阿剑、牛福、德林、道友、老湖、护士、棒球帽、脚步迟疑的女人、弃婴、警察也依次登场。
在想象界,“我”的意识在霍尔果斯口岸和圣保罗教会医院之间不断游移。霍尔果斯口岸,这是连霍高速(连接江苏连云港和新疆霍尔果斯市的高速公路)的最西端,“对世界的想象就是对连霍高速尽头的想象。那时候,我们多想变成一只鸟,飞到连霍高速的最西端,飞到霍尔果斯,去看一看世界的尽头。看一看我们的梦想的尽头。”对于霍尔果斯口岸的想象,也是对于一段过往情感的眷恋,对于梦想的憧憬。在茶舍,随着道友给“我”展示的一张张图片,“我”眼前也呈现出白雪覆盖的群山、墨绿色的丛林、偶尔出现的斜拉桥、赛里木湖、装饰华丽的马车、戴着白色锥形毡帽手里擎着猛禽的哈萨克少女。然而片刻的感动之后,这些场景如同那逝去的感情一样,让“我”感到荒诞,跑那么远仅仅为了留下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吗?而那昔日的恋情,“年少的梦想,其实就是个悬浮在我们头上,闪着七彩光芒的微薄的肥皂泡而已。”昔日的恋情,呈现出片刻的炫目光辉之后,迅速地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一切归于虚无与荒诞。豫东小城里的圣保罗教会医院,是“我”昔日的恋人丁楠工作的地方,“我”曾经准时等待着丁楠“从这个爬满常春藤的灰砖小楼里像仙女一样飘出来”。在想象界除了恋人丁楠外,还有樊娜,“我”的妻子。“我”与樊娜显然是被日常琐碎折磨的中年夫妻,妻子要带着孩子游玩,而“我”却要和好久不见的哥们聚聚,自然免不了喝酒助兴。“喝死在外面,正好”。妻子的责备之语,也是对中年夫妻生活状态的形象诠释。除此之外,全文再未提及妻子樊娜,“我”的思绪总是飘向昔日恋人丁楠。在医护人员通道,猜测到标本室时联想到陪丁楠看恐怖片的场景。当自己不小心受伤时,还在迷迷糊糊中想起了丁楠,还在想,“如果我们没有分手,我也一定送给她那种迷人的肉桂色的内衣,天天把她揽在臂弯里”。
这样我们似乎可以按照现实界与想象界、显性与隐性双线并行的方式分析这篇小说,按照惯有的阅读经验,阅读重心多半倾向于想象界、隐性层面,去寻找背后的“深度模式”。而且作者也刻意描写了一些意识流,尤其是“青鸟”意象。文本中多次出现“鸟”的意象:在联系到霍尔果斯口岸时,臆想自己变成一只鸟,飞到那里,看一看世界的尽头,看一看梦想的尽头;在医护人员通道看到护士“淡蓝色的衣服像鸟一样从她的身体上轻盈地飞走”,“青鸟,我突然想起这个词”,“青鸟,我还在想着这个词。青鸟飞远了”;自己受伤时,还在想象在医护通道看到的那名护士躺在丈夫的臂弯,“那肉桂色的文胸像青鸟一样飞去”。鸟的轻盈飞翔似乎是作者实现其远方梦想的形象载体,同时,后面关于“青鸟”的描述则似乎又指向了肉欲的狂想,压抑着我对丁楠、对女性的渴望,而“飞走”“飞远了”的重复强调,又夹杂着些许淡淡的忧伤,隐含着我对逝去的恋情无法排遣的追悔与眷恋,“青鸟”是主体欲望的诗意呈现与落寞感喟。
然而,当我们按显、隐双线并行,并将期待视野投向隐性层面,怀着猎奇心试图探究我与丁楠的情事纠葛、寻找文本背后的深度模式时,我们发现这条线索却总是隐忍不发。作者并没有刻意地交代这条线索的起承转合,而是呈现出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状态,犹如笼罩在现实界的一层粉红色的轻纱,渗透着哀婉伤感的氛围。“背景”似乎并不愿意转换为“前景”,上演悲欢离合的情事纷纭,而自甘“退居二线”,乃至消弭于无形中。
文似看山不喜平。“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重新走向了圣保罗医院,寻找护士长丁楠,读者也期待着一场精彩“见面戏”。然而作者此时总是迟滞不前,耐着性子描写楼道里的见闻。先是护士站,一位画体温曲线的护士,再是病区,各色病人及其家属,接着是医护人员专用通道,更衣柜前换衣服的护士。继续前进,在狭窄通道的出口与一个高出我半头以上,戴着深蓝色棒球帽、蓝色一次性口罩及一副墨镜的男子相撞,随即很快消失。在狭窄通道的门外,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个脚步迟疑的女人,她抱着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小孩。“她似乎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没有目的与方向。似乎每迈出去一步,都会面临着选择,像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读到此时,我们已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两人与后面发现的弃婴的关系。而且作者也刻意描写了几个细节印证了这种可能,“我”第一次从医护人员通道回来之后,心烦意乱,“我把烟头戳在啤酒箱子上,让暗红色的烟头在纸箱上无聊地游走,一支烟燃尽时,我发现,烟头烫过的地方,呈现出一个黑糊糊的丁字”。后面发现弃婴时,在他身下铺垫的纸箱子上面清清楚楚地有被我烟头烧灼出来的丁字,所有的细节都强化了这两人与弃婴的联系。虽然如此客观地呈现与确凿地描述,但作者主体显然要拒绝这种联系。为了拒绝这种联系,作者也是多次描写了她的眼睛:初次相遇时“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丝惊恐和慌乱”;回到小花园石桌边我想起与她对视时“从她眼里闪现出来的孱弱的善良的光芒,呈现的是那样一种母性的温情”。这一眼神,作者不惜笔墨:“用秋水明媚、星眸微转这样的词都不足以形容她。任何与她相遇的人,都会被那种目光深深击中。那种充满哀怨的,充满了万般柔情的眼神,只属于林黛玉,只有用‘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来形容”。如果这样一个有着充满母性温情眼睛的母亲做出弃婴这种行为,“这简直能让人疯掉”。
“世界真他妈疯了”。当着警察的面,我无意中带着反讽的味道说“这一家人,他妈可把这个沉重的包袱扔掉了”。当然,正如“我”与警察的争辩中所言弃婴现象包含着基本的伦理道德、复杂的社会与伦理问题,客观的分析,源头的解决,都可以洋洋洒洒地写篇长文,但“我”还是无意中这般说了。“无意”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特别关注的字眼,失言、口误、玩笑等往往暗示着主体的某种无意识的流露。“我”无意中说出的反话,从一个侧面表达出“我”被那“秋水明媚、星眸微转”“充满母性温情的眼神”蒙蔽所带来的愤慨之情,也就不难理解我的咒骂“世界真他妈疯了”。
似乎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终于在延宕迟滞中引出了弃婴事件。与小警察的争论,以及朋友们的义愤填膺,也有可能将这一事件导向对于道德伦理的探讨,从而卒章显志,结构全篇。这是不是“我”开篇提到的等待着我们的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我”在这座楼里遇到的使整个夜晚变得离奇和怪异的事情呢?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将这一文本看作对一个弃婴事件的描述,上升为社会现象的探讨道德伦理的评价。然而,作者又是笔锋一转,“节外生枝”。在与朋友的嬉戏中,“我”被牛福一拽栽倒在草丛中,脖子被啤酒瓶碎片刺中,“我感到有一股黏稠的液体从我的颈动脉喷薄而出,眩晕与失重感突如其来,就像空中骤然绽放的烟花,整个人像从高处毫无征兆般突然坠落下来。”出人意料的意外发生,从读者意犹未尽的弃婴事件中突然反转到受伤事件,完全打乱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料想的各种结果在我突兀受伤的情节中戛然而止,读者欲罢不能,而作者却不管不顾,硬生生结束全文。事件意外发生,叙述意外结束。
当然,静心一想,这一受伤情节作者在前面还是做足了铺垫。从病房对面小花园里石桌边的喝酒聊天,在弥漫着啤酒花的醇香中,我们想到小时候在老湖父亲的小卖部喝酒。再到从医护通道回来,回到石桌边,“我踢到了一只啤酒瓶子。它滚到石凳上发出一声碎响。我似乎还有点情绪似的,又加上一脚,把碎瓶子踢到凳子后面的草丛里”。这一脚也预设了“我”的悲剧,当“我”被牛福拽倒时,正好被“我”前面踢到的碎瓶子刺中脖子。虽在情节设置上显得突兀,但在事实逻辑上倒也是交代得清楚明白,合情合理。这念念不忘的啤酒终于在文章的末尾再度出场,发挥了它终结者的作用。
搁置这一草蛇灰线的千里伏笔,文章开头兄弟间的友情、“我”与丁楠的昔日的恋情、医院看望老湖父亲的亲情、众人批判弃婴行为的人情,都只是层层反转中的过客,而作者卒章显“血”,“血是那么猛烈地喷射,溅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从文末介绍可知,作者有医学背景,如同余华对暴力和死亡的叙述客观平静、丝毫毕现,作者也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写我受伤后的意识流动。在血液喷射、生命垂危时,“在越来越模糊的意识中,我开始胡思乱想,乌七八糟地替整个世界担忧起来”。过往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诞,而我依然在脑海中闪现出护士的文胸、丁楠的呻吟,还有那两颗内疚或颤抖着的灵魂,“他们是否在万般的煎熬和深深的忏悔中,是否跟脚步凌乱,抬着我匆忙飞奔着的兄弟们一样,将在巨大的不安与惊恐中渡过这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作者一路写来,兜兜转转,似乎总是在引领我们不断探究,而当我们被调动起兴趣时却突兀转折,笔锋一宕,引向他者,不断挑战也戏弄着我们的期待视野。短短的文字,作者笔锋顿挫,不断反转,移步换景。这种反转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突转”,“突转,如前所说,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当然这里的反转并未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如果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反倒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方式预定了结局。不过,这里的“反转”也是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的。在反转中必然面对前后片断乃至句子之间的距离与落差,构成了阅读的“空白”,“每一句子相关物都包含有一个‘空白剖面’,它承继前一个相关物,又追寻下一个相关物,它回答先前句子的期待(记忆背景中的现在部分)。因此,每一阅读瞬间都是延伸与记忆的辩证运动,并且与过去(正在不断消退的)视野一道构成或唤起一个未来视野。游移视点同时通过二者开辟航路,并在前进中将它们融汇为一。”这种游移视点将“空白”与反转联系起来,形成了层层反转中的移步换景。从隐性的恋情到显在友情、亲情、人情诸般情事纠葛,意外受伤,情节突兀,却也有章可循,诸般温婉情事反转终结于意外之血。血是生命的律动,是自我的延续,是自己给世界的最内在的、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献祭,与心在流血这一隐喻相比,故事中身体的破损与血液的涌出,正是作者的想象界(心流血)与现实界(身流血)达成和解的意象表达。作者在叙事中以主人公第一人称“我”的身份,以鲜血的涌动与流溢,洗刷这无情与荒诞的人性之夜。“日暮向风牵短丝,血凝血散今谁是”,流血伴随的快感,如同“我”受伤意识模糊之际却替整个世界担忧一般,荒诞反讽中瞬间消解了所有的崇高。如果我们不苛求于某种核心主旨的表达,某种深度模式的探求,不苛求于某种叙述的规范,某种叙事传统,而只是对于某种状态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理解题目中“或”的复义与开放,并非所有午夜的人都已入眠,或:圣保罗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