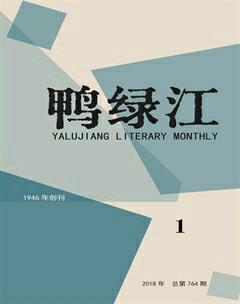人与人性的变奏
刘恩波
1
所罗门王的权杖上刻着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时间变着戏法,淘汰了新与旧的差别。当然就精神走向而言,文学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信物。一段历史消失了,文学却以生命标本的方式贮存了岁月的气息、情感的温度和心灵的底色。
走进李铁的小说,你会为他笔下五颜六色的生活故事所震慑困扰,那里面充满了沉甸甸的时代重压感,拥挤着社会变革潮流中涌动的灵魂悲喜的气泡,还有人性深处不泯的幽暗中的亮光。
读李铁,在我,是接触到人生的某个撕裂的断面,是淬炼情感和心智的火花,也是拥抱岁月风尘里未被湮没、变质抑或毁掉的灵性。
每个人都有故地、梦乡、源头。作家尤其如此。有些地方有些角落就成了他們生命里割舍不掉的根和网,成了心念中久久辗转徘徊的港湾或者驿站。就此意义来说,李铁与工厂之缘之情之亲,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在他心目中,“生活一线是最好的大学”,在锦州火力发电厂,在最底层工人群落,他一干二十来年。如果我们借助文学通常的比喻,会说李铁仿佛一个摸着黑走到天明的夜行者,因为有一盏名为工厂的灯始终为他亮着。是的,李铁的小说十有八九要写到工厂,它的辉煌它的落寞,它的仁爱它的残酷,它的窝囊它的柔韧……工厂风波,工厂命运,工厂故事,构成了小说家李铁的文学版图。但是,即便这样,我依然不赞同以题材本身来看待作家的地位、身份和价值感。我不想将李铁视为一个纯粹的写工业题材的作家。因为好的小说都是大于题材的。无论什么样的题材,一旦接通人性,开始梦想的旅程,走进生命的旋涡,颠覆灵魂的架构,则这题材便被赋予了魔法、诗意和魂儿。
李铁笔下,写得最好的是草根阶层的人,普通人,工人里的凡夫俗子,或是为着生活这根藤绕来绕去的苦命人、苦情人、苦心人。她是《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崔喜,她是《花朵一样的女人》里的春兰秋菊,至于乔师傅、刘雪、荔枝和她母亲,乃至《手影》中的养母养女,一干人等,均在此列。每个时代都有边缘人,每个角落都有生命的真义,每个身影里都有诗。李铁拥抱这些小人物的视角是平视的,没有俯瞰,怀揣着温暖,于是让他字里行间的人物都有了温度、体征、气质和性格。人物可以小,但精神不能小。这是艺术创作上的辩证法。应该说,李铁深谙此道。
李铁写人,写得朴素,地道,鲜活,落地生根。用道家语句说是,见素而抱朴。这么写人,是要有根基的,在生活中厮混久了,那人物自己就来找你了,恳求着你把他(她)写出来。正如李铁的夫子自道:“我觉得生活底子太厚的作家写作是一种流淌,虚构反而是强加给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管道。”是的,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就在李铁的笔端自由自在流淌着,矛盾着,挣扎着,惶惑着,失落着,盼望着……作家追逐他们深邃的精神痛苦,扫描定格他们力不从心的错位与失衡,凝聚起在场者的一分关注的热情,留下一抹印痕,一缕回音,一声叹息。李铁不需要远距离审视他笔下的人物,他的现场感,他的介入意识,让他的人物火苗一样蹿到我们眼前,精彩地为我们演绎出人生的悲喜剧荒诞剧。
2
阅读李铁的小说,你会感到那些人物可以在脑子里过电影,他们是独特的人生命运的拷贝、剪贴和投影。譬如,崔喜,就像一棵来自乡野的植物被移植到城市的土壤,即使嵌入了都市文明的枝叶,但那根还是乡土的,于是只能错位着生长嫁接。城与乡的距离感和矛盾,古典的乡情和现代观念意识的难以融化,从一系列的细节深处,投射着冰冷而又漠然的光彩。崔喜想从发式、穿戴、步态和神情等各个方面融入到城里人的样板模式中,以改变自己出身的卑微和低贱。当她终于把自己弄得近乎脱胎换骨之际,其实还是没有归属感。城市精神和乡土风情依旧内在地撕裂她,将其分割为两个无法统一的生命体。崔喜是历史弯道里不愿落伍的人,也是被现代化浪潮裹挟、缠绕乃至扭曲、异化的祭品。其背景深处叠印着农耕社会与都市文明不相协调的生命画卷与颤音。在小说中,人与人性的变奏是在女主人公和两个男性之间展开的。崔喜和她丈夫宝东,崔喜和他的恋人大春。他们的故事穿插连缀起两个群落的生活协奏曲。就马克思的经典说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言,我们看到了人性在社会关系里的变化、整合及其制约。爱欲本身也是受着道德、律法、习俗、观念等等外在因素调控的。宝东是城里人,尽管形象猥琐,属于下岗再就业人员,但在渴望城市生活的崔喜眼里,却不啻一根救命稻草,好比救赎一个人前途和赐予其梦想的挪亚方舟。嫁给宝东她是心甘情愿的。有了孩子更多了一层欢乐。但好景不会很长,李铁及时打断了这个乡下女人的浪漫憧憬和不切实际的梦幻。她的丈夫在做爱时喊出了相好的名字,尽管那是女人故意引发的,为了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她出去找工作,却难以接受那些带有色情意味的特殊服务要求;她从早市买回几只小鸡放在纸盒箱里养起来,结果有一天宝东踩到了鸡屎就把小鸡扔到了窗外;当她去婆婆那里告状,等到的还是婆婆的带着城里人优越感的歧视和傲慢……这下子挪亚方舟瞬间变成了撞到冰山的泰坦尼克号。于是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崔喜的人生中也出现了她的“杰克”,就是那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小伙子大春。他们沉醉在爱恋里不能自拔。
李铁写人物,是琢磨透了才写的。崔喜的魂魄几乎透过了《城市里的一棵庄稼》的纵深腹地,带着她的淳朴、野性、活力、狡黠、顽皮……置身于小说艺术的画廊里。这部作品的高潮是写到大春打算和崔喜回到乡村过日子,给崔喜一天的考虑时间。到了第二天,雪后的早晨,阳光强烈,与此对照的是女主人公的无精打采,她像一棵被晒蔫的植物,见到大春,只说了一声,“我不能和你走了,再见吧”,然后转身就走。乡土式的爱情最终败给了城市的诱惑和生命的庸常惯性。
鲁迅当年曾经探讨过娜拉出走后的得失。已经猜到了她最后可能还要回来的尴尬。崔喜,想要出走,想要回归乡土,但她连出走的勇气都没有,便乖乖放弃了。一百多年了,女人的归属感,依旧是文学不老的话题和母题。从易卜生到李铁。说不尽的人生之谜。
3
在李铁的小说中,塑造得最好最到位的无疑是女性形象。这些人物仿佛是从生活海洋里汲取的几滴水,却每一滴都映照渗透着大海的颜色和气息,足以承载人生和人性的个中滋味。endprint
有智者曾经指出,你明白女人,就明白世界。
但明白女人,写好女人,又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我读李铁,感觉他是女性的知音,解人,有点川端康成的味儿。他们都擅长品鉴咀嚼女性世界的悲苦、悲凉和悲哀,并且给予美的表现、描绘和观照。写法也都很细腻,别致,入情入理。但不同处在于,川端康成那儿,背负着日本文学的物哀和幽玄两大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东方佛禅意识。物哀,是见证生死轮转无常;幽玄,是归于空寂出世间的涅槃之道。李铁没有宗教文化背景和渊源,他的价值观里主要是现实主义的生活流、意识流,这样他笔下的女性多是挣扎在现实生活场里的苦命和苦心人,为了生活本身,匍匐着挑起命运的重担,踏踏实实地出现在人生的聚焦点和无情岁月的流水线上,听凭时代的喝令,体认社会规则的惩处,隐忍着年华老去的无奈和空幻。
仔细盘点一下,李铁的女性画廊里出现了乔师傅(《乔师傅的手艺》)这样的为了学会技术不惜用贞操换取的执拗的个性人物;有《工厂上空的雪》里的刘雪那样以古老的良心做事而义无反顾不知悔怨地在历史转型期受到刁难和冷落的悲摧者;也有像《冰雪荔枝》中的那对母女,盯梢男人的奸情结果却砸了饭碗断了生活后路的难以两全的无辜的人……
哀女性之悲苦,叹女人生存之痛,惋惜女性世界的轮转无常,李铁果真有菩萨心肠,更有一副艺术家与之怜悯唏嘘,共相体味化解的襟怀与情调。搀扶着那些可敬可怜可歌可泣的女人们往前走,浸润其中,沉吟良久,让李铁的小说因此充满了人间气息,人情的况味。每一次掩卷,我就想,如果不写这些女人的悲苦喜乐,那李铁作品的成色至少会减掉几分。
4
历史走远了,会留下生命的印记。时代走远了,会留下女人的足迹。尤其是处于社会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个体命运的起伏沉落,更容易淬炼磨砺作家的火眼金睛。李铁审视女工们的肉身精魂,不是雾里看花,而是耳濡目染,走进了生活场景的腹地,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他写女工的悲欢喜乐,有点像德莱塞当年写《嘉莉妹妹》那样卷入其中,充满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痛感与悲悯。索尔·贝娄说德莱塞的小说“简直就是从人生中撕扯下来的”。李铁同样有着那种从直接经验本身寻找文学创作冲动的契机和理由。于是,展示那些花朵一样的女人历经凄风苦雨的人生变数和精神陶冶,乃至在社会挤压磨炼的过程里造就的人性异化和心灵救赎,就成了李铁小说中非常吸引读者的一个现象或曰层面。
用小说照亮女人幽暗的生存,李铁在《乔师傅的手艺》里将性爱和手艺做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置换和交易,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性在现实的冷酷法则前的无奈、脆弱及其最后的反弹。小说尾声以年华老去的乔师傅现场直轴的场景,将这种人生的变奏刻画得精彩非凡,“这场直轴对于乔师傅来说,就像一个老处女终于等到了钟爱一生的男人……积累了一生的热情和欲望,像雨后的太阳喷薄而出,顿时照亮了她生命的全部价值。她花白的头发散发出芝麻油一般香甜的味道,她的汗气像海风把周围的空气都吹得清新而又略带一些腥气,她的身体像过分成熟的果实一碰就会爆裂……”这里,李铁的笔端凝聚着生命灼烧的光芒,像是用画笔在勾勒一幅人物的线条画,充满了诗意和激情。乔师傅用身体作为代价换来的手艺历经岁月的湮没和沉淀,终于派上了用场,但是,小说的最后一句,“整个人就像一面墙那样向后倒去”,作为不祥之兆,还是让我们嗅到了一种即将实现梦想而又功败垂成的苍凉。那是乔师傅一生形象的定格。也许直轴就如同一次迟来的真正的性爱,会弥补当年那个青春女性的陷落与迷失,在此精神异化的人物褪去了生命的重压,而即将返回最初的灵肉合一的伊甸园。然而,衰落的肉身毕竟承载不了那降临得太晚的幸福时刻,这触目惊心的反差和逆转,将小说推向一个极限,那断裂中的高潮,不也正寓意着女人悲苦命运的写照?
《乔师傅的手艺》是我最早看到的李铁的小说。他取材工厂生活,有着相当丰厚的工人阅历和体验,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拒绝把这个人视为一个单纯的工业题材作家。只因为他对人性把握得那么有层次有味道。其实,这个故事超出题材来看,完全可以跟张爱玲的《色·戒》相对比着看。王佳芝走向易先生的怀抱,跟乔师傅委身斜眼刘,都是迫不得已,都是女人在社会关系网络里的投身饲虎之举,一者为了革命事业,一者为了自己的手艺。用身体本钱换来生存权利生活尊严乃至家国情怀的兑现,王佳芝和乔师傅用的是同样的筹码。而结局一样凄凉惨淡。用性爱换的东西,迟早会被剥夺。因为这构成了个体生命和灵魂的错位。爱是不对等的,爱就将萎缩,被利用,被异化成别的。
《乔师傅的手艺》让我看到了李铁的手艺,他的道行与才情。
还是那句话,不要把他单一地定性为工人作家。那是题材决定论的偏见。
5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助他者的口吻说:“我们每人都是人的一半,是一种合起来才成为全体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就是那个流传甚广的“男人一半是女人”的说法的由来。古老的情感和智慧从发源那天起,就磨砺淬炼融汇着古今创作者的头脑和心灵。给他们带来一段又一段的故事、传奇和小说。打开情爱世界,这人生和人性的魔盒与试金石,每位作家和艺术家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
阅读李铁,读多了看透了,你会发现他特别善于处理男女关系,他对男女关系的把握和理解,既是人性的,又是社会的,既有时代感,又有价值关怀,而且通常他的肯定、赞许、潜意识上的讴歌,其主要对象多为女性。像刘雪,像乔师傅,像崔喜,像荔枝,这些生活中的弱者、无辜者、失落者,都是李铁用全部热情和笔力去予以呵护、悲悯和褒扬的人物。
《工厂上空的雪》,让我们目睹了一个纯净的灵魂在庸常社会关系网里黯然消失的过程。人类的生存危机,越到后来就越是精神境界的困扰、迷惘和堕落。尤其是面对惩罚、报复和打击等等来自体制毒瘤的魔法,正直的人如果不低头,就有点孤军奋战的意味。李铁笔下的刘雪,闪烁着心灵强大的光芒,尽管她在那个环境里属于弱者。不被理解,没有人帮扶,小说里的“我”和鲁达,两个本来与刘雪有着难以割舍情感的男人却都以瞒和忍的方式站在了强权的一边。写男女关系不难,写出男女关系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社会内幕和权力体制的操纵,写出一个让人趋于麻木的环境体制对人的良知的蚕食,写出内心深处的挣扎和撕裂,才是李铁小说的高明之处。这种透过表象揭露实质的写法当然是不拘一格的。那是一个有法眼和慧根的作家才能秉持的格局、认知和气象。刘雪当然输了,那潭湖水一样明澈的眼睛在看清了人性的某种丑陋,生存空间的令人窒息的无奈之后,在自己不慎跌落进去的水沟里,“变成了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本来她想为厂里的劣質货讨个说法,结果没有讨到,却在急三火四寻找厂领导的路上发生了意外的悲剧。这篇小说除了带给我们生命的悲怆意识,还有一层荒诞的色彩。一个纯净的女人在寻找自己另一半的人生之旅中,却先后遭遇了两个窝囊的男人。这不是荒诞是什么。endprint
在李铁那里,男女关系的实质是社会关系,是文明与不文明的争夺和较量,妥协与反抗。甚至是道德伦理和生命意志之间的撕裂性对峙及其融解。
这一点有他的小说《男女关系》可资为证。
这一次,在男人和女人的价值指数上,人性无所谓高低,两者扯平了。这是个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通过“我”和杜小蕊还有吴志文的近乎扭曲异常的关系,揭示了那个性压抑时代的精神痛苦和生命抑郁。为了拯救受伤的吴志文的家庭困窘,“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出钱出力,得到的补偿是吴志文让“我”和他妻子杜小蕊睡一个屋。这种畸变的男女关系,其实在电影《春桃》中已经有过展示。只不过,李铁变本加厉,而且选择了禁欲时代的特殊背景,造就了两个人同床却不能交欢的灵肉分离的人性荒诞感。每当他们把持不住的时候,女的就让男的背诵厂里的技术规范,机器的运作原理、控制指标和冷油器出口温度什么的,以便转移注意力。也许生命中最深刻最有表现力的关系就是男女关系,李铁抓住了这个把手,用以开掘历史和社会中那些罕见的,但又充满了人性变奏内涵的丰富精神资源。
6
从写作的风格和样态上看,李铁属于从传统现实主义向诗意心理现实主义逐步转换和过渡的探索者。传统笔法,注重人物塑造,情节曲折生动,悬念突转别开生面,高潮段落风生水起,尾声常常横生枝节。而到了心理层次的进一步深化阶段,则是摆脱了情节的单一指向,向着细节迈进,用写意的笔法写实,用生命感悟的方式代替了故事性本身的轻车熟路。
李铁的小说大都属于线性叙事,符合经典的文学传统中着意起承转合的故事路数。从写法上看,他早年和中期的写作更多欧·亨利式的风格,故事节奏明快,铺排伏笔有声有色,悬念迭起而又合情合理,结尾处陡然一转,暗藏机关。他的晚近之作则有了契诃夫式的心理意味上的探索,将人物从单纯的情节布置向纵深的灵魂开掘处延伸。
按照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艺术的基本目的在于利用人们熟悉的事物呈现出人们不熟悉的面貌,以此克服习惯造成的令人窒息的麻木感。
走进李铁的小说世界,我们会感到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突然被什么东西照亮了,获得了一种新生,获得了陌生化效果。那是人生和人性的变奏,是小说的丰富本性的拓展和开掘。
譬如,在《冰雪荔枝》中,荔枝为了惩罚父亲无所顾忌的偷情行为,写了一封匿名信,不出意外地导致父亲从科长宝座上被撸下来。作家精心布置了女儿为父亲过生日的情节,“那一晚,父亲毫不含糊地喝醉了”,结果从醉话里女儿套出了实话,成为日后的口实和把柄,将父亲拉下马,断了他的钱财来源,以为这样就没有女人们缠着他了,却没想到从另一方面这也造成家里的财源跟着断了。好心弄成了糟糕的事。你想避开原来糟糕的事,结果碰上了一件更糟糕的事。这不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二十二条军规”吗?而李铁的故事深谙此道,他的画龙点睛之笔,让这篇有深度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不知不觉地从悲剧走向了荒诞,从对命运的揭露走向了哲理层次的审视和延伸。
有意思也有意味的还在于,李铁的许多作品结尾处的处理,堪称精彩和高明。从这一点上看,他对故事结构的把握还是相当得手和刻意的。当然,形式为内容服务,直到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这是小说艺术辩证法的胜利。李铁是写实的高手,他小说中虚的部分不够多,就是给人想象和带有审美距离的东西不够多,但是,他用倒高潮的逆转和横生枝节,一下子会让小说的时空骤然出现颠覆性的效果,结果那些人物总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他们的生死转换、命运涂抹还有心理意愿的落空与幻灭,造成阅读上的极富冲击力的震撼。
崔喜没有告诉大春她自己也是个乡下妹。也许说出来的话,大春可能会主动退出,两个人的生活就不会那么拧巴(《城市里的一棵庄稼》)。“若干年后,我对妻子说,我和杜小蕊都守住了,所以我才敢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妻子反问,真的守住了?我说真的守住了,有杜小蕊还是处女为证。妻子冷笑一声,你们守住的不就是一种形式吗?”(《男女关系》)这样的质问,是对人性本意的洞悉和穿越,究竟是守住,还是媾和,更代表那个禁欲时代的精神胜利呢?也许小说作者也不置可否,而这恰恰显示了小说写作本身的智慧。用昆德拉的话讲,小说是智慧的发言和微笑。而年事已高的乔师傅在现场直轴的画面接通了一个人命运的密码,她最后一刻“整个人就像一面墙那样向后倒去”的造型(《乔师傅的手艺》),是小说的开放性结尾,她生死莫测,也无须挑明,但她用那样的壮举毕竟洗刷了一生的耻辱,点亮了人性幽暗处的生命火把。这值得,当然值得。
7
阅读李铁的小说,看他在不动声色游刃有余的笔走龙蛇中,探究着人心的莫测,人性的诡异和人情的变异更改,其间裹挟着时代的痛痒,历史的误区盲点,还有命运混沌的乐章。晚近的李铁,在题材上越走越宽,突破了以往对于工厂和工人生活的情有独钟的偏爱,他的《牺牲》和《手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实力派作家苦心孤诣的不懈追求。
写身边的事,还是写想象中的事,关乎小说作者的心理需要。但在成熟的作家那里,两者似乎都不可少。抓现实题材,还是侧重历史题材,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打通和融汇,是构建文学心理时空完整感的三个通道。当然每个作家摄取艺术灵感的方式不同,他们对题材的进入、梳理和把握,也就各行其是各有侧重。
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可以比作一口井。有多少种井,就有多少种作家。重要的事情是井里要有好水。最好是汲出定量的水,而不是把井水抽干,再等待它渗满。
李铁在创作题材上的有意识转换,也许就是在汲完了定量的水之后,在等着另一次新的开采。工厂作为他的精神富矿,也得经过一段周期性休整。于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两篇别致而又意味深长的作品。
《牺牲》属于谍战类创作,这一类题材在近年影視剧和文学领域都成为走红走俏的品种。当然李铁写《牺牲》,像是客串,而不同于转型。是尝试,而并非险中求胜。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竟然入戏了,何况演得惟妙惟肖,戏假而情真,至少在我这里应该喝满堂彩。endprint
透过历史的硝烟,透过情感的波澜,李铁让他笔下的人物一一登场,又一一消失。或者凄凉,或者悲壮,或者莫名所以地走出人生的舞台。这一次李铁把汪伪时期的南京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他写了美女特工的身心分裂,写了跑堂伙计的大义灭亲,写了老谋深算的线人流星一般地陨落,写了将革命和爱情糅合在一起的生命传奇,写了飞蛾扑火的信仰高于一切……复合的主题,扑朔迷离的情节推进,一浪高过一浪式的戏剧化渲染,戛然而止的收煞,都让《牺牲》充满浪漫而又带着柔情的色泽和光彩,仿佛在历史远去的脚步声中,挽留住几许动情而未泯的人的灵魂的颤音。
如果说《牺牲》让我们发现了李铁的多侧面性,创作手法上的弹性,以及不断蜕变进取的信心和雄心,那么《手影》则像一道强光,照亮了李铁小说最混沌幽暗的地带,那是人性之诗,如一首凄美而苍凉的歌谣。
说实在话,《手影》某种程度上更像戏,两个人物互相较劲,尤其在小说的后半段展开了旗鼓相当的对决。故事大概的脉络是这样的,王翠华未婚领养了一个女儿,只因为那女孩是她恋人吴国栋车祸身亡后留下的生命见证。那个叫青苗的女孩被领回家后,由最初的审视漠视到后来的接纳磨合,一对没有血缘之亲的人逐渐互相认可了对方。当然这个过程为小说家提供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细节描绘和勾勒的机会,李铁用充满灵性和感情的笔触,写了两人在心理上逐个层次的转变。如果小说就按照通常模式的惯性思路往下走,这充其量是个相当主旋律化的好心人找回人间温情的故事。但是恰恰就在我们习以为常不再期待陌生感的一刻,李铁让他的小主人公动了不该动的念头,青苗开始迫不及待地让王翠华承认她就是自己的亲妈。这里的转弯,就等于为小说拧上了戏剧的发条。尽管王翠华在心理上早就把青苗当成了骨肉至亲,但情感上认同,并不等于理智上也将失去对真实身份的判断和确认。亲情伦理上的感应,代替不了生命认知,这是李铁这个令人难過而悲哀的小说的真正内涵和意图所在。
《手影》作为心理窥视类作品,将人性的复杂至极的微妙性和丰富性打造得浑厚结实晶莹剔透,有着动感的美丽,充盈着近乎神奇的质朴天然的气息。那对近乎母女的二人互相猜忌,疑惑,转圜,躲避,退守,攻击,你来我往,欲罢不能。小说更奇妙处还在于,用女孩玩手影到最后表演手影,缓冲进而升华了艺术动人魂魄的内在张力。作为闲笔和插叙,同时也为高潮到来做了有效的铺垫,手影的出现,是该小说诗意展示的集中浓缩与写照。
而有了《手影》这样如同心灵雕刻一样的作品,李铁的创作既承接了以往的写实神韵,又拓展了人物的心理表现空间,进而凝聚起更加蔚为可观的能量和气势,令人刮目相看。
8
林斤澜先生当年就写作问题提出了中肯又精彩的界定,他说,一言以蔽之,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嚼过的馒头。怎么写?——偷来的锣鼓。
圣经上还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的题材素材都是别人用过的,无非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爱恨情仇之类的永恒演绎。至于如何讲故事,写人物,布置玄机,展开冲突,如何铺垫,倒叙还是插叙,等等,也都是在借鉴前人和别人的基础上再向前拓展迈进。
阅读李铁的小说,找寻他写作的起点和落点,探究其风格架构、精神指向,会发现他大体上走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是工厂中工人的群像,将他们的苦辣酸甜、情感和命运,充分地故事化、仪式化、艺术化,并且置于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去审视国有企业转轨、下岗、再就业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从中发掘开凿小人物身体里血脉里潜藏的生命质感和心灵气象。
在写法上,他的小说有中国古典演义小说的底蕴,像《水浒传》那样写环境写人物,基本上用了工笔和白描。一些细节深处的聚焦、勾勒和刻画,又带有《史记》绘其形传其神的风骨。他有时候大处落墨,有时候又小处发威,营造了小说艺术的整体情境上的底色和气脉。看《手影》,错落交织的结构,完全像是心灵的意识流,两个人物的戏剧化较量,又充满了命运的神秘感与象征意味。这篇小说既写实,又写意,甚至带点表现主义的气息,就是人物动作已经高度梦幻化精神化。譬如女儿固执地认为那个照管她的人就是亲身母亲,连同一系列的猜疑、困扰和小题大做,其实她已经完全生活在命运谜题的幻觉世界里不可自拔了。这是李铁的有意识的尝试和探索,这篇小说标志着他创作上的高度和写作上的成色。
从《男女关系》到《牺牲》,包括《手影》,我们不难看到晚近的李铁有一种不甘落后不甘重复自己从前路数的可贵努力和突围意识。一个小说家只有走出心灵的围城,摆脱既定的规范和制约,打破传统的格局与宿命,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条新路。
当然,仔细领略这些作品,也能感到李铁还需要越过许许多多的障碍和栅栏,方能走得更高更远。传统现实主义的窠臼和局限在于,那种小说往往限于就事论事,就人写人,当那个时代和历史的背景置换或者模糊以后,那些当年的故事是否还经得起后人的咀嚼和咂摸,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现在的人们读卡夫卡,而不怎么读德莱塞,原因就是卡夫卡的故事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事,它有抽象性概括性象征性,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读者,都会被那种异化的存在感和生命的挤压和变形,而感同身受地觉得那是自己心灵的困扰和迷惑。
我喜欢一句话,真正精彩的故事是原意背后生发寓意。会讲故事,你的故事只有一个层次,只有把故事渗入更多的夹心层,犹如钻石用特殊的刀工让人看到各个层面的精彩和光亮,那才是炫目的小说之光。
李铁在创作的道路上跋涉了很久,写下了一系列绚丽晶莹多姿多彩的作品,他的耐力,他的苦心,他的坚持,让他的小说结出了累累硕果。这有他几百万字的作品,获得的各种荣誉,还有小说被收录各种选刊权威选本为证。但是与此同时,我还由衷希望他未来的创作,能够打破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事的固定思路,走向更加多元开放的永恒精神的滩涂,去寻找更美妙的心灵之花的绽放。
【责任编辑】 行 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