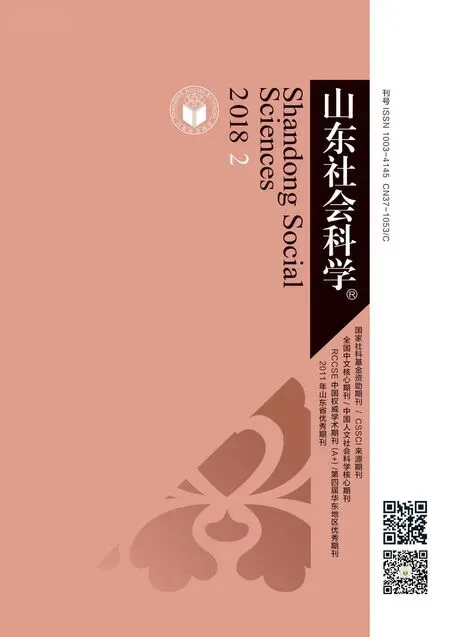马克思的“自由三部曲”
白 刚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欧洲的自传始于对自由的爱”(赫勒语)。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为人之自由而奋斗的“自由之子”,马克思的自传也始于“对自由的爱”。马克思就是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战和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奋斗的永恒主题,但自由似乎也是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争议不断的主题。实际上,在马克思及其相关著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发展和演进的清晰历程和具体内涵的。在此,笔者尝试总结出马克思自由思想发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论文》时期: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马克思是一个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一直影响和鼓舞着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从一切对超验对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哲学)宣言”:“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并强调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的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对青年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代表着反抗一切形式的限制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权威,不管它是来自宗教教义还是希腊神话。尤其是在伊壁鸠鲁这里,青年马克思还找到了最明显、最关键的反抗宗教神权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现实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这里,马克思还是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为了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反对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开战*在当时的德国,在宗教领域开战要比政治领域相对安全,并且此时的马克思对哲学的兴趣和积极性远远大于对政治的兴趣和积极性(参见[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8页)。是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流。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斯多葛派、怀疑主义都是古代自我意识哲学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鸠鲁代表的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此时正热心于自我意识哲学和精神自由的张扬。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只关注原子的“直线运动”,注重的是原子的物质存在,而伊壁鸠鲁则还说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质料和形式:“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5、28、24页。原子不仅是现象世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形式原则。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否认原子的“偏斜运动”。原子的“偏斜运动”并不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是意味着一种摆脱必然性控制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作为德谟克利特直线运动的“反题”,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识对物质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类思想超越盲目命运和自然法则的最终胜利。*[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马克思之所以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仍然受盲目命运和自然法则的必然性的束缚,而否认偶然性的意义。而马克思认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观点,认为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概念”。④正是在承认原子偏斜运动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运的束缚”而追求个性和自由的意义上,马克思称伊壁鸠鲁是“古代真正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说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先声,他的哲学给人类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装”(马克思语)。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选择,虽然还没有完全超出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但也预示了未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语)之路。
在马克思这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丧失,他反对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类精神变成单一的黑色。在《博士论文》中,为摆脱宗教束缚而获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马克思诉诸的已不再是对神的顺从和屈服,而是作为哲学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张自我意识哲学自己创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识哲学能使人从“阿门塞斯王国”的阴影中脱离出来,投入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能够进行独立哲学思考的人就摆脱了宗教命运的束缚,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主张通过确立自我意识哲学来通达精神自由的。因此,马克思此时与伊壁鸠鲁有着共同的哲学理想,也即哲学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⑤。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心灵的宁静,比自然本身更有利于精神自由的获得。所以,马克思也认同和主张到哲学即人的自我意识中去寻找和实现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鸠鲁的说法就是:“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⑥正是在“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意义上,马克思把哲学与自由等同了起来,其实质就是自我意识摆脱神的统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确立。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指认的反对宗教的“哲学(自由)狂欢”,以致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甚至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是彻底站在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立场上来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他作为黑格尔的最优秀的学生颁给自己的“毕业证书”。
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此时的马克思还带有青年黑格尔派的强烈的反对宗教色彩和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思辨意味,还意识不到唯心主义哲学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欢幽静孤僻、自我直观的实质。虽然他批评康德和费希特只是在天空飞翔,也不太喜欢黑格尔的古怪调子,并强调自己只关心地上的事情,但这时马克思所追求的作为摆脱宗教束缚也即神权统治的自我意识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哲学自由”,还缺乏稳固的现实基础做支撑。而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接触,并最后在《资本论》时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莱茵报》时期: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
如果说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追求个性和自我意识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摆脱了“宗教神权”的统治,那么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新闻出版自由”则是为了摆脱“封建王权”的统治。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强烈反对的就是普鲁士政府的“封建王权”。但这也同时表明,马克思开始从关注一般哲学问题转向分析具体的政治现象,也即从“哲学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对此,马克思的传记作家梅林有着明确的指认:马克思已经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自从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以后,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现在他在《莱茵报》上继续进行这个斗争,而不再是去“纺他那哲学的线了”*[德]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特别是在《莱茵报》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更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政治斗争”和新的自由追求。马克思此时最为关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谓精神自由——哲学自由,而是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政治自由,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从书斋走向社会,面向和解决具体现实生活问题的开始。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对“自由”马克思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不然,建筑师同海狸的区别就只在于海狸是披着兽皮的建筑师,而建筑师则是不披兽皮的海狸。”*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67、202、166、179、189页。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与现实的亲密接触而深刻认识到:“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摒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③由此可见,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已不再是被当作人类本性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就是人类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贵的“装饰品”。马克思对作为人类本性的自由的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卢梭的观点: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所以,马克思在该文的最后借斯巴达人之口号召人们奋起、甚至用“斧头”去“为自由而斗争”:“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④但此时,通过报纸与现实亲密接触之后,马克思已不再认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强调“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⑤。在这里,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权利的获得和保障,自由报刊就是号召广大人民为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而斗争的有效手段和直接体现。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而新闻出版自由却是自由的体现,自由报刊的本质就是自由的本质,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质,自由报刊就是现实的自由。如果人们享有新闻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体的现实自由:“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⑥可以说,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已经把自由的本质及其获得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而不再单纯依靠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演绎。为此,德国那些脱离现实、喜欢幽静孤僻而空谈自由的所谓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评:“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因此“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⑦由此可见,在走出书斋开始接触现实之后,马克思已不满足于抽象的、空洞的、单纯说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来越关注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应该享有的各种真实的政治权利的自由。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稳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
当然,马克思此时还只是看到和反对封建王权对人的政治自由的限制,还不能深入王权背后深刻认识到和挖掘出真正制约和束缚人的自由背后的强大“物质力量”——经济利益根源。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还不能具体确定是何种社会关系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此时反对的还只是作为普鲁士政府王权的外在体现的书报检查制度,并意识到“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制度”*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153、176、186页。。正是书报检查制度阻碍了人们追求和获得现实的自由,并引发了革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张通过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②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获得和实现,寄希望的还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权统治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立法”,认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强调“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同时,针对封建统治者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担心,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不断运动一样。”③与之相反,新闻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实现,而决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实的自由,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民主文明的体现。
与《博士论文》时期相比,马克思此时对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实现的理解和追求,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他已经从宗教批判前进到了批判政治与社会制度,这也是马克思离开书斋开始走向社会的真实反映。但总体上看,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还是处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善良愿望和理想主义阶段,幻想着通过和平的“立法”来实现和解决问题,仍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莱茵报》的实际工作,却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须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埋下和获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的“种子”和“原动力”。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后来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自由”(市民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而这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资本论》时期:全面的人的“个性自由”
如果说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是到“哲学”和“法律”中去寻找自由的真谛及其实现,那么到了《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时期,马克思开始逐步认识到对自由的真谛及其实现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学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语)。对此,恩格斯后来也有着深刻的认同:对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到“经济”中去寻找,实际上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获得,不仅需要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更要摆脱“经济权力”——“资本”的统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认识到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后来又在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里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集大成的《资本论》中,资本更是摇身变成了具有“幽灵般现实性”的统治一切的“自动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获得和实现真实的自由,仅仅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摆脱资本这一“神权”和“王权”附体的“经济权力”的支配。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实现自由背后所必须摆脱和克服的巨大物质力量。而马克思此时已经深刻认识到,要想彻底摆脱资本这一“经济权力”的支配,仅仅“献身哲学”和“出版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最彻底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和批判。
自马克思开始真正接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就逐渐认识到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这些“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作为支配力量的物与物背后所隐藏着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性和革命性,就在于揭示和强调资本的本质并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可感觉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超感觉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但这一关系又是以资本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颠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现出来的。这一关系,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天网,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纳入其中,完全受其控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现实。这一“抽象统治人”的实质,是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的,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马克思语)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在资本作为“经济权力”的这一强大抽象力量的统治和压榨之下,工人确实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④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874、683页。。所以,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工人对资本都是一种“绝对从属”和“被统治”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追求和实现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人之自由”,也即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还在于使政治经济学由关于“物”——资本增殖的理论,转变成了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论。所以说,《资本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把人和人类从压迫他们的种种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个性的形成的思想。”*[苏]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汤侠声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最关心的,就是在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突破资本牢笼的无形统治,形成全面发展的人的自由个性,仍然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中心主题。
在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们看来,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自由的源泉,而作为“看不见的手”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在进行“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的同时,就已经在实现着所谓的自由。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通过“私有制”和“价值规律”完全实现了自由,历史在资本主义这里“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在这里殊途同归了。但马克思却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异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谓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也只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自由,是贸易的自由、财产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义,只是一种“自由的错觉”,而决不是真实的自由。为此,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认为“自由竞争”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同义语”的妄断:“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价值规律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最大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它掩盖了为什么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反而走向了不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们要想摆脱资本的权力统治,获得真实的个性自由,就必须通过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④。正是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才能彻底取代私有制而消除雇佣劳动和异化,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⑤这实际上就是用“自由劳动”来代替“雇佣劳动”,用“合作化生产”来代替“私人化生产”,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的个人”,从而真正使人从“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走向共同生产的“自由个性”,最终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马克思语)。在马克思这里,“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是彻底的、绝对的和全面的:人应当从一切类型的非人的统治关系——统治、压迫、奴役、剥削、疏离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真正还给人自己,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所以说,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所有制革命”,才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这里,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实际上也就是“自由王国”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质都是使人彻底摆脱外在“必然性”——资本、必然劳动和自然的盲目控制,获得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强调:“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因此,“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此“联合生产”的基础上,也即“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页。。在马克思这里,“自由王国”的建立和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是同一个过程,都是人摆脱资本的统治而获得独立性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即人的个性摆脱劳动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觉的自主劳动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在此意义上,《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追求的废除雇佣劳动的“劳动解放”,的确是“最高级自由革命”(塔克语)。这一“最高级自由革命”的实质,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或“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⑥正是在“劳动解放”这一“最高级自由革命”的意义上,我们说体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劳动自由”才是《资本论》的灵魂,这一灵魂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也同是在“最高级自由革命”的意义上,劳动才不仅仅是人单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马克思这里,作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说到底,《资本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的证明,更是人的“个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义实现。
马克思“倾其一生”并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写的三大卷《资本论》,决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赚钱作合法性论证,更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上是为了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自由而斗争”。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还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法]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刘成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为自由而斗争,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谛,他的一生都是在迎着“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