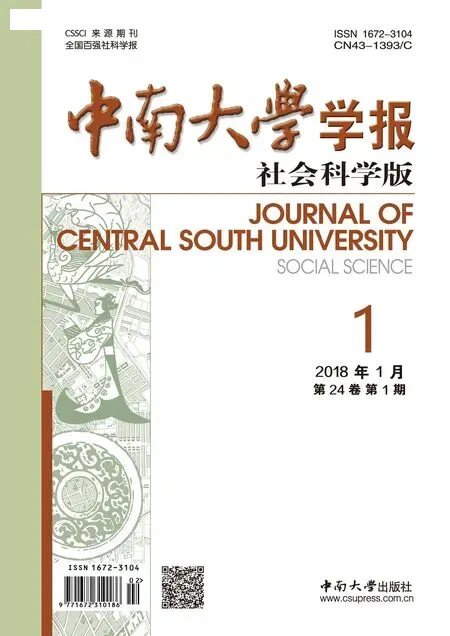论我国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及其政策支持
严惠麒
论我国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及其政策支持
严惠麒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环境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折射出中国深层次的社会排斥危机。引入福利三角解释框架,发现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福利主体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环境弱势群体,使其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应有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之外。在这一过程中,环境弱势群体遭受多维度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排斥,处于劣势地位,并且这种排斥反向作用于社会福利推动者,随着社会“再造”,不断恶性循环。提出实施基于福利三角框架的社会融合政策,有助于从根本上解除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此外,社会排斥话语和福利三元理论的引入,提供了环境弱势群体研究的新范式与理论模型,未来可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开展新的研究。
环境弱势群体;社会政策;路径;社会排斥;福利三角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处于社会深刻转型期,社会分化加剧,快速嬗变的利益分配制度、资源分配格局、社会阶层关系和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紧密交织,一种新型的弱势群体——环境弱势群体产生。简言之,环境弱势群体是指在环境资源利用、生态利益分配、环境污染受害、环境风险承担等方面处于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地位的群体。比较突出的如“污染企业一线工人”“污染企业周边居民”“生态恶化地区的农村居民”等[1],他们的产生并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天赋条件或地缘因素,他们谋求基本生活需求的能力处于弱势地位,受社会结构转型、国家政策与自身条件的限制,面临环境权利保障的各种困境。
现代文明和工业技术的高度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剧烈变化,直接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不同阶层在承担与环境有关的负面效应时往往权责不对等,环境弱势群体需要更多地承担起经济发达地区或其他阶层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成本。随着环境正义和环境公正理念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弱势阶层环境权利的公平公正问题。美国1982年的“环境正义运动”和1991年的“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都是环境弱势群体对抗环境不公平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变迁,中国环境保护制度也得到不断完善,相继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配套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为环境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提供了一个基础性框架,但是目前具体针对环境弱势群体的政策与法规过于简单笼统,有些规定过于分散,甚至有冲突之处,环境公正问题难以解决。
本质上,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上来看,考虑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与现实条件,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是筑牢社会安全网的重中之重。因此,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环境权益的背景下,加强环境弱势群体的保护与补偿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公平尤为重要。回顾文献,国内关于环境弱势群体的研究尚少①,且多以农村地区或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其权利保障困境的社会与制度根源缺乏关照。总之,保障环境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益,推动环境权益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政策的执行,尚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环境弱势群体权益难以保障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其发生逻辑与过程机制如何?如何构建有效的社会政策支持网络化解危机?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引入社会排斥理论,借用西方福利三角分析框架,深入解读现有社会经济体制背景下环境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困境,并谋求社会政策支持路径。
二、社会排斥理论及其适用性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法国,最初被用来表述“大量失业者无法被纳入国家福利保障制度,从而被排除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外的现象”[2]。目前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3]和英国社会排斥部(Social Exclusion Unit,SEU)[4]对社会排斥的定义,其认为社会排斥指的是某些社会成员因贫困、疾病、犯罪或其他重要社会关系断裂或缺失而造成的教育、就业、社会互动等多方面权利与机会被剥夺的现象。
社会排斥理论产生后,其研究领域与适用范围不断扩展。西方社会的大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借用社会排斥概念解释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健康、教育、住房、犯罪、社会参与”等问题[5]。20世纪90年代,社会排斥的内涵扩展到公民政治与社会权利研究领域,根据西班牙学者弗罗莱的观点,社会排斥包括对特定群体经济与政治上的排斥,前者将其排斥在市场关系之外(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后者将其排斥在政治关系之外(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6]。在实务方面,英国及欧盟成员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引入社会排斥概念,重新诠释社会成员的福利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试图通过社会政策重新调整社会资源分配,消除社会排斥,实现公民权利,促进社会融合。此外,社会排斥正被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接纳与吸收。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陆续引入社会排斥理论研究本土社会问题,诠释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社会现象与矛 盾[7−8],在中国情境下,运用社会排斥理论解释环境弱势群体问题,考量如下:
第一,弱势群体是社会排斥研究的普遍关注对象。西方社会已有大量文献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自2000年被首次用于社会保障制度评估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并开展社会排斥研究,研究对象涵盖流动人口、失业人员、城市贫困家庭、失地农民、艾滋病患者和残疾人等众多群体[9−10]。这些群体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变革,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权利缺失,受到各种不平等待遇,广义上,这些群体都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鉴于此,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环境弱势群体问题也可考虑纳入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第二,环境问题研究可以采纳社会排斥分析话语。社会排斥理论最早被用于解释欧洲福利国家因经济危机带来的“新贫困”现象,人们认为这种“新贫困”的出现并非由个人因素导致,而是工业重建和经济快速变迁带来的社会产物[10]。发展到今天,社会排斥理论已从最初的关注贫困问题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994年,欧盟理事会发动的人类尊严与社会排斥项目(The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Project,HDSE)主要探讨五个领域的社会排斥:健康、就业、住房、社会保护与教育,强调这些领域公民权益的公平公正。环境权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同样关涉环境正义与社会公平,不分种族、文化、性别、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他们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的权利。
第三,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有助于揭示环境弱势群体权利困境产生的深层根源。社会排斥话语具有四大基本特征:一是多维度,即将社会看作一个大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四个并行且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二是关系性,即不仅仅关注个体或家庭层面的资源缺失,更关注社会层面的制度与关系排斥;三是动态性,强调社会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不同的状态,且具有累积性和连锁性,在某一层面遭受的排斥往往导致其他层面的排斥,这些排斥又会施以反作用,导致多重排斥与弱势;四是社会排斥过程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往往呈现趋进或远离社会期待的动态反应[11]。这些特征决定社会排斥理论有助于深度剖析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环境弱势群体权益的缺失不仅仅是资源匮乏或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社会权利的缺失,借助社会排斥理论有助于揭示隐藏在表层排斥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特别是环境弱势群体被排斥的过程与机制。
第四,社会排斥理论的引入有助于推动社会政策发展,解决环境弱势群体的被排斥境遇。在实践层面,社会排斥理论一出现就与社会政策紧密结合,是欧盟在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理论。英国及欧盟国家非常注重使用社会排斥概念,英国政府甚至专门成立社会排斥部处理与社会排斥相关的社会问题。在欧盟一体化进程和国家危机背景下,欧盟希望通过改变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12]。随着我国环境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排斥研究可为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三、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产生逻辑与过程
要将社会排斥作为概念工具诠释环境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危机,有必要厘清一个重要问题,即界定社会排斥的施动者与作用对象。在这里,福利三角(Welfare Triangle)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福利三角最早由美国学者罗斯提出,他认为社会总体福利的提供者源自三个部门:国家、市场与家庭,三者构成一个社会的福利整体[13]。此后,一些学者陆续扩展了罗斯的福利三角理论,如将志愿组织或社会团体作为第四个部门加入福利多元组合的分析框架中[14]。具体来说,运用福利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分析环境弱势群体的排斥危机优势如下:首先,狭义的社会福利概念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社会福利的三元或多元福利提供部门同时也是弱势群体环境权益现状的主要施动者,它们的行动或推动环境正义发展,或排斥社会成员享有公平的环境权益。其次,与社会排斥理论一样,福利三角的分析范式强调不同行动者(施动者与作用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过程,强调它们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社会成员公平权益的实现。最后,福利三角能与社会排斥有效结合,促进社会政策的发展。比如,1998年,欧盟组织依据社会排斥理论,发表了13个成员国范围内的人类尊严与社会排斥项目的调查报告,并结合福利三元提供主体,提出解决社会排斥的制度安排[15]。
简言之,本文将借鉴福利三角的分析框架,结合社会排斥的作用机理,探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主体作用下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界定的弱势群体建立在社会政策话语体系下,强调社会公正程度和公民权利的影响,而非简单个体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弱势群体的分布跨越多个社会阶层,他们是位于边缘地带、处于被排斥状态的农村与城市弱势居民,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居民、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城市低收入人员等。
(一) 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
西方流行的社会排斥思想流派将社会排斥归因于制度与体制排斥,认为体制因素影响个体、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的机会和资源,制约改善排斥状态所需的权力与渠道来源[16−17]。弱势群体的产生本身就与国家制度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在我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中,确实存在阻碍环境弱势群体环境权益实现的因素:
一是社会结构的深层排斥。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本质上是社会结构的排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如孙立平认为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断裂的深层次社会结构性场域背景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与权益的分配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距,逐渐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弱势阶层[18]。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弱势群体在整体上处于社会排斥状态,环境方面的排斥则是这种深层结构的表层体现。以农村地区为例,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农业税的征收导致农村地区发展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加上资源、土地等自然要素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大量工业废弃物从城市转移到农村[19],广大农民最终承担了城市生产的外部环境成本,却无法获取生态环境补偿机会。再如,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民工大量进城就业,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既不同于农村居民,也不同于城市居民,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结构”,他们长期从事脏、乱、差的工种,工作环境严重危及自身健康,却无法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环境权益被严重忽视。又如,国企体制改革与结构性调整导致城市失业与下岗人员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同样难以享受环境福利,成为城市不良环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二是社会环境保障制度的缺陷。实现环境权益保障公平公正是涉及国家生态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需要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保障制度。环境弱势群体因各种原因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良好环境权益的享有等方面处于不利处境,尤其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关怀,改善现有不公平的分配机制。然而,我国环境保障制度发展薄弱,在制度设计(环境权益的制度设计与实施)与程序公正(环境事务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权)等方面尚不完善,客观上强化了环境弱势群体的被排斥状态。我国环境权益保障采取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环境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制定、解释、实施与监督。弱势群体在环境政策决策和执行体系中长期处于失语、弱势地位,话语权的缺失让他们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20]。以生态补偿机制为例,弱势群体不对等的环境权益的牺牲理应得到经济补偿,尽管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生态补偿范围有限、标准偏低,且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生态目标不到位”“受害群体补偿不到位”等问题,难以担起重任。
(二) 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在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与机遇的同时,也带来风险与挑战[21],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衡,很容易削弱社会融合、加剧经济排斥,主要有:
一是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本质上就具有社会排斥性质,纯粹依靠市场竞争配置环境资源,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平等加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显著,但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企业作为加害方侵害弱势群体环境权益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它们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环境与生态补偿责任,但是市场逐利性质导致其在追求经济效益与保护环境二者相冲突时往往选择前者。以企业偷排为例,据中华环境联合会不完全统计,至少有80%以上的企业未执行或未严格执行达标排放,进行各种偷排漏排的“小动作”。又如,随着城市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大和城市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大量工业企业向农村转移,也导致环境污染更多地向农村蔓延,让人胆战心惊的“癌症村”形成的重要幕后黑手就是现代工业污染。
二是市场“失灵”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会加剧对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市场力量无法有效率地支配市场要素或无法满足公共利益时往往造成“市场失灵”现象。市场失灵理论强调公共产品、经济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对市场效率的负面影响,认为公共产品的外部效应使完全竞争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带来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弱市场效率。以外部性为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定义,当企业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外部性就出现了,或者说外部性是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额外成本或收益。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与财富的同时应当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然而,良好环境行为的公共属性、外部效应与高额成本往往让企业望而却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加上市场体系发育不充分和市场机制运转不灵、缺乏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与考核体系等问题的存在,尽管企业是环境资源的最大受益者,但其追求经济利润消耗的环境成本与生态破坏等不利后果却更多地压到了环境弱势群体身上。
(三) 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力量
个体条件、家庭和社会组织或团体是保障环境弱势群体权益的重要支持网络,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社会支持力量尤为重要。发展不健全的社会网络制约环境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造成社会排斥,表现为:
一是个体能力不足与社会资本缺乏的制约。进城务工人员、失业人员和农村居民等环境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个人能力不足、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社会资本缺乏等问题,面对制度缺陷与结构失衡难以形成有效的自我保护。当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因普遍缺乏自我保护与环境维权意识,或因为缺乏经济能力与环境知识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与法律保障。此外,环境信息不对称与获取成本高昂也使环境弱势群体很容易被排斥。环境弱势群体自身因为人力资本与社交网络有限本来就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企业作为环境资源的最大获利者与破坏者,最能详细掌握自身生产及排污状况,也最能知道如何采取措施降低污染,但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隐瞒关键信息。地方政府也因地方经济利益与政绩等原因忽略环境弱势群体的利益,对环境污染信息进行截流,为企业提供便利,造成环境信息严重不对称。
二是有限的家庭支持的影响。家庭是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尽管家庭的规模、结构与功能发生一定改变[22],但仍然是个体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力量,甚至,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会导致成员间交往更密切,依存关系与凝聚力更显著,家庭与亲属网络是家庭成员“应对现代风险社会时不可缺少的援助体系和资源传递的渠道”[23]。环境弱势群体大多来自经济贫困、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家庭关系网络较单一,面临环境风险与挑战,家庭支持网络难以排忧解难。比如,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家庭与亲缘关系依然重要,因为原初家庭关系网络具有高同质性和乡土性等特质,面临环境权益受侵害时,很难获得“异地生存”所需要的家庭支持,也难以获取同质性家庭交往圈的支持。
三是支持性社会组织发展滞后。作为社会发展的“安全阀”与“稳定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事业,能够灵活依靠社会自治机制发挥政府或市场机制力所不及的作用,消弥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带来的各种缺陷,比如社会不公正、资金短缺与效率低下等,从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有助于推动环境弱势群体环境权益保障的实现,比如推动社会关注与扶持、沟通政府、企业与环境弱势群体间的关系、宣传国家环保政策和传达民意、促进相对公平等。然而,我国各类环境志愿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发展滞后,往往采取政府推动、“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普遍面临官方性、不透明、效率低等问题。在我国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整体发展滞后的大背景下,遭遇环境权益排斥与社会政策障碍的环境弱势群体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极其有限。
综上可知,三元施动者不仅单独影响环境弱势群体权益的实现,它们之间也存在互动机制,简述如下:一是国家制度缺陷和社会结构失衡加剧贫困差距,影响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反过来,环境弱势群体有限的社会资本与网络也会加剧制度排斥与结构缺陷;二是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经济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不可避免地受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催生国家环境保障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三是市场机制和社会之间同样存在互动关系,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和环境信息排斥导致环境弱势群体私人生活领域及外部环境权益保障发展滞后,作用于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化机制如社会支持网络发展不健全等也会催生环境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进一步分析,环境弱势群体所遭遇的社会排斥是福利三元施动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国家制度及社会结构因素难以提供环境弱势群体亟需的制度、权利与政策支持,造就政治维度的排斥;市场优胜劣汰法则与市场失衡是导致环境弱势群体遭受经济维度排斥的主要致因;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力量缺乏的短板加剧环境弱势群体“边缘化”,形成社会维度的排斥。政治、经济、与社会子系统排斥相互影响,最终通力作用于环境弱势群体,形成社会排斥合力,并且这种排斥通过社会的“再造”循环往复、不断累积和传递,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以初步勾勒出环境弱势群体遭遇社会排斥的结构图(见图1)。

图1 基于福利三角的环境弱势群体社会排斥危机
四、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支持路径
环境弱势群体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他们享有最少的环境权益与资源,却承担最严重的环境后果,他们在环境权利与资源分配中的被排斥地位亟需引起重视。在环境公平与正义理念下,需秉持“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原则[24],换言之,保障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是衡量环境公正乃至社会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都是缩小社会差异、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社会政策的进步伴随着社会排斥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可以说,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二者相辅相成。简言之,社会排斥支持社会政策的制定,并能很好地与社会政策相结合,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社会政策能帮助社会成员摆脱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就中国而言,尽管人们意识到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但社会政策水平仍然非常低下[25]。因此,在我国消弭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可从发展社会支持政策的角度展开思考。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针对社会排斥产生逻辑、运行机制与过程的剖析是解决环境弱势群体被排斥问题的关键,文中嵌入的福利三角分析框架是挖掘社会排斥的多维特性、产生逻辑与运行机制的有力工具。福利三元主体作用于环境弱势群体的过程处处体现社会排斥的三大核心解析要素:分化与整合、参与和参与不足、中心与边缘[14]。盖言之,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下,环境弱势群体一方面心理压力增加、社会焦虑和社会矛盾扩大,导致社会分化加剧;另一方面社会参与不足、环境权益被剥夺,导致社会不公平扩大,最终出现贫困和边缘化程度趋重。据此,环境弱势群体社会支持政策的制定需要重点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说,可在福利三角框架下参考如下措施:
(一) 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寻求更加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
鉴于我国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原因,国家和政府仍占据和支配着主要资源,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在市场和社会尚不能有效发挥治理作用时,保障环境弱势群体权益,实现环境与社会公正需要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面对结构性与制度性的社会排斥,需要从根本的制度角度扭转其不利处境,秉持公平公正原则,保障环境资源公平分配、环保成果公平享有、环境义务平等履行。国家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坚持三大原则:一是程序公正,即在制定、实施与环境公正有关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与其他政策时应遵循基本的规制与流程,保障环境弱势群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26];二是实质公正,即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切实保障环境弱势群体享有实质意义上的公正,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如制定弱势群体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建立弱势群体环境管理机构、保障公众参与制度等;三是执行公正,政府部门在制定合理环境制度的基础上需要充分保障政策的执行到位。
(二) 强化市场调控政策,促进环境权益公平分配
市场发展失衡很容易削弱社会融合,加剧经济与社会排斥,发展与市场调控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消除环境弱势群体被排斥困境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市场体系尚未充分发育,市场机制运转不灵,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企业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损害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逃避或拒绝承担起救济环境弱势群体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发展社会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控势在必行,比如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又如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为弱者的环境权益受损保驾护航等。
(三) 推动社会政策发展,依靠多元社会力量强化环境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面对社会支持网络中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个体失灵”,需要发挥第三部门力量的作用救助环境弱势群体。依据“协同治理”(collaborate governance)理论,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家庭、公民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均可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因此,在环境领域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方面,可由各行动主体在协商与对话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最大程度地保障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如在我国可利用ENGO等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利用其专业性为环境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环境教育、就业指导和组织动员等帮助,增强环境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社会排斥理论能被运用到基本需求、风险规避与可持续生计等研究领域中,但任何一种理论或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都要关照现实。社会排斥和福利三角分析理论的引入,需要考虑到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急剧变革阶段,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等在内的转型内容与目标还远未实现。本文着重分析了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及其产生逻辑、三维主体的关联与过程,不足的是,各类主体在此问题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的权重,尚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着力为此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在后续研究中将更加关注具体案例与量化模型。
注释:
① 笔者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发现,目前仅有十余篇直接以“环境弱势群体”为研究主题的相关论文。
[1] 刘海霞. 环境弱势群体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4(1): 90−93.
[2] Lenoir R. Les exclus: Unfrançaissur dix [M]. Paris: Seuil, 1974.
[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ackground report: Social exclusion—poverty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DB/CD).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3.
[4] Social Exclusion Unit. Social exclusion unit: Purpose, work priorities and working methods[M].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7.
[5] Burchardt T, Le Grand J, Piachaud D. Degrees of exclusion: Developing a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C]// J Hills, J L Grand, D Piachaud.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Mathieson J, Popay J, Enoch E, Escorel S, Hernandez M, Johnston H, Rispel L. Social exclusion meaning, measurement and experience and links to health inequalities. A review of literature[EB/OL]. http://www.who.int/social_determinants/media/ sekn_ meaning_measurement_experience_2008.pdf.pdf.
[7] 曾群, 魏雁滨. 失业与社会排斥: 一个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4(3): 11−20.
[8] 吴新慧. 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状况——“社会排斥”的视角[J]. 社会, 2004(9): 10−12.
[9] 许小玲, 魏荣. 社会排斥与弱势群体: 一个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J]. 前沿, 2012(11): 123−127.
[10] Silver. Reconceptualizing social disadvantage: three paradigms[C]// Rodgers G, Gore C, Figueiredo, J B Social exclusion: rhetoric, reality, responses.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1995.
[11] Silver H.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J].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1994, 133: 531−578.
[12] 彭华民.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一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分析路径[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23−30.
[13] Rose R.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C]// Rose R, Shiratori R.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 Johnson N. 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7.
[15] Duffy, K. Opportunity and risk: Trend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M].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1998.
[16] 盛文沁. 试析欧盟的反社会排斥政策: 缘起, 措施与绩效[J]. 社会科学, 2009(11): 30−40.
[17] Todman L C. Reflections on social exclusion: what is it?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U.S. conceptualizations of disadvantage? and, why Americans might consider integrating it into U.S. social policy discourse[EB/OL].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 download?doi=10.1.1.195.9865&rep=rep1&type=pdf.
[18] 孙立平. 断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9] 洪大用. 当代中国环境公平问题的三种表现[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3): 39−43.
[20] 黄巧玲. 农民的环境弱势地位与制度的伦理关怀[J]. 理论探讨, 2009(1): 101−104.
[21] 彭华民. 福利三角: 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J]. 社会学研究, 2006(4): 157−168.
[22] 王跃生.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2): 60−77.
[23] 马春华, 石金群, 李银河, 等.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 社会学研究, 2011(2): 182−216.
[24]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5] 王思斌. 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6): 83−91.
[26] 黄巧玲. 农民的环境弱势地位与制度的伦理关怀[J]. 理论探讨, 2009(1): 101−104.
A study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vulnerable groups’ socialexclusion crisis and its policy support
YAN Huiq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rights issue of environmental vulnerable groups reflects deep social exclusion crisis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introduces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welfare triangle, and finds that three welfare subjects of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interact to work together, which causes environmental vulnerable groups to be excluded from du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process, the vulnerable groups suffer multidimens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xclusions, and thus are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Moreover, with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such exclusion reversely acts on the three social welfare promoters and creates a vicious circle.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at carrying out social inclusion policy built on welfare triangle framework could help fundamentally relieve environmental vulnerable groups’ social exclusion crisis. The introduction of both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 and welfare triangle theory provides both new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oretical pattern for environmental vulnerable group study, which makes newly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society possible.
environmental vulnerable groups; social policy; path; social exclusion; welfare triangle
[编辑: 谭晓萍]
2017−06−20;
2017−09−26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道德规制视阈下的农业面源污染行为防治研究”(17YBQ11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农户农药法规遵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16M592439);“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资助项目
严惠麒(1986—),女,湖南洞口人,法学博士,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后,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美中经济与法律研究院合作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18
C913.7
A
1672-3104(2018)01−01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