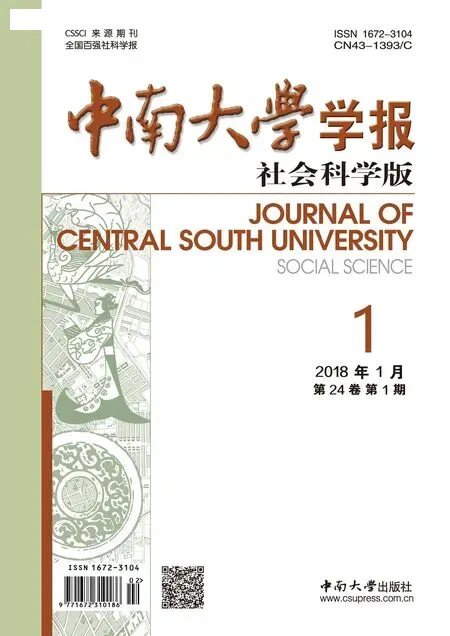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民族生存战略及其评价——新文化观观照下的新文化运动
王攸欣
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民族生存战略及其评价——新文化观观照下的新文化运动
王攸欣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以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观观照新文化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是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的生存战略选择,并不只是新文化激进派的观念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得也有失,是整个民族作为基因群体在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的生存适应能力的表现。正视这样一种适应能力的根源与局限,进行深入的反思,冷静理性地探索一个世纪以后变化更剧烈的文化、历史语境中的民族生存新战略,并提出新战略的基本方向。
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运动;生存战略
一、近年新文化运动研究述论
作为20世纪中国颇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新文化运动一直是学界的聚焦点之一。“五四”运动又往往被看作是这一文化运动的高潮,每逢周年尤其是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关研究成果与纪念文章甚多。在中国知网检索,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的文章已经有18 000多篇,无人能一一过目①。笔者选择性地浏览相关文章,发现有些只是较为陈腐的观念表达,有些则是力图脱离却无法摆脱陈旧观念牵绊的模式化阐释,甚至亦不乏追逐风潮之作。当然,也有不少成果,称得上深入探讨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渊源、历史语境和人性根基,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历史及历史阐释的复杂性。这些成果关涉文学、哲学、历史、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学科。因文献量太大,而且已有综述性的专题文章,本文不拟全面评述前人成果,仅就近些年有特色的文献,略加述论。再在新的文化视域中,针对学界普遍存在疑问而又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新思考,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和历史,作为新的民族生存战略的思想资源。
根据“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学术会议纪要整理成稿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圆桌论坛)》②,显示了多学科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反思,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各个面向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历史评价问题。如杨联芬注意到不能把现实状态尤其负面问题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后果。杜维明也指出“历史运动是社会合力的产物”③。根据《百年回看<新青年>,重思新文化——第九届中国文化论坛会议综述》一文来看④,具有代表性的各派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重要论题如《新青年》的时代,新文化运动中各派对孔子、家庭、人民的观念及其后果,《新青年》与文学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些重大的话题,如朱苏力、王绍光与甘阳、张祥龙等讨论的究竟是思想运动影响社会还是社会决定思想的问题,陈来主持讨论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伦理的冲击问题,干春松和朱苏力关于中西社会结构差异的讨论,都触及了本文将要论述的核心论题。
从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效果而言,不同学者的判断差异很大。邓晓芒在《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中认为新文化运动(该文称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根基和生活方式基础,启蒙者的观念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缺乏切实的联系,因此失败了,于是提倡第三次启蒙[1]。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尚有可议。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实际的权力运作、政治斗争,民智民德、风俗习尚等等远超过这场文化运动。但从文化层面上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不失为一种研究方式。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下卷第二部及其独立论文《科学话语共同体与新文化运动的形成》[3]中都探讨了科学话语共同体的问题,研究了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与话语方式对新文化运动产生影响力的历史过程。从一个特定角度探讨了文化事件与历史进程的中介因素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具有历史整体感和专业性,对文化研究有启示意义。陈平原的长篇论文《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4−5],从各个维度出发,深入历史、文化语境以及《新青年》作为同人杂志的特点、策略与过程,探讨了新文化运动产生巨大文化影响力的文学和个人因素。同时也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大语境中探讨了《新青年》形成特定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因缘,是出色之作,值得特别提出。
对于新文化运动内涵的复杂性及其价值取向,论述者不少。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全面反传统的文化思潮,有人认为是彻底批判儒家文化的思潮;也有人认为并未全面反传统,且并非彻底反儒家思想。孔范今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晚清启蒙运动的深化,对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式的批判否定,是出于策略性的选择,正是这样一种选择,开拓出新的文化空间,不宜轻易否定[6]。贾小叶综述了199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辩证、清晰地梳理了各种不同倾向的观点,并予以理性评价[7]。欧阳军喜则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只着眼于礼教制度风俗的层面,并没有否定儒家心性论和精神传统,所以新文化运动只是改造、重建儒家传统[8]。
多数学者仍坚持认为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的民主、科学、个性、人权、自由等观念来批判中国传统,尤其是批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秦晖则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确实是儒家思想,但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误解和现实选择的偏失。因为构成对个性、自由、民主压抑的,实质上并非儒家思想——这只是传统文化的表层因素——而是法家观念和体制,这才是文化的内核。并批评影响甚大的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说”和“告别革命”说[9]⑤。郑大华等学者试图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新文化运动,把《学衡》派也看作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那么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概括将发生基本的变化,也就是把新文化运动看作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运动。一方面触及了新文化运动的关键,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以往新文化运动概念所包含的价值取向[10]⑥。刘禾等移民美国的学者则出于自身的生存境遇和民族的历史语境,以198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新文化运动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存在天然的局限。在国内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颇有一批赞赏者,也引起一些自由主义或新文化运动精神坚守者的批评[11]。当然,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本文无法一一述评。从这些成果所体现的研究者以自己的生存“前结构”对于历史的理解和阐述中,可以从某种意义上体会到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真正意涵。历史的阐释史也可以说是“效果历史”[12]。
在笔者目及的多数研究成果中,还是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缺失,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新文化运动那一代知识者普遍自觉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在进化论的哲学框架中,看待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中华民族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机会问题;更缺乏在对世界、人性、历史和文化的整体领悟中,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一“三千余年之一大变局”中的实质性突变——这种突变既是历史语境的,又是生存方式的——由此也必然带来作为功能性体系的中国文化的相应调适甚至剧变。我们应该以整体的、过程的、辩证的眼光去进行研究和评价。本文试图以笔者近些年来提出的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观,观照新文化运动,把握住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并对其历史后效作出评估。
二、基因同异创化论大要
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观的要旨是:人类是基因的承载者,每一个体延续扩展自身基因是生命的本能。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作为物种发展出高度的生存适应能力(其中大脑智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够创造出复杂有效的群体适应方式。生存在一个特定地理范围的群体,具有共同的基因库和相近的自然环境,创化出文化来实现这种基因延续的本能。文化可以说就是以基因延续资源分配为中心的功能性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政治体制、风俗习尚等。基因同异创化论认为,任何文化的整体形态及其具体显现方式的形成,都是根源于不同层级基因主体的基因组共同性总是有着各种程度、维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主体在基因延续、扩展的机会利益上,共同性程度不同。每一基因承载的个体,既可在个体的立场上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思考、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可站在包括自己在内的基因主体如家庭、家族、民族、人类的立场上,处理与其他人、其他家庭、民族的关系,因此形成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或人类普适性的观念。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中也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立场。不同个体在不同情境的交往中,也肯定会有不一致的选择。这样,不同层级的基因主体在长期的竞争与协调过程中,必然创化出包容着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社会体制、风俗习尚的文化整体。基因同异创化论的“同异”,特指不同主体之间的基因组共同性与差异性。“创化”一词指不同层级的基因主体在竞争与协作中创造性地发展演化出特定的同时也是丰富多样的个体与群体的生存样式。所谓不同层级基因主体的基因共同性和差异性,从生物学基因研究的专业角度来看,又是什么含义呢?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这个基因组由23对染色体组成,包括约 2万~3万个基因,30亿个碱基对。人类基因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人类个体的基因组差异,主要由基因复制变异(copynumber variation)即DNA分子片段的复制、插入或删除、复杂多位置变异造成,占比平均高达人类基因组的10%,也就是说基因组共同性仅约90%。一般说来,在遗传上越亲近的个体,基因组共同性越大,基因主体的基因利益共同性也越大。个体作为基因主体,是所有基因主体中实体性最强的,因此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传播自身基因的动力。血亲家庭是基因组共同性很大的基因主体,因此,家庭成员的基因利益共同性也是很大的。还有家族、亲族、民族、种族、人类等主体。村落、单位、国家等主体则是基因主体泛化的结果。基于基因主体生理形态的差异,不同层级的主体会在自然适应和文化生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在特定主体立场上建立起来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因为不同基因主体既有利益的共同性也有利益的分歧,所以在行为方式中,既会有协作的一面,也会有冲突的一面。以具体例证来说,个人主体更倾向于传播自身基因,民族主体则主要不会致力于特定个体基因的传播,肯定需要建立起有利于这个民族内部优异基因的延续扩展规则——因为一个特定民族总会与其他民族处于资源和生存竞争中。当然,这种带有选择性的规则创建是否成功,取决于各种复杂的自然、历史因素[13]——所以,这两种主体间就既有并不完全一致的目标,又肯定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因为任何个体基因的延续扩展,都是民族基因的选择留存。而且较低层级的基因主体如个体要实现其自身的目标,也绝对需要依赖于较高层级的基因主体如家庭、家族、亲族、民族、人类的协作,获得基因延续的生殖资源和生存资源。目标的不一致性决定着,如果某些特定个体过于偏执于自身的基因利益而不顾及群体利益,有可能恰恰会成为被淘汰的基因主体,降低基因延续的机会。但要真正完全超越个体基因利益,又是非常难的。这就有不同层级的主体如何真实、准确地理解、认识自身和环境关系的问题,包括对其他主体的准确认识。认识能力的低下或者认识结果不符合实际状态,都可能带来不能很好地适应世界的后果。适应是任何基因主体的根本需求,没有适应,特定主体的基因延续机会就会降低甚至消亡。文化正是在这种根本的需求上创化出来的。文化在宗族、民族、人类立场上所创化成型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总是对个体基于自身本能和其他利益形成的价值倾向产生约束、限制作用,对个体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实行激励、奖赏。这就使得某些个体超越纯粹本能的限制,表现出利他倾向。由此也可以获得更好的个体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也包括基因延续机会的利益——这种基因利益既包括个体自身基因的延续、扩展,也包括近似基因即家族、亲族基因的延续、扩展。因此,尽管在地球上各个相对独立的地域产生的文化会有各种差别,但一种成熟的文化肯定会存在繁复、微妙、辩证的特征,涵容各种看上去矛盾的价值取向和存在方式,才可能存在下来。而不够成熟或成功的文化涵容性较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或许早已被淘汰。当然,即使是涵容性本身,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涵容性的程度不是衡量一种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根本标准,只有文化覆盖的基因群体的生存适应性才是衡量文化价值最根本的标准⑦。这种新的文化理论不同于此前已有的各种文化理论,如文化演化论、历史特殊论、文化传播论、以个体或社会结构为核心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生态学等,这种新的文化理论,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新的社会生物学文化论⑧。
三、以基因同异创化论观照中国文化
在基因同异创化论的观照下,整个中国文化、历史,自然包括近代史与近代文化史,将呈现一种新的面貌。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种基因图谱已有较为清晰的结论。但基因图谱与具体文化因素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特征不可能还原为基因表达,暂时还很难去进行对应性研究,更不可能描述。本文运用基因同异创化论观照文化,只是提出观照框架,显示文化总体创构的根源和过程特征,着力点还是在文化状态本身。据现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发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考古发现的辽西查海遗址带有礼器性质的玉器距今已8 000多年。但在商周以前,并没有大体一致的文化形态,而是由各个地域文明构成了“满天星斗”[14]⑨。商周两代,尤其殷周之际,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周公姬旦历来被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尊为宗法礼制的创构成型者。在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里,中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创造者,孔子、孟子集大成的儒家文化和老子、庄子继承创新的道家文化成为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发生重大影响的具有互补性的两大文化支脉。儒家文化所着力建构的是以仁、礼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规范和制度,辅以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价值教化,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宗族传承为目标。在汉以后成为中央集权制宗法农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三纲五常成为简明扼要的伦理纲领,通过教化与选举体制进行了有效的推广⑩。唐宋以后,吸取佛教、道家心性论、境界论以及践行方法,形成宋明理学与心学。从儒家经典中凸显《四书》,在科举制度化的运作中,得到了较为切实的传播,却不可能彻底改变人的自然本性,因此造成了假道学人格普遍存在的状态,甚至在人性压抑中更彰显了人性之恶。道家文化构建了以超功利性的返朴归真和个体自由为核心的价值准则,缓解在基因延续机会和生存资源竞争中的人际关系,也舒缓了个体的竞争焦虑,对历代士大夫阶层甚至普通百姓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标杆。以儒道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着眼于在有限的自然生存资源条件下,压抑、消解个体的本能和欲望,来实现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儒家有较强的等级观念,道家则等级观念不太强。中国文化缓解了竞争的剧烈性,却忽视以至贬低从对自然的认识和开掘中去增强人的获取生存资源和扩展基因延续资源的能力,因为那样可能导致欲望膨胀,难以平衡稳定。这种文化的基本理路和取向,从中国历史的不同维度、焦点来看,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成功的一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往往相互纠缠,相生相克。成功的是对于个体本能的文化压抑总体来说是相当有效的,降低了由生存竞争而大规模杀戮的几率⑪——这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根本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种族繁衍的目标。在蒙古人种的基础生理条件上,自然环境和文化赋予中华民族较强的适应能力,勤苦、耐劳、忍辱,敏感、内敛、克己,既有着自强不息的规训,又有着超越性的反思。在中国文化熏陶下的相当多的个体是较为克己去欲、安贫乐道的,但与此相伴随的多是独立、强健人格的相对萎缩。当然,每个时代也都有践行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人格的“大丈夫”[15]。鲁迅所谓“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的“中国的脊梁”也史不绝书[16]。这类“大丈夫”和“中国的脊梁”,在中国的正史上,绝对数量确实不少⑫,但在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都是非常低的。所以这既是中国文化教化的成就,又是其缺失,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着力于在自然资源较为匮乏、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生活方式、生产资源动力不足的处境中构建稳定的宗法秩序,选择了对个体人格与欲望进行压抑的基本策略。这种策略缓解了残酷的争竞,却导致了独立人格和个体权利的缺失,群己权界不够清晰,向自然界探索获取资源的意愿与能力弱化,生存忧患意识浓郁,幸福感较为缺乏;也导致了对于没有经受适当文化教化因而欲望强烈的野蛮群体和个体的制约乏力,权力掌控者享受了过多的资源,尤其是皇权对生殖资源和生活资源的占有程度惊人。因此,中国历史朝代频替,治乱相寻,清明公正的时代甚为罕见。对于任何民族的历史,如果仅以理想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准则——不论是中国文化理想还是西方价值准则——进行观照,都总是存在各种缺陷的。以今天的全球视野来看,如果说文化较大地影响了所覆盖民族的生存状态,那么相对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生存能力与生存状态而言,中国文化并不是最优秀的文化,也不是最鄙陋的文化⑬。19世纪以前,在没有和欧洲民族形成直接的大规模的生存资源竞争时,中华民族处于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就维持基因延续机会与繁衍族群人口数量这一文化根本的目标来说,中国文化是较为成功的。因为创造中国文化的祖先们的基因,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而高度同一且有效地延续和扩展着⑭。在新的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恰恰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原来没有的新因素,如现代性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结构、西方医学和人道主义观念,使中华民族能够在19—20世纪这短短的200余年中大规模繁衍,由18世纪末的2亿人口扩展到21世纪初的将近14亿人口。这些西方因素,正是因为洋务、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
四、以基因同异创化论观照新文化运动
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处境发生了“三千余年之一大变局”⑮。严复因留学英国而对世界大局有所了解,此后长期浸润于英国文化和学术,形成了清明、沉稳的理性精神,同时又接受了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原理。严复在甲午战败后写下了《论世变之亟》(1895)一文疾呼:如果不改变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不改变官员士大夫苟利自私之品性,学习西方文化,提倡自由平等、创新开源,“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则“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⑯。这样一种亡国灭种的表述,既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士大夫普遍的生存危机意识深化的表现,又是此后维新、革命观念日渐激化的推动力之一。反观20世纪的世界史,主导这个时代的西方文化和各列强达到了并不以此为目标的文明程度,“灭种”之说或为夸大之辞,“亡国”却是清王朝的结局。但“国”并不是西方列强“亡”的——这个“国”仅指政权,非指人民。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最重要的变化在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时期——竞争范围全球化。部分竞争对手掌控生产资源的能力、社会调节的能力以及战争能力都远在本民族之上——这成了影响中华民族文化战略、生存状态调整的关键性因素。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都有非常自觉的意识,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有清晰的表达⑰。但文化作为基因群体的生存方式,并不只是认识观念的变化就能很快作出全面、适当的调整的。历史积淀的时代越久,某些在长期的自然、人文环境适应中形成的文化深层因素如价值观念、人格形态、风俗习惯就越难以改变。这些因素不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适应的较大合理性,即使到了语境剧变的现代,也仍然有其存在的部分合理性。有些甚至是人类文化的普适性因素,如同情弱者的价值倾向。只是其普适性和其他文化相比,具体表现方式、程度有差异;在中国社会中与此相反的势利却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即使“势利”也有某种生存选择的理由,却并不符合文化创构的价值理想。但生存的焦虑和直接的竞争压力会对这些已经形成的理想性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构成冲击以至碾轧,剧变中的社会状态会使多数人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价值观念的混乱和行为方式的失范。即使是时代的启蒙者,也可能因为这种民族生存的急迫感而忽略了普适性的价值、伦理原则。如梁启超在接受进化论的基础上,为激励民族意识,不少论述中就带有了“强权主义”的色彩。虽然他晚年有所调整回归,但因其文章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伦理传统有极大的冲击⑱。
在20世纪的前20年,对欧美与日本民族和社会有所了解的中国学者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中华民族落后的症结,找到了可以效仿的生存模式,可以通过文化革新迅速调整整个民族的竞争能力和生存状态。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新取向的一次突出而集中的表达。就这种文化应对战略而言,新文化运动既是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境遇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积累了较为有效的有关西方文化的经验。只是这种经验仍然是相当有限、不够深入的。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一些基本观念,如个性解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平等、国民性改造等等,在晚清时期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孙中山、鲁迅等人的著述中,早已有较充分的表达。有些表述甚至在激烈性、深刻性上并不亚于新文化运动者。如谭嗣同深受宗法伦理之苦难,极愤三纲五常之网罗,舍身变法,大义凛然,但其改革方略并不成熟,颇多幻想,思想驳杂,一意激进。章太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真正深入的领悟,秉承了其中不少优秀的质素,站在民族立场上,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辩护,虽然并不能达致逻辑自洽,却表现了作为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和价值[17]。王国维以自己的孤独、忧郁体验和刻苦学习,深入到西方文化的精神和哲学思维层面,对叔本华、尼采哲学有深刻的理解,代表着最早正视人性中非理性因素之根本地位的先觉者。同时王国维又在《红楼梦评论》(1904)等文中反思、批判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取向[18],强调直面现实和再现理念之真[19]。鲁迅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个体、人性被压抑的特殊体验,对西方文化中的个性主义和天才蔑视凡庸的新“神思宗”(唯心论)思潮情有独钟,认为激发起国人的独立人格和个性主义精神才是“角逐列国”,并存于世的根本。王国维、鲁迅两人当时都只被极少数人关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新文化运动不同于晚清的思想运动呢?或者说这两场思想运动究竟有没有质的区别?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思考和回答。或许站在各自立场上,焦点、维度不同,都有各自的理由。笔者以新的文化观进行观照,尝试对新文化运动作出新的历史和文化史定位。
首先,新的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实质上是民族作为基因群体的生存方式和策略的整体性调整。民国创立,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不同于晚清思想运动的历史、文化语境。戊戌维新运动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实行维新改制,被慈禧、荣禄等人镇压。辛丑以后,慈禧主导的政权被迫恢复了戊戌变法的部分新政,但维新派和革命派主将们都在政治上处于被压制、通缉的状态,这些人物宣扬新观念多半都在海外。尽管梁启超、章太炎的文章在国内也曾风靡一时,甚至触及权力高层,但影响范围毕竟是较为有限的。慈禧、光绪去世后的清末宪政运动,激化了各种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引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颁布了临时约法,从政治体制上确定了民主共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基本的人权包括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晚清思想运动的主张。但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鉴于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社会大乱而倡导的孔教运动,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构成了对民国临时约法基本价值取向的反动。所以陈独秀异军突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更名《新青年》,实际上是以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宣扬中华民国建国的文化理念,其形势就远非清末思想运动可比。而且不久后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与胡适、蔡元培等人一起,借助国家最高学府也即文化权威机构的权力话语,使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声势浩大。以往的新文化运动研究似乎很少注意到这一特点,有意无意地误以为新文化运动是民国体制的对抗者。
其次,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进一步推广,又借助了“五四运动”——这是一场以反对签署“巴黎和约”为核心的政治运动。这场学生运动与当时的北洋政府,从国家利益诉求上说,也并非对立。政府要员、巴黎和谈代表有意透露相关绝密信息,激起国内学生、民众运动[20]。因为在思想界有孔教运动的背景,所以新文化运动相对于晚清思想运动来说,对于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及历代统治者作为意识形态的后效,进行了更为系统、严厉的批判,构成一个新的特点。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是西洋文明输入后,促成吾人最后之觉悟的运动,也就是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而“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 悟”[21]。胡适提出了以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准则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重新估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价值,涉及到根本的价值准则问题⑲。胡适以其美国留学的亲身体验,试图推广美国的民主政治与生活方式。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比清末更为推崇,介绍更为系统深入⑳。关键的是,在运动过程中确立了新的西式话语系统的权力话语地位,而且这种权力话语体系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这个体系里包括西方的各种学术理论和伦理观念,如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唯理论、进化论、唯意志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运动后期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年代以后仍然具有崇高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并不能说建立了权力话语,就能够把这种复杂话语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准则在社会实践和国民性改造中成功实施。不过,正是这种话语体系,凸显、巩固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史地位,使之成为一个不断被阐释、推崇的文化事件,俨然成为划时代的界标。如果以超越这个已经被窄化的话语体系的眼光来看西学东渐的过程,新文化运动也可能被看作次一级的时代界碑,或许年开始的思想运动才是更重要的文化史路标。本文并不拟纠缠于对这两场基本方向一致的思想运动的重要性作出详细比较,而是着力以新文化理论观照这场延续多年的可以合二为一的文化运动,视之为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界史语境中的生存文化战略,并审视其结果,作出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评价。
文化和历史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史来看,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难以想象的复杂性至少在描述、评价时表现出各种简单化、偏执性的缺失。首先是作为理想性的文化观念和作为某个群体生存方式的文化状态之间的联系与区分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观念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问题未得到细致辨析。这既关涉怎样评估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状态的关系,也涉及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历史状态的关系。其次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语境的巨变和作为民族生存方式的文化的延续性与变异性之间的微妙关系未能得到足够的注意,城市乡村的生存方式的相互渗透和冲突未得到充分关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于历史或现实的决定性因素缺乏适当的整体领悟和分析,也缺乏以过程性的眼光对民族的生存基础与现实选择作出辩证的审视。如果要对这些方面都作出论述,非一篇论文可以实现,此处只能简要论之。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格局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身处危机中的中国不同倾向的文化论者都以个人的特定文化教养、利益立场、智力水准、视域范围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关系。对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及形成此状态的原因,文化所起到的作用等,往往缺乏深刻透彻的理解。文化激进派或局限于目前情势,或仅着意于中西比较,认为中国文化陈腐不堪,黑暗吃人,无视文化、历史中有利于民族延续扩展的因素;文化保守派或视域封闭,或由于民族自尊心之需要,认为中国文化优异绝伦,举世无双,对历史的残酷、阴暗视若无睹,以文化典籍中表达的理想性观念代替对于历史本身的体察。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1915年及随后几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缓解陈独秀们的民族危机感,反而因两次帝制复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加深了。所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宣言《敬告青年》中就首先提出:中国社会如果青年不能奋其智能,更新思想,“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从而陈“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义”供青年“抉择”[22]。他的《我之爱国主义》(1916)更出惊世危言:“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 也”[23]。这也是当时陈独秀们真实而普遍的生存感受,这种感受可能导致接受、运用西方思想的激进性,会形成并不一定适度的观念和方式,是应予以体谅的。其实,整个人类历史,既是一部吃人而存人的历史,也是文化缓解吃人残酷性、增加基因留存机会的历史,不同民族的历史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中国历史既是相当残酷又不是最残酷的历史,中国文化也不是最成功或最失败的文化。关键在于经过历史和文化选择留存的基因承载者的适应能力如何。
似乎从来没有人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选举制度及其适应性的表现,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主体适应能力的表现。新文化先驱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凸显,其实是具有特定生理基因和文化传统的基因群体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调适的结果。保守派们的凸显也同样如此,他们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激进派。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优良因素,也始终在起着作用。在中国这一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相对有限的区域中,繁衍生息着13亿多人口,是一个可观的文化成就。这种成就实际上借助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医学和社会体制的引进,使人口得到爆发性增长。但中国文化的选择机制,相对而言,扩展了较为优秀却并非足够优异的基因留存。人性中恶的因素,也没有得到融合了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适当的控制、调适,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同样是难以直面的。不管我们对今天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未来走向如何评价,作为基因承载者的民族主体,才是历史责任的真正承担者,而不是从整体中抽取出来的所谓激进派或保守派,更不是任何其他派。而且这一点无法改变。相互对立、攻击、消耗、调协、整合也同样显示出民族主体的适应能力。这只有站在基因同异创化论新文化观的超越性的历史高点上,才能真正透彻认识。而在当今时代,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语境,使人类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共同基因库。如何充分利用各个次级基因主体即各个族群、种群的适应智慧,调协各种文化生存方式的关系,是中华民族生存战略的新课题。这样的时代,不应过于强调民族的相对封闭、独立的群体生存方式,也不应有过于焦虑的生存心态,躁动不安。尤其是对于整个群体而言,应该建立起充分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其实,在现代化的生产效率下,如果不激化社会矛盾,作为族群,不可能失去基本的生存利益,尽管仍然有着自己族群特殊的基因利益。如果中华民族以较健康、开放的文化生存方式与世界各个族群交流,有可能更充分地获得延续、扩展民族基因的利益。这是极少人能够意识到而实质又是根本的利益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毫无疑问会损害这种根本利益。
注释:
① 仅以“新文化运动”为检索词的主题统计,不包括以“五四运动”为检索词的统计。涉及此主题的研究著作暂无法较全面统计,或不下数百种。
② 该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07期,会议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讨论由陈卫平主持,秦晖、杜维明引言,邓晓芒、何怀宏、任剑涛、萧功秦、汪荣祖、谢遐龄、张宝明、徐贲、寇志明、罗多弼、杨联芬、许明等有讨论发言(排列按发言顺序)。
③ 笔者在1999年武汉大学召开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曾提出类似的观点,当时获得与会学者认可,但后来学界关注似不多。请参见笔者《中国文化文学专题十三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第十讲《从闻一多文化观看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或陆耀东等主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所收拙作《闻一多文化观点略论》。
④ 此次会议参与者有董秀玉、李学军、杨国荣、童世俊、杨国强、陈卫平、甘阳、张祥龙、王绍光、朱苏力、杨立华、干春松、唐文明、丁耘、陈来、吴飞、陈赟、罗岗、张旭东、吕新雨等40余人(排列按综述行文顺序)。
⑤ 袁伟时等人不同意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批评不当的说法。
⑥ 郑大华主持《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走向——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笔谈,对新文化运动有集中讨论。
⑦ 基因同异创化论在笔者近年的著述中有所阐述,其中最集中的是《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4期)、《再论新文化观及<红楼梦>根要》(《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两文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基因同异创化论的新文化观。另在《新文化观观照下的中国婚姻生育制度与风俗之变迁》(《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有具体的运用。
⑧ 各种文化理论可参看卡罗尔·恩伯与梅尔文·恩伯所著的《文化人类学》,中译本为《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 作者把中华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包括丰富的史前文化形态。这些地域文明中甚至可能包括域外传播过来的文明,如成都三星堆文化。
⑩ 秦朝创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实行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对儒、道文化有所压抑,但国家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尤其是文字统一,为后来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播,有所贡献。尽管汉朝政治制度也如汉宣帝所言“本以王霸道杂之”,即儒法互补而成,或所谓“儒表法里”,某种程度上又疏离了先秦原始儒家的价值取向。
⑪ 文化要完全消解资源竞争带来的杀戮,从已有的人类历史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杀戮也并不少。这不只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生物包括人的自然本性中有着生存资源竞争尤其是性竞争倾向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在压抑个体本能的有效性上有程度的不同,但评价一种文化是否优秀,不仅在于压抑个体本能的有效性,还有着更复杂的标准,根本在于生存适应性。
⑫ 这类人物之多也和中国地域广阔、历史绵长、人口众多、史籍丰富有关,正史中往往着意表彰。
⑬ 近代以来的中国保守主义者,往往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论证其优异性来获得民族自信心。激进主义者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加快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其实都是不够客观理性的。还有人做折衷之论,认为文化无高下之分,也是无视不同文化在根本功能上的差别。
⑭ 现存的其他民族的基因延续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惟同一性有程度之异,中华民族的基因同一性肯定不是最高的。但基因选择规则近代以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民族来说,有得有失。
⑮ 晚清同光重臣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他洋务派、维新派大都有类似的变局观,如徐继畲、冯桂芬、王韬、郭嵩焘、张之洞、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请参看吴福环《洋务论者的“变局”观》(《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孙邦华《西潮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观”》(王中江主编《中国观念史》,中州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⑯ 严复《论世变之亟》,原载《直报》,1895年2月4—5日。引自《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6页。
⑰ 本文这种提法似乎近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略有不同。笔者认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的概括比其学生柯文等人提出的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中的中国中心论更合理。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概括并不能看作忽略了中国的主体地位。笔者此文不仅认为中国近代接受了西方的冲击,而且认为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为中国这个主体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生存、历史语境。中国史学界对柯文观念的认同更多地源于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体意识和自信需求,恰恰显示了不够自信的生存状态。
⑱ 如其《自由书·论强权》,《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关于梁启超当时的强权主义色彩的论述,请参看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梁启超未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术思想和坚定立场,每以观念宣扬者自居,多引入、介绍各种思潮,在维新、革命,立宪、共和之间游移,但因其倾心民族自救,能克制私欲,顺势而为,在文化运动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虽然他不赞成新文化运动观念,甚至有所批评,但实质上却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背景。
⑲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⑳ 但新文化派主导倾向还是推崇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而学衡派更推崇希腊古典主义、人文主义。
[1] 邓晓芒. 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J]. 粤海风, 2013(4):3-6.
[2]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 北京: 三联书店,2004.
[3] 汪晖. 科学话语共同体与新文化运动的形成[J]. 学术月刊, 2005(7):104-113.
[4] 陈平原.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3): 1−31.
[5] 陈平原.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下)[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1): 116−155.
[6] 孔范今. 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5(6):1-9.
[7] 贾小叶. 激进主义思潮研究述要[J]. 中国文化研究, 2015(4): 89−101.
[8] 欧阳军喜.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J]. 历史研究, 1999(3): 42−56.
[9] 秦晖. 新文化运动的主调及所谓被压倒问题——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J]. 2015(9): 72−81.
[10] 郑大华.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J]. 广州大学学报, 2005(1): 10−15.
[11] 刘禾. 跨语际实践[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12] 贝奈戴托·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历史与编年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
[13] 王攸欣. 中国文化文学专题十三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
[14]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15]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141.
[16] 鲁迅.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C]//鲁迅全集: 第六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18.
[17] 王攸欣. 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论要[J]. 浙江学刊, 2014(4): 68−78.
[18] 王攸欣. 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为纪念《红楼梦评论》发表110周年作[J]. 曹雪芹研究, 2014(4): 6−23.
[19] 王攸欣. 论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传统意境论[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9(1): 128−132.
[20] 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1994.
[21] 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J]. 青年杂志, 1915, 1(6): 1−4.
[22]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青年杂志, 1915, 1(1): 1−7.
[23] 陈独秀. 我之爱国主义[J]. 新青年, 19162(2): 1−6.
Strategy for national survival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ts evaluatio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light of the new cultural concept
WANG Youx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present essay, by taking the new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gene-identical-discrepant Evolutionism to observ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holds that the movement is the Chinese nation’s choice of the survival strategy under the conjoint power of var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concept movement of the new culture radicals. The movement is both gainful and losing.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adaptability and existence of the whole nation as a genetic group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We must face up to the roots and limitations of such an adaptability, carry on deep reflection and make sober and rational explorations of the new strategy for national survival at a time of drastic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 century after this movement.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new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briefly in the essay.
the gene-identical-discrepant Evolutionism;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urvival strategy
[编辑: 胡兴华]
2017−04−25;
2017−11−08
王攸欣(1966—),男,湖南湘乡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哲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21
G122
A
1672-3104(2018)01−015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