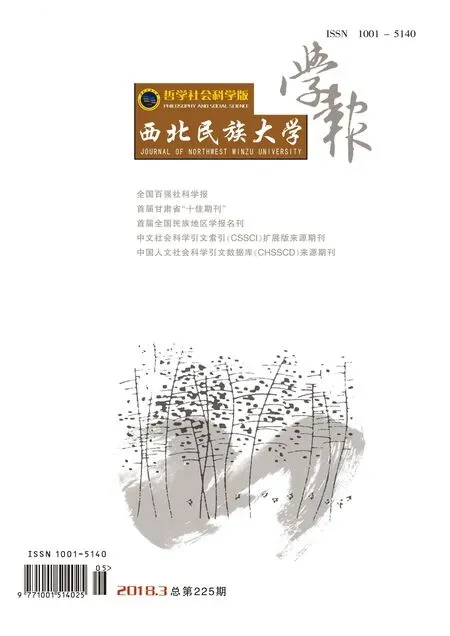明代归附人研究述评
王竞成,周 松
(1.甘肃省考试院,甘肃 兰州 730030;2.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明代是帝制时代晚期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王朝。明朝统治时期,有大量非汉人群体进入内地,居住生活,成为明朝的臣民,是为“归附人”。明代史料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归附人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内迁之后,在身份定位、经济生活、社会关系、心理认同各个方面呈现出与内地居民同质化的演变,逐步融入明代内地社会。
明朝覆亡以后,在学术领域已经有人提到了明代归附人的相关史实,如顾炎武《日知录》的《徙戎》《胡服》篇,但是总体而言仍然较为零散,更无系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明代归附人历史淡出了历史记忆。
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研究西域色目人元朝进入内地后的汉化问题。该书功力深厚,方法新颖,问题集中,研究深入,使中国传统考据学登上了新的顶峰,实现了中国史研究与国际汉学界的接轨,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当然也影响了以后的史学家遵循陈先生开创的研究道路和指出的方向,向下延伸至明代乃至以后外族入居内地,自身汉化的研究。他的问题设置和研究路径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近90年以来,明代归附人问题受到中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形成了许多重要成果: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张鸿翔先生最早将明代归附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故宫档案,进行研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20世纪50—70年代的30年中,明代归附人研究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均归于沉寂,张鸿翔早年的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遂使这一问题退出了大陆民族史、明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海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却仍在持续进行,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取得重要成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司律思先生(Henry Serruys,CICM,Ssu Lü-ssu,1911—1983),他对明代内附少数民族,主要是内附蒙古人问题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明代归附人研究在大陆学界的边缘化处境才获得改善,进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代表性的学者有奇文瑛、彭勇、高寿仙等人。西方汉学界在司律思谢世后,21世纪又有鲁大维(David M.Robinson)等学者继续耕耘在该领域,不绝如缕。此外在一些通史性质的民族史专著中如莫俊卿、杨绍猷《明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中都涉及明代归附人,但是限于写作主旨和篇幅的影响,不可能进行具体叙述。明代归附人专题研究仍以论文为主,专著很少。
一、早期研究(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新史料发掘与考证
明代归附人问题的早期研究成果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张鸿翔的系列研究成果和20世纪50—60年代司律思的论著。
张鸿翔在继承了传统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利用故宫未刊明代档案,整理出大部分明代少数民族世袭武职的基础史料。其《明外族赐姓考》以“赐姓”为切入点,统计了106名获得明廷封赐汉姓的民族人士,探讨了赐姓原因、赐姓数量的时代变动等一系列问题,是研究明代内附民族的首篇专题论文[1]。《明外族赐姓续考》系《明外族赐姓考》的续作。作者增补了更多内附民族活动内容,以《续考》来辨析同名外族的现象,涉及398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范围。该文详细讨论了与赐姓相关的族别、时代、时代差异等环节,并关注了授职等级高低和各地安插分布情况[2]。显然两篇论文的研究思路除了受到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启发之外,明代人黄瑜《双槐岁钞·赐降虏姓名》、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赐降虏姓名》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其产生了影响。
史料应用方面,除了《实录》与档案之外,地方志的广泛利用是其重要特色。张鸿翔在《明史卷一五六诸臣世系表》一文中,针对专门记载内附民族将领的《明史》第一五六卷,在家族世系和主要事迹等方面进行了钩稽整理,拾遗补缺,完善了《明史》原文的缺漏错讹[3]。他的《明西北归化人世系表》汇集西北内附民族47户,251人的来源地区、承继关系和分布地域,主要资料依据是《实录》和“武职选簿”,参以明代各类史籍,内容详实,线索清晰[4]。他最有代表性的明代内附民族研究作品是《明代新氏族同名录》,于1931年—1936年间撰述完成。该研究在广泛爬梳近170种史料的基础上,著录了3267名归附民族人物的部族所属、内附安插、武职袭替的基本情况[5]。在《武职选簿》档案未公开面世之前,几乎成为学界利用武职档案从事研究的唯一资料来源。张先生的论著以考证精详、内容丰富、追求材料穷尽为特点,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史学的治学之道。同时也分析了民族内迁与分布规律,以及与内地军卫体制的关系等,为日后中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张著所引用的“武职选簿”档案直到2001年才正式影印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因此其资料出处与现行版本绝然不同。
此后的40年中,中国鲜有学者涉足这一问题。相反,国外明史学者司律思则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作者对明蒙关系系列研究成果中的两篇长文:《洪武朝附明蒙古人:1368—1398》分12章,描述了元末蒙汉关系中的一些表现,分析了洪武朝蒙古人归附的相关文献,指出归附蒙古人的主要来源,详细探讨了他们与明朝官僚体制间的关系及其在内地的分布,突出了汉化表现[6]。《附明蒙古人:1400—1450》实际上是《洪武朝附明蒙古人》的续作,作者强调他研究的是永乐朝到正统朝的归附蒙古人,主要是北京地区蒙古人的个体和团体、在京卫中的生存状况;华北地区以及中国中南部的蒙古人;还有包括禄米、草场牧地在内的生活条件等内容[7]。以上两文目前尚无完整汉译本。在个案研究上,《明代早期封爵蒙古人》讨论了17位受到明朝封爵的蒙古宗室、高官的情况[8]。司律恩的另一文章则讨论了锦衣卫中外族人士比例极高现象的原因和锦衣卫中的少数民族官员在明朝的作用[9]。经济生活方面,《明朝政府给予蒙古人的封地》认为明政府将大量无主土地赐予内附蒙古人用做牧场[10]。换言之,内附蒙古人掌握了大批内地土地田产,但他们的经营方式很快由畜牧转化为农业生产。作为国外对明代归附人研究的第一人,司律思主要利用《明实录》作为基本研究资料,这一方面表现出他并没有大量吸收张鸿翔的研究成果,也反映出缺少档案新资料支撑的史料短板。国外学者评价他和他的作品“精通语言学,熟悉蒙古语和汉语,研究的兴趣和领域广泛而实用,对其所研究的领域了如指掌。他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方法,重点在于对所研究课题中的全部问题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对历史进程和文化现象,往往不作直接的理论上的论证,而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基本的分析。”[11]44虽然有此局限,但是他的思考角度和分析深度所体现的研究水平至今仍未过时。令人遗憾的是其论著被国内译介不够,其在国内的影响比较有限。
二、中期研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恢复与发展
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明代归附人问题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中外学者们对明代内附民族分别在政治(民族政策)、民族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和社会与经济等角度开展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研究。研究方法和视野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亦即不再满足于材料搜集和基本事实考订的传统考据方式,而是在归附人生存状态、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变迁、民族关系的新变化等前人关注较少的领域进行探索。
学术界认为明代一般民族政策的特点是“恩威并施”,这一精神原则也适用于明朝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明代对归附人的政策可分为吸引与接受、任用与防范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明代的招抚政策和安置政策,它是政府接收明朝所辖境外民族进入内地的政治前提。后者集中体现在明代的“达官”管理制度。
对于前者,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宝日吉根的《试述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认为朱元璋对内附少数民族采取了五项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根本利益,缓和了民族矛盾,也有利于其内地的发展,“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2]69。王雄《明洪武时期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归纳了明政府针对蒙古归附者的三项安置措施,描述了洪武朝对蒙古降众的招抚、安置、任用的基本情况。作者认为明朝二百余年中,内地蒙古人生活安定,为明朝效力的结果源于朱元璋洪武时期的招抚和安置政策[13]。吴云廷《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则将研究时段锁定在“土木之变”前后,认为明朝的降人政策经历了由招抚为主到限制为主的转变,认为正是这一政策的变化导致内附蒙古人被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14]111。奇文瑛《论“开原控带外夷”》对明廷以开原城控制外族的原因、开原卫所的职责和变化三方面进行了讨论,分析了明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与内地王朝的关系[15]。
明代内迁民族分布总的特征是全国遍布,重点突出,宏观散居,微观聚居。蔡家艺《关于明朝辖境内的蒙古人》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蒙古人的来源、数目、分布、生活情况,很早提出故元遗兵中包含相当数量汉军的事实,得出了蒙古人在全国普遍安置的看法[16],是一篇系统研究入明蒙古人的论文。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探讨了明朝初期蒙古人入居在内地的原因、地点、生活待遇、职业以及在明朝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分析了3点内迁原因,提出主要分布于南北两京等5个地区,主要职业是屯田、养马、做官、从军,指出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北部边防,为中原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7]77。刘冠森《明朝初期中国内地蒙古人的住地和姓名》分别讨论了内地蒙古人的居住地区和改易汉姓汉名的情况,并给予了积极评价[18]。
入明归附人的民族文化特点、生活传统与内地居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明朝统治者继承了赐予姓名,消除内迁民族特征的传统,极大地促进了归附人与汉族间的姓氏趋同。蔡志纯《元明蒙汉间赐名赐姓初探》选取元明两代间的赐名赐姓现象为研究对象,指出其产生的原因与实质,认为统治民族的统治者给被统治民族赐姓赐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实行的民族政策。“元明二朝的统治者为了突出统治民族的统治地位,利用特权以强制的手段对被统治民族赐姓赐名,实行民族分化,笼络一些被统治民族为上层,迫使被统治民族的人改变其民族特征,以强制为同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存在着民族的自然同化。”[19]91
这一时期研究归附人问题的成果中,明代“回回人”研究异军突起。明代“回回人”研究既是回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明代归附人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先生是较早关注明代内迁“回回人”问题的学者。他用力最勤,成果丰富且极为扎实。他的系列文章《关于明代回回的移向问题》[20]、《明代入附回回姓氏汉化考》[21]、《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考》[22]、《明代西域入附回回的职业结构》[23]、《明代西域入附回回人及其分布》[24]基于对史料深入细致的梳理、研究,从迁徙特点、分布规律、汉化表征、职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完整构建了明代内迁“回回人”历史的基本面貌。一些观点,如明代“回回人”仍然沿袭了元代由西北迁往东南迁徙;“职业结构的变化又决定了回回民族经济特点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促使了回回民族本身的最终形成”[23]50等极有见地。和的研究证明,明代大量穆斯林入居中原,回族处于形成之中。这些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同。
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恢复和延续了明代归附人研究的学术传统,研究的重点相对集中在民族政策和内地分布状况及其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描述上。作为明代归附人演变和新的民族群体发展壮大的明代回族史研究则取得了较为全面的推进。
三、近20年来的新发展(2000年至今):深化与突破
随着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新档案材料的公布和研究的深化,21世纪明代归附人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中奇文瑛先生尤为突出。
(一)制度研究
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化的研究成果是针对特定对象研究招抚安置政策的特殊性。代表性的是奇文瑛《论明朝内迁女真安置政策——以安乐、自在州为例》立足于明朝北族大规模归附的背景,提出除了一般的安置措施之外,明朝在东北地区专门设立安乐、自在两州,是明朝招抚安置女真族不同于其他族类的一大特色[25]。《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的价值在于以三万卫为例区分了少数民族军籍武职和寄籍“达官”的身份差异,指出其产生的原因在于洪永时代军事环境的变化导致政策更替的结果[26]。《明洪武时期内迁蒙古人辨析》分析了南下故元官兵的由来、民族构成和蒙古人特点,认为所谓南下蒙古人中“汉族占有相当比重,其中的蒙古人也具有久居中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内在因素的存在,才使明朝的招抚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27]59《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特别强调了故元官兵与明朝军制的内在关系,大量利用《武职选簿》论证了大批故元官兵被安置在北方的事实,同时也分析了明朝的戒备手段内在矛盾性的原因在于族属难辨[28]。《明代“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达官”考》利用“选簿”资料指出“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达官”与“安乐州达官”的同质关系及其规模大小不同的原因所在,具有启发性[29]。奇文瑛《论明后期辽东安乐、自在州的变化——兼及辽东行政问题》在其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置于明代中后期,认为辽东安乐、自在州作为专管内迁女真达官的特殊建置,明中期以后随着对女真政策的调整,自在州南迁辽阳,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指出辽东军政体制下文官有权却无相应运行机制的矛盾[30]。刘景纯《明朝前期安置蒙古等部归附人的时空变化》认为明代对蒙古人为主体的北方“归附人”实行积极的招抚和安置政策,洪武朝经历了从北边、京师和个别地区安置向全国分散安置的过程。永乐以后,形成了京师集中安置的新模式被以后诸朝继承下来,只是在南北“两京”之间有调整和反复而已。成化以后的安置地转往江南地区[31]。柳素平《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分别从特权、治安、叛乱、边防的一些事例,认为“达人”“给明代政治种下了许多隐患”[32]133,而这一切与明朝维护皇权的需要、统治者个性和权宦势力有关,从而全面否定了归附人的政治意义。针对司律思的研究,王雄又作《明朝的蒙古族世家》,对所谓18家,20爵蒙古世家的事迹作了全面钩稽考述,据此分析了明朝的民族政策和蒙古中国化问题,内容详细,同时也指出了个别世家从族属上说并非蒙古族,而是“回回人”等民族,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错误[33]。
(二)社会生活研究
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归附人内迁后社会经济生活,婚姻关系的特征,扩大了归附人历史研究的范围。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讨论了“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任职情况及其社会生活的面貌[34]。高寿仙《明代北京及北畿的蒙古族居民》立足于北直隶地区进行区域研究,从来源与安置(分布地域)、职业与待遇(社会经济地位)、从猜忌到融合(民族融合)的三个角度深入研究了明代北京地区的蒙古族居民[35]。彭勇《论明代北京的民族构成及其生活》分别讨论了汉族、蒙古族、回族、女真族、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在明代北京民族构成中的作用,突出了京畿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特点[36]。周松《明朝北直隶“达官军”的土地占有及其影响》以安置在北直隶的军卫中的达官为例,认为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内地生活中,上层达官通过奏求、给赐的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并逐步适应了内地的经济生活模式,其经济身份也演变为汉式地主。明朝通过赐地免征粮科等方式对达官们进行经济笼络,即使在明朝中后期土地清丈之后,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达官经济优待政策。广大达军则转化为汉式农民。达官军经济生活的内地化是其融入内地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原因[37]。奇文瑛《碑铭所见明代达官婚姻关系》利用碑铭达官婚姻资料,结合档案和实录,揭示了明代归附达官进入中原后婚姻关系的面貌和变化情况,在资料运用和研究视角上实现了突破[38]。元亡明兴,明朝正式规定革除所谓“胡元故俗”。事实上,在明代包括皇室在内的社会上层并没有真正摈弃元人服饰。周松《上行而下不得效——论明朝对元朝服饰的矛盾态度》利用传世图像资料考察明朝禁止民间“胡风”的要求和保持“胡风”的现实反映出的是政治需要和文化传承间的矛盾性[39]。
(三)个案研究
笔者长期跟踪研究吴允诚家族及其所部归附人在明朝军事体系中的演变。笔者在《洪武朝塔滩蒙古与明朝的关系》考证认为“塔滩”就是阴山山脉以西地区。这里从洪武朝至永乐初年曾活动过一些北元的残余势力,他们一方面与明朝保持着相对平静的关系,一方面也有部众不断南下归附明朝,拉开了永乐初年大规模内附行动的序幕[40]。《入明蒙古人政治角色的转换与融合——以明代蒙古世爵吴允诚(把都帖木儿)为例》以吴允诚(把都帖木儿)降明朝后的活动表现出明朝对待归附人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归附人极强的适应性[41]。吴允诚所部“达官军”后来大部调入北直隶卫所,《明朝对近畿达官军的管理——以北直隶定州、河间、保定诸卫为例》的研究展示出明政府采取了以达官世官管领达军,宽严结合应对治安事件,坚持达官优遇政策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将达官军改造为明朝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推进了归附人内地化的进程[42]。彭勇的《论明代忠顺营官军的命运变迁》指出忠顺军的前身是由入仕明朝的蒙古、女真和回族等少数民族组成的达官军,隆庆二年改称为“忠顺军”。他们与内地汉族各军兵种一起入戍京畿、修守长城等。明清易代后,这批少数民族最终完成了从另类到普通身份的转化,其社会地位与内地汉民族没有区别[43]。笔者在此基础上,作《从西蒙古草原到华北平原——明朝忠顺营源流考》考证了明代后期的“忠顺营”作为北直隶诸卫的“达官军”后裔,源自洪武时代漠北杭爱山的北元部众,在把都帖木儿等人的率领下归附明朝。他们在明朝多次迁徙,得到从杭爱山—塔滩—凉州—北直隶定州、保定、河间诸卫的内迁线索。少数民族的同名现象极为普遍[44]。明代归附人多有汉式姓名,似乎可以避免重名,然而汉名的重名现象同样存在,给当代研究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明代达官民族身份的保持与变异——以武职回回人昌英与武职蒙古人昌英两家族为例》选取明朝的“回回人”和蒙古人中以昌氏为汉姓,甚至还拥有共同汉名的家族,在比较两个昌氏家族演变的基础上,探讨明朝内附少数民族武职的历史活动,分析其共性与个性,指出不同民族在内地发展的结果也明显不同,认为影响少数民族在内地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其自身的特质[45]。和宁王阿鲁台是永乐至宣德时期东蒙古最重要的领袖。《明代内附阿鲁台族人辨析》考证了南宁伯毛氏家族与阿鲁台的亲缘关系,钩稽了阿鲁台败亡后其子嗣亲属的降明事迹以及明朝的招抚努力以及安置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朝招抚措施的实效,强调了归附人贵族经过了身份转化,适应和融入明代社会的历史进程[46]。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指出万历朝鲜之役的明朝军队包括了降明的暹罗兵、黑人兵(葡萄牙黑奴)、日本兵,其数量自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不等,为朝鲜之役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折射出了当时东北亚世界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交流[47]。
(四)附明回回人研究的新进展
(五)综合研究
对明代归附人进行综合性探讨的论著较少,因此综合性探讨是今后本课题研究的发展方向。美国学者鲁大维《明代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民族:蒙古人与1461年的流产政变》一文中,选取1461年的曹钦之变为突破口,详尽分析了附明蒙古人与明朝政府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明廷把多数蒙古人安置在京城和周边地区,并进入世袭军户体系。因此,附明蒙古人的命运是由朝廷的政策塑造的,这是附明蒙古人参与政变的背景。由于土木之变,政府对蒙古人的疑惧加深,促使数以百计的蒙古军官加入未遂政变。虽然如此,附明蒙古人在政治上持久的忠诚、朝廷和华北地方间的密切关系、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和明代对武装力量的管理等几个方面都反映出流产政变的意义与附明蒙古人的真实处境[57]。《明朝治下蒙古人臣属的形象》一文意在通过明朝对京畿地区蒙古人群体看法的考察,深化对于附明蒙古人的理解。这篇文章的突出特点在于,作者以相当大的篇幅细致入微地阐述了附明蒙古人形象发展变化,以及此类形象在内地社会中的传递过程。作者认为,对京畿地区蒙古人部众的看法因时代、地域和环境的不同呈现了多样化的改变[58]。奇文瑛《从归附人视角看明朝民族关系》大量运用档案资料,研究认为明代长城内外的民族关系表现完全不同。长城以外军事对立,冲突表现为常态;在内地,由于明廷对归附人政策宽松,生活稳定,多民族杂居并存的现状不仅没有改变,民族交融的形势沿着历史的轨迹,持续继续发展,直至清朝建立[59]。奇文瑛多年研究的最新成果——《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北京和辽东地区的内附民族,突出了明朝军事制度的变化对“归附人”的影响[60]。这是目前该问题最为完整的研究成果。
奇文瑛先生高度关注明代军事制度与归附人安置两者间的密切关系,对明代归附人问题的深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问题与展望
近百年来,明代归附人研究肇始于国内,起点较高,但后续研究发展曲折。在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期,恰恰有国外学者继之以发扬光大。近30多年来,明代归附人研究走出低谷,取得了空前的进步。总的来看,国内学者成果较多,对细节的把握得更好,在一些难点领域已经获得突破。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独特,高度关注与附明少数民族相关的各类线索,在史料运用上也在尽可能追求广泛性,这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但是,不可否认,长期坚持以本课题作为专门研究方向的学者很少,仅有和、奇文瑛等先生进行了连续研究,其他不少论文尽管水平较高,但明显缺乏持续性,尚属于学术兴趣游移所致,这是本课题研究面临最大的缺憾之一。
从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明代归附人由于生存环境的根本性改变,他们既没有在内地建立少数民族区域政权,也没有形成大面积集中分布的居住格局,反而是不断紧密地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明代归附人问题更多是明代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史中的独特领域。有些学者已经尝试以制度史的角度分析归附人的历史活动,如奇文瑛先生对“军籍”和“寄籍”区分明代少数民族武官就是今后深化本课题研究的重要突破口,然而真正有意识在学术实践中贯彻这一认识的作品还不多见,此为缺憾之二。
在诸如“达官”概念,达官制度的确立和内涵等理论环节尚存有争议;面向明代的归附人研究仍然呈现明代中后期研究薄弱的前大后小现象;在归附人的发展归宿研究上与清代研究对接不够等诸多不足。
明代归附人问题的史料较为零散,材料本身缺少内在联系。今后的研究应该对《明实录》《武职选簿》等现有史料进行精细化考证,深入挖掘明人文集、碑铭、家族谱等史料,扩大史料搜索范围,疏通整理出史料间的内在联系,既有助于摆脱史料自身的时间桎梏,更能在史料线索链条的重建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所以,现阶段明代归附人问题研究仍然需要更加扎实的史料考证工作,这是今后研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内亚史、东亚史、明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层出不穷。除了理论更新之外,针对史料中包含大量档案文献的特点,可以尝试建立“明代归附人信息数据库”,加大量化分析力度,并采用可视化(Visualization)表达等新方法,推进这一课题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