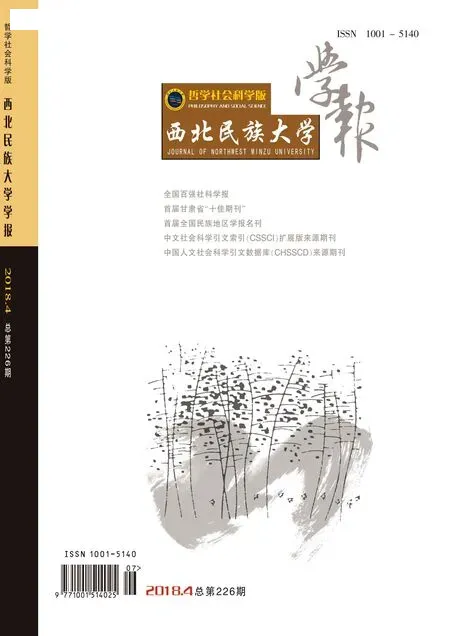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形成
李世武
(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严格来说,博厄斯才是艺术人类学之父,艺术人类学诞生的标志是其专著《原始艺术》的出版。人类学之父泰勒在文化进化论的观照下,将原始艺术置于文化进化的低级阶段。在他看来,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艺术,包含在整个文化进化的历史进程中。他为人类学的研究划定了范围,也明确将艺术纳入文化之内,但却没有建立艺术人类学的学科体系。此前艺术哲学家格罗塞等人研究过原始艺术,但毕竟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抽象、思辨的研究,注重思维的相似性和文化研究的历史维度,强调艺术的普遍性和原始部落中优美艺术的存在,使博厄斯在方法论上超越了前人。博厄斯认为,美是跨文化、跨民族的普遍现象,只不过各民族获取美和鉴赏美的方式不同。这种观点在当时而言,具有振聋发聩的划时代意义。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分析了面具这一独特的艺术门类[1]。在美学问题上,“列维—施特劳斯是和现代西方美学保持最为一致的人类学家。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持有强烈的歧视性观点的唯美主义者。但他不是用他的审美意识和其他文化中的美学进行比较,而是作为观察另一种文化的视角。”[2]221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过博厄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努力,现代艺术人类学已经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特点:认同美作为人类天性和跨文化研究美的可能性;西方现代美学对艺术人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现代美学在博厄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时代早已形成并盛行。鲍姆嘉通、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学说,早已传遍欧美学术界。面对如此强势的西方现代美学体系,博厄斯选择了回避。他声称不想讨论美学哲理,而是将研究范畴限定在原始艺术的范畴内。列维—斯特劳斯则从现代西方美学的视角去观察部落社会的面具。
20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类学家,比前人更加自觉地意识到现代西方美学范式在解释非西方艺术时面临的困境。更为深刻的是,他们甚至认识到自身无法摆脱现代主义范式的制约,同时也作出了种种积极的努力。1981年,自莱顿的《艺术人类学》出版以来,艺术人类学领域形成了三个主要视角:图像学、美学和功能主义。美学视角仅仅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三大视角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人类学家就审美是否是一个跨文化范畴的问题展开争论。参与这场争论的学者有霍华德·墨菲、彼得·高、杰里米·库特、乔安娜·奥弗林、杰姆斯·维纳、皮纳·韦伯纳、马库斯·班库斯、珀涅罗珀·哈维、克里斯蒂娜·托伦、提姆·英戈尔德、费利西亚·休斯—弗里兰、乔治娜·波恩、索尼娅·格雷格、阿尔弗雷德·吉尔、迈克尔·敖汉龙、彼得·韦德、罗伯特·莱顿。其中,莱顿、吉尔、墨菲等人,如今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人类学家。以艺术人类学家对“审美是否是一个跨文化范畴”的讨论为中心,我们可以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形成进行讨论。
一、罗伯特·莱顿:图像学视角
作为辩论的正方代表,墨菲强调的不是通用的、跨文化的审美标准(universal aesthetic),也不是独立于文化的艺术审美标准。他的意图在于:坚持美学概念是可以在跨文化分析中使用的一个概念。作为反对者的代表,奥弗林则强调,“美学”这一术语,是鲍姆嘉通于1735年的首创。伊格尔顿认为,这一术语的原初历史意义是资产阶级和精英的概念,起于理性启蒙运动时期。他认为,不能用美学这一现代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去翻译他者关于美丽的观念。无法用现代美学观理解他者的美学观。他举例说,Piaroa(皮马)人的美学观根植于生产性语境,具有实用目的,不存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供人凝视的对象。库特支持墨菲的观点,认为非西方民族,比如约鲁巴人中就存在与西方美学范畴充分重叠的本土美学范畴。再如,丁卡人词典中没有“美学”一词,却似乎有“美丽”一词。墨菲用育伦古的田野实例证明,育伦古人的视觉艺术效果在英国艺术家布里吉特·瑞丽的作品中也有出现。墨菲甚至试图建立一种元美学语言,提出一种更具有文化适用性的美学定义,去为跨文化翻译服务。奥弗林指责说,墨菲和库特的这种尝试依然是在一种现代主义范式中进行的。库特指责反对者蓄意选择最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美学定义。他认为可以用民族志经验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范畴,从而尝试克服他们自身的现代主义假设。奥弗林认为墨菲和库特无法实现目标。最后,墨菲也意识到,即使建立了元语言,依然无法克服现代主义审美范式对人类学家的束缚。元语言乃西方美学的一部分,比较、对比、判断都是现代审美意识的一部分。发现、定义“原始艺术”,本土美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都是现代审美的内在愿望而已[2]201-234。
莱顿参与了“审美是否是一个跨文化范畴”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并不反对在跨文化分析中使用审美这个概念。他关注的是艺术人类学家判别美的作品或艺术品的标准,并对审美观念跨文化翻译中遭遇的语言障碍提出质疑。他建议用18世纪以前的概念,如优雅(grace)或亲切(graciousness)去更好地把握Piaroa人关于美的理想。持18世纪以前美的概念的人类学家,可以摆脱现代主义美学的拖累[2]223。莱顿显然也意识到现代主义美学在研究非西方艺术方面的效用有限。在1981年出版的《艺术人类学》中,他承认不存在普适性的艺术定义,但有两种定义可以适用于多种文化中的艺术。“一个是运用美学的术语,另一个是把艺术看作特别偏爱运用形象的优美的传达。”[3]他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美的愉悦和运用形象增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是艺术品共有的特征;但是也存在只具有其一的例外情况。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象征和美是艺术最重要的要素,二者必居其一[2]224。从他对艺术定义的接受来看,莱顿并不排斥将美学研究运用于跨文化分析中,同时我们看不出他直接接受了现代西方美学体系。莱顿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最具有创造力的部分是对潘诺夫斯基视觉交流理论的运用。他在评价吉尔能动性理论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了视觉交流(visual communication)理论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4]。我们可以把莱顿视为一位不排斥在跨文化研究中使用美学视角,同时,也意识到西方现代美学体系在跨文化分析中的局限的人类学家。由于他的理论开拓性主要在于将图像学中的视觉交流理论运用到跨文化的艺术研究中,我们可以视他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持图像学视角的学者。
二、霍华德·墨菲、萨利·普莱斯、杰里米·库特:美学视角
墨菲的研究,实际上有深刻的分析美学的印记。他的研究是在试图建立一种普适性的美学话语,这种话语被称为元语言。墨菲对元语言的期许是,其能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超越文化差异而被用于跨文化的分析中。他对美学的定义是:“美学关注的是刺激对感官的定性作用。刺激可能是物质的形式,源于可以看到、感觉到和听到的世界的属性,或者可以源于对某一观念的理解。这种刺激被集成在人类文化和行为体系的许多不同方式中,并且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层面加以解释……美学涉及从一系列广泛的视角进行品质上的评价:包括柔软度、硬度、明亮、重量、亮度、锐利度等等。”[2]234如果我们因为墨菲强调美学是在跨文化分析中的一个有效概念,就认为他固守于本土美学的领域而忽视其他视角,则未免偏颇了。墨菲早已觉察到问题的复杂性,并试图加以综合。早在1994年,墨菲就注意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3个主要视角。从图像学的视角来看,艺术具有意义编码、表现性和创造特殊意义的属性;从美学的视角来看,艺术具有审美效应和相关意义;从功能主义来看,艺术在仪式和宗教中、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和在令人愉悦的过程中发生作用。他综合了这三种视角,将艺术定义为:“艺术品具有语义的和/或审美的属性,以表现或再现为使用目的。”[5]墨菲认为,这个定义是在人类学上有用的,并且是与欧洲人的概念重叠的。他在2006年主编的《艺术人类学读本》中,重申了这一概念。作为修正,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品兼有语义属性和审美属性。他依然坚持建立艺术研究的元语言[6]。
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以墨菲、普莱斯和库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从美学视角进行的非西方艺术研究,也不能对他们的思想一概而论。他们三人在对美学问题的认识上是有细微差异的。墨菲试图建立一种美学的元话语,但并不排斥从图像学和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开展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从他对艺术的定义就能看出,他在宏大的学术史视野中试图综合现有的方法。但就个人的研究而言,他专注的是美学视角。依托于田野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他将育伦古美学与西方美学进行跨文化对比,得出共性,其实就是在寻找审美通则。从他对美学所下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追求。这和他曾经申明其意不在寻求跨文化审美通则的观点是相抵牾的。此外,即使墨菲建立了元语言(metalanguage),去比较不同的审美体系,但元语言仍然属于西方美学的范畴[2]233,23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最彻底地偏向于审美视角的是普莱斯。普莱斯明确将本土美学研究作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任务。首先,普莱斯不回避西方文化对西方人审美经验的规训。其次,她坚信原始人有自己的本土审美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和西方人的方式一样,是受原始人的文化所规训的。最后,研究非西方本土美学是为了扩充西方人的审美经验并矫正文化偏见。她认为是审美框架的固有性和合法性保证了艺术作品的生产。无论原始艺术和非西方艺术都一样[7]。普莱斯的观点显然有积极的一面。她接受了现代主义美学范式对西方人的局限,并正确地指出文化对审美经验的规训是一个跨文化、跨民族、跨文明阶段的普遍现象。我们不应无限制地夸大审美经验的文化差异。她将非西方美学的研究作为扩充西方人审美经验和消除文化偏见的手段,显然克服了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很值得肯定。然而,她和许多美学研究者那样,陷入了一个泛美学的牢笼。她将审美作为艺术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有失偏颇的。泛审美的艺术研究,用审美经验遮蔽了艺术经验。吉尔的批评一语中的。
库特成功地揭露了现代主义美学的种族中心主义本质。前文已经论述过现代主义美学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现代主义美学体系有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对于非西方艺术,尤其是印度和中国之外的非西方艺术,现代主义美学诞生时期的美学家是从根本上忽视和歧视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野蛮民族根本不可能有美的艺术(fine art)体系。他们认为,那些物品是粗糙的,处于艺术进化的初级阶段。库特的研究,对于反艺术线性进化论,反艺术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而言,意义重大。库特试图用身体力行所获得的民族志经验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范畴,从而克服现代主义的假设[2]225。实际上,艺术人类学界可以成功地利用民族志经验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对艺术的阐释。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完全拒斥、克服、超越西方现代主义假设,人类学家们仍然力不从心。
墨菲、普莱斯和库特,可以视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持美学视角的代表性学者。艺术人类学中强调审美视角的这一派别,在建构跨文化分析的审美元语言、用民族志经验批判现代主义美学范式、扩展西方人的审美经验、矫正审美偏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现代西方人类学家,他们依然无法拒斥、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假设。这一派别的研究还有用审美经验遮蔽复杂、多样的艺术经验,从而陷入泛审美主义泥沼的潜在危险。
三、阿尔弗雷德·吉尔:功能主义视角
在这场争论中,作为反对派的吉尔和奥弗林一起对墨菲和库特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他们认为,美学一词以—ics结尾,因此和政治学(politics)、经济学(economics)一样,都是某种学术话语符号的开始。美学一词是具有原始内涵的哲学话语,但在学科中,它却具有了特定的名称和特定的所指范围。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西方哲学固有的话语,主要关注艺术对象和艺术传统,同时也关注风景和花。“对美学而言,我们应当从深渊中后退,而不是被这个术语的实用词源关系所诱惑,像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词汇那样。”[2]225吉尔在他影响深远的遗著《艺术和能动性:一种人类学的理论》中,更为明确地阐述了他对在艺术人类学中使用美学视角的反对态度。在艺术人类学中持美学视角的学者认为,艺术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详尽地研究不同文化中所固有的美学特征,即研究本土美学。他们承认并接受西方艺术审美传统对西方人的审美规训,同时,强调异文化美学的客观存在。研究异文化中的美学,是为了扩充西方审美经验并超越西方人自身的文化狭隘性。吉尔则认为,对非西方美学的阐释并不能构成艺术人类学。他相信,非西方文化观念体系中存在和西方文化观念体系中相似的成分。但是,对本土美学和本土审美语境的研究,实质上是在强化和延伸西方人的审美感知,即对非西方艺术品的感知。他认为,不可能为以美学来描述和对比文化建立一个普适性的参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将由艺术品所引发的社会、情感反映,如恐惧、渴望、敬畏、沉醉等都归入审美感受的范畴。因为,将这些概括为审美感受是毫无意义的。他放弃了墨菲、库特和普莱斯以研究本土艺术的审美语境为中心的方法,而是从社会性的角度出来,将研究艺术品生产(production)、流通(circulation)和接受(reception)的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作为艺术人类学的任务[8]1-7。
吉尔敏锐地洞悉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审美路径所暴露的问题。其一,美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分支学科,其产生时间为西方18世纪理性启蒙运动时期,是资产阶级和精英化的,它所研究的特定范畴主要是西方的艺术对象、艺术传统,兼及风景和花。其二,艺术人类学的本土美学研究,本质上是在强化和延伸西方人的审美感知,也就是用西方人的审美感知方式去感知非西方艺术品。其三,无论是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研究,还是墨菲等倡导的作为艺术人类学中心范畴的本土美学研究,都要警惕将所有艺术经验都等同于审美经验的误区。这是一种泛审美化的方法,其实是一种诡辩术,我们已经熟知美学界的这种套路。只要人们开始讨论一种艺术经验,美学家就极力论证它属于审美经验的范畴。当傩舞仪式中的舞者戴着用于驱鬼逐疫的丑陋面具,美学家会说,丑也是一种美。泛审美化的观点除了自身难以自圆其说之外,它还遮蔽了其他的艺术经验。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审美经验是艺术经验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是否在场,或者说如果在场,那么与其他艺术经验相比较,审美经验究竟是主要经验还是次要经验,要依据文化差异和具体的语境来分析。
吉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显然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尽管他并没有在著作中直接表明这一点。他对特罗布里恩群岛库拉圈独木舟船头板的研究,以及他将技术与魔法联系起来的观点,无疑都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对巫术、技术、贸易等论题所提出的观点的影响[9]。吉尔的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理论模型,无疑从库拉圈的贸易模式获得了灵感。另一个关键证据是,吉尔在比较艺术人类学和艺术社会学的差异时指出,艺术人类学聚焦的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直接语境,专注于个人;艺术社会学聚焦的是制度[8]8。个体性与集体性,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和社会学家杜尔干的重要分歧所在[10]。在这个意义上,吉尔的能动性理论,可以说是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一种延续。他完全抛弃了美学和图像学,继承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并批判地吸收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原创性。因此,他的遗著在艺术人类学界以及西方艺术哲学、艺术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将吉尔视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持功能主义视角的学者。
四、结语
人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以丰富、发展自身的传统。泰勒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吸收,成就了古典文化进化论,继而影响了弗雷泽的“巫术—宗教—科学”进化学说。进入现代人类学时期以来,作为对古典人类学的超越,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以直接获得的田野实证经验为建构理论的基础,因此有了功能主义和历史特殊论的创造性收获。如果列维—斯特劳斯不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获得分析文化的工具,很难想象他会获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学科细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而学科交叉,可以看作是学术共同体对学科细化导致的方法论僵化进行的自我免疫。人类学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其他的学科。如艺术哲学家格罗塞、布洛克等,都受到人类学方法的启发。
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交叉领域乃至交叉学科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形成,也是在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完成的。在人类学诞生之前,历史悠久的西方美学传统,已经对艺术进行了形而上学的追问,形成了庞大而艰深的学科体系。艺术人类学家发现,根本无法直接将西方美学传统移植到他们所关注的史前岩画和现代原始部落艺术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美学,尤其是现代西方美学所忽视或歧视的对象。这些对象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方式与西方艺术大相径庭,格格不入。于是,艺术人类学家只好另辟蹊径。现代西方美学成为他们自觉反思的对象,这种自觉性正是艺术人类学理论创新的推动力。莱顿试图退回到18世纪以前,用优美和亲切等未经现代西方美学浸染的术语去解读非西方艺术,同时成功地将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中的视觉交流理论作为分析艺术的有效工具在实际研究中运用。墨菲等坚持在跨文化分析中使用美学概念的学者,试图用民族志经验去批判现代主义范式,扩展西方人的审美经验。盖尔干脆放弃了美学和视觉交流的视角,继承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基本学理,扬弃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形成了功能主义的视角。如今,我们可以将视觉交流、本土美学和能动性作为这场理论创新的核心术语。艺术人类学绝不是现代西方美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糅合,艺术人类学可以看作人类学界对现代西方美学的一种挑战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