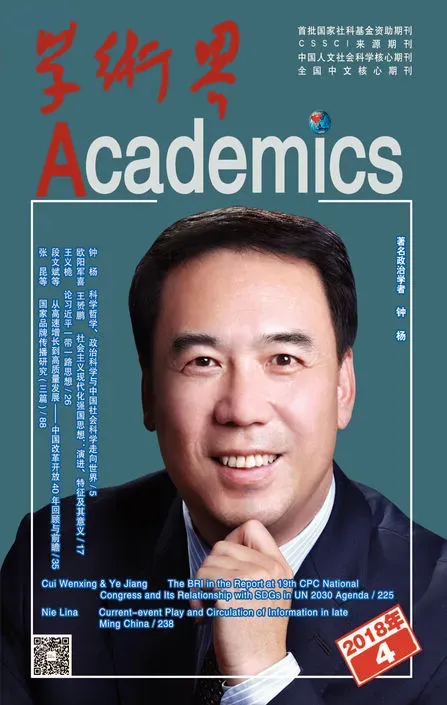另一场“脱欧”
——英国废除《人权法案》运动及其“反人权”传统
○ 傅 乾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引言:另一场“脱欧”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一举震惊世界。人们忙于理解,英国人为何逆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潮流而动,毅然选择脱欧。与此同时,还有另一场脱欧也在英国酝酿多时,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就是废除《人权法案》甚至脱离《欧洲人权公约》(下称《公约》)的运动。最近两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特蕾莎·梅(Theresa May)都是铁杆废除派。卡梅伦自2006年起就力推此事,2015年将其写入《保守党政纲》。〔1〕梅则主张,与其脱离欧盟,不如脱离《公约》,并着手将其写入2020年《保守党政纲》。〔2〕
与前一场脱欧一样,后一场同样令人费解。这一次,英国人似乎不但要破坏欧洲共同体的团结,还要违背二战以来的政治正确——“人权”信仰。要知道,“人权”如今堪称准宗教,它有它的“福音书”《世界人权宣言》,有它的“教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它的“枢机主教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有它的“宗教法庭”欧洲人权法院。不仅如此,英国人此举似乎是数典忘祖,须知《人权法案》号称“丘吉尔的遗产”,是对丘吉尔所倡《公约》的国内法化。再往前追,不正是洛克的“天赋人权”论奠定了西方现代政体的基础吗?
那么,这是不是多数英国人的想法?总体来说大致如此。〔3〕首先,普通民众大多反感《人权法案》。这一点已成共识,就连力保《人权法案》的人也不得不承认。〔4〕其次,大多数媒体要么对废除一事推波助澜,要么热衷传播《人权法案》负面信息。比如,当保守党2014年宣布废除计划时,右派报刊群起欢呼,《每日邮报》标题是《人权闹剧的终结》,《太阳报》说:“我们将把《人权法案》扔进历史垃圾堆”,《每日快讯》封面写作“人权癫狂的终结”,《每日电讯报》指责欧洲人权法院法官曲解《公约》服务自身需要。虽然《卫报》《镜报》等偏于反对,但也被指在报道相关新闻时以讹传讹。甚至有人说:“一个政治家只要否定《人权法案》,不管多么失实,通常都能赢得媒体的掌声。他若挑战成见而坚称它是一项重要立法,往往会收获一片嘘声。”〔5〕与此同时,议会2011年时曾成立权利法案委员会调研应否废除,结论是《人权法案》大失民心,应另起炉灶。〔6〕最后,这一立场也写入女王2015、2016年度讲话。〔7〕
那么,英国人为何动此想法呢?直接原因是欧洲人权法院针对英国的若干判决。这些让人激愤的判决主要集中在囚犯权利、反恐、驱逐非法移民等领域,代表案例有温特终身监禁案(Vinter v.UK)、赫斯特政治选举权案(Hirst v.UK)以及卡塔达引渡案(Abu Qatada v.UK)。
先看温特案。温特1996年因杀害同事被判终身监禁,10年后获假释,旋因聚众斗殴再度入狱,出狱不久又杀害妻子。于是,他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但温特认为,对他的判决“残酷、不人道且有辱人格”,伙同另两位各背四项命案的囚犯〔8〕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结果,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以十六比一推翻英国法院判决,认为原有判决剥夺囚犯改过自新的希望,应允许其服刑25年后复审,以获假释机会。
赫斯特案则涉及重犯是否有选举权问题。赫斯特是一名因过失杀人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按英国法律被剥夺选举权。于是他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该法院在2004年判决:英国法院原有判决侵犯了选举权这一基本人权,认为“囚犯被剥夺人身自由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公约所规定的对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并要求英国改变这种“一概剥夺”囚犯选举权的法律。〔9〕
最后是影响最大的卡塔达案。卡塔达号称“本·拉登驻欧洲大使”,是约旦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神职人员,参与策划“9·11”等恐怖袭击,在欧洲鼓吹圣战。2001年起英国政府多次对其监视居住和逮捕,几度试图把他引渡至约旦受审。但他以在约旦恐遭酷刑为由,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2012年该院初审判决英国败诉,而当时处理此事的内政大臣就是现首相梅。复审时该院才推翻原判,这一刻英国等了十多年。
这三个大案,每一个都引起公愤。英国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欧洲人权法院为何如此偏袒杀人犯和恐怖分子,而事关民众安危,本国法院和政府为何说了不算。同样,英国政府也因处处受制而忍无可忍。从这些案件可见,英国人想废除《人权法案》情有可原:他们无非是想防范恐怖袭击,驱逐非法移民,从欧洲法官手里夺回司法管辖权,代之以英国人自己的权利法案。
但深究之下,除了这些现实考量,此类事情还有观念和文化层面的渊源,即“英国核心价值”(British core values)。再往深处说,可能还有来自一种特殊历史记忆的“身份认同”。因此,虽可笼统地说人权是英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认同,但此“人权”非彼“人权”。桑塔耶纳有言,英国人“讲究口音更甚于措辞,讲究措辞更甚于观点”,〔10〕用来形容英国人对人权的态度同样不错:他们对救济人权比解释人权更讲究,对解释人权又比宣示人权更讲究。《人权法案》就好比洋腔洋调,说的也是“人权”,但总让英国人听着不舒服。
其实,英国人这种感觉由来已久,至少在洛克时代就已出现。如今人们大多认为,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为光荣革命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也是英国近代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但实际上,洛克学说在当时处于政治辩论的边缘,辉格党的主流将其视为旁门左道,宁愿从普通法中提取更为传统的论证。到法国大革命高扬“人权”旗帜之时,英国又出现了埃德蒙·柏克,被后人奉为保守主义的鼻祖,他将“人权”斥为“填塞鸟类标本的废纸”;在人权哲学的丛林尽头,“你看到的只有绞刑架”。同时代还有边沁这位功利主义创始人,痛诋“人权”是“凌空蹈虚的一派胡言”。如此形成的传统,使英国人对“人权”这种舶来品大多冷眼相看。其原因除了挑剔“人权”本身的质量问题,还因为英国人自恃是权利保护的老字号,只认源远流长、血统高贵的本土名牌——“英国人的权利”,不认什么“巴黎时尚新品”。可以说,英国人废除《人权法案》的想法,是与英国近代以来的“反人权”传统一脉相承的。
故而,研究这一问题,既需要人权法学和宪法学的角度,也需要思想史和法律史的角度。目前,从前者出发,国内已有若干研究。〔11〕笔者则试图从后者入手,聚焦背后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反映的“英国性”。首先介绍《人权法案》的来龙去脉;其次追溯英国近代“反人权”的三大思想传统;最后从三大传统中总结“英国性”,深化对英国人权利观念的理解。
二、《人权法案》的来龙去脉
如前所述,《人权法案》是对《公约》的国内法化。它于1998年通过,2000年生效。然而,英国早在1951年就签署了《公约》。也就是说,时隔半个世纪才将其国内法化。因此,要理解为何废除,可先回答它为何难产。
这一切要从《公约》谈起。二战后,丘吉尔鉴于纳粹对人权的迫害和苏联极权的现实威胁,呼吁制定一部《人权宪章》。此呼吁得到热烈响应,于是在英国政治家法伊夫(David Fyfe)主持下,《公约》制定出来,其间,它从英国的权利保护传统多有借鉴。随后英国率先签署,但由于英国法律的双轨制,《公约》在国内并无法律效力。不仅如此,随着后续议定书的出台,英国与《公约》的隔膜愈发严重。这主要体现在是否授予个人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的权利上。英国对此极不情愿,直到1966年才同意。
此后又有人开始呼吁变公约为国内法。〔12〕但最初应者寥寥。理由多样,其中之一是:英国的人权保护足够健全,无须画蛇添足。为此议会曾出具报告,认为并无证据表明制定此类法案的国家人权状况好于英国,说明它们“在人权方面作用极其有限,毕竟一国的政治氛围和传统对于人权保护更为重要”。〔13〕后来,以丹宁勋爵为代表,很多英国法律人都表示反对。他说:“我希望我们不要把公约列入我们的法律……主要理由之一是它的形成方式与我们所习惯的任何方式都不同。它只对原则和例外情况做了概括性的规定,因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很容易引起无休止的争论。”〔14〕
既然如此,为何还是制定出了《人权法案》?这首先是由于国际压力日渐加大:一是有越来越多的签署国已将公约内化,二是欧洲人权法院在个人申诉案件中多次判决英国败诉。另一个原因是,英国行政权日渐扩张,导致很多人受到权利侵犯却无从救济,这使英国权利保护的神话逐渐破灭。再者,随着英国1972年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法成为直接适用的上位法,而它承认《公约》的法律效力,于是英国等于间接将其内化了。而间接还不如直接,它不但使英国法院丧失主动权,而且使个人申诉舍近求远、费时费力。因此议会最终达成共识,在工党主持下制定并通过了《人权法案》。
法案虽然通过,英国人的怀疑态度仍在,因此最初拟订法案时就加入了诸多限制。在对权利的列举上限制不多,基本是从《公约》上照录,因为它们基本上均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属消极“自由权”。
最主要的限制,是有关解释和适用这些权利的规定。英国人精心设计了一套机制,平衡议会主权与司法审查、国家主权与公约义务。这套机制包括:立法上,一方面要求在解释和执行既有立法时“尽可能”与公约权利保持一致,在引入新立法时,内阁应就是否抵触公约权利做出说明,另一方面又规定,若确实无法保持一致,在做出说明并经议会表决后,亦可获得通过;司法上,一方面规定法官应“酌情考虑”欧洲法院的相关判决,另一方面却说明“酌情”不等于“亦步亦趋”。此外,英国法院若认为某项制定法抵触公约权利,可发布“不一致声明”,但它又规定,这种声明仅为建议,不能推翻制定法,是否修法全凭政府意愿。
这套平衡机制之精妙,是很多废除派都愿意承认的。但是,纸面上的平衡到实践中却愈发失衡,天平是向着司法审查和欧洲人权法院倾斜。“酌情考虑”变成了亦步亦趋,“不一致声明”也愈发具有推翻制定法的实际效果,总之,“斯特拉斯堡法理学”占据优势。但激起公愤不是这些,而是前文提到的欧洲人权法院判决。〔15〕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些判决纵容囚犯和恐怖分子,危及公共安全,伤害民族情感,却只是为了迎合一种书呆子式的人权观。
保守党顺势而起,要求废除《人权法案》,声称“英国的人权保护历来基于实际情境,而非仅仅事关抽象原则”。〔16〕英国当代保守主义学者斯克拉顿也批评道:“自从《公约》纳入英国法律以来,法官发现自己……不得不允许公开与英国社会为敌的人留下来,蛊惑青年加入圣战组织、反对收留他们的社群……这一切都拜一个理念[人权]所赐,其严整的几何轮廓是沿着通往虚无的陷阱而绘就。”〔17〕
但是,这种意见除了源于现实考量,还源于英国人特有的权利观和文化认同。这可由最近两任首相的相关言论加以印证。卡梅伦在2014年保守党大会上说:“对《公约》的解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们判决我们不得引渡恐怖嫌疑人;……如今他们还要给囚犯以选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可是写下《大宪章》的国度……一个时时挺身而出捍卫人权的国家……保守党赢得下届大选并组成政府后,这个国家将会有一部基于自身价值观的新《英国人权法案》。”〔18〕在他早先一段话中,这种在权利保护上自力更生的愿望更加明显:“是时候改弦易辙了,应保护本国土生土长的诸自由权,处处体现英国的法律遗产,以使人民对权利有归属感。与此同时,还能让英国内政大臣在公民自由权与保护公共安全之间保持常识性的平衡。”〔19〕
类似言论也出于梅之口。她在2013年引渡卡塔达后,仍然批评《公约》和“对我国人权法的疯狂解释”。她说,驱逐卡塔达耗时12年,公帑170万镑,“于公众、于我本人,均不可接受”。〔20〕2016年,她更明确地阐述了她的权利观和英国认同:“我听说,有人讲这说明我反人权。可是,人权并非1950年起草《公约》时发明的,也非1998年它借《人权法案》内化为国内法时发明的。这里可是大不列颠——有着《大宪章》、议会民主和世间最公正法院的国度——我们自己有能力保护人权,并且既不危害国家安全又不束缚议会手脚。一部由议会表决修订的货真价实的《英国人权法案》,不仅能保护《公约》所列权利,还能保护《公约》未列入的英国人的传统权利,比如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21〕
从这些言论可知,英国人要废除《人权法案》,有着自己文化认同的原因。他们自豪于自身的权利传统和司法制度,信任议会权威,讲究公民权利与公共安全的平衡,权衡权利保护的得失。而这种历史记忆,又根源于英国悠久的“反人权”传统。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了解今日英国人的想法,不妨回顾一下塑造他们信念的那些思想传统。
三、“反人权”传统
英国“反人权”传统主要有三:普通法、保守主义、功利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三者有分有合,但都批判抽象“人权”。
首先看普通法。普通法可谓英国法政思想的重要母体。它有两大属性:以习惯法为本和法官造法。它们决定了“英国人的权利”不但有异于欧洲的人权或自然权利学说,而且其司法适用的历史也要古老得多。习惯法主张权利源于习惯,而非自然或理性,〔22〕普通法不过是共同的习惯,它所保护的权利是约定俗成、业已享有、适合特定风土人情的权利。法官造法是指,权利有赖于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普通法不过是无数法官在个案中创造的救济手段。这两种属性的结晶,就是著名的“英国人的权利”。以此衡量,“人权”在英国人看来只能是赝品,它既非业已享有、适合风土人情,也缺乏司法救济过程的历练。
如前所述,至少在洛克时代,“人权”已受冷遇。当时参加光荣革命的辉格党人很多都是法律人,尤其是几位主要的宣传家,如阿特伍德(Atwood)、佩迪特(Petyt)等。他们论证议会下院的权利、反抗权和废立君主的权利时,是到历史中翻箱倒柜寻找先例。〔23〕反过来说也大致成立,对于有先例可循的事情,他们才认为自己享有权利。因此,当洛克从人性和自然状态出发,推演出一些想当然的权利时,他们大多深感不适。这期间,政论小册子多以宣扬“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为主,这类说法才是真正的英国特色。〔24〕
循此一传统最清晰地阐明普通法权利观与人权之别的,当属19世纪宪法学家戴雪(A.V.Dicey)。戴雪揭橥“无救济则无权利”与“法律主治”之义,对于正式的权利宣言、宪章或保障条款不甚看重。他说,英国人传统上“注意于救济侵权行为的损害,胜似宣示人的权利或英吉利人的权利”。〔25〕正是这种从司法救济入手的务实倾向,使“英国人的权利”逐渐通过法院判决确立起来,无需成文宪法的正式宣示。由此便有戴雪之名言:宪法“在英格兰,不但不是个人权利的渊源,而且只是由法院规定与执行个人权利后所产生之效果”。〔26〕因此,只要法律主治之大义“苟不废弃,宪法下之权利必能永存”,无论宪法宣示与否。反之,如相关权利没有化入一国法律、习俗和风尚,即便有正式的保障条款也无济于事。而且,宪法可保障某权利,即意味着可废止它,足见此种保障极不可靠。
诚然,英国历史上不乏《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这类宣示权利的正式文件,表面看似与法国《人权宣言》相差不大。但在戴雪看来,“以法意论”,两者判然有别:英国的文件“与其称之为对于人权的宣告,毋宁称之为对于君主特权或积威的否认。而且在否认之余,两种著名公文均用一种司法判决的方法判定君权的滥用均作无效”。〔27〕用今天的话说,它更注重的是让公权就范,而非私权的声张。因此,它的效力不在于用成文宪法赋予它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也不在于详尽罗列人权,而在于严格划定权力的边界,在这边界之外,正义服务于习惯和传统。因此在普通法中,权利是一个司法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书斋里的定义。
故而,英国人也并未将某些权利抬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在戴雪看来,权利也好,宪法也罢,不过是“普通法律运行于四境内所生结果”“原来同是权利,我们甚难以指出某项权利应比他项权利较受制宪者另以青眼看待”。〔28〕虽然他也重点论述了三项权利,但对他来说它们并无特殊地位,也无绝对的含义。如言论或思想自由,都是法律之下的自由。〔29〕
戴雪所论未必能完全代表普通法,但确实成为后世法律人“反人权”时诉诸的权威。除他以外,至少还可举出梅因(Henry Maine)及其弟子斯蒂芬(J.F.Stephen)。前者是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先驱。他认为,剥离历史、只讲自然或理性,“产生了或强烈地刺激了当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智力上的恶习,如对实在法的蔑视,对经验的不耐烦,以及先验理性优于一切其他理性等”,最终结果就是革命或无政府状态。〔30〕后者是著名刑法学家,秉持一种冷峻现实的功利主义,不但批判洛克自然权利说,也批评密尔后期抽象思辨的功利主义,曾留下传世名著《自由·平等·博爱》〔31〕。因为密尔虽然并不赞同天赋人权说,他的结论却可用“自由平等博爱”来表述。普通法的这种传统观点延续至今,塑造了英国人对《人权法案》的态度,上文提到的丹宁勋爵和几个“人权”案例引起的纠纷,可以说与其一脉相承。
除普通法以外,还有一种与之渊源甚深的思想传统也对“人权”深怀戒惧,这就是英国的保守主义。它在权利观上与普通法近似,都强调权利源于传统,重视权利的司法救济,只不过更突出普通法权利观的保守特质,既看重“法律与秩序”,又擅长寓新于旧、守先待后的技艺。它至少可追溯到主导着光荣革命进程的“老辉格党人”,代表人物就是萨默斯勋爵(Lord Somers)。他是《权利法案》的主要起草人,同时也是洛克后期的恩主。但他起草的《权利法案》基本没有采用洛克话语,通篇都是《大宪章》语言,诉诸英国人的古老权利论证革命正当性,有意无意间寓新于旧、寓革命于反革命。例如《权利法案》开头有言:“前所主张和宣告的林林总总的权利和自由,都是本王国人民古已有之、不容置疑的权利和自由……。”〔32〕
不过,这一传统的鼻祖当属柏克。他批评法国革命的人权观“在形而上学上越是正确,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越是虚假”。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柏克深知社会之复杂,晓得实际政治需要平衡盘根错节的利益和观念,这种平衡不仅是“善与善的平衡;有时候也是善与恶、恶与恶的妥协”。在他看来,复杂的现实好比稠密的介质,“人权”这束光线穿过其中必然发生折射,这时墨守权利原轨,无异刻舟求剑。〔33〕
这种不切实际若仅止于书斋,尚无大弊。在他看来,陈义甚高之说的危险在于,它足可消解成规,却无力重建秩序。它煽起游谈无根、狂热偏激、轻率盲动的心态,使人变成“形而上学的愁容骑士”“把经验鄙夷为文盲的智慧,至于其他的东西,则他们已经在地下埋好了地雷,轰然一声,一切古老规范、一切先例、宪章和议会的法案都灰飞烟灭”。在这种人权面前,“任何政府都不要奢望幸免于难,不管其统治多么悠久,管理多么公正宽容。”〔3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柏克反对一切人权。〔35〕相对于抽象人权,柏克表彰“实实在在、于史有征、世代相传的”权利,也即由普通法所阐明的权利,这实际是柏克对普通法传统的继承。〔36〕在柏克看来,英国人的权利“有一份家谱和显赫的祖先”,从《大宪章》到《权利请愿书》再到《权利法案》。〔37〕其一以贯之的精神是敬奉祖业,传之久远,将权利看作遗产,将继承作为守护权利的方式。对于这份家产,应守先待后,而非抛家舍业,“以犯罪换贫穷”“舍利益以丧美德”。〔38〕
后来,柏克对人权的这种批评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信条。19世纪著名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就是一个显例。他也像柏克一样,一边批判抽象人权,一边为“英国人的权利”正本清源。他曾说:“在英国人的权利之中有某种比人权更好的东西”〔39〕“基于抽象权利和原则的政治制度终是镜花水月,自由唯一稳固的正当基础是法律,一国旧有的法律体制与新的立法机关之间若无契合,后者必将失败……。”〔40〕在他看来,起草《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宣言》的朗顿、塞尔登、萨默斯“全是实践家,都不会徒言抽象权利”“他们知道一旦承认抽象的臣民权利,免不了进一步承认抽象人权,这样一来,他们政体的真正基础便隐而不彰”。〔41〕因此,这几份文件一脉相承,都在重申英国人古已有之的权利,〔42〕也正是这种“尊重先例、崇尚因袭、信而好古”的态度,使“英国人的权利”远比法国的“人权”货真价实,前者使英国人在政治上成为“神所庇佑的特殊选民”,后者只带来“抹平、无政府和专制”。〔43〕
在20世纪,迪斯雷利这种权利观在另一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那里得到了继承。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说,1989年她受邀参加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会上宣称,法国是人权保障的先行者,《人权宣言》是世界首份系统保障人权的法律文件。撒切尔回应道:“人权并非肇端于法国大革命,而是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融合。我们有1688,那场静悄悄的革命,议会令国王俯首听命。它不是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我想他们忘记了义务与责任。”〔44〕不难想见,当今在人权问题上决意脱欧的卡梅伦和特雷莎·梅二相,其实是在步撒切尔夫人的后尘。
第三种批判“人权”的思想传统是功利主义。大体上,它主张权利的内容取决于切乎实际的功利计算,而非想当然的教条。其先驱可追溯到休谟。休谟虽没有集中批判自然权利说,但他从情感心理学和历史功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自然正义、原始契约等相关命题。在他看来,正义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权利亦然。〔45〕但这一传统真正的鼻祖当属边沁。他曾说:“一听到‘自然权利’,我就透过纸背看到一簇刀枪剑戟阑入国民大会,伴随对总统孔多塞的欢呼,他口口声声说要清君侧。后来,这些刀枪剑戟在光天化日之下冲着通情达理之人亮出来,仿佛为作奸犯科之徒准备的绞刑架”。〔46〕由此可见他对“人权”何等厌恶。因此,他曾四评法国《人权宣言》,最脍炙人口的一篇叫做《无政府的谬误》。其批判可概括为两点:“人权”言之无物,败事有余。
其言之无物源于两点:语义空洞与表达上的混乱矛盾。在边沁看来,“权利”概念本即虚指,无法指向任何实存之物,“法律”“制裁”“主权”则相反,故而“权利”要靠后者界定。“权利”尚且如此,“自然权利”就更无从谈起了。表达混乱主要源于对物理、法律和道德范畴的混淆,例如,《人权宣言》在表达“不可”(cannot)时,就在这三个范畴之间随意切换,造成语意混乱。表达上的矛盾则主要源于人权说在理论上宣示权利的绝对性,在现实中又不得不承认其限制。总之,在边沁看来,这种矛盾混乱和语义的空洞共同导致“人权”成为言之无物的胡言乱语。〔47〕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人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边沁称其为“法律的死敌、政府的颠覆者、稳定的杀手”〔48〕。他认为,人权说蕴含的完美标准使人人都能以之判定实在法为恶法,从而使法律丧失权威。这一逻辑运用到衡量政府合法性上,后果尤为明显。“人权”说想当然地设定合法性的“最低”标准,但以此衡量,现实中绝大多数政体都不合格。这样一来,法律无权威,政府无合法性,无政府状态就势不可免,而在无政府状态之中,毫无权利可言。
因此在边沁看来,从实然层面讲,权利是法律的产物,从应然层面讲,法律不应不计后果地保护个人抽象权利,而应以权衡利弊为基础,“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此种观念成为后来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19世纪的奥斯丁就继承边沁,将功利而非权利作为基本原则,将形而上的人权说逐出法学,将法学限定于对实在法的概念分析。他批判声张人权者“嘴边只挂着‘人权’‘主权者的神圣权利’‘不可剥夺的自由’‘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始契约或协议’和‘不可侵犯的宪政原则’之类的口号”,却不曾权衡利害,也不做任何妥协,结果就是不惜以暴力行私意。〔49〕20世纪的哈特在否定“人权”上不如两位前辈彻底,他甚至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和“人人平等享有的自由权”,但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强调权利的法律属性和义务基础。〔50〕
从以上对英国近代“反人权”三大思想传统的概述可知,从戴雪、梅因、斯蒂芬到丹宁,从萨默斯、柏克、迪斯雷利、撒切尔夫人到卡、梅两相,从休谟、边沁、奥斯丁到哈特,英国的“反人权”思想根深蒂固、阵容庞大。与之相对,“人权”思想在英国其实是异质而边缘的。只是由于美国革命造成的洛克神话,由于辉格派的历史叙事,更由于“人权”在二战后成为一种信仰和政治正确,这一点往往隐而不彰。因此,索解今日英国人反《人权法案》乃至整个脱欧运动的缘由,必做的功课之一是把它置于英国特殊的法政思想史背景之中。
四、“英国性”
探寻英国人反《人权法案》的思想渊源,有必要做一追问:这反映了英国人何种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或身份认同,或者说,这是否有所谓的“英国性”(Englishness)在作祟?
对此,不妨从三种思想传统之共性谈起。三者各有侧重,且有所分歧。由其共性观之,或可更见精髓。由上文可见,反对抽象人权说便是其共性之一。换言之,它们与现代主流“人权”说正相反对。“人权”说之特质可由两组修饰词反映。一是“自然、不可让渡和神圣的”,见于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强调人权的绝对性。二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51〕,见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强调列明之人权项目皆不可少。那么,这两组修饰词反映着什么思想特质呢?简单说,就是立场寸步不让,内容越多越好,至于能否兑现、如何兑现,则暂且不管。其根源,在于只顾逻辑、不顾事实,只顾普遍、不顾特殊,只顾完美、不顾实用;以严谨而至美妙,用之于世间却往往落空。
英国人的性情和观念则大相径庭。三种思想传统的共性或可以“英国性”名之。它的特点之一即“非逻辑性”,借用艺术史家佩夫斯纳论英国建筑的话说:“毋庸置疑,非逻辑性必须被列为一种英格兰特性。……英格兰人厌恶把思想体系推向逻辑的终点……。”〔52〕这种非逻辑性在艺术上表现为不统一、实用主义、即兴、无原则,引申到文化特性上,则是矛盾、折中、虚伪、就事论事。这种特点,使英国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政治上,都失去了狂热和激情,但收获了便利和宽容。故而,英国在艺术上出不来瓦格纳和尼采,政治上也避免了罗伯斯庇尔和希特勒。
以此观之,演绎式的人权观说显然与这种“英国性”圆凿方枘,而普通法、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人权说的排斥,不过是它的具体表现。它们都更偏爱某种“非逻辑性”,警惕强求逻辑一致造成的破坏。英国人不会只知其一不计其余,在他们眼里,除了逻辑,还有事实;除了普遍,还有特殊;除了现代,还有传统;除了自由,还有权威;除了权利,还有义务。正因为他们要兼顾诸多矛盾的双方,才会鄙夷逻辑,安于非逻辑带来的小小不便,寻找平衡折衷带来的乐趣。
故而,相对于人权说主张人权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内在尊严”,普通法宁肯固守权利源于习惯而成于司法救济的信念,保守主义以守先待后、寓旧于新为维护权利之上策,而功利主义则坚持功利之外慎言权利之神圣。三者共同主张任何权利都是法律之下的权利,其内容和边界取决于法律的界定。更准确地说,它们认为,法律如何界定权利,取决于技艺理性、审慎明智和权衡利弊——凡此三端,皆可视为调和矛盾、折衷息事、就事论事这种“英国性”的体现。因此,当欧洲人权法院以人权为由,判定英国法院不得剥夺囚犯的选举权时,当它以不人道为由,判定英国不得判处杀人犯终身监禁且不许保释时,当它以相关权利会在目的地国受到侵犯为由,禁止英国驱逐外籍恐怖分子时,很多英国人无法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概言之,这三种思想传统及其蕴含的“英国性”,使英国人对《人权法案》始终心存芥蒂。它体现了英国人源远流长的权利观及其保护路径,而与“斯特拉斯堡法理学”格格不入。托克维尔曾说,英国的司法体制“这架庞大古老的机器”同法国司法的现代化工厂相比,显得“复杂而不一致”,看上去“模糊、阻塞、迟缓、昂贵而不便……然而自布莱克斯通那个时代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彻底达到了司法的伟大目的……在英国所有的法庭,都可找到维护他的财产、自由与生命的最好保障。”〔53〕
这大概也是英国人在人权保护问题上更愿意“脱欧”的底气所在。
注释:
〔1〕David Cameron, Balancing freedom and security:A Modern British Bill of Rights,Speech to the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26 June 2006;Conservative Party, Conservative Party manifesto,2015.
〔2〕Christopher Hope,“Theresa May to fight 2020 election on plans to take Britain out of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fter Brexit is completed”, The Telegraph,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12/28/theresa-may-fight-2020-election-plans-take-britain-european/,访问时间:2017-2-18。
〔3〕当然,反对声音也有。媒体之中,《卫报》也主张保留。政党中,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基本持反对态度,保守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卡梅伦的文胆杰西·诺曼(Jesse Norman)就明确反对,参见Jesse Norman and Peter Osborne, Churchill’s Legacy:The Conservative Case for the Human Rights Act,London:Liberty,2009。此外,苏格兰等亲欧地区也大多反对,跟脱欧类似。
〔4〕全国民权理事会承认,公众对《人权法案》缺乏了解和认同;人权专家阿莫斯(Merris Amos)也承认,《人权法案》虽卓有成效,“但大众对它并不了解,公共形象不佳,很不受人尊重”,参见Commission on a Bill of Rights,“A UK Bill of Rights? The Choice Before Us”,Vol.1,2012,pp.28-29。
〔5〕Roy Greenslade,“Right Rights vs Left Rights:How the Newspapers Line up on ECHR”,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greenslade/2014/oct/03/uk-bill-of-rights-national-newspapers,访问时间:2017-2-9;Jesse Norman and Peter Osborne, Churchill’s Legacy:The Conservative Case for the Human Rights Act,London:Liberty,2009,pp.36-37。
〔6〕它虽然主张另起炉灶,但承认《人权法案》的优点,认为应继续将《公约》国内法化,参见Commission on a Bill of Rights,“A UK Bill of Rights? The Choice Before Us”,Vol.1,2012,pp.28-33。
〔7〕Queen’s Speech 2015,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queens-speech-2015;Queen’s Speech 2016,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queens-speech-2016,访问时间:2017-2-9。
〔8〕两人名叫班柏(Bamber)和摩尔(Moore)。班柏曾杀死养父母、姐姐和两个年仅6岁的外甥,摩尔杀死了四名与他有染的同性恋男子。
〔9〕唐颖侠、史虹生:《从赫斯特案看英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演进》,《南开学报》2014年第5期。
〔10〕George Santayana, Soliloquies in England and Later Soliloquies,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22,p.54.
〔11〕唐颖侠、史虹生:《从赫斯特案看英国人权保障机制的演进》,《南开学报》2014年第5期;屠凯:《2015年英国宪法学焦点:〈1998年人权法〉的存废》,《中国宪法学年刊》第十一卷,第220-227页。
〔12〕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3〕Report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a Bill of Rights,HL 176,1978.
〔1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刘庸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331-332页。
〔15〕其实推翻的数量极少,截止到2010年只有三百件左右,在一万五千件来自英国的个人申诉案中仅占2%,参见Commission on a Bill of Rights,“A UK Bill of Rights? The Choice Before Us”,Vol.1,2012,p.90。
〔16〕Conservative Party,“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the UK:The Conservative’s Proposals for Changing Britain’s Human Rights Laws”,2014.
〔17〕Roger Scruton,“Limits to Democracy”, New Criterion,2006,Vol.24 Issue 5,p.20.
〔18〕David Cameron,“Speech to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2014”,http://press.conservatives.com/post/98882674910/david-cameron-speech-to-conservative-party,访问时间:2017-2-18。
〔19〕David Cameron, Balancing freedom and security:A Modern British Bill of Rights,26 June 2006.
〔20〕Alan Travis,“Theresa May criticizes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after Abu Qatada affair”, the 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08/theresa-may-human-rights-abu-qatada,访问时间:2017-2-18。
〔21〕Theresa May,“Home Secretary’s Speech on the UK,EU and our place in the world”,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home-secretarys-speech-on-the-uk-eu-and-our-place-in-the-world,访问时间:2017-2-18。
〔22〕普通法也主张习惯与理性并重,但它讲究的是“技艺理性”,而非纯粹理性。
〔23〕J.G.A.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82-228.
〔24〕这类作品按时间顺序可选列如下:Henry Care, English Liberties,or,The Free-born Subject’s Inheritance,1650;William Penn, The Excellent Privilege of Liberty & Property Being the Birth Right of the Free-born subjects of England,1687;Wagstaff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Englishmen,London:Printed for A.Baldwin in Warwicklane,1701;Francis Plowden, The Rights of Englishmen,Dublin:George Bonham,1792;William Young, The Rights of Englishmen,London:Printed for John Stockdale,1793;Basil Montagu, Thoughts upon Liberty and the Rights of Englishmen,London:Printed for J.Butterworth and Son,1822。
〔25〕〔26〕〔27〕〔28〕〔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44、245、243、245页。
〔29〕以戴雪论言论自由为例:“议论的自由在英格兰实不过是一种权利,任何人得用之以书写或谈论公私事务,但以12个店主人所组成之陪审团不至视作毁谤者为限。这样‘自由’常依时节不同而变异……”,〔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3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1、51页。
〔31〕〔英〕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冯克利、杨日鹏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32〕毕竞悦等编译:《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3页。
〔33〕〔34〕〔35〕〔37〕〔38〕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Vol.VI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12,108-109,109,83,88.
〔36〕冯克利:《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文史哲》2015年第1期。
〔39〕Hansard XCIX,20 June 1848,958.
〔40〕〔41〕〔43〕Benjamin Disraeli, 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35,pp.60;56,23;23,205,28.
〔42〕“《权利宣言》把我们权利和自由的谱系追溯到《权利请愿书》,进一步又可追溯到《大宪章》,后者又以同样的方式起源于亨利一世宪章和忏悔者爱德华之法”,Benjamin Disraeli, 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35,p.43。
〔44〕Daniel Hannan, Inventing Freedom:How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Made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roadside Books,2013,p.331.
〔45〕“在人们缔结了获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不理解前者,就无法理解后者。”〔英〕休谟:《人性论》(下),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1、517-615页。
〔46〕〔47〕〔48〕Jeremy Waldren ed., Nonsense upon Stilts:Bentham,Burke and Marx on the Rights of Man,London:Methuen,1987,pp.74,34-39,73.
〔49〕〔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50〕H.L.A.Hart,“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64,No.2 (Apr.,1955),pp.175-191.
〔51〕《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载徐爽编著:《人权指南》,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52〕〔英〕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249页。
〔5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2-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