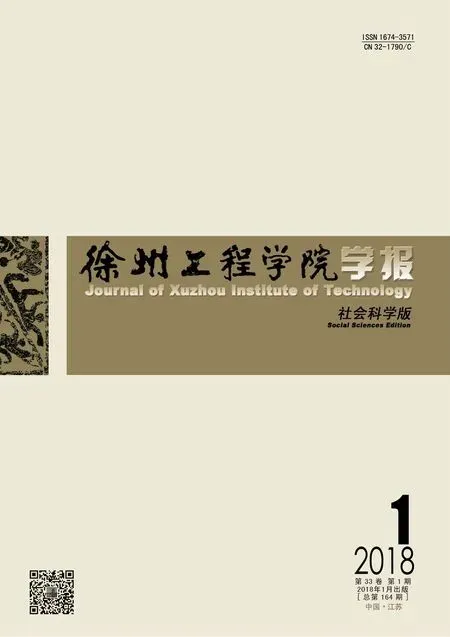除祓与祈子:中国古代寒食清明荡秋千的文化阐释
杨丽嘉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关于秋千的文献梳理与分析
据文献记载,秋千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隋炀帝编《古今艺术图》云:“北方戎狄,爱习轻跷之态,每至寒食为之。后中国女子李芝兰,乃以彩绳悬树立架,谓之秋千。或曰本山戎之戏也。自齐桓公伐山戎,此游戏始传于中国。一云正作千秋字,为秋千非也。本出自汉宫祝寿辞也。后世语倒为秋千耳。”[1]
作为现存较早的一部考证事物起源、沿革的类书,《事物纪原》将散见于宋以前关于各种事物起源的历代文献搜集起来、汇集成书,为后代积累和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关于秋千起源和传播,《事物纪原》提供以下有参考价值的信息:1.从地域上看,秋千,起源于北方山戎,最初功能发挥于军事训练,齐桓公伐讨山戎将其带回齐国。2.荡秋千的时间多为寒食节。3.秋千游戏的主体为女性。4.秋千的形制之一,用彩色绳索系于树上。5.汉代,秋千游戏流行于宫廷,其功能在于“祝寿”。
山戎,春秋时期活跃于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其生产方式以山林狩猎、高山游牧为主。先秦时期,中原的华族称北方少数民族为戎,因其生活于山中,故称“山戎”。《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初北方有孤竹、山戎”[2],《史记·五帝本纪》亦载尧之时,北方有“山戎、发、息慎”[3]。山戎族,以狩猎和游牧为生,民风骁勇善战。荡秋千要求参与者有较强的轻捷性和灵活度,游戏特性与山戎民族特质相呼应。在河北承德、丰宁、滦平、平泉等地考古发掘有山戎墓葬。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山戎代燕,燕告急于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3]145古代孤竹国的疆域,大致在今滦河流域,辽宁省的锦西和河北省的迁安、卢龙一带[4]。春秋时期,齐伐山戎三次,鲁伐山戎一次。齐桓公时,齐国的疆域,东不超过今山东半岛西部的弥河,南不过泰山,西在今山东齐河县一带,北在今天津市南界以南[5]。弥河主体在今山东省潍坊市境内,潍坊市境内至今仍有清明节荡秋千的民俗[6]①。历史地理考据和现代民俗学材料进一步佐证《事物纪原》所载的齐桓公讨伐山戎将秋千带回齐国,基本可信。
寒食、清明荡秋千习俗屡见于历代的笔记和诗文中。五代《开元天宝遗事》描写了唐玄宗后宫寒食荡秋千的盛况,“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7]。杜甫《清明二首》“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风俗同”[8]。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满街杨柳绿烟丝,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缭乱送秋千”[9]。则反映了民间荡秋千的情状。此时,秋千不惟北方地区所独有,蜀地和江湘地区也存在。而荆楚地区荡秋千的风俗,则可追溯到南朝的《荆楚岁时记》,“立春之日,……又为打球、秋千之戏。”[10]“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袨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10]不同之处在于,南朝时荡秋千的时间多在立春日。
宋代描写宫廷、贵族、民间女子荡秋千活动诗词不胜枚举,如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张先《青门引·春思》、王禹偁《清明》、陆游《三月二十一日作》和《感旧未章盖思有以自广》等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描述了北宋都城汴梁清明节金明池临水殿的“水秋千”表演,“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侯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11]“水秋千”与传统荡秋千游戏相异,带有杂技色彩,大概为现代跳水运动的前身。荡秋千为清明时节市民娱乐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秋千还是宋代皇室祭祀先祖的惯例活动之一。绍兴十三年,宋高宗采纳大臣的建议重建景灵宫供奉祖宗衣冠,宫殿建成后,在殿内设“掌官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灯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睺罗。帘幕岁时一易,岁月酌献二百四十羊。”[12]寒食秋千和元宵节的灯彩、七夕的摩睺罗一起,作为祭祖仪式的组成部分。
元末,熊梦祥根据自己在京为官时对北京的了解,撰写了现存最早的专写北京地方史地的《析津府志》。明末此书亡佚,后代学者从《永乐大典》《日下旧闻考》《宪台通纪》等文献中整理辑佚,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析津志辑佚》。此书保留了有元一代北京宫廷和达官显贵之家清明寒食荡秋千的珍贵史料。“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然有无各称其家道也。”[13]清明寒食是元代宫廷中最富丽的节日,专有“戏蹴秋千”的服装、珍馐美味异于平时,足显示出此节日和荡秋千的重要性。“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更点出了荡秋千的功能,一为“除祓”消灾,二为“散怀”取乐。
明代宫廷中的秋千游戏,见于刘若愚《酌中志·明宫史》:“三月初四日,宫眷内臣换罗衣。清明则秋千节也,带杨枝于发。坤宁宫及各后宫,皆安秋千一架。”[14]清明节因荡秋千游戏而被称为“秋千节”,且每个宫苑都竖立秋千架,盛况亦必不凡。李开先《观秋千作并序》则记载了家乡山东章丘一带的民间秋千游戏,“东接回军,北临大河,庄名大沟崖,清明日,高竖秋千数架,近村的妇女,欢聚其中,予以他事偶过,感而赋诗……”[15]清明节,一个小村庄竟竖立秋千“数架”供妇女游戏,秋千花样名目繁多,据此,或可推测荡秋千可能有着某种非凡的象征和功能。
清代宫中,在燕九日有秋千表演,“山高水长在圆明园之西,俗呼西厂,地势宽敞,直陈大戏。每岁正月十九日,例有筵宴……有西洋秋千架,秋千旋转,下奏歌乐”[16]。秋千表演规模似有元代遗风,然而时间在正月十九日而不是寒食清明。民间的秋千游戏,如李振声《秋千架》所说,“无处无之。仕女春图,此为第一。”[17]
寒食荡秋千是北方山戎族的传统,自唐代以来,荡秋千成为寒食、明清节清明节宫廷和民间重要的游艺活动,明清时期,“秋千节”甚至成了清明节的代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一种自主的存在,和动物界不同,人类的游戏行为,不仅仅是自然的冲动或者习惯,游戏有着理性的一面。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一种“意义隽永的形式”,一种社会功能。[18]从文化研究的层面,把游戏当做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来理解。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对成人和有责任心的人而言,游戏这个功能是可以抛弃的,游戏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推迟和暂停的,游戏绝对不是身体之必需和道德之责任强加于人的。只有当游戏被认为是文化功能比如仪式或典礼时,游戏才与义务和责任之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18]9。
寒食、清明为祭祀祖先以表彰孝思的节日,唐开元年间玄宗下《寒食诏》,对寒食祭扫进行官方规定,“于茔南门外奠祭,彻馔讫泣辞食馀,于他所不得作乐”[19],整顿寒食游玩踏春游艺行乐之风。但“于他所不得作乐”的法令,似乎与《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天宝宫中寒食节“竞竖秋千架”的盛况相矛盾。段成式《酉阳杂俎》从养生和医学的角度解释寒食节秋千、蹴鞠,“寒食有内伤之虞,故令人作秋千、蹴鞠之戏,以动荡之。”[20]寒食禁火,人皆食用冷餐,会伤及脾胃,所以通过荡秋千和蹴鞠来发散五脏郁结养护身体。将游戏行为的驱动力归为生理需求并无不妥,但似乎无法解释何以宋代寒食宗庙祭祀惯例中有“寒食设秋千”之俗。
“元丰年间,修景灵宫十一殿成。其国祭日适在寒食节假中者。百官趋行香。见梭门与秋千并建于庭中。”[2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先秦以来,宗庙祭祀为国之重典。宗庙不仅仅是祭祀活动的场所,其本身既是仪式的中心,也是国家事务的中心和权力象征的中心[22]。《礼记·曲礼》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23]直述祖庙及其相关祭祀器物在国家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灯楼、秋千、摩睺罗等仅仅作为运动娱乐设施而存在,将其置于宗庙之内似乎有违礼制。宗庙之内设置秋千等,固然有希望祖先亡灵能够继续享受人间行乐的意味。而“上元结灯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睺罗”将上元、寒食、七夕三节并举,将秋千与灯楼、摩睺罗等量齐观,昭示着三者的宗教意涵和信仰意义。
就宗庙祭仪和民间习俗的关系而言,宗庙祭祀和民间的祭祖活动在祭祀内容和文化意涵上并没有太明显的区隔。宗庙祭祀固然以权力身份的强化为仪式活动的核心,但二者共同的信仰基础在于祖先崇拜,皇室的宗庙祭祀仪典与民间祭仪风俗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关联。对民间寒食及相关节日风俗文化内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代宗庙祭祀寒食设秋千这一习俗的祭祀和文化功能。
二、“上元结灯楼”和“七夕设摩睺罗”的宗教意涵
上元节,其名源于道教三元节,《唐六典》卷四载“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24]。上元节为天官赐福之日,观灯为主要习俗。历来文献记载上元张灯之俗源自《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祭祀太一之事[25],“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26]。太一就是太极,汉武帝祭祀太一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27]。据洪迈《容斋随笔》,宋代在太平兴国五年到淳化元年间三节皆张灯,“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25]292。
道藏《正一威仪经》云:“正一燃灯威仪,灯象星形,助天光明,延年续命,却祸消灾。”[28]道教中的灯象征着星辰,可照见幽冥驱散黑暗助天光明,亡魂赌此光明,可得解脱,具有延续生命的意涵和功能,是道教永生思想的体现。佛教中,灯代表佛祖,是智慧的象征。灯能够冲破黑暗指引光明,佛法如灯,可照破世界的黑暗,燃灯为了礼佛。《佛说护身命经》云,在诵读《护身命经》时“劝令一切族姓男女供养香花杂彩燃灯续明,复能流转读诵,皆救人疾苦厄之者,现世安吉”[29]。
又据敦煌文献记载,晚唐人燃灯功德的宗教指向之外,可保“国泰民安……增万福”(敦煌文献第3262,3263卷)。
可见,宋代宗庙祭祀“上元结灯楼”惯例,融合了佛、道二教教理和灯的宗教象征意涵,具有超拔祖先亡灵,追求神仙境界和无量佛土的永生意味。同时,可以祈国安民、降福纳祥。
宋景灵宫“七夕设摩睺罗”之祭祀惯例,清代的张尔岐在《蒿菴闲话》中即有所评论,“既云生子之祥,又不当止为女人形;要是儿女嬉戏之事,设之原庙何居?”[30]宋代七夕京城售卖摩睺罗的习俗,《醉翁谈录》《东京梦华录》《岁时广记》《梦梁录》中均有记载。摩睺罗,又名“化生”,梵语音译,一种土制或蜡制的婴儿形偶人。摩睺罗,原指佛教的八部众神之一的摩睺罗神,唐代借用其名来指七夕供养的化生偶人,《辇下岁时记》载“七夕,俗以蜡做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妇女宜子之祥,曰化生”[31]。唐诗人薛能《吴姬》诗之十曰:“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银台弄化生。”[32]描述了唐宫廷中元节后妃以化生祈子之俗。宋代,“七夕前,修内司例进摩睺罗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造,悉用缕金珠翠”[32]。修内司按照惯例进摩睺罗,数量大,用材名贵、制作精美。唐俗将化生浮于水上祈福,而宋宫廷所进摩睺罗“大者至高三尺”,似乎难浮于水上。因此,或可以推测大摩睺罗即为七夕设于原庙之物,其意在企望祖先护佑皇室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江山社稷永固。
综上所述,宋代景灵宫之祭祀惯例“上元结灯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睺罗”。其中两项均有着祭祀祈福求子的宗教意涵,独“寒食设秋千”,仅为护养内脏、嬉戏取乐之功用,似乎难合常理。且寒食唐宋游艺项目颇多,蹴鞠、斗鸡、马球为何被排除在祭祀惯例之外,而独选秋千之戏?或许,秋千运动本身即为某种宗教和信仰的民俗表征?
三、除祓·祈子:“寒食设秋千”背后的民间信仰
上文《析津府志》所载元代北京城清明寒食节秋千游戏的盛况,“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然有无各称其家道也”[13]。“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解释了时人荡秋千的心理动机:“除祓”和“散怀”。何为“除祓”?《说文解字》释“祓,除恶祭也。”[33]“祓”,祭祀行为,目的在于消灾祈福,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解释“祓,祭以除灾害,拔除不祥”[34]。《诗经·大雅·生民》“以弗无子”,郑玄笺:“弗言之祓也。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天子疾而得其福也。”[35]作为祭祀行为,祓的功能在于祛除天子疾病、祈福于天、求子。祭祀时间、地点、方式不同,通常于岁首在宗庙、社坛中举行[36]。而三月三上巳节水上祓禊为盛。故而,从字源和礼俗文化的意义上说,“除祓”一词,至少揭示了元代北京清明寒食秋千游戏的信仰功能。
今山东莒北“秋千会”据当地传说为驱逐缢鬼,超度亡魂的祭奠行为[37],泰山市则流传着一则石敢当以秋千为法器驱除妖魔的民间故事,其所念咒语为“一绳荡起千秋净,乾坤浩气今何存,岂可任由尔等胡乱作为?”[38]高高荡起的秋千具有清除乾坤之内的妖魔之气,因此当地人供奉石敢当,相信秋千可以降妖除魔,在清明节家家户户荡秋千,祈求妖魔不侵平安吉祥。山东的潍坊有一种说法,“悠一悠,不长秋”,认为春天荡秋千,可以驱除秋天的瘟疫,白浪河边的沙滩上,每年清明节前一月提前设立“转秋千”,供民众悠荡[39]。山西省晋南、晋东南一带,荡秋千是春节传统竞技活动,春节除旧迎新,荡秋千能够除疾病、“掉灾”[40]。
寒食、清明秋千游戏其参与主体多为女性,高承《事物纪原》卷八梳理秋千缘起和流变,特析出中国女子李芝兰,用彩绳悬树立架设秋千之说,或许意在为秋千游戏的女性特质寻求源流上的合法性。然而,推求秋千游戏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源流上的合法性似乎不及习俗上的承接关系更具说服力。《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条载:“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饮熟’,……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11]67《礼记·内则》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23]1171,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称为“及笄”。“上头”乃成年礼,即将女孩散发用簪挽成成人样式。由以上引文可知,至迟在宋代女子行及笄之礼的时间为寒食前一天,清明日在寒食的第三天,时间序列十分紧密。据此,或许可以推断,至少唐宋以降的秋千游戏,可能为女子成年礼的仪式之一,而仪式的功能为祈子。
从地缘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疆域主体在今山东省境内,唐都长安、宋都开封均位于中国的北方,北方地区的某些文化遗存或许可进一步佐证秋千游戏的祈子功能。山东莒北地区的秋千节习俗中流传着有关秋千起源的民间传说:
很久以前,有户人家娶妻,一妖怪变成新娘干扰娶亲。两个新娘难辨真假,一个道士空地竖起百尺高竿,周围堆上干柴,对两个新娘说,你们谁能跃上高竿谁就是真的新娘,否则就是妖怪。妖怪上当,跃上竿头后被道士烧死。此后,每年这个时节,人们都架起高竿,点燃篝火,欢聚一处,载歌载舞,祈福驱邪。后来人们又在高竿上拴上绳索,在上面表演各种动作,后来此活动演变为秋千[37]。
顶替新娘母题是此传说的核心情节,新娘被顶替,女子的婚姻受到妖怪的威胁,道士用计惩治杀死妖怪,合法的婚姻得到维护。后人以仪式的形式模仿道士烧死妖怪的情节,来驱邪祈福。仪式的演变促成了秋千的诞生。当地,每年春分次日,家家在院中或门前空地上搭起秋千架,让家人游荡,以示人丁兴旺。由此可见,秋千游戏的仪式功能在于驱除妖邪维护女性合法婚姻,而合法的婚姻恰恰是人类生育和繁衍的基础。
山东潍坊至今仍流传着寒食节荡秋千祈子习俗,祈子主题贯穿于从秋千架的选址、秋千的搭建、秋千的朝向、上梁仪式到荡秋千的整个过程中。如,秋千可以搭在当年或是前一年已经生儿育女的人家门口,生男孩的优先于生女孩的。秋千的参加者必须是村里两年之内结婚但尚未生子的年轻夫妻。搭建者由已婚生子的年轻人担任。荡秋千时已婚已育的夫妇先荡,已婚未育的夫妇后荡。荡过秋千后当年怀孕的,生下孩子后的第一个寒食节一定要去荡第一回秋千,以感谢秋神的保佑[40]。荡秋千作为仪式的象征,传递着生育能力,秋千成为男女交合感孕的神圣场所。宋皇室宗庙祭祀“寒食设秋千”亦可能有着相同的仪式功能。
从起源上说,秋千游戏出自汉武帝后宫祝寿之辞。高承《事物纪原》“一云正作千秋字,为秋千非也。本出自汉宫祝寿辞也。后世语倒为秋千耳。”此说最初见于唐高无际的《汉武帝后庭秋千赋》的序:“况秋千者,千秋也。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戏。”[41]将秋千的起源与汉武帝联系起来,并认为秋千游戏的文化功能在于祝寿。
《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在歌颂武帝的文治武功四海宾服之后,正面铺陈后宫秋千游戏的情形,其首句点名秋千游戏的时间,“当是时也,初度禖燕之辰,未届亲蚕之日”。其时大概在“禖燕”之日后,亲蚕之日前。“禖燕之辰”,指二月高禖祭祀。高禖祭祀是皇室祈求皇子的祭礼,周代已经存在,《礼记·月令》云“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宾御,乃礼天子所御……”[23]631郑玄注之:“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于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23]631燕子被上古先人视为嫁娶的象征、生子的预兆,因此在春分燕来之时,要以太牢祭祀高禖,来祈求皇子。“亲蚕”乃蚕礼,汉代皇后在四月亲自主持蚕礼。《隋书·礼仪志》记载“汉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之立禖祀于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42]。高禖祭祀在秦汉之后不再是常祀,汉武帝因得太子较晚故恢复高禖祭祀。至隋代高禖祭祀仍设在春分之日,以太牢祭祀。然而,春分到亲蚕的四月之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其间恰恰涵盖了寒食清明两节,故此处秋千游戏不排除就是寒食清明荡秋千的习俗。唐代文人诗文写作偏向借古喻今,借汉喻唐。如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汉皇”即唐明皇;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宣室”实际唐室。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不排除其借汉喻唐以讽戒当朝的可能性。“赋”文体特质在于铺排想象,作者极可能借唐代后宫秋千习俗加以铺陈渲染成文。因此,汉武帝后庭是否有秋千之戏,暂时难下定论。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晚年好方术、宠信术士、痴迷于求仙,为求仙,多次听信方士之言,在宫中修建求仙之宫殿、设置求仙的台阁、制备各种求仙器具。“又作栢梁、铜柱、承露仙人掌”,“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而置器具以致天神”[3]72。汉武帝年幼封地为胶东,即今山东胶莱谷地以东,包括现在的威海、烟台、莱州平度、蓬莱、龙口、青岛等地。武帝多次封禅泰山。他信任的术士之中李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等人均为齐人。又据《史记·孝武本纪》载在文成凭借道术“佩六印,贵振天下”后,“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3]73。齐地方术极大地影响了汉武帝的求仙行为。齐地恰恰是有典可查的秋千游戏传播的第一站,山东潍坊、莒北等地现存秋千习俗及文献显示该地区秋千游戏的文化功能为驱灾和祈子。汉武帝朝,齐地的方士极有可能将秋千游戏作为驱灾异祈皇嗣的仪式进献给武帝,以之祝祷他长生不老、国运隆昌。因此,唐人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并非无稽之谈,汉武帝后庭可能确实有秋千之戏,其文化功能实为“祝寿”。但“祝寿”非秋千游戏的原始功能,而是民间秋千游戏进入汉武帝后宫,应君王之喜好而附会衍生出的新意涵。
四、寒食:秋千文化意涵生成的时间场域
作为民俗活动的秋千游戏主要在寒食、清明时节进行,鉴于寒食节和清明节之间的置代关系,本节将聚焦寒食节,讨论秋千游戏的文化意涵。民俗学界对寒食节起源、历史变迁、文化功能的流变等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此不赘述。
节日本身的文化功能是秋千文化意涵的生成的关键情境。寒食节的节俗核心在于“禁火”“改火”。现有文献对寒食“禁火”的记载,首见于桓谭的《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43]。将寒食禁火的习俗归为介之推。曹操的《明罚令》进一步解释了“禁火”的原因,“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之推。……云有废者,乃致雹雪之灾”[44]。认为废除或不履行寒食“禁火”吃冷食的节俗,会触怒神灵,引发自然灾害。寒食节俗经由神化介之推与自然天道的运行联系在一起。
此联系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路史·发挥》云:“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惠民哉?以顺天也。……成周盛时,每岁仲春命司煊氏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季秋纳火,民咸从之时。凡国失火野焚莱,则随之以刑罚。夫然,故天地顺而四时成,气不愆伏,国无疵病,而民以宁。”[45]“改火”“变火”呼应着宇宙运行的规律,关系到民生和国运。自然界四时交替,不同季节的树木生出不同颜色气质的火,周王朝因时制礼,通过“改火”“变火”来沟通人与自然,借由人力对火的控制来控制宇宙运行的规律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季春出火”是四时之始,“禁火”继而“改火”带有除旧迎新的意味。除旧迎新的仪式性在于摒除和抛弃前一个宇宙周期的不完整性,去迎接和塑造新一轮的完整性。此亦除祓的意义之所在,在仪式中驱除前一个周期内的厄运,以洁净的生命迎接新的开始。唐宋之后宫廷和民间寒食节制换新衣的习俗恰为其象征性的文化表征,延续着周礼水滨祓禊之俗礼,“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20世纪90年代,荡秋千的活动在台湾高山族中非常普遍,不论是居住在山区还是居住在平地的高山族,都有此项活动。通常,秋千运动多在农业祭有关的仪式中进行,如曹人、邵人、鲁凯人等。邵人、鲁凯人在春暖花开、风和日暖的日子里举行播种祭时,搭有秋千架,供社里的妇女们荡秋千,纵情欢乐,以象征将来一年中谷物等得到丰收[46]。曹人在播种祭的最后一天傍晚,需采葛蔓,持于树上做秋千,然后到祭田旁的田舍里取出火把,点火持归,携着火把荡秋千,来回5次,而后下秋千,持火把回家,以此火把起灶中火,为之改火,并以新火烤猪肉而食之[46]。“改火”和荡秋千时曹人播种祭与大陆地区古代寒食节习俗的共同点。仪式中荡秋千充当着将新火种传递到炉灶中的重要媒介,既关联着祭田的神圣空间和家灶的世俗空间,又象征着新与旧的交替,具有接引功能。同理邵人、鲁凯人的播种祭女性秋千游戏中,秋千亦作为沟通神人的媒介而存在,在交感巫术的作用下,神灵经由秋千将生育繁殖的能力传递给荡秋千的妇女,以保证谷物丰收。
以叶舒宪教授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张,解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应依托“四重证据法”立论。四重证据包括:传统国学古籍材料、新出土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文字材料、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活态文化、图像与考古实物。曹人播种祭中的荡秋千改火仪式,作为活态文化,不失为古代寒食节改火习俗的文化遗留。据此或可照见古代寒食节秋千游戏的文化功能。荡秋千游戏发生于寒食节的节日场域之内,可能是“改火”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季春出火”的信仰观念使寒食节成为四时之始,具有节宣气候除旧布新的文化内涵。受节日时间场域的规约,荡秋千作为神人沟通的媒介发挥着接引圣俗、转换新旧、传播生育能力的功能。
结论
典籍记载的秋千游戏主要发生于寒食、清明节节俗场域之内,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寒食节禁止和提倡的不同态度,既规约了文献对寒食节的书写方式,也限制了民众庆祝节日的繁简与否。西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的需求屡禁寒食,此时期对寒食的表述多带有抵制和批判的意味,民间寒食节俗活动亦呈现出相对单调的色彩,少有荡秋千等其他相关节俗活动的记载。唐代之后,统治者将寒食定为国假,期间举行国祭,文献对寒食的书写亦相对世俗化、娱乐化,展现出节俗立体丰富的层面,荡秋千、换春衣、镂鸡蛋、斗鸡蛋等民俗游戏方冲破文字的迷障显现真容。
古典文献的书写情境和书写方式遮蔽了民间寒食节俗的本相,这导致了历代学人对秋千游戏的单向度认知。现代民俗学、人类学对人类文化遗存的发掘和探讨,则有助于现代人接近文化遗产的本相。拣选参详现存各地各民族秋千游戏的民族民俗资料,秋千游戏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消灾、丰产、祈子为其主要的文化功能。这与中国古代寒食节本身所具有的节宣四时、除旧布新的节日内涵相契合。荡秋千可能是寒食清明节重要的祈福仪式,通过荡秋千来驱邪、祈求婚姻美满多子多福。仪式中,荡秋千与传宗接代、人类的繁衍的义务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游戏的理性驱使人们加入其中完成义务履行责任,故而荡秋千成为历代宫廷和各地民间寒食清明重要的游艺活动。惟其如此,有宋一代才将寒食秋千与上元灯楼、七夕摩睺罗一起,设置于宗庙之内以之祭奠先祖。《事物纪原》对于秋千游戏的起源和传播的梳理,虽有失简陋,但“山戎”“寒食”“女子”“祝寿”等关键词之内隐含着上述文化意义。惟囿于文字书写历史的传统,忽略了活态的民间节俗,难以呈现事物的原貌。
[1]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5.
[2]皇甫谧,宋翔凤,钱宝塘,刘晓东.逸周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62.
[3]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3.
[4]宋坤.中国孤竹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61.
[5]钱林书.春秋战国时齐国的疆域及政区[C]//复旦史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立七十周年纪念(1925-1995)论文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内部资料,1995:403.
[6]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第8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7]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
[8]周振甫.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第5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9:1716.
[9]周振甫.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第13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9:5190.
[10]宗懔.荆楚岁时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12.
[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70.
[12]脱脱,等.宋史2[M].北京:中华书局,1992:1766.
[13]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03.
[14]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79.
[15]李开先.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7.
[16]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50-151.
[17]杨米人.清北京竹枝词十三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64.
[18]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5-6.
[19]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8:439.
[20]高濂.遵生八笺[M].成都:巴蜀书社,1992:113.
[21]陈元靓.岁时广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165-166.
[22]张光直.美术、神话和祭祀[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27.
[23]郑玄.礼记正义: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4]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5.
[25]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91.
[2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78.
[27]李曼.唐代上元节俗的历史考察[D].陕西师范大学,2014:10.
[28]正威仪经[C].道藏:第18册,257-258.
[29]佛说护身命经[M]//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702.
[30]张尔岐.蒿菴集·蒿菴集捃逸·蒿菴闲话[M].济南:齐鲁书社,1991:338.
[31]华夫.中国古代名物大典[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1485.
[32]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43.
[3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3:8.
[34]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M].台湾: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557
[35]许嘉璐.中国古代礼俗辞典[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357.
[36]莒县政协.莒北秋千节[J].春秋,2011(3).
[37]杜友龙.民俗娱乐·民俗运动和古老项目[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46.
[38]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第8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208-209.
[39]周巍峙.中国节日志(山西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210.
[40]魏玮.秋千的生育信仰功能研究——以山东潍坊地区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2010:29.
[41]李昉,宫梦仁.文苑英华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22-123.
[42]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46.
[43]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47.
[44]杜台卿.玉烛宝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1-122.
[45]罗泌.路史发挥[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2.
[46]石奕龙.风情万种的高山族飞天之戏——荡秋千[J].台声杂志,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