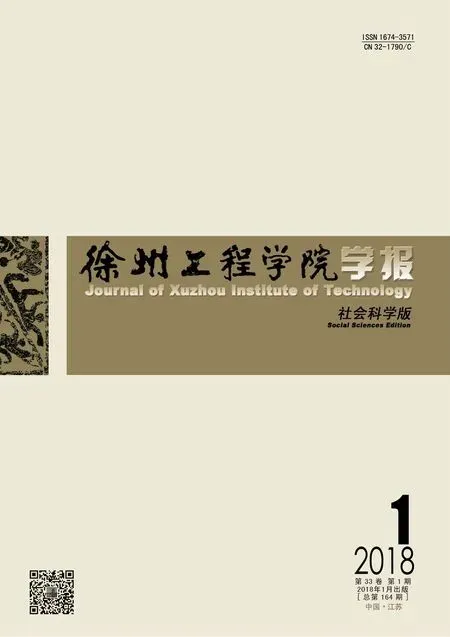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认同
杨年丰
(徐州工程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文天祥(1236-1282),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文天祥21岁进士及第,被理宗擢为状元。他年少有为,才学突出,却生逢南宋末世,仕途崚嶒、屡遭贬谪。宋咸淳三年(1267)元朝攻打南宋重镇襄阳,四年后,忽必烈改国号“大元”,元军向南节节进逼。文天祥“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1]480,德祐元年(1275),奉召勤王,“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1]486。南宋君臣在和与战问题上首鼠两端。经历了一系列的矢志抗元、复兴宋室的活动后,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在五坡岭猝遇元军被俘,元至元十九年(1282)就义于元大都(今北京)。
七百余年来,文天祥一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诗文更是屡屡成为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如《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自他逝后,对他的祭祀一直未断,其诗文也不断被整理付梓,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对他的景仰也未停止,即使是在元朝当代,统治者也允许他的塑像和牌位奉入学宫,明清两代,更是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形成了对文天祥的形象记忆和身份认同。
一、志士成仁——从生祭到死祀
南宋景炎三年,文天祥在五坡岭被元兵所俘,此时,厓山行朝已经覆灭,作为南宋状元丞相的身份被俘,文天祥的生死大节引人关注,“天留中子继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早年曾追随文天祥一道抗元的王炎午与友人刘尧举谈及此事:“丞相见执,就义未闻,豪杰之见,固难测识。”王炎午认为文天祥被囚,只有以死存节,遂作了《闻文丞相被执作生祭文》。这篇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生祭文”以沉恸感泣的笔调,历陈文丞相“可死”之义:“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西,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蹡,子胥脱走,可死。”[1]795-796王炎午担心的是“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祭文反复说明古今忠臣死节之道,强调若文天祥以死国之忠,可为万世立纲常之表,辞恳情挚,奋发激昂。对于这篇祭文,茅坤称赞其“一段激劝至情,千古可掬”,易代之际,“不有死者,无以见道之界”[2]276-279。文天祥个人的生死之情,系挂的是民族大义,“以文丞相忠义,死固其寻常事,不应以此薄待之;然事关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为”。文天祥被元朝刑戮,王炎午作了《望祭文丞相文》,说他为“扶颠持危”的“名相烈士”,其精神光照日月星辰,“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文天祥的就义体现了成就忠君与自我道德实践的意义,数百年来一直为士人所景仰。中国历来有“忠”的传统。先秦时,忠还是相对广泛的道德原则,带有双向的约束性。随帝制的演进,官方史书常以表彰忠节来提高忠臣地位,尤其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创立了《死节传》《死事传》,对儒家士人而言的君臣关系中的“忠”作了重新界定:臣对君单向的“忠”。这种所谓的“忠”,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道德之完成,这是一种不计成败的道德自我实践[3]。
宋代受理学运动的影响,地方上常建立先贤祠,祭祀对象通常是作为地方士人典型的先贤。这些先贤常为出身、仕宦或寓居地方的“乡先生”“乡贤”。这些祭祀及祠庙的活动,许多是地方的自发行为。士大夫作为地方精英,重视乡里关怀,积极推动设立先贤祠,还以地方史志书写的形式留传。地方精英通过这些形式,目的在于展现地方意识、凝聚地方认同,进而是构建地方文化传统。
除了上述地方上以先贤祠的形式表达纪念,文天祥死节的形象还广为士人以诗文作品形式歌咏,如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汪元量的《浮丘道人招魂歌》等,类似真挚感人的作品在明人程敏政所辑《宋遗民录》中还有很多。
在与宋末情形相似的明清之际,文天祥更为忠臣义士所模仿类比,特别成为殉国者寻求人格认同的对象。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被发现于苏州承天寺古井中。郑思肖未曾见过文天祥,但对他十分景仰,《心史》中便收入许多颂扬文天祥的诗文,知名的如《文丞相叙》。《心史》“侃侃铁笔,直攄愤懑”[4]303,《心史》出土后得以刊刻并流传后世,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天祥与郑思肖的忠节形象,也在清初成为许多明遗民的心灵寄托。宋以后,在理学环境下,各朝逐渐重视臣节,对文天祥死节的评价也产生极大影响,各地出现奉祀文天祥的现象:“百世而下,祀公于所生之乡、所死之地、所经历之境、几遍方域矣。”*《江南通志》,赵宏恩等监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天祥成为南宋以后忠贞正义的化身。
二、留取丹心照汗青——自传与他传中的形象记忆
文天祥死后,关于他的记忆透过各种形式留下记录,慢慢渗透到士人心中。王炎午、谢翱等人哀悼的诗文可说是最早的追忆,这些诗文固然表明时人对文天祥之死的纪念与敬重之意,但仅靠这些诗文流传保持这种记忆,随着时间日久,恐必逐渐被遗忘。
文天祥生平所作诗文丰赡,颠沛流离、起兵勤王、狱中经历等都有诗文记载,尤其为人熟知,如《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纪年录》等后期诗作,更是其表明心志的代表。诗文提供了后人回忆的机会,也成为后人为其作传、歌咏的凭据。文天祥的诗词与传记在元末明初首先建立了关于文天祥的记忆。他在元代以降逐渐为人所知,上面的诗作有关键性影响。元末明初时的陶宗仪就曾说:“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5]52
文天祥早年对诗歌的看法是“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主张诗以非有意为之为高。但其后期诗歌明显转向有意识、反复地表白自己的心志[6]295。“是用血和泪,是用他整个生命写成的。”[1]“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1]621如《指南录》即是记德祐二年(1276)于皋亭议和被拘,乘隙自镇江脱逃,南下至温州欲与宋王室会合的经历;《指南后录》(又称《文山诗史》)则是记五坡岭兵败被执,自广东被押解往燕京北行历程,及在燕京狱中生活;《纪年录》则是在狱中时所写自传。这些后期诗文是了解宋末抗元史事及文天祥生平的重要史料,也是后世颂扬文天祥或褒奖忠节时常引用的材料。他的诗文作品也不断被后人收藏整理,如元时所刻道体堂版《文山集》元末毁于战火,但一些吉安士人家中仍有收藏,“乡郡旧尝刻公遗文,兵后板废,今士大夫家间存其本”。永乐十四年(1416),杨士奇在京师见到文天祥《集杜诗》和邓光荐《文山督府忠义传》,即抄录收藏,并为作跋。*宋遗民邓光荐曾作《文丞相传》《督府忠义传》,其中《文丞相传》已不传,杨士奇所见的是《督府忠义传》及刘岳申所作《文丞相传》。刘伯涵、朱海点校,杨士奇著《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7页。
明景泰年间,为《文山集》作序的李奎云:“稽诸往代忠臣烈士能以节义文章为世崇者,亦莫有出之公右矣。或曰:‘文章特余事耳,曷足系公之重?’予独曰:‘不然。’文章乃忠节之英华,忠节非文章无自而著。斯集也,又所以发公幽潜之光,不特为一时人臣劝,殆欲风厉天下万世,俾民食君之禄者,人人以忠节自励。”“文章乃忠节之英华,忠节非文章无自而著”点明:人臣的忠节需要透过文章才能得以突显![1]
与文天祥相比,同时期抗元的,如陆秀夫、张世杰等人,虽然在事迹与经历上较文天祥更为丰富或曲折,但都没有留下太多表明心志的文字,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后人对他们的了解。文天祥所作诗文作品,为后人提供了追忆的线索,他曾歌咏的地方也成为名迹,成为士人怀古、吊古、追忆往事的地方,如著名的惶恐滩,清康熙初年,明遗民方以智于此悲壮自沉,即是在人格的认同,并追随文天祥的心志[7]164-200。
文天祥誓不降元,但元人一样给予这位忠臣很高的评价:“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8]12533-12540编纂者先以伯夷、叔齐之例,说明文天祥起兵勤王之举虽明知其不可为,但成就了自古士人所追求的“仁”。科举出身且身为状元的文天祥视死如归,更证明了宋代以科举取士的成效,也可作为士人效法的目标。作为官方史书,虽然所记载内容会有争议,如有认为内容简略失当,甚至有贬低文天祥之意的,但作为正史,以其权威性成为士人认识文天祥的重要资料和途径。
其实,宋史成书前,吉安士人刘岳申已作有《文丞相传》,刘岳申与文天祥嗣子文升交厚,他又参考文天祥著作,利用遗老的传闻,撰写该传。刘岳申《文丞相传》在内容上较宋史本传丰富,并影响宋史文天祥本传的内容。其赞云:“殆天以丞相报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疏阔,论其无成,谬矣!夫非诸葛公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乎!”在崇敬之情外,刘岳申认为文天祥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宋亡,都是天运使然。文天祥历经各种死境却未死,最后却死于燕京,可说是“死得其所”,因为“天以丞相报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也是从天运而说。赞中所言“或者咎其疏阔,论其无成”,也应该是时人对文天祥并非全面正确的批评[1]。
明初,胡广曾对《宋史·文天祥传》与刘岳申《文丞相传》的优劣有一番评论:“广集庐陵先贤传,恒病《宋史·文天祥传》简略失实。盖后来史臣为当时忌讳,多所删削,又事间有抵牾。乡先生前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为丞相传,比国史为详。大要其去丞相未远,乡邦遗老犹有存者,得于见闻为多,又必参诸丞相年谱及《指南录》诸编,故事迹核实可征。故元元统初,丞相之孙富既以刻梓,后复刊见《岳申文集》。近年,乐平文学夏伯时亦以锓板。于是,岳申所撰丞相传盛行于天下,而史传人盖少见。”*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 。这段话同时揭示了文天祥传在明初流传的情况:刘岳申“所撰丞相传盛行于天下”,而《宋史》中的本传“人盖少见”。从上面对二文的比较可以看出,刘岳申所撰传时间上距文天祥逝去不远,宋朝遗老还在,见闻可靠,真实有据。胡广兼采正史与刘传内容互参考订,并取证于文天祥的文集,也撰写出《文丞相传》,其后,包括明代黄淳、曾皋,清代郭景昌、赖良鸣等,屡以传记形式追忆文天祥其人其事,但所作传内容上均不出刘岳申所作及《宋史》本传。刘岳申所作及《宋史》本传二传成为后世士人写作文天祥传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无论是时人歌咏、还是文天祥的诗文或是文天祥传记,内容上不尽相同,可强调文天祥的忠义与死节一致,几乎都围绕文天祥之死来立论。其实文天祥仕宦及勤王的经历并没有显著的事功,然而皆由于其“死得其所”,“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宋绪:《元诗体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自己所作诗文作品留给后人了解、认识、追忆他的事迹的机会,后人并透过传记、诗文作品,为他建立起忠烈的形象,内容焦点都在他以死节成仁取义、报宋室养士之效,这也成为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留传的基本面貌。
因文天祥其人其事的记忆与留传,在明清时期甚至还产生了传奇色彩。景炎二年,文天祥所部收复梅州,欲复江西,派部将攻下兴国不久,兵进赣州,时元将李恒遣兵援赣,大败文天祥军队,文天祥也仅以身免。史称空坑之役。《宋史》记载:“江西宣慰使李恒援兵赣州,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邹沨于永丰。沨兵先溃,恒穷追天祥方石岭。巩信拒战,箭被体,死之。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但作于前的刘岳申《文丞相传》中所载的情节颇有戏剧性:“元帅李恒以大军乘其弊,追及于庐陵东固之方石岭,都统制巩信驻军岭上力战,箭被体不动,犹手杀数十人,乃自投崖死。大军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溃,天祥几被执,值山径险隘,有大石忽坠,塞其路,乃得脱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当时有吉水人萧文琬“督馈饷”幸而不死,“退而笔记是日事甚详”,所以明代谢缙补充:“宋丞相信国文公兵败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数间屋,忽然自山顶震落当路径。元兵望而大惊,稍却,丞相由是得脱去。邹沨辈以余兵拒战。”*此处为转引,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十二《萧君师文墓表》,清乾隆三十二年吉水解氏敦仁堂刻本。[6]200。“石大如数间屋”,“自山顶震落当路径”,情节更加具体细致。而相石的传说在江西就有永丰、庐陵、兴国等几个地方,清初遗民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载有“相石”传说,内容一致,地点却被附会到了广东潮阳。康熙末年,张尚瑗《潋水志林》考辨此事,认为“相石”传说虽“旧时志兴国者,亦皆引之”,其实是对“大贤名迹,好事者乐为傅会,以资美谈”,但作为志书“著以传,著不可误也”[9]10。
张尚瑗身为地方官,以“著以传,著不可误也”的标准编纂志书,考辨文天祥兴国之战,重视的是这些史事是否可征而信。他还在知县任内特别厘正兴国县内的祀典,带着地方官的使命感。方志本身可说是集政治、教化、修史为一身,有时也能反映一地士人所试图营造的地域认同与地方特色[10]327-328,是记录地方共同的历史记忆,对于兴国地方的士人来说,相石传说代表着家乡与文天祥之间重要的历史记忆,且这种记忆也早已深入地方。透过地方志的书写,将这种记忆反复记录,不断强化文天祥与本地的联系。
三、从文丞相祠到九贤祠——中央与地方系统中的身份认同
“凛凛宋忠臣,赫赫元世祖。礼遇各有道,声光照千古。”*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28册)。这是姚广孝在明永乐年间拜谒北京文丞相祠后所作诗的四句。元代对文天祥及其后人礼遇有加,然而因为政治原因,文天祥死后一直没有专祠的建立。入明后,刘崧任北平按察副使时感慨:“丞相当宋亡之三年使被执留燕,五年而就义。又后九十三年,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求丞相当日事,罕有能言者,盖遗老尽矣。没追忆高风伟烈而不可见。”*刘崧:《槎翁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24册)。洪武九年,刘崧在大兴县学(后改为顺天府学)西设立文丞相祠,并把此处作为文天祥死节的柴市,建立“教忠坊”。永乐六年(1408年),太常寺少卿刘履节以“天祥忠于宋室,而燕京乃其死节之所”,请求为北平的文丞相祠“正祀典”。至此,北平文丞相祠正式入祀,责成顺天府官在每年二月、八月中旬,以少牢之礼致祭,祠庙成为京师九庙之一[11]1305-1306。
北京是文天祥的死节之地,刘崧选择在此为文天祥立祠,但建祠及入祀典的时候,北京还不是首都,所以文丞相祠还只是像庐陵地区的文丞相祠一样,仅是一般地方上的先贤祠庙。永乐十九年,成祖当权,定都北京,这时的文丞相祠就具有了代表性意义,“公死于燕京,今顺天有祠,所以风天下也”*平观澜修:《乾隆庐陵县志》,黄有恒、钱时雍纂,乾隆四十六年。。因为建祠是在京师,文丞相祠就具有了“风天下”的代表性意义,已非最初作为地方性的先贤祠所能比拟的了。此后,许多士人到了京师后,或是官员在京师任职的,拜谒文丞相祠成为他们常见的活动,*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且,文丞相祠在府学旁边,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教化意义,历次顺天府学重修时也多会将文丞相祠加以修葺。*沈应文:《万历顺天府志》,张元芳纂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此后,明清两朝帝君都对文天祥忠义之名大加褒扬。如明宣德二年,宣宗遣官致祭褒奖其忠义:“人臣之义,当务尽忠。此人心如铁石,元君百方诱之,终不屈,可谓万世不磨。”[12]658此后每年春秋仲月遣官致祭才成为定例。正统元年(1436年),河南布政使李昌祺提出追谥[12]407-408,景泰七年(1456年),韩雍上奏,为文天祥、谢枋得追谥[12]5734-5735。
清代皇帝对文天祥也非常推崇,如康熙帝赞扬文天祥“其忠君忧国之诚,洵足以弥宇宙而贯金石”*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即位后就将文天祥等40位历代功臣从祀历代帝王庙;苏州的忠烈祠获得朝廷的资助重修。乾隆帝即位不久就撰写了《文天祥论》,来肯定文天祥的忠节。对宋代以来因理学的影响,越来越重视纲常、人臣之义的士人而言,文天祥自然是应该效法的典范之一。不论和平还是战时,上述这些在京师由皇帝亲自主持或参与的祭祀及追谥活动,都是用来激励臣节的方法。
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今吉安),“吉为江右上郡”,被吉安士人推为乡里先贤之首的就是北宋的欧阳修,南宋以来,吉安士人逐渐形成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南宋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与庐陵赵汝厦在庐陵县学内建三忠堂,祭祀欧阳修、杨邦乂、胡铨三位庐陵乡贤。这三位都是维系国家纲常的重要人物,建祠崇祀就有浓厚的教化用意,其中也包含了地方士人对有功社稷的乡贤的崇敬。南宋末年,州守李芾曾“集四忠一节行状、铭碑、谥议,刻之郡斋,名《景行编》”*刘将孙:《养吾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于州城南立祠祭祀。文天祥少年时游学宫,见学宫中所祀欧阳修等四忠一节乡贤像,就发出“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自许[1]。“四忠一节”都是吉安人,也自然成为吉安士人效法的典范,文天祥在广东五坡岭被俘,翌年元宵节作《元夕》诗感怀:“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世事争强弱,人情尚废兴,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1]349“死不愧庐陵”正呼应了他少年时在学宫拜谒乡贤的自我期许。
曾作《文丞相传》的刘岳申认为吉安风俗有三:好文学而尚节义;其次好治生而尚敦朴;其次好奉上而尚悫愿。*刘岳申:《申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岳申为代表的吉安士人一直试图营造本地为忠节之邦,士人们在为地方的各种祠庙或儒学作记时,总反复述说“四忠一节”诸贤传承的关系,“欧阳公以道德明秀可为公卿望吉士。其后,忠襄杨公、忠简胡公、文忠周公、文节杨公,相继迭兴,至丞相文信公,独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不辱庐陵”*平观澜修:《乾隆庐陵县志》,黄有恒、钱时雍纂,乾隆四十六年。。元代庐陵士人彭士奇曾编《庐陵九贤事实录》,收欧阳修、欧阳珣、欧阳守道、杨邦乂、杨万里、胡铨、胡梦昱、周必大、文天祥等九位出身吉安的忠节乡贤事迹。明初吉安府学内的明伦堂就建有“九贤祠”。无论是“四忠一节”还是“九贤”,这些乡贤事迹的宣扬,代表吉安士人对地方文化特色和传统的标榜,也正是由于地方士人的不断推崇,吉安地区才会不断涌现忠节士人的形象,也才会形成崇尚节义的风气,“四忠一节”“九贤”等成为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士人效法的典型,更成为地方传统中的历史记忆。
正德初年,吉安出身的前翰林学士尹直为庐陵所撰文丞相忠义祠记云:“夫忠义系于世教,历代推褒,正以励臣节,式不轨也。肆我太祖高皇帝,一区宇之后,即祀公就义之所。永乐初,既饬公祠。景泰中,又易公名。孝宗皇帝,特允臣言,建庙称禋溥及督府诸忠义。一时台省忠良,奉扬休命,贤愚歆慕,益知人臣死忠,弥久弥彰,而感激之心,勃勃如也。”[13]171
通过官方倡导、士绅精英的弘扬、民众的景仰,祭祀文天祥的祠庙遍布其家乡、任职地、所经之处和遇害之地,文天祥作为“忠君爱国”的典范,名垂青史,俎豆千秋[14]108-113。
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这些祠庙与古迹的象征意义就更加显得突出。明清之际,士人面临与宋元之际相似的情境,“说宋”的风气更胜于以往,更有不少士人至南宋忠臣的相关遗迹处凭吊以明志,因为这些遗迹不仅是与文天祥相关,其存在也是提醒士人政权更替的事实,并提供了以怀古排遣自身境遇的场所。
明清之际,追寻、效法文天祥的士人就很多,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铨明亡后随同乡揭重熙募兵抗清,失败被捕,被要求作书招降揭重熙,他引《过零丁洋》诗拒绝。在狱中曾赋《正命铭》:“经严猾夏,义大复仇。民安弗获,主辱何求。生不负学,死不降志;取义存仁,庶毕吾事。”[15]377后四句语意与“衣带赞”无几。与文天祥同样状元出身、曾入内阁的文震孟,向以忠节著称,时人将其与文天祥并称,在苏州素负声望,他直言上疏对抗阉党,被视为如文天祥转世。文震孟之子文乘鼎革之际起兵抗清,事败被执,临刑不忘追寻先祖:“临刑时,南拜三、北拜三,伸颈就戮,神色不改。衣带中有绝命词曰:‘阀阅名家旧姓文,一身报国九原闻;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卧白云。’复大声曰:‘吾祔信国祠,公其许我!’”[26]
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以前的、已经成为过去的的时代,纵然是后起的时代,也渴望它的后代能记住它,给它以公正的评价,这是文化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正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这里有一条回忆的链锁,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臆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及其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场景和典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人的历史充仞其间,人性在其中错综交错,织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人的阅历由此而得到集中体现[16]21,32。
文天祥足迹遍及各地,且写下大量的纪行诗表明心志并供后人追忆,也成为后人为其作传、歌咏时的凭据。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而集体记忆有其对应的群体,并透过不断回忆的方式凝聚认同感。中央和地方的祠庙及祭祀活动也提供了士人追忆忠节形象的场合,这样,士人们借助于集体记忆的媒介——诗文、传记作品、祭祀活动等保存与强化记忆,建立起时空转换中关于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身份认同。
[1]文天祥.文天祥全集[M].熊飞,漆身起,黄顺强,等,校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2]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3]王赓武.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M]//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4]郑所南.心史[M].陈福康,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修晓波.文天祥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M].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张尚瑗.潋水志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1985.
[10]吕妙芬.阳明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M].济南:新星出版社,2006.
[11]张廷玉,杨椿,汪由敦,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董伦,解缙,杨士奇,等.明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萧赓韶.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M]//中国祠墓志丛刊本:第30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
[14]高茂兵.文天祥祠考论[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29).
[15]张岱.石匮书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6]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