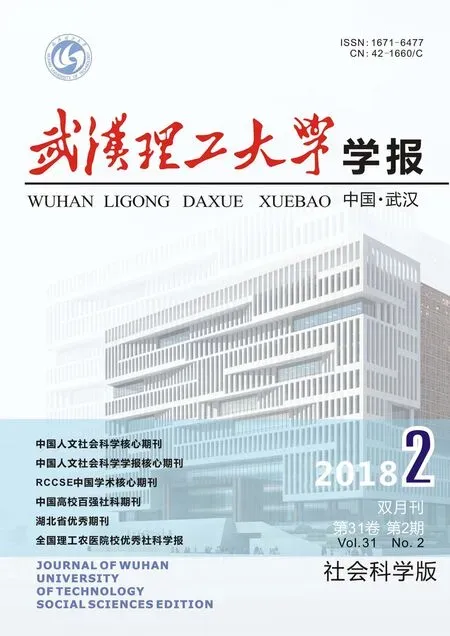中国艺术历史的当下问题
周韶华
(中国国家画院 国画院,北京 100048)
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内在的逻辑,艺术作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有着明晰的发展规律。在受到某些外在冲击的时候,文化基因有着发生突变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会出现不同于原来轨迹的情况,但这种变化依旧是有规律的。这种时期,往往也是文化发展的困惑期。
近代中国艺术的发展,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文化突变过程。进入明清时期,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困难阶段。艺术何去何从本来应该成为当时的艺术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是封建统治的政治性、民族性问题成为了具有一定“建设”意义的历史因素,将艺术安置于“不创只续”的阶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方文明的介入,导致了“华夷之辨”。在政治和经济上,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其实也是文化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现,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陷入阐释的冲突。中国艺术遇到了西方文明的强行介入,在战争的炮火里痛苦地明白了自己故步自封的末路。这让文化和艺术自身更加迷惑,但同时也敞开了一条以前都没有走过的路。
面对未知和困境,敢于突破的人往往要承受更多的批评,但是这条路却必须要走。否则,就只会重复而无发展。到了当代,更多的问题,也伴随着更多的机遇摆在我们面前,谁能迈出第一步?这一步应该是思想意识与文化自觉:必须要明白,中国艺术并不是中国古代艺术,而是中国文化体系下发展出来的艺术。我们以前的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的有机衍生体。当古代文化走到尽头的时候,古代艺术也就失去了成长环境。我们现在发展了中国的新文化,而新文化体系下很多艺术家还在坚持古代艺术的形式和体系。谁能够去思考新文化体系下的艺术问题,而且是多元文化下的艺术体系?同时也要追问,原因是什么。时代在催促着我们反思。
艺术问题之所以不好解决,是因为必须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双轨问题。其实,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在理论问题上基本找到了解决方法,但还存在没有思考清楚的问题,需要根据时势推进来突破,但这些学者并没有实际操作的能力。理论自洽,相对容易,但是实践又是另外一套系统。二者的结合并非想象和希望的那样顺利。理论自洽,并不一定能与实践结合,能与实践结合的自洽理论,还需要不断寻找结合的方法和途径。理论是时间的结合,庞杂到可以成为一个学科,但是却被忽略了。这也就更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游离。我认为,当代中国艺术最大的问题,在于超越和突破。中国艺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优势,但是历史悠久,惯性就越大,突破也就越困难。并不是说中国的艺术家不想寻求突破,但是历史的力量太大,尤其在历史体系面前,突破其实是时代问题。我认为,艺术在现代的超越和突破,主要表现在媒介材料问题和神韵问题上。
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媒介材料是形式变革的重要因素。现代的媒材无比的丰富,充分运用各种媒材,艺术才可能有超越的物质和形式条件。当下每年都要搞“兰亭展览”,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重复二王的风格,媒材并没有取得很好的革新。太多的艺术流于形式框架的束缚——没有哪个艺术理论断言,中国画只能宣纸和毛笔,不能用油画棒——尤其在当下日新月异的技术面前,很多新的材料和形式应该进入艺术家的视野。我们对比西画的发展,每一次优化工具、颜料的革新,都带来技法上的极大提高,技法的提高又带来更丰富的内容,进一步带来观念和视角的变化。我觉得时间和空间,都应该成为表现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一味地求新就是好的形式。现在太多所谓的创新艺术,国内看不懂,国外也看不懂。这类艺术其实已经脱离了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更算不上是艺术的基因突变,只能算是脉络之外的横空出世。没有根基的事物都是游离的状态,没有办法在艺术发展史上留下一笔,而只能是短暂一时的哗众取宠。每一个重要的艺术家、大哲学家、物理学家,都是在相关的行业发展史上有着他的位置,都是行业历史的缔造者。我们日后可能的艺术载体,应该是人类文明史的逻辑产物,而艺术却在这种逻辑下迷失了。盲目地求新求变,追求所谓的不一样的东西,恰恰是对自己行业发展逻辑和历史不了解的表现。在物理学上,牛顿、洛伦兹、爱因斯坦、薛定谔、霍金,每个人都在物理学发展史上有着自己的地位,而且发展轨迹非常清晰,没有哪个人突然自己制造出一个逻辑外的理论。虽然艺术属于人文学科,但是翻开哲学史、文学史,有着同样的脉络。艺术属于自由的范畴,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但是不能不讲道理地想象。
我们很多艺术家之所以求新求变,是因为看到西方文明体系下的很多艺术过于大胆。但是没有看到那些艺术之所以发生突变,恰恰是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不了解别人的文化,如何了解这种变化的本质?举例来说,“印象派”看似和以前的艺术出现断层错位,实则归根于光学的发展。没有牛顿的三棱镜,也就很难有现代色彩的基本概念,这是西方物理文明对艺术形式的必然影响。毕加索的作品,又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哲学条件紧密相关。很多艺术受到后现代哲学的影响极大,看似矛盾的艺术形式,恰恰是文化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些艺术形式并不怪异,而是合理。
反观我们当下国内的艺术,看似合理的表现,恰恰是不合理的东西。在现代文明和新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审视以前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就会感到过于保守、过于老套。而那些一味求新的艺术形式,也常常都游离于历史逻辑之外。
第二个层面,就是表现内容的问题。现在的很多艺术家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兰亭碑帖之类,并不是说题材老套,而是表现形式和思维形式没有创新。历史是一个宝库,以前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作为关照对象,但是当下的事物不能被我们忽略,将来可能的事物也可以成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国风归来》《大风吹宇宙》《大河寻源》等,都是极大地扩展了绘画的表现范围。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一直在反思中国的艺术创作,感到中国艺术的发展创新问题非常严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上来”。举国上下都形成一种新的风气,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唤醒和启发。我们面临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思路是什么?于是我不断思考艺术的发展方向。从文化的角度上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呼唤民族大灵魂,唤醒中国文化精神。那民族灵魂和文化精神又是什么呢?不是空想,要去寻找。于是第一个思想就是大河寻源,寻找文化之源——中国文化五千年是如何走出来的。行动之前,必须阅读。梳理文化的脉络,而后沿着线索寻找源头。我认为水是文明之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都在青海,那里有着很深的文明根源。中国文化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海洋文化——这就是“三大战役”。
我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黄河、长江、大海”三部曲,追溯民族大灵魂,考察民族源头,追求民族文化大复兴,找到了很多表现素材。但历史的器物不能直接搬上画面,必须要进行艺术的创作。所以直到2013年才全面铺开。我曾经追溯到商周青铜器、仰韶文化、甲骨文,这些内容里面蕴藏着太多的艺术精髓,内容庞杂、难度太大,既成体系也有些零碎。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寻找新的感觉。人们必须注意历史的精彩之处,例如画像石,现代绘画艺术很难达到那时候的造型程度,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帛书,均美不胜收。但是,这绝对不是仅仅的拿来主义,我们需要用现代的意识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否则艺术的历史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回到了过去。关键还是思考问题的方法、思路。在这些历史面前,现代的思维非常重要,否则就会被历史比下去。
在时间方面,首先要明白历史文化究竟是什么。进行大量阅读,搜索历史的脉络,才能明白历史符号的内在精神。而空间方面,就需要行万里路。我的艺术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孤身一人上过高山,下过大海,进过无人区,就是用生命在创作。考察长江时,很多人是坐着游船在江面上取景,但我一定要站在高山上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长江。从宜昌看到重庆,全方位、多角度、广泛取景,深度考察长江的内在气质。无论艺术表现的对象是什么,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思考和表达方式。
我在80年代做出来三大架构。《梦溯仰韶》《汉唐雄风》这些都是黄河仰韶文化的侧面,《荆楚狂歌》是长江文化的内容。同时,通过《荆楚狂歌》发现了民间美术的精彩之处。《国风归来》源于《诗经》的《国风》。2008年时我正值80岁,长江、黄河、大海告一段落。而面对着此时的人生阶段,我在思考后面还能再做些什么?我认为应该是超越问题。中国绘画要超越,不仅需要跨越时间维度,更要跨越空间维度。但是人们的观念是非常难以突破的,过去是艺术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封闭系统,人们有一种思维定势。好像国画离开了诗书画印就不是中国艺术,如果想要超越的话,最好就是超越三界九天外,跨越空间。于是我把视角转向了空间,就有了《星空系列》。
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但是这确实不应该惊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之道,岂在表里?而是既表且里,表里之间,周乎万物。以前的表现对象,都是肉眼可见的,既不是宏观的天体世界,也不是微观的量子世界。而现在我们有扫描隧道显微镜,有射电望远镜,可以看到大量的周遭之外的世界,人类的认识能力空前地发展。为什么这些宏观和微观的世界不能成为我们表现的对象呢?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是艺术观察视角的革命,而宇宙和粒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表现对象的革命。我个人认为,那些被物理学推理出来的,但是还没有被证实的,都可以成为中国艺术形式的表现对象。
其实宇宙题材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因为这个题材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突破。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对宇宙的思考,那么康德哲学是不会形成系统的体系的,人类对自我认知规律的思考很可能就呈现出另外一个状态。回到艺术角度,如果缺少了认知系统,那么《判断力批判》的美感问题就会有极大的缺失。面对宇宙,我们要敬畏又要审美。而我认为现在对宇宙的认知,应该颠覆康德类似“物自体”的那些概念,而我们现在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也远远超越了当时所谓的认知结构形式。
因此,无论艺术对时间、空间的概念,还是在审美和认知上的超越,都很有可能成为不同文明历史的脉络交叉点。艺术的每个节点,都是历史。它和哲学史、物理史,都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理应相互关联,不应独立。而所谓的超越,不是横空出世,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推动历史的发展。
第三个层面,就是中国艺术的精神。很多艺术工作者对艺术精神的“信条”倒背如流,但也只是照本宣科,其中缺少创新的内容,而且即使有超越传统的某些感觉,也大都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不都能够在实践当中呈现出来。如果没有了中国艺术的精神,那就丢了根本。
在三江源,我最大的收获是用艺术去感受生活。在早期的西方美术,最基本的观念就是实证主义,要追求物质性,追求物理世界的本质。而中国文化是讲精神的,讲意象、心相,强调心灵世界。去研究一下现在的艺术发展脉络,就可以发现,很多艺术忽略了心性、灵性、意境等。到了三江源,我就发现艺术的那种气场。绘画是否有氛围,取决于是否进入那个气场。进入之后就会灵气勃勃,有如天构,形成天人合一,天地同源。真正的大象,就是天地人的同一。现在的艺术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进入艺术本身,没有进入艺术的境界。现在的艺术家受到的干扰很多,很多问题还真不是艺术的问题,而是艺术周边的问题。
我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句话——戏剧表演首先是进入角色。进入角色之后,表演的那个人才是角色的生活,而不是演员表演的那个人,否则就是表现演员自己,而不是表演角色的精神世界,不是表演的艺术。老子讲“大象无形”,没有形态的东西,如何去琢磨?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感悟,一种精神的感悟。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气,是浑然一体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气场。艺术是一个大的气场,进入中国的精神世界,要区别于西方艺术的实证主义。从“场”来理解艺术,回到心灵气场。立书尽言,言不尽意,要做到深刻的理解,除了画像之外还必须传神。感受自然的精神,感受生态,不是艺术家本身,也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艺术家结合了自然本身。就在这个场域中,艺术自己不断地生发、展开,形成这个场域中的一片天地。你说这是海德格尔的东西也好,说是黑格尔的理论也罢,但这确实是中国艺术的生命经络。一定要有精神的自由。
为了明白宇宙问题,我征求了很多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包括天文台的一些专家的意见。我认为时间是无限的,但是他们并不赞成。按照目前理论物理的理解,我们可视的范围内的宇宙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河外星云我们不容易观察。我很小的时候,在威海老家观察天空,银河系是分层次的,大小远近,层次立体而非平面化的。后来我到了青海无人区去考察星空,感觉可以伸手揽月,就在眼前。宇宙系列就是要解决超越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进行跨越,而且同时做到自然和自由的跨界。我在猜想,时间可能是很短的一个维度,但是鉴于它和空间、质量的关系,它可能在延长、缩短、弯曲,各种错综纠缠,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时间、空间、质量系统。我无法知道这种猜想是否在物理学上是正确的,但是我却能够保证这在艺术层面上它就是正确的。这是精神自由的尺度下形成的情态表现。何谓对?何谓错?基于自然的基础上,表现情态的自由,这是人类在“自然”和“自由”之间的伟大畅游。我有个方章,叫“攻克不可能”,要跳出艺术的维度来看艺术,这就要有超越、跨界的思维。艺术是包容的,是想象力的。在战国时期、魏晋时期,文化都是开放包容的,现在一定不能封闭保守。
开放的心态,不仅要包容别人,更要包容和鼓励自己的拓展。要去寻找最具代表性的元素深挖其中的艺术内涵。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完全做到,因为我觉得需要分门别类做出系统。有人说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就是感悟性的,相对于西方的那些理论来说不成体系,所以我们古代很难出现像黑格尔、康德那样体系性很强的学者。但是,这也不是说中国理论就没有体系。而且,无论如何的片段化,经历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总会形成体系。所以,对于我们当下的艺术家来说,历史的体系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特别是汉唐文化,我做的《汉唐雄风》系列,是把国家美术、宗教美术、民间美术等素材抓住。在民间艺术上,有《国风归来》。如果深挖历史,就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也总在感叹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大量的艺术空白区,只有少数搞美术的人在关注。其实这比很多花鸟鱼虫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做现代美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素材。
当然宗教艺术非常重要,因为它留下来的艺术遗迹实在是太多了。不能忽略宗教文化的力量。中国文化有三大成分,宗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看了许多宗教遗址之后,我异常感动,将之纳入我的艺术作品。这些宗教文化并不是外来文化,而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不读书,不调查,很多东西就进入不了视野,它们就只会变成客观对象,而不是一种精神形态,更不是承载精神内涵的观照对象。
历史是发展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只要停滞下来,就意味着倒退。一个不会塑造历史的艺术,是没有竞争力的,那样的话我们在西方艺术面前就很难有话语权。曾经的民族灾难,是我们文化发展方向的混乱时期,艺术开始孕育出各种胚胎,蕴藏着很多可能。而在现代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艺术的形态一定会有所变化,也必须有所变化。这种形态以前是什么,现在要成为什么,以后可能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以一种大艺术的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才能回答得出来。而这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更是中国艺术历史对现代艺术家的发问,也是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对未来的交代。
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