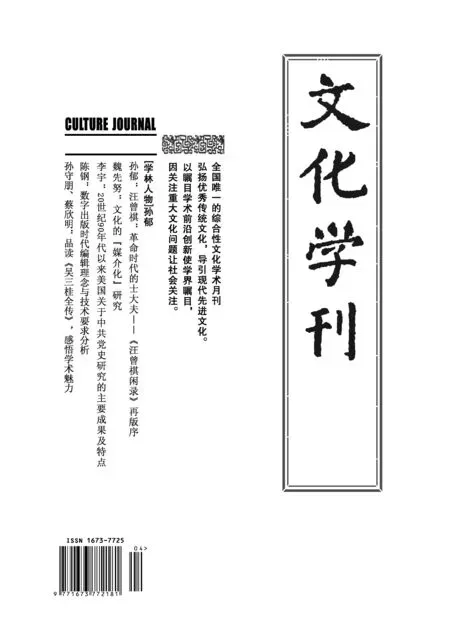《呼啸山庄》经典化的历史探析
张永怀(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文学经典的永久魅力往往在于作者用他们自己的玄想奇思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的价值意义和理解评判。艾米莉·勃朗特已被举世公认为文学史上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正是因为其《呼啸山庄》所拥有的恒久艺术魅力。小说既没有描绘汹涌澎湃的历史画卷,也没有表现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它仅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英国北部约克郡荒原的虚构的爱情与复仇故事:一个被人从街头捡回来的弃儿希思克利夫,从小备受凌辱,唯独主人家的千金小姐凯瑟琳却欣赏他身上的那份野性。长成少年的希思克利夫对凯瑟琳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可是世俗的等级观念毁灭了他的爱,那份强烈的爱变成了对外界社会的强烈的恨,并进而变成了一个个残酷无情的复仇阴谋。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最后都化作呼啸的狂风,掠过孤寂的坟头,吹向荒凉的原野……
一、《呼啸山庄》在国外经典化的历史
《呼啸山庄》一经问世随即遭普遍非议,有论者曾指出它是一部生涩的书,从整体看,是狂野、混乱、支离破碎的……在整个虚构的文学领域,从未见过对人性中最恶劣的那些形式做过如此令人胆战心惊的描绘。就连姐姐夏洛蒂也不得不承认在小说之上大都笼罩着一种漆黑的恐怖。锡德尼·多贝尔的《柯勒·贝尔》一文于19世纪50年代首次对艾米莉在创作方面的杰出才能做了褒奖,尽管被错误地判定为夏洛蒂的早期作品。
19世纪末,艾米莉的名声逐渐超过了《简·爱》的作者夏洛蒂。1883年,阿尔加侬·斯温伯恩撰文阐发了对她的盛赞,称其“最精彩的部分,梦境和发疯的章节,就其出自想象的真实情景所表现的那种充满激情和栩栩如生之美而言,还没有哪一个诗人胜过她或者说堪与伦比。弥漫全书的气氛是那样高昂、雄浑,那些活灵活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最终也几乎给那种高尚的纯洁与冲动的率真这一总的印象所冲和了。”[1]该论断揭示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而且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几乎同一年,传记《艾米莉·勃朗特》问世,玛丽·罗宾森对传主生前女友提供的资料进行披露,进一步打破了女作家的神秘感,指出“并非她不谙世事缺乏经验才使她将小说写成了《呼啸山庄》那种样子,相反正是她那虽有限而且反常但却精确真实的经验,而且是由于她的气质而变得特殊的经验,才使她将它写成了那种样子。”[2]1900年,玛丽·沃德认为作品是作家所属凯尔特古老民族气质、英国现实生活和文学传统,以及欧洲大陆浪漫派文学诸多因素相融合的产物。沃德也提到了小说的缺点,这位女评论家似乎想为艾米莉就此再行辩解,但又未能像畅谈其长处时那样尽情表达自己的说服力。
20世纪以来,对其研究进入多元化阶段。戴维·塞西尔称它“是唯一一部未被时间尘埃遮蔽的小说……明显地独立于19世纪小说主流之外,她不仅仅关心不受时间地点影响的生活的根本方面,也将人置于‘他们与时间与永恒,与死亡和命运和万物的本质的关系中看待’。”[3]
20世纪50年代,英国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从社会批评与阶级斗争的视角,对希思克利夫进行了辩护,认为他最初只是通过反抗向压迫者寻求公道,只是在此过程中,他本人受到压迫者的影响而变坏,“这些势力驱使他通过反抗来争取更高层次的自由,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诱他沦落,从而决定了他复仇的性质”。[4]W.S.毛姆评述说:“我想不出还有哪本书把爱情的痛苦、迷醉和狠毒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5],将艾米莉形容为奇异、神秘、朦胧的人。切斯特顿认为,艾米莉虽然是伟大的作家,但也指出其想象力有时是超人性,甚至是非人性的,她把男人想象为怪物,称把希思克利夫看作人,是创作上的败笔;而将他看作魔鬼,才是成功的。以其男性中心的眼光来看,艾米莉像午夜的风暴一样毫不亲切宜人,不过,他还是看出了日后女权批评中所关注的“艾米莉这类伟大的维多利亚女性内心都有某种躁动不安的成分”。[6]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对其评论逐渐由外部转向内部。无论是对其艺术建构、人物塑造,还是主题演绎的研究,评论家都自觉地立足其本身的艺术性,以文本为基础进行阐释,从而赋予了小说解读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希思克利夫对老门户自耕农厄恩肖一家和农业资产阶级林顿一家的侵犯,是工业资产阶级作用的一种隐晦曲折的表征。不过,由于希思克利夫也是企图再现一种惨无人道的社会的种种罪恶,他就体现了一个在精神上拒绝,在行动上合作的自相矛盾的统一体;而这确实就是希思克利夫的这个人物的悲剧。他对现存秩序的挑战,既因他的跻入其间而被扭曲,又因他拒绝接受强加其身的自我约束的限制而变得卑鄙”。[7]
同时,美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希利斯·米勒指出这部小说“似乎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吸引着更多人的评说”[8],它是“不确定性”的特殊形式,在理论上体现在无法确定的语言之外是否存在解释性原因,或者无法确定这种存在解释性原因的想法是否产生于语言结构本身。这是小说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能够做出决定的问题,同时也是这部小说阻止读者做出决定的问题。”[9]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称之为“神秘莫测”的文本。在这一阶段,多元化评论的发展不仅在各个评论家各抒己见中继续,而且评论不断向新领域开拓与深入,至今意犹未尽。藉此,小说从20世纪初的褒贬不一嬗变为他们眼中最伟大、蕴涵最丰富的作品之一。
二、《呼啸山庄》在我国经典化的历史
《呼啸山庄》在我国的经典化始于20世纪。随着1930年伍光建第一个中译本《狭路冤家》的问世,它作为域外小说就不断被翻译、阅读、评论、改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0世纪前30年,它仅仅被作为《简·爱》的陪衬一笔带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只有对其一般意义上的介绍及流于印象式的评点,未对其展开深入研究。1935年,周其勋等翻译的《英国小说发展史》一书中只有寥寥几笔:“爱弥莉·布朗蒂在《狭路冤家》里也务必使她的女主角娇美可爱,虽然没有这样趋于极端。”[10]1937年,金东雷错误地点评道:“爱米离著有神怪小说。”[1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几乎没有产生有价值的研究。即使有,许多著述也“披上了一层政治文化的外衣”[12],小说在当时中国的评论与接受发生了文化变形,仅仅被视作特定社会阶级斗争的图解。比如,有人就认为:“《呼啸山庄》是描写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残酷斗争的小说,它的主题是围绕着爱情描写对压迫者的反抗,小说揭示了被压迫者强烈的爱和恨。”[13]总之,这时期的研究对小说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鲜有关注。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啸山庄》的翻译与研究再度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并取得了大量的有益成果。改革开放之初,许多评论者对小说进行了重新评价,拨乱反正,推陈出新,为新时期小说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杨静远选编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较为全面地将西方艾米莉评论介绍到国内,成为当时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称得上新时期《呼啸山庄》研究的滥觞。此外,她还发表长文讨论时代与社会背景、文学环境、个人经历与创作的关系,以及西方勃朗特批评史与学术史、普通读者接受史和她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愧为“中国勃朗特姐妹学术史研究的第一人”。[14]此后,《呼啸山庄》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向新时期研究界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和绚丽的光彩,其经典地位在我国得以确立,多元视角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研究《呼啸山庄》电影改编方面,国人也取得了不少成果。1981年由高骏千翻译,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电影研究学者乔治·布鲁斯东的《从小说到电影》一书。该书第三章详尽讨论了《呼啸山庄》改编的影片,引起了国人对该领域的关注。刘岩将原著的电影改编划分为先锋派“作者”的艺术电影和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两大脉络。通过细察两大脉络中的典型代表影片,指出不同改编影片几乎都承续了原著中引人注目的哥特式“幽灵”,“幽灵”的每一次重返都凸显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书写实践,从而在不同脉络和模式中,原著的电影改编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改变不断被重构。梁建东讨论了导演阿诺德在新语境下如何利用实景、自然光和手持摄影等现代拍摄手法来重写和翻拍原著,认为这种大胆创新在给影片带来奇特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使得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缺乏完整性与逻辑性。覃志峰分析了2011版同名电影中的现代元素,认为它展现了导演阿诺德别样的电影诠释思想。
周建华的英语硕士论文通过考察小说原著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电影改编,讨论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改编影片的作用,认为1939年惠勒版电影表达了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随着经济压力和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产生的男性的焦虑,因此影片一味地夸大女性欲望及其危害性,而焦虑也成为男子气概的标志,崇高的悲剧英雄主义情结被用来应对男性的文化焦虑。1970年版反映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妇女运动的兴起,妇女的性别意识和独立精神得到强化,而对男性而言,他们的不安全感不再是焦虑,而是绝望的痛苦,好莱坞通过诉诸男性暴力与男性侵犯来应对这种绝望。1992版翻译则反映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肆意鼓吹的传统女性美德和传统的家族主义。高辉的硕士论文通过探寻小说文本的电影改编及不同改编影片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认为无论是改编,还是重写,都印证了朱丽娅·克里斯特瓦“文本即生产力”的论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1847年小说问世至今的一百七十多年中,《呼啸山庄》与评论家联袂而至。从初版遭受冷落,到后来被视为英语语言中震撼人心的杰作与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其经典化毫无疑问与评论家的参与密不可分。正是如此之多评论家的参与及近年来电影等大众传媒的介入,使艾米莉其人其作的精神内涵被不断挖掘与提升。从历史方面看,《呼啸山庄》的经典化过程,正是一个从文学边缘到文学中心的位移过程,对当下重新认识世界文学名著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1][2]Miriam All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The Bront⊇s[M].Boston:R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4.411.443.
[3]David Cecil. 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M].London:London Constable Co Ltd,1934.147-150.
[4]Arnold Kett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M].New York:Hutchinson House,1951.140.
[5]Maugham. Ten Novels and Their Authors[M].Toronto:William Heinemann Ltd,1954.229.
[6]G.K. Chesterton. The Victorian Age in Literature “The Great Victorian Novelist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71.
[7]Terry Eagleton. 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s[M].Basingstoke: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05.412.
[8][9]张中载,赵国新.文本·文论——英美文学名著重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25.133.
[10]克罗斯.英国小说发展史[M].周其勋,译.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371.
[11]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21.
[12][14]张和龙.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英国作家研究(上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431.434.
[13]陈焜.论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