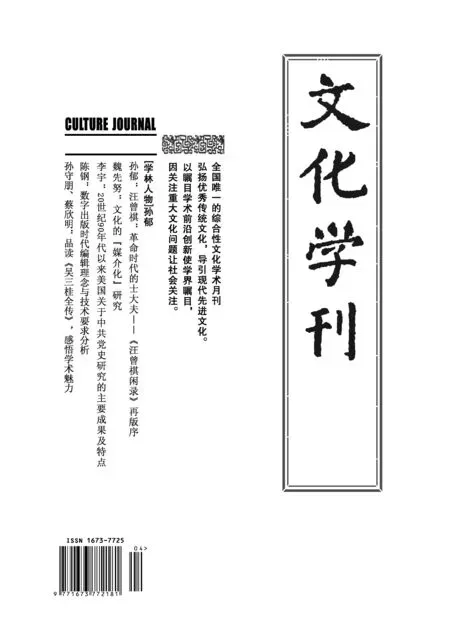从仕女画看明清主流女性审美
郑皓怡(中共漳州市委党校,福建 漳州 363000)
仕女画,顾名思义,是以仕女为描绘对象的画种。中国古代仕女画历史悠久,马王堆汉墓帛画中已经可见仕女身影。汉魏六朝时期,仕女画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科诞生,此时期的仕女形象还残留着某种神化色彩,骨相清奇,仙风道骨。盛唐时期,仕女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张萱、周昉为代表的宫廷画家,将仕女画的发展推向了高峰。此时期的女性形象丰腴健美,雍容华贵,极大地反映了盛唐气象。到了宋代,随着主流审美的变化,仕女画开始转向端庄柔美的风格,而时至明清,随着市民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社会需求量大增,仕女画迎来了新的高峰。此时期的仕女画,已经褪去了前代浓重的说教意味而主要满足观赏功能,涌现出仇英、唐寅、陈洪绶、焦秉贞、冷枚、改琦等仕女画大师,仕女画也逐渐脱去了匠气,迎合了文人的审美,表现的对象亦从前代的贵族妇女扩大为所有美人,其技法风格也逐渐成熟,并显现出程式化的趋势。而其创作美人的依据往往是文人创作的品鉴书籍,秉持的标准即是当时通行的纤弱抑郁的病态美,带有强烈的私有化、物化女性的特征。鲁迅说:“唐伯虎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1]明清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鲜明体现出封建文人的女性审美观,“赏的是娇花照水之颜,观的是弱柳扶风之色”。[2]
一、程式化的构图
明清仕女画中的仕女形象具有强烈的程式化特征,体现了当时男性对于美女的单一标准。
首先,对于年龄的限制。画中美人集中于“豆蔻”“及笄”“二八”,最多不过二十。徐震的《美人谱》点出了美人青春的短暂,“美人艳处,自十三四岁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颜色。譬如花之初放,芳菲妖媚,全在此际,过此则如花之盛开,非不烂漫,而零谢随之矣。”[3]卫泳的《悦容编》则告诉男人必须珍惜有限的欣赏美人的时间,“红颜易衰,处子自十五以至二十五,能有几年容色。如花自蓓蕾以至烂漫,一转过此便摧残剥落,不可睨视矣。”[4]而半老佳人,虽然“调适珍重,自觉稳心”,但已是“如久窨酒,如霜后橘”,丧失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对于美人年龄的限制,因为作为观赏对象必须年轻,不仅是因为其柔软纤细、娇羞婉转、生命力旺盛,更因其涉世未深、少不更事而易于控制和型塑。
其次,对于美人形体的描摹。明清女性审美带有强烈的私有化倾向,视女性为器物,功能便是满足性欲和提供子嗣,带有强烈的工具理性。如李渔所言:“娶妻如买田庄,非五谷不殖,非桑麻不树,稍涉游观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为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买姬妾如治园圃,结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花亦种;成荫之树宜栽,不成荫之树亦栽,以其原为娱情而设,所重在耳目,则口腹有时而轻,不能顾名兼顾实也。”[5]《姑妄言》第三回也言:“即妾之一字,亦立女二字合成,不过比婢女一道又略高些。其为物也,原是取乐之具。可以放去,可以赠人,可以换马……生子之妾犹可赠人,可见是不足为重的了。至于妻子,要他生儿育女,为宗祧之计,主持中馈,为当家之用。”[6]无论是妻是妾,各有分工,但妻子还能被当人对待,婢妾、妓女则视为玩物,这种观点完全将女性置于依附、从属的地位,以反衬男子伟岸刚强的气概。
《美人谱》将美貌定义为:“螓首、杏唇、犀齿、酥乳、远山眉、秋波、芙蓉脸、云鬓、玉笋、荑指、杨柳腰、步步莲、不肥不瘦长短适宜。”[7]这是修辞上对女性的物化,呈现在仕女图中便是细眉长目、樱桃小口、削肩折腰、双手白纤,虽然“多不露足,盖以为亵也”。[8]但是画中女性大多明显表现出含胸、屈膝、折腰、驼背的不自然姿态,显然是缠足造成的身姿,这种柔弱美人的形象在当时社会影响深远,远不止文人仕女画。例如,杨柳青年画中的标准美人画法是:“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慢步走,勿乍手,要笑千万莫张口。”[9]又如,民间画像的口头禅:“将无项,女无肩。”[10]武将肩宽似无颈项,以示雄伟,美人瘦削似无肩膀,以示柔弱,这样的美人,有一种“倚风娇无力”的柔弱娇羞之态,能激发男子的怜爱和保护欲。甚至还有大头小身的病美人形象,如陈洪绶的《仕女图》、改琦的《元机诗意图》,将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形象也画成了长眉细目、削肩折腰的模样。
与西方高度写实且注重以人物脸部表情表现其内心状态相比,似乎中国画师更擅长通过人物动作与背景而展现其情感。如明代佚名所做《千秋绝艳图》,不同朝代的数十个美人虽服装各异但形态雷同,只能通过动作和手中所持物品判别。然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造型,其一律呈现“被观看”的姿势,身体侧立,目光一律下视,不与观众有眼神交流,完全暴露于男性观众的视野之内。神态几乎都是一种冷漠哀怨的神情,突出幽娴贞静之态,而面目的雷同更造成了一种肃穆感。清人郑绩曰:“写美人不贵工致娇艳,贵在于淡雅清秀,望之有幽娴贞静之态。”[11]甚至为了要突出“幽娴贞静之态”,要尽量弱化外在的艳丽。明清的美人画,将美人一律画成面目雷同、神态抑郁安详、容貌清秀而决不美艳、不可引起邪念,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在仕女画中,各种春闺怨、宫闺怨是最常见的主题。场景或在绣房或在庭院,利用精致的奁具帷幔或亭台楼阁、山石花鸟、红墙碧瓦,营造出一种清新淡雅、幽怨缠绵、哀婉孤独的类似艳体宫词般的氛围,而其中的美人,一定是笼罩在一种淡淡的哀伤之中。画中女子或伤春悲秋,或思念远人,或倚栏凭思,或顾影自怜、或捧心蹙眉,且画面中都是只有女性,鲜少有男性。虽然画面中男性缺席,但可以从画中女子百无聊赖、翘首期盼的神色之中看出缺席的男性才是真正的主角。
二、物化隔离和女性空间的营造
标准的美人画,绝不仅仅只有美人,而是一个由人物、景物甚至声音和气味组成的完整体系,一个只属于女性的空间。中国古典仕女画作最注重景物的烘托,甚至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注重类似仕女画中场景的营造。
徐震《美人谱》中罗列了美人所需的物品,如居处要有“金屋、玉楼、珠帘、云母屏、象牙床、芙蓉帐、翠帏”,案上除了梳妆必备的“象梳、菱花、玉镜台”,还需有“兔颖、锦笺、端砚”“绿绮琴、玉箫、纨扇”“毛诗、玉台香奁诸集”。[12]卫泳的《悦容编》则更加详细点出了鉴赏美人的方法,包括美女的选择、美女的居住环境、室内陈设,特别是美女的各种情态。美人所居,虽不是“沉香亭北,百宝栏中”,“亦须为美人营一靓妆地,或高楼,或曲房,或别馆村庄。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与闺房相宜书画,室外须有曲栏纡径,名花掩映。如无隙地,盆盎景玩,断不可少。”[13]这种人景相融的观念在明清的仕女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品妓书籍与仕女画、花榜等品鉴女性的作品,文人雅士们戏谑般地将科第同对名妓与鲜花的审美结合起来,既体现了男性对于世俗功业和欲望的追求,又寄托了现实失意的落寞。晚明文人以与妓女酬答作画为风雅,以青楼女子为模特,所谓“鬓影衣香,形摹神绘,以为选胜寻芳者作问津之筏”。图像完成之后,另请名流题诗跋咏,为“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14],既彰显文人风雅,又提高了名妓声誉。妓女是古代唯一可见的女性,明清名妓的居所,是那个年代唯一对外界开放的女性空间,在此,文人们不仅描写名妓的美貌,更仔细描摹她们的生活空间,以及她们在这个诗意空间里的活动。
如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描写旧院的风情,细致地描绘了衬托美女的环境:“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一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搊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视觉听觉嗅觉都营造了香艳而迷人的气氛,难怪“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英雄风矣。”[15]
再如,清代许豫在《白门新柳》中描写名妓文宝的居室:“每值夏夕,独坐一凉篷,悬名人书画,灯数盏,以枣花帘障之,舱内供建兰、茉莉数盆,旁侍一女童,时徜徉于青溪长板间,见者疑为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16]冒辟疆写其爱姬董小宛赏菊之美:“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画。”[17]
文人在此,精心营造了一个封闭的女性空间:“一个空间性的统一体——一个由山水、花草、建筑、空气、氛围、色彩、香味、光线、声音,以及被选中而得以居住在这里的女性和她们的活动所构成的人造世界。”[18]
生花妙笔下,这些文人心目中完美情人的形象逐渐形成一个人物、家居、声音和香味的多层次的体系,营造出了一个缥缈的幻境一般的童话世界。然而这种女神化或魅影化的趋势,却是一种物化隔离,它将女性逐步抽象成为一系列支离的意象,诸如螓首蛾眉、柳腰桃面,连同她们精致的生活空间与优雅的文艺活动一起,分散于风景、家居、佩饰、宠物、侍女之中。经过这个过程加工过的仕女,只是一个美丽的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可以共同生活的真实女性。
明清是仕女画的高峰期,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19]但同时也是其走向衰落的时期,正如文震亨在品鉴书画品第时说:“仕女画是‘近不及古’”。[20]在明清文人笔下,仕女也成为了美景的一部分,供高高在上的精英男性欣赏。仕女画的主角虽是女性,但描绘她的无一不是男人,正是由于男性对于艺术话语的垄断,仕女画成为了纯男性的艺术,丧失了作为女性的专有属性,描绘的只不过是男性幻想中的完美情人。正因如此,在高度程式化的构图中,仕女画逐渐丧失了灵魂,美则美矣,全无生气,沦为花鸟一般的玩物。
[1]郑倍倍.明清仕女画柔弱化形成的原因及审美特征[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44):117.
[2]鲁迅.鲁迅文集全编·杂文下[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308.
[3][7][12]徐震.香艳丛书(美人谱)[M].上海:上海书店,1991.9.10.9.
[4][13]卫泳.香艳丛书(悦容编)[M].上海:上海书店,1991.66.67.
[5][清]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中华书局,2013.177.
[6]杨东方.明清士人的世俗生活——以话本小说为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226.
[8]姚灵犀.采菲录[M].上海:上海书店,1998.49.
[9]张小萍.陶瓷明清仕女图纹审美倾向[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72.
[10]徐寒.中国艺术百科全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88.
[11][19]李信斐.明清文人仕女画的女性形象及审美文化解读[J].文教资料,2011,(21):82-83.
[14]何延喆.改琦评传[M].天津:天津美术出版社,1998.66.
[15][清]余怀.板桥杂记[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9.
[16][清]许豫.香艳丛书(白门新柳)[M].上海:上海书店,1991.4981.
[17]徐元济.闺中忆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29.
[18]巫鸿.时空中的美术[M].梅玫,肖铁,施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260.
[20][明]文震亨.长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