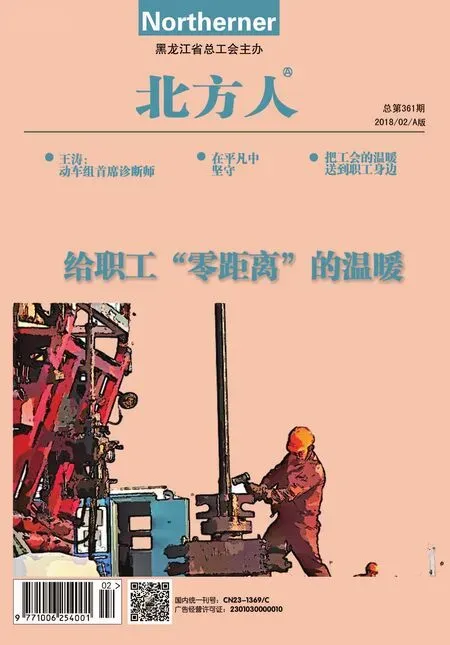我为何愿意为知识付费
文/张从志
知识付费正以飞快的速度崛起,短短两年内吸纳大量资本、流量,各种平台、各类课程纷纷涌现。而优异的市场表现背后,知识付费能给用户带来什么?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如何融入人们的生活?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学习者有不同的答案,但他们的共识是,互联网能改变知识的存储传播平台,但最后一步——知识的内化终究还是要靠个人完成。
“学习”成了消费习惯

2016年8月,刚过不惑之年的刘震东在“知乎”上刷到了一场Live的预告,标题很直白,叫作:“你还在使用上世纪的厨房设备么?不考虑升级么?”出于好奇心,加上对主题感兴趣,刘震东指尖一触点了进去,“赞助”19元后,他获得了参与该活动的特权。
成为付费用户后,刘震东和其他人一起在指定的时间进入Live的界面,一位热爱烹饪也喜欢研究家庭烹饪设备的建筑师作为答主,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为他们解答了“我为什么要升级厨房”“电饭煲除了拿来煮饭外我还可以做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听下来感觉还不错。”这是刘震东第一次使用知识付费产品。
刘震东与这场Live的“偶遇”其实算不上巧合。2016年被业界称为“知识付费元年”,几乎每个月都有知识付费产品爆红。4月,问咖、值乎出现;5月,分答、知乎Live面市;6月,得到“李翔商业内参”、喜马拉雅 FM“好好说话”推出……在知识付费概念的狂轰滥炸之下,用户迟早被好奇心出卖。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刘震东对新技术新产品更有异于常人的敏感与热忱,从参加完第一场知乎Live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只要在APP中遇到适合自己的好内容,都会下单为课程付费学习,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消费习惯。”刘震东说。像刘震东一样的消费者数量正在快速增加。2016年8月,企业智库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网民有过为知识付费的行为。2017年2月,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则估算出,2016年知识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610亿元,同比增长205%,使用人数约3亿人。
暂居美国的全职妈妈李响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她记得更早的时候,在如今的付费课程出现之前,网上其实已经有很多免费资源提供,比如在喜马拉雅APP上的蒋勋讲红楼梦、蒋勋讲诗词,还有英文有声书,那时候都是免费的,在跑步或者做饭的时候,她就会打开来听一听。
后来在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上开始涌现各类付费课程,李响发现有的课程质量还不错,便开始加入付费用户的大军。她买的第一套付费课程是田艺苗讲古典音乐,听了整整一年。“我那会儿特别想对古典音乐有一点儿入门知识,听了之后记住的不多,但是听的过程还是挺享受的。”
对购买付费课程的行为,李响也用了“消费习惯”一词来概括。虽然买的数量不多,目前在喜马拉雅和中读上总共购买了5套课程,但她对这种学习方式非常认同,每一个都学得很认真。
“我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人比较排斥付费。”李响时常会为“中读”写一些文章,读者一般要花0.99元或者1.99元才能看完全文,但是转发到微博上,她看到评论中经常有人对此表示不满,甚至骂脏话,她觉得很气愤。“比如有些报道是记者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调查采访,然后写出来的,你凭什么免费看人家的成果?我自己也写文章、拍照片,有一些网站也会用我的文章和图片,我就觉得应该尊重知识,知识是应该付费的。”
填充“无效时间”
2008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李响进入外交学院国际法专业继续深造,随后顺理成章地进入法院工作。在北京的法院端着令人艳羡的“金饭碗”,李响却感到极不适应,觉得透不过气来,因为无法融进体制内的那种工作氛围,她工作得很不如意。
不顺心的时候,她拾起了自己从小喜欢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学习插花、茶道,像读大学那会儿一样,周末闲下来就去北京各个博物馆晃荡,有时找到某个犄角旮旯、小胡同里去看展览。站在那些画、那些作品面前,她那颗焦躁不安的心才能得到抚慰。她也开始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看到的、想到的点点滴滴。
后来结婚有了孩子,李响干脆从法院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然而,在家看孩子并不比职场轻松,她需要一刻不停地盯着孩子,用她的话说就是多出了大量“无效时间”。在这种状态里,她似乎能看到生命一点点流逝。
2017年9月,因为丈夫的工作调动,李响夫妇带着4岁的小儿子搬到纽约暂居一年。“在全家搬来纽约前的一两个月里,打包邮寄东西是我生活的主旋律。除了灿若星辰的博物馆,我对这座城市没有任何预期和设想。作为中国古老艺术文化的痴迷者,我感觉自己是一株即将被拔出土壤的老松树。”李响后来写下了这段文字。
寄居异国他乡,失去自小浸润的文化土壤,她更需要抓住点什么。李响回忆那时候,她在中读上看到了刚刚上线的刘越老师讲的《谁在收藏中国》,这档音频节目第一季将会到访英美顶级博物馆,逐一讲述其内收藏的重要中国文物的经历、劫难、艺术价值。“我正好有一本书,也叫《谁在收藏中国》,书里有一份美国博物馆地图,标注了收藏中国文物的几座重镇。听了几期,我把这份地图从行李箱里拿了出去,感觉不再需要了。”
“这种知识付费课程很适合我这样的人。”李响对记者感慨,以前自己看孩子的时候除了构思写作选题就只能发呆,有了这些课程以后,她一边盯着孩子,一边戴上耳机,接收那个与眼前迥异的艺术世界带给她的讯息,自己也不再是一无所获。
“那段日子,每天先送孩子上幼儿园,我会散步穿过深秋时节的中央公园,经过Bethesda喷泉、瞭望台城堡和埃及方尖碑,来到位于第五大道的大都会博物馆,静静地坐在这些艺术品前,打开音频,听听刘越老师略显激动的声音。这些文物并未尽数展出,还有一些没看到,但能在米开朗琪罗和蒙克特展期间,在人头攒动的古希腊和欧美艺术大厅之外,有冷泉亭这样一处容我安放思念情绪的静谧之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李响说。这些一段段的,被分成20分钟左右的声音为她的生活注入了一股安静的力量。
缓解“中年危机”
刘震东对付费课程的痴迷有些不同。他们夫妻在深圳工作稳定,有一个8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属于中国当下典型的中产家庭结构,相应地,也被中产阶层普遍面临的问题所困扰,如孩子的教育问题、职场竞争的瓶颈、精神生活的贫瘠等等。
采访过程中,我向他抛出了一个滥觞于当下的概念——中产阶层焦虑,试图对他的境况加以描述。但刘震东认为自己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焦虑,他更愿意用“中年危机”一词解释自己。41岁的他的确已经步入中年,家庭事业都渐渐稳定,但如果换种说法,也是陷于停滞。稳定意味着不再有大变故,但也需付出某种代价。
行业大环境的巨变也投射到刘震东的身上。在移动通信业工作的他亲眼看见手机短信和语音通话是如何在微信的打击下一败涂地的,新技术新产品秋风扫落叶般将旧的事物送入历史,这足以震撼到他,也加剧了他的危机感。他开始驱使自己去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学习新的知识。
他在“得到”上购买了许多管理、创新类的付费课程,比如全球创新260讲、吴军的谷歌方法论、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等。每天起床后或上下班路途中,他都会打开APP看看内容更新了没有,看一段或听一段订阅的内容,睡前也会看一会儿。
刘震东说自己确实从中了解到了一些前沿的知识和概念。在全球创新260讲里,他听主讲人介绍了一种“混合现实”的概念,就是把虚拟技术应用到现实场景中,比如你开车在路上要找餐馆或商场,它会直接在虚拟眼镜上投射给你,告诉你方向,指引你过去。刘震东称,自己了解这些概念后再进一步学习,就可以据此给公司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和思考。
事实上,刘震东更多的付费行为并非来自工作需求,他为自己订阅的课程大多数可以归入人文艺术的范畴,其中以音乐、美术、电影、历史最多。尽管工作都是与技术打交道,但并没有妨碍他对艺术的喜爱,付费课程的意义则在于使他能够借助专业人士的引导去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对美的鉴赏力和理解力,而这些精神层面的熏陶是他更为看重的。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知识付费内容亦成为刘震东的补给品。在刘震东的付费目录中,围绕儿童教育的内容占据了半壁江山,他还为儿子购买了喜马拉雅出品的智能音箱,可以语音点播节目,孩子每晚都用它收听儿童节目并乐在其中。刘震东相信,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一代,儿子这一代人更容易接受这种新的学习方式。
这种学习方式也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增添了新的元素。“我和太太一般晚上会与孩子一起学习一些儿童教育在线课程,如阿卡索口语、学而思网校内容、喜马拉雅听书等。”亲子学习的家庭场景在付费课程的介入下变得更加便利和有趣,不仅能为一家三口提供更多的互动空间,也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是对线下教育的一种补充。
刘震东说,国外的教育理念是提倡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有更多时间游戏玩耍。但他还是选择给孩子报了很多兴趣班,数学、英语、小提琴、画画、游泳都没落下。而有了网络付费课程后,有些辅导班,比如英语口语就可以用线上学习的形式代替了。刘震东告诉我,这样孩子至少不用跑去课堂,减轻了一些负担。
本质仍然是学习
与刘震东的习惯有些不同,他太太还是更喜欢传统的学习方式。除了偶尔听一些免费的管理销售课,她主要还是参加线下课程,比如沙画课、演讲课。刘震东告诉记者,在线学习和线下学习都是学习知识,学习方法和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形式有差别。
“线下的体验比线上要好一些,毕竟你是在现场,有老师和学生的互动交流,课后的学习评估和跟踪机制也更加完善。而线上学习的优势在于学习的便利性和多媒体化,不需要固定的时间地点,各种资源都能很方便地找到,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也都比线下低。”刘震东对两种学习方式的优缺点做出了分析,他认为理性选择是在时间、内容和成本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线下学习,否则,当然是线上学习方便些。
“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浅尝辄止的学习,它跟内容质量水平有关系,是讲座还是课程,音频还是视频,跟这些形式没有关系。现在一窝蜂做起来的APP,有很多不是很实在,你从它做的界面就能看出来,花里胡哨的。”李响在选择课程的时候很慎重,虽然是全职妈妈,但是时间其实有限,一旦跟风就会贪多嚼不烂。
除了在选择课程上表现出的理性,李响在听课时更有心得。她告诉记者,工作以后自己常常和小伙伴去听讲座,很多是艺术家办的或者博物馆办的。有一次她们去听敦煌研究所一位所长开的讲座,讲座干货很多,但同去的小伙伴都当作凑热闹,在下面听一听就完事了,李响则保持着上学时的习惯,一边录音一边做笔记,回去后整理成文进一步学习消化。以前她在故宫学宋代工笔画的时候,老师会领他们去看很多画展,李响也会把老师解说的过程录下来,回来后整理成文字发给其他同学,同时把录音也发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和你只是跟着老师听一遍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今从线下走到了线上,李响还是保留了做笔记查资料的学习习惯。“比如邵彦老师讲中国山水画,因为有的地方讲得非常丰富细致,有的地方稍微学术一点儿,我要是觉得信息量太大就会记笔记。”
随着知识付费的火爆,舆论的焦点也出现分化,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批评这些课程正在颇为肤浅地迎合用户的浮躁焦虑情绪,是贩卖知识而非传授知识。李响对此不以为意,她认为主要还是看学习者的个人态度。“其实只要你认真对待,线上付费课程的学习深度并不比线下的浅,同样能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