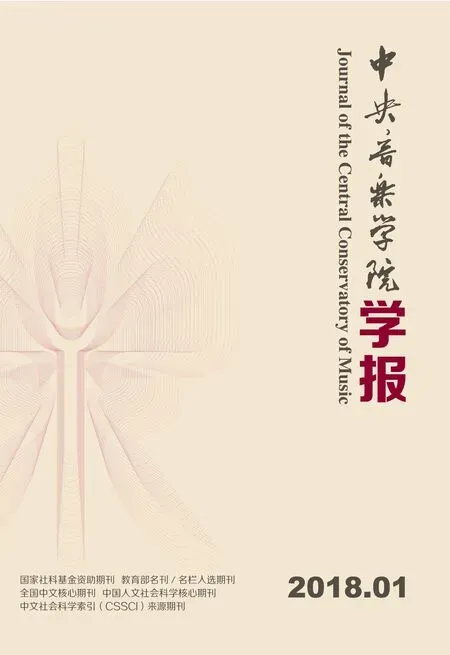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刍议
——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若干教学与实践为例
和云峰
关于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的相互关系,应说是个老生常谈但又常议常新的话题。本人拟围绕此“话题”(后文简称“人才培养”)并结合本人所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系列课程的几点感悟和一得之见阐述于后。
一、人才培养历史及模式
写作期间不时耳闻:此类话题院学术委员会还用组织研讨?还需要说吗?!结果不言而喻——民族音乐对作曲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已被业内“严重”认同!
(一)让历史说话①部分资料参见、转引自和云峰:《辛勤耕耘一甲子 桃李芬芳忆往昔——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调查、研究、教学60年》,《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第20—27页。
从1950至1964年的近14年里,中央音乐学院部分理论、作曲、指挥、表演专业的师生在“人才培养”中创建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与实践模式。应该说此举对其后中国民族音乐与作曲人才的教学、培养及创作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1.关于“走出去”
“走出去”发起于1950年7月,当时李井然、李佺民、郭淑珍、隋克强、廖胜京等10名师生参加了中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访问团文化组,先后赴云南、贵州、西康②地区名。民国初年称“川边”,受四川省节制,1923年升格为省,特别行政区,1925年改称西康特别行政区,以康定为首府。1955年撤销建制,分别划归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等地访问演出和实地调查,除采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素材外,还进行了一些音乐创作活动*中央音乐学院校史编辑部:《中央音乐学院院史》(1950—1990),1989年(内部印刷)。。
1957年后,中央音乐学院还对“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调查,采录到部分音乐资料;发掘和抢救出了一批濒临灭绝的乐种、曲种、剧种及珍贵乐曲;发现了一大批身怀绝艺的民间艺人。在1956年、1958年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人员就随行调研并且对达斡尔、鄂温克、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维吾尔、蒙古、锡伯、彝、白、佤、瑶、水等民族的传统音乐展开普查……。“走出去”活动一直持续到1964年,其间,先后吸收了中央文化部门所属艺术院校和单位的音乐、舞蹈、戏剧干部30余人参与调研,其中就包括学院师生何乾三、沈灿赴(四川甘孜和阿坝)藏族地区,郑小瑛赴(福建)畲族地区,方暨申赴(贵州)侗族地区,陈梅赴(延边)朝鲜族地区,钟子林赴(青海)土族、撒拉族、藏族地区。与此同时金文达、陈宗群、郑伯农、陈恩光、郭石夫、黄继堃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后文),其中部分成果分别以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研究著作三种形式(依发表时序)存照于世。

调查报告均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例如《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调演采访报告》(1957年内部发行),《少数民族文艺调查资料汇编》(1958年内部发行),《民间歌曲》(1961年内部发行),《说唱音乐》(1961年内部发行),《说唱音乐曲种介绍》(1961年内部发行),以及简其华、毛继增:《云南省民间音乐采访记录》(1962年内部发行),何芸、杨友鸿、孙幼兰:《广东、海南黎族音乐采访记录》(1962年内部发行),毛继增执笔:《白沙细乐》(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4年油印本)等。其中《白沙细乐》(调查报告)是迄今对该乐种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调查和整理。报告分概况、来源和历史、艺人的简介、演奏形式及乐队编制、乐曲介绍、音乐的初步分析、乐器、结束语、附录一《北石细哩》的演奏、附录二以及《北石细哩》调查报告意见等部分*详见和云峰:《纳西族音乐史》,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研究著作有:《中国民歌》(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55年),《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1—3辑,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56—1958年),《苗族芦笙》(中国音乐研究所编,1959年);何芸、简其华、张淑珍:《苗族民歌》(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59年),毛继增:《西藏民间歌舞——堆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59年),毛继增:《西藏古典歌舞——囊玛》(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0年),《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0年),《民族器乐改良文集》(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1年)以及《民族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等。
2.关于“请进来”
1951—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广泛开展了学习民间音乐系列活动,在“走出去”基础上又“请进来”不少民间音乐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杨元亨(管子)、朱勤甫(打击乐)、赵春峰(唢呐)、曹东扶(古筝)、白凤岩、张天恩、朱仲禄*民间歌手。1922年生于青海省同仁县保安镇。其祖父与父亲均是当地的著名歌手。其自幼酷爱民歌,自七八岁唱“花儿”至今已60余年,为闻名全国的“花儿王”。演唱高亢流畅,真假声转换自如,生动朴实地表现了“花儿”无穷的魅力。50年代编著第一册词曲皆备的《花儿选》,灌制唱片《上去高山望平川》《尕老汉》《千里眼》《白鸽子》等。1985年创作歌曲《黄莺声声向柳梢》获全国少年儿童“小百灵”奖作品奖。1986年获全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比赛“花儿”辅导二等奖,“花儿”词曲创作三等奖。曾在中央音乐学院(1953)、西北艺术学院(1954)等教花儿音乐和民歌演唱。为青海花儿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理事。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青海分会副主席(转引刘波主编:朱仲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戏曲、曲艺表演艺术家有良小楼(京韵大鼓)、李桂云(河北梆子)、曹宝禄(单弦)、周全安(昆曲)等。在此期间,还邀请了部分民间音乐团体如西安鼓乐(现称长安古乐)等到学院教学、演出及交流。
在今天看来,上述“一出一进”系列活动,为民族音乐教学和作曲人才培养开创了新的教学与实践模式*和云峰:《关于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教育》,载《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上、下),第十章,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版,第471—491页。,也为传统与当代互为关联的创作之路开启了全新的探索路径。
⑦ 排名不分先后。
(二)让现实发言①
20世纪以来,将传统音乐(“母语”)纳入创作素材俨然已成为中国作曲家的思维定势和创作习惯(仅以少数民族音乐素材为例)。譬如贺绿汀的《森吉德玛》,马思聪的《阿美山组曲》《西藏音诗》《牧歌》,江定仙的《康定情歌》(编配),朱践耳的《黔岭素描》《纳西一奇》,石夫的钢琴曲《新疆组曲》、交响诗《帕米尔之歌》、歌剧《阿依古丽》、舞剧《文成公主》,郑律成的歌剧《望夫云》,雷振邦的《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黎英海的(改编)《嘎俄丽泰》《小河淌水》,桑桐的钢琴曲《苗族民歌主题小曲32首》、管弦乐《苗族民歌四首》,陈钢的《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陆华柏的《康藏组曲》,刘炽的《阿诗玛》《新疆好》,白诚仁的《苗岭连北京》,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瑞丽江边》,鲍元恺的《炎黄风情》,王西麟的《云南音诗》,盛宗亮的《西藏袖舞》,谭盾的《地图——为大提琴&录像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协奏曲》,叶小钢的《西藏之光》,陈怡的《多耶》,瞿小松的《Mong Dong》,郭文景的《滇西土风》,张小夫的《诺日朗》,何训田的《阿姐鼓》,唐建平的《成吉思汗》,张千一的《青藏高原》《长白颂》,杨天解的《瑶山的春天》《苗寨狂欢节》等等。此外,陈其钢、周龙、刘索拉、秦文琛等人的作品也较多涉及“中国元素”。近年来,陕西作曲家群体中,赵季平、饶余燕、韩兰魁、张豪夫、陈大明、崔炳元、程大兆、张大龙等的创作以乡土特色而引人注目、影响渐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创作体裁广涉民族管弦乐、交响乐、室内乐、声乐,但创作素材则着力借用陕西地域性民族民间音乐,如秦腔、碗碗腔、郿户、陕北道情、老腔、民歌和西安鼓乐等等。整个作曲家群体似乎都在尝试对传统音乐基因与现代作曲手法的不懈探索和融会贯通⑧参见龚佩燕:《陕西当代作曲家重要作品目录简介及其作品地域风格特点分析》,《陕西教育》,2014年,第5期,第4—5页。。
(三)思考
通过前述历史与现实,我们对“人才培养”间的相互关联及其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直观的认识与了解,在此基础上,也引发了笔者对如后几点关于“模式”的思考(仅一己之见,目前尚无解决方案提供参考)。
思考1:教学模式——欠本土化?关于此类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历史地看待和分析。其一,就历史而言,自“西乐东渐”后中国音乐教育几乎全盘西化。当然这几乎也是个“全球化”的问题——全世界几乎所有非西欧国家的音乐学院都是以欧洲音乐教学体系为范本的。因而过多纠结于此纯属庸人自扰!因为历史不可以被选择,更不可以重新来过。其二,就分析而论,中央音乐学院最重要的教学传统与模式,基点就是教授西方音乐理论、遵循西方音乐体系。前述两点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能否在此传统(基础)上有所突破或渐进“改良”?或移步换型?或选择为我所用?
思考2:思维模式——欠话语权?众所周知,在创作(体裁)方面迄今绝大多数作曲家都沿袭了西方传统,而且这种定势仍将继续,因而关于“中与外”“雅与俗”“古与今”这些流传并困惑中国人千年的话题(思维模式)仍然将伴随着“西乐东渐”与“华乐无存”等观念持续良久。犹如业内共识: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似乎都在苦苦追寻着西方的步履,唯恐落后和不及,从而才会出现学人(刘天华等)对传统民乐的改造,后继者(彭修文等)变民族乐队“交响化”这一现实,不得不催人重新思考或审视。而近现代传入的“作曲技法”与古而有之的“音乐学研究方法”这“一无一有”,更是造就了作曲(实践)与理论(构建)两条截然不同(坊间称“两张皮”)的发展路径。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民族音乐学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的引入,则使不少学人囫囵吞枣……其中不少“方法”还有待更进一步“中国化”的实践检验(将另文讨论,此不赘述)。
思考3:创新模式——欠成熟化?就目前的某些理论建树与实验性创作而言,笔者认为仍然处于“邯郸学步”或“呀呀学语”阶段——除去模仿还是模仿。但换个角度看——能学会、学像、学好也属不易。除作曲方法与音乐理论外,类似的事例还可举出很多,例如西洋发声(之前没有)与民歌唱法;再如国际上流行年久但我国当下仍然流行的诸多(例如奥尔夫、柯达伊等)音乐教学法,似乎都属西乐东渐“前因”和当下创新模式欠佳所遗留的必然“后果”。
思考4:审美模式——唯西方论?从目前国内的创作、演出、评论等相关指标与体系看,均以西方为准*和云峰:《中国当下音乐现状与问题评析》,《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1期,第59—69页。,原因有四:其一是评价体系有些扭曲;其二是唯西方马首是瞻已成通例;其三是墙外开花墙内“必香”似成惯例;其四是拾人牙慧现象普遍盛行(限于篇幅,不做详述)。
二、人才培养方法及建议
当下,在“人才培养”中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或改善的问题,结合本人19年来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系列课程”的教学积累与经验总结,提出如下建议:
(一)应适度增加学习课时
本人曾多次强调:若依照现行的本科教学方案,要想将中国各少数民族音乐逐一或简单阐释都是难以做到的——中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有的民族还有很多不同支系),况且较多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背景、绚丽多姿的音乐表现形式,甚至有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用音乐记录、传承和表述的……因而即便每个民族平均只做一讲(2学时)也大致需要近4个学期*此按每学期15周计算(其中除去“10·1”黄金周或期中、期末考试二周)。才能完成。
(二)应适度增加相关课程
自建院以来,只有笔者为本科生开设过相关的例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等必修课程;选修课也大多为本人首开*详见和云峰:《关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系列课程”的依托背景、教学模式、实施原则》,《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59—64页。,例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鉴赏”(1998;内部教材、出版教材*桑德诺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鉴赏》(中央音乐学院十五“211”工程教材建设项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少数民族基础理论”(2000;内部教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赏析”(2004*桑德诺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附赠电子课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2004*桑德诺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次印刷,2010年第4次印刷。)等。目前使用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2011;增订本)是本人对以往系列教程的全面修改、整合、增订,也是专门为音乐学系(音乐学、艺术管理)本科生撰著的必修课教材。
(三)应适度调整授课方式
作为本科阶段的选修课,民族民间音乐类教材的编写、授课方式应遵循既通俗、又专业的基本理念。所谓通俗,即修读本类课程或阅读本类教材的学生均可在教学计划内根据兴趣主动地掌握每章(讲)的主要内容;专业,即内容上尽可能详尽、实用、前沿并且体现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详见和云峰:《关于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课教学的实践与思考》,载周巍峙主编:《民歌对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158—168页。。
(四)应适度调整授课内容
教学应提倡以“学生为本”,针对不同专业(含表演)和学历层次(本硕博)的学生开设相应的课程。
譬如针对本科生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就注重并强调阅读、讨论、鉴赏三个环节。通过阅读,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部分较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通过讨论,让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歌曲、器乐、舞蹈、说唱、戏剧)、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有一定的理性认知外,从理论上进行一般性的总结、归纳,并掌握其主要的音乐风格与流布特点;通过鉴赏,让学生不断提高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修养和认识,增进对祖国大家庭音乐文化遗产的熟知与感情。
针对研究生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研究”*详见和云峰:《关于音乐学研究生选修课的几点实践与思考——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为中心》,载和云峰主编:《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2005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学工作会议论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版,第256—273页。,则以专题研究为抓手,以课堂讨论、课下阅读、论文撰写为主,以田野采风、学术讲座、音乐会观摩为辅。授课之余,我们还注重通过音乐会来弥合音乐学与作曲人才间的游离。例如“黄安伦归国作品音乐会*2005年12月17日,由和云峰等监制的“黄安伦归国作品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2005)、“陈怡室内乐作品音乐会*2006年12月29日,艺术管理专业策划主办的“陈怡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2006)、“梦到起始——中央音乐学院首批藏族学生作品音乐会*2006年6月9日,由和云峰等监制的“梦的起始——中央音乐学院首批藏族学生作品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学院音乐厅举行。”(2006)、“湘魂——白诚仁个人作品音乐会*2007年6月24日,艺术管理专业策划主办的“湘魂——白诚仁个人作品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精彩亮相。”(2007)、“流金岁月——施万春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2007年12月15日,由艺术管理专业策划主办的“施万春声乐作品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2007)、“杜鸣心室内乐作品音乐会*2008年12月14日,由和云峰监制的“抚琴回韵——杜鸣心教授80寿辰室内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2008)等,尽可能多地为民族音乐与作曲人才提供进一步的专业认知与视听感受。
三、人才培养理念及实践
关于“人才培养”的话题很多、疑问也很多,有的问题涉及理念且可谓积重难返,仅此还应着力推崇以下做法:
(一)做到敬畏传统
此传统既包括东西方音乐历史中的“大传统”,也包括音乐院校各自特色的“小传统”。首先,力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与教学模式;其次,改变唯西方“是从”的思维模式。作曲人才应逐渐改善创作理念,防止“以中国艺术家的名义创作但更多面对的却是西方听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批音乐家与国内受众有一定距离的原因*陈其钢:《中西音乐关系论——答〈光明日报〉梁枢》详见搜狐文化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59672065_298671)尚音爱乐(2017—07—24)。)”的尴尬局面。其次,应进一步客观地看待并正视东西方音乐各自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此方面,我们课程结合“音乐类非遗”项目,例如“天山神韵——新疆传统音乐会”“来自彩云之南的天籁——云南原生态音乐会”“戏梦浮生——首届中央学院戏曲专场晚会”“老北京印象——听老爷子讲昨日的北京多媒体视听音乐会”“黄土恋歌——陕北民歌专场音乐会”作为教学与实践的进一步补充,在强调西方的同时也不忘慎终追远……这一系列的做法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提倡礼敬民间
这个话题似乎显得过于沉重但也十分现实。单就记谱与演奏而言,中西方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可谓截然不同:在中国音乐传统中,一般允许打谱者(各类文字谱)见人见智,例如“骨谱肉腔”的存在方式就在无形中为同一乐曲的解读留有了极大的想象或创作空间——极个别者甚至等同于“再创作”。此种传统虽然常因过于信马游缰而被诟病,但其结果也可以成为某种门派林立的基础“门符”。而在西方传统音乐中,对各种谱式的解读往往或更多强调并结合旋律、和声、配器等综合因素展开,因而再创作的空间很小,反之较多强调传承规范、表演统一、逻辑合理;在演奏方法上,中国传统音乐较多讲求一种内在的即兴与随性,有时每次演奏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变奏”性质,或近乎等同创作一部“新作品”,而西方则多以保留和尊重传统为首选,无形中较少留有“创新”的可能。因而在授课之余,我们曾邀请了诸多民间社团,例如丽江洞经古乐会、福建十番古乐会、河北子位吹歌等民间社团,以及苏州评弹、侗族大歌、哈萨克弹唱、广西多民族歌腔、漫瀚调、二人台、蒙古族长调与呼麦、赛努拜尔·吐尔逊及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艺术等民间艺人,为满足音乐教学和作曲人才培养提供更多与民间接触的机会,让学生面对面地亲身体察或耳濡目染,倡导并引领其对民间音乐的礼敬。
(三)倡导知行合一
首先,应强化民族音乐理论学习与作曲人才培养的力度。对于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的培养,还应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把这作为基本的教学方式纳入到日常教学、研究当中,例如“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的创立就属此种尝试之一。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是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创办的每两年一次的学术性、公益性系列活动。“音乐周”含学术展演、学术研讨、学术典藏、英才扶持、走进殿堂、走进高校等计划,旨在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研究、保护、传承、鉴赏、品评等提供鲜活的经典案例。第一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详见宋姣:《首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活动纪实》,《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52—156页。和第二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详见孙聪:《文化与沟通——第二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活动纪实》,《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59—160页。,在回眸中央音乐学院60余年民族民间音乐调查、研究、教学之同时,亦将部分成果分享至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艺术殿堂及高校,以期共享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为今人提供一种多样性的音乐存在形式,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认同、遗产共享,提供慎终追远、不忘其宗的理念及认知,也为民族音乐与作曲人才提供进一步的践行理论的机会。音乐周期间,我们还兼顾“人才培养”。例如第二届音乐周,我们邀请了作曲家鲍元恺教授在学院演奏厅和清华大学大礼堂做了:“洋为中用”到“中为洋用”——《炎黄风情》25年来的跨文化传播学术讲座;此外,还邀请了德国作曲家老锣参与“中国音乐文化与电视选秀”的研讨,其在研讨会上留下的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人们学不到“中国作曲”,“中国作曲”的理论也脱离了它本该成为的样子。于是,结局显而易见:几乎所有从中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家只会“说”“西方的音乐语言”,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在音乐中讲中文”。所以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极力地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代表着中国文化,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作品的听众依旧少之又少,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是如此。此转引的虽然只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一家之言,可在某种程度上此种旁观者的“清”值得专业音乐工作者们重视(详见老锣: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音乐——中国的希望还是噩梦?原载《昭华民族音乐》(http://mp.weixin.qq.com/s/VVDoFeuvDN_x0brnKqUccA)。。总的看,诸如此类的学术讲座与讨论,都为“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良好的作用。
其次,应强化民族音乐理论与作曲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正如坊间所传,“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诞生,至少需要七个条件:即生逢其时、胸怀大志、天才、博大、高产、创作生涯完美、心灵世界丰富……”*引自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著,张雪梁译,杨燕迪、孙红杰校《音乐中的伟大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7页。我们希望在民族音乐理论的滋养下,能催生更多、更好的作曲人才与作曲家。
余 论
历史地看,中央音乐学院作为一所以教
授西方音乐为主体和己任的院校,其主要办学目标“锁定欧美”,间或“放眼世界”无可厚非。客观地看,利用西方作曲技法讲述“中国故事”,学好西方音乐理论发出“中国声音”的传统应该得到真正的尊重并且代际承传……
本人认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教学传统看。既要教好西方传统音乐,尤其是西方作曲技法及理论;也要学好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创作手法。使之更好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并在此基础上“百花齐放”或“推陈出新”。在“人才培养”方面,既要允许百花齐放,又应允许百家争鸣;既要真正了解西方,又要真正懂得中国;既要强调理论研究,又要重视创作实践;在教学模式坚守与教育理念上做到勿忘本来,汲取外来,面向未来。
第二,从现有模式看。一时想要改变“唯西方审美评价体系”并非易事,但加强东方审美评价体验却非难事;其次应加强作曲人才的培养及实践,以弥补优秀作曲人才“青黄不接”现象的持续——近来曾有人疑惑、感叹:“……现在能拿得出作品的郭文景、叶小钢、陈其钢、周龙、陈怡都已经年过六旬,50岁、40岁、
30岁的作曲家在哪儿呢?”*详见张学军:《广交六十岁庆生 余隆质问作曲家断代》,千龙网中国首都网(http://culture.qianlong.com/2017/0926/2057994.shtml)。这个设问值得认真回答和反思。
第三,从未来发展看。首先,要真正了解西方音乐文化。“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了解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远不像大多数人认为得那样理想”。其次,要加强中国传统音乐训练。因为对本国音乐历史和民族民间音乐知之甚少,自然就会对传统音乐缺乏应有的尊重。也就是说,那些希冀用自己对西方音乐肤浅的知识来“改造”中国传统音乐的言行才能适可而止。再次,要辩证认知中西音乐对立。因为对乐曲、乐谱、乐器、理论等认知不足,也会产生不良后果。有作曲家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或者满足于一知半解,或者是盲目地妄自尊大,或者是武断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大多数民族器乐作品是出自那些对中国传统和西方创作音乐一知半解的作曲家或特别是演奏家之手;没有西方人的认可,他们就几乎没有其他退路”*陈其钢:《中西音乐关系论——答〈光明日报〉梁枢》详见搜狐文化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59672065_298671)尚音爱乐(2017—07—24)。。
最后,借用王阳明语录结束全篇:“夫学、问、思、辨,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因为: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不也如此吗?光说不练或光练不学,理论脱离实践或实践缺乏理论,都是不圆满或违和的,只有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才可谓“不行之不可以为学”*〔明〕王阳明著:《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此一得之见,仅供参考或自勉、共勉。
(文章依据作者在“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