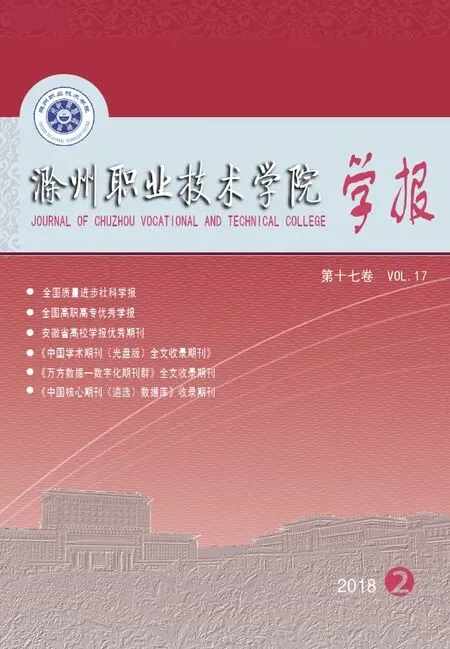浅论元明戏曲作品艺术价值影响因素的构成
唐义武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戏曲通过现场舞台表演,能更好地调动现场广大观众的情绪,把戏中人物的思想,剧中情节,矛盾冲突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更深的层面熏陶感染观众,进而达到教育宣传的目的,其取材、价值与政治形式、社会思想控制、作者审美取向都与其流传效果与影响力紧密相关。
一、政治社会形势对作品价值构成的参与
元朝尖锐的民族矛盾、高压的剥削政策、腐败的吏治、繁华的都市生活都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囿于文化上的落后,致使蒙古族在马上得到天下后,依然采用武力征营天下。突出表现是元朝统治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政府中主要官员都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即使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也是担任虚职或副职。元朝还法律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须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1]。终元之世,民族对立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动荡不安。除此之外,在经济上,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据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如朝廷给予西域商人放高利贷的特权,中原人民为缴纳赋税,常向西域商人借银,结果连本带息越滚越大,以致倾家荡产都还不清债。元代经济掠夺以江南地区被害尤烈。据《元史·食货志》载: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予江南”[2]。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每年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元末农民起义军韩山童部就以“贪极江南,福夸塞北”的极端不均作为宣传口号(见叶子奇《草木子》)[3],表达了南人对于元统治者掠夺的愤恨之情。这一系列的高压政策致使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种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饱尝艰辛,思想情感备受煎熬,人生阅历厚重丰富。
与军事力量的极强性和统治的铁腕性相比,元朝统治者在维护其统治的文治方面却略显不足。一些不切实际的施政政策严重影响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比如元人在用人方面以蒙古人为主,少用汉人,这样的选吏政策,致使决策层对治理区域经济、政治、文化、民风等不甚了解,特别是在元统治初期常常造成决策失误,如圈汉人农田为牧场。元代曾取消科考达七十余年,只是到统治末期才开科选拔人才,但在选拔任用官吏上人坚持以蒙古族为主官、汉人为副职的政策。科举制不行,文人的晋身之路堵绝,导致当时社会文人的自我放逐,有的在醉生梦死中沉溺,有的转向内心世界选择了归隐修身,也有的选择融入市井,把聪明才智投向各阶层人士都喜爱的戏曲创作中来。
为了迅速获得财政高额税收收入,元代统治者很重视商业经营,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许多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如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居民多至四五十万。北方的真定,大同、汴梁、平阳;南方的扬州、镇江、上海、庆元、福州、温州、广州等地,均颇具规模。随着大中城市的涌现,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元代的这种政治社会环境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民族压迫政策的推行导致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吏治腐败、冤案累累的社会现实也为触觉敏锐的作家的取材提供了天然丰富的题材。同时,重商主义的实行,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市民的增多,也为戏曲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优良的场所和大批忠实虔诚的观众。
在这样的环境中,戏曲迎来了高峰。首先是作家蜂起,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其次是创作成果丰硕,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佚。从元代戏曲的题材看,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神仙道化等许多方面,涉及层面异常广阔。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仔细观照其作品特别是代表作,我们会发现,那些最有影响,流传最广,后代认同感最强,评价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反映揭露社会腐败最为深刻、反映人民呼声最强的作品。
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官吏贪墨,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冤狱重重,悲剧屡屡发生。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以其如椽巨笔,实录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深刻展示了元代窦娥极度恶化的生存空间,将愤怒批判的矛头直指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在《救风尘》和《望江亭》中都叙述了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下层民众不堪凌辱,奋起自救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在《单刀会》和《西蜀梦》中则更多流露出刘蜀正统论的思想,抒发了当时人民希望恢复汉族正统的治理愿望。又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描写了“存赵孤”的故事。宋王室自认是春秋晋国赵氏的后裔,对保存赵氏的程婴、公孙杵臼等多次加以追封。南渡之际,徽、钦二帝被掳,赵宋王朝风雨飘摇,“存赵孤”更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具有强烈政治暗示的话题。作者在当时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大胆写出这样的剧作,精神可嘉。更为重要的是讴歌了为正义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结局也给风雨如磐时代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对此剧王国维曾言:“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4]。悲剧乃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可以说正是由于现实的黑暗残酷才给了当时作者无穷的创作源泉。
同样取材历史的白朴的《梧桐雨》和马致远的《汉宫秋》也不同于前代的同题材作品。《梧桐雨》虽然写的是传统的李、杨爱情故事,但主旨已迥异于前者。较之于他人赞誉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和揭露李杨耽于享乐、贻误朝政的不该,白朴的主旨却是要经过二人悲欢离合的爱情巨变,向经历过沧桑巨变的观众宣示更为深刻更为沉痛的人生变幻的题旨。通过人物的遭遇传达江山满眼人事已非的怆痛。而这正是宋元易代之际的背景在作者心中投下的深重的阴影。而取材于昭君出塞故事的《汉宫秋》,故事的题旨也不同于以前人们的看法。此剧不是为了赞扬昭君和亲的功绩,也不是宣扬匈奴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而是重在叙述小人当道、兴风作浪,平日以股肱之臣自居的朝廷大臣却无法给予皇帝任何帮助,替主上排忧解难的现实,而是相互推诿,将皇帝推入一个可悲的境地之中。其中更多的是抒写家国衰败之通,是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而涌起的阵阵难以明说的困惑和悲凉的人生感受。而整出戏的结局也是在浓郁的悲剧气氛中结束,传达出深沉的人生落寞之感。这样的结局安排和主旨选择,可以说是暗合着作者切身现实生活之叹的。
二、思想控制对戏曲作品创作的影响
相比于统治上的严酷,元代在思想上的控制则要宽松的多。为了加强对对广大汉族的统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元朝的统治者继续采用汉族人习惯了的儒家思想来对人民进行思想教化与控制,他们沿用宋代的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人民,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但是,元朝统治集团毕竟是不同与汉族的外族,他们大多性格粗犷豪放,重视实利,在很多方面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们推行儒家思想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程朱理学对思想的禁锢相对于宋朝来说明显弱化。同时元朝为了拉拢其他非汉族的族类共同管理广大的汉族居民,又采取了尊重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的政策。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元代的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现象。
正是由于元朝黑暗的社会现实和较为宽松的思想统治环境,才为众多优秀剧作的产生和流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都具有思想解放的特点,描绘了大胆追求爱情的封建女子,勇敢的向封建家长挑战,表现了主人公对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渴望。有的显示市井女性有胆有识敢做敢为的性格特征,有的显示了被禁锢的封建大家闺秀青春思想萌动,勇于冲破无形阻力,大胆追求理想生活的信念。可以说,正是由于元朝时期思想控制松弛,儒学影响削弱,才为众多优秀戏曲的出现登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对比明清戏曲我们就能发现其重要性。明代社会相对元朝安定的多,明初思想控制也极为严格,特别是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对戏曲创作影响极大。如《御制大明律》专设《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建国初还颁发榜文明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5]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控制下,明初戏曲,不管是杂剧还是传奇,都没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作品。杂剧取材狭窄,产生了所谓的宫廷派剧作家,其作品也净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语言也渐趋华丽雅致,作品本身也缺乏直面现实的基本抗争精神。此期间创作了许多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明初传奇也具有同样特点,内容上带有浓厚的伦理教化意味,充满者道学气,语言骈俪典雅,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有影响的作品。直到明代中后期,统治者耽于享乐,荒淫腐化,思想控制松弛,才出现了众多直指社会现实弊端,敢于抒写事实的有价值的作品,批判性和讽刺性大大增加。如徐复祚的《一文钱》,王九思的《中山狼》,徐渭的《四声猿》(《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及署名王世贞的《鸣凤记》。特别是有些作品的批判性和讽刺性非常尖锐,这和明代后期的污浊社会现实及思想控制松弛密不可分。可见统治者思想控制的严密与疏松影响着戏曲作品的创作,特别是直接影响戏曲的表现内容与价值取向。
三、作家的性格品性对构建戏曲作品价值的影响
特定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只是给创作个体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取材源泉和广阔的创作背景,同时期的众多作家中,有才智者不在少数,擅创作者亦汗牛充栋,很多人的作品数量也是很可观的,但是不见为后人所看重称誉,亦是其作品价值不为后人所认同。除去题材方面的原因外,跟作家的人格品行亦有关联。以关汉卿为例,他的性格在其散曲《南吕·一枝花》中表现最为明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6]。在血与火的动荡社会中度过前半生的关汉卿又处在科考之路长期废止、士子地位下降的元代社会,养成他开朗通达而又倔强韧性十足,甚至有点愤世嫉俗的性格。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对元代社会的黑暗揭露最为尖锐深刻。创作态度关注下层民众,敢于为人民大声疾呼,叫出人民的心声。因此,其作品获得当时后人的认同和高度评价,当然也由于其他的原因,但是这方面绝对占据着重要一面。而白朴自经丧乱,心灵饱受创伤,较早看到了社会凋残山河破碎的情况,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意于政治,而是流连山水之中风月场里,看淡一切,心中有沧桑之感,性情变的平和起来。因此,在其《梧桐雨》中往往流露渲染的是浓重的人世沧桑的哀感。其他人的作品亦是一样,可以说,同样的现实生活,仁者见仁智者见者,各取所需加以熔铸,将个人之色彩融汇于作品之中。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看待社会的方式,取材的角度,作品反映生活的方式,应对外界压力的态度。这一切都是构成作品价值重要参与因素。
明代汤显祖,受泰州学派罗汝芳以及著名的反封建斗士李贽的影响,性格不同于一般人。传说当朝首辅张居正曾先后两次让汤显祖为自己的儿子陪考,并许愿让其高中鼎甲,但正直的汤显祖每次都断然拒绝。正是有了这样坚定正直的性格特征才敢于写出像《牡丹亭》那样在当时人看来大胆出格的作品,以致后来有人极度诅咒他,甚至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但正从反面证明了他的作品的价值,有多少人咒他就有多少人爱他。
与他们明显不同的是清初戏曲家李渔,在有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中,他缺乏前辈人非儒薄经的胆识和勇气,不敢直面社会现实和忤逆统治者的意志,采取了回避的创作策略。在取材方面有意避开了政治和社会深层次问题,以道学风流和二为一的优游闲人自居。李渔虽然潜心与戏曲的创作与演出的技巧研究,取得一定成就,但其戏曲作品创作的内容大多在男女风情的范围内变化,格调不高,有媚俗的倾向,甚至有一种以娱乐为宗旨的追求,因此,没有多少堪称杰出的作品。反观清代最著名的两部戏曲《长生殿》和《桃花扇》的作者洪昇和孔尚任则采取了积极面对的态度,后者把取材的视角勇敢的选择了当朝和前朝易代之际的领域,前者以史观今,咏叹了帝王之情,展现了历史沧桑,将史的内容和情的悲剧串联在了一起,在当时获得了许多人的极高赞赏。此二剧体现了思想意识控制严厉的清中期创作者身上难能可贵的独立品质以及强烈的个性人格操守,正是这种人格品质和操守,使他们的戏曲取材不同于时人,从而构成他们戏曲作品为后人看重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特殊政治形势提供的广阔社会生活材料是一个重要前提,宽松的自由创作环境是一个重要保障,但更重要的是创作者的人格品性,它直接影响着创作主体对外部威胁给自己创作带来的压力的应激反应,从而影响自己作品的取材观照角度和主旨的选择。几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着一部戏曲作品价值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