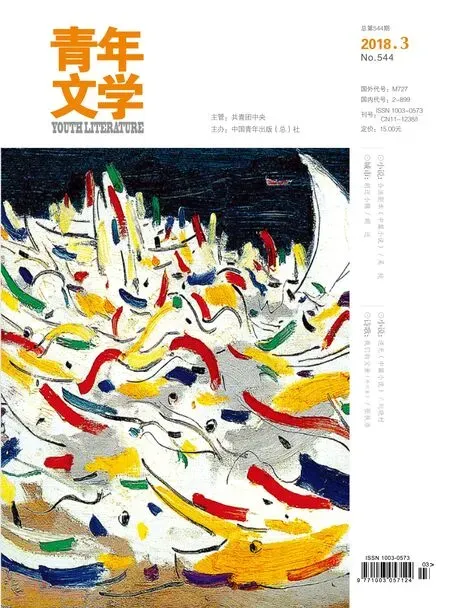字 号
⊙ 文 / 侯 磊
我到山东东阿去参观阿胶的生产,在养殖场里手持一尺长的胡萝卜喂那头可爱的黑驴王子,我一边逗它,一边想起从前的事。小时候随父亲在郊区走夜路,四下里黑灯瞎火,我摸着前面一片热乎乎软乎乎的东西,好像是一面墙变软了。我疑心自己学会了穿墙术,待往旁边一转,绕过去才看到,原来是头大驴子的屁股!幸好,那驴子睡熟了,它没尥蹶子踢我。
这便是最普通的驴子。当驴子和字号凑到一起时,便有了阿胶。
一
二
而想起那些过去的字号,多少有些心酸。想当年,北京城里东单、西四、鼓楼、前门、王府井、大栅栏,外加天桥、菜市口、花儿市,更有那一条条的旧货街、皮货街、绣花街、木器街、干鲜果子街、玉器街、灯笼街、图书文化街……鳞次栉比的老字号,排列出一部敢比《东京梦华录》的北京版来。沿着街捋,挨着家逛,吃吧,买吧,玩吧,可着劲儿地造(浪费、花费)吧……一辈子也说不尽哪!
字号是有生命的,给它们命的是血汗,要它们命的是历史。崇尚现代化生活的今天,老字号旋风般地退场。也就个别厌恶快餐并怀抱旧式光阴的人,才想着到“八大楼”“八大居”“八大堂”之类的饭馆点哪个菜;还想着逢年过节,给亲戚提拉一稻香村的点心匣子。在穿衣方面,绝少有去瑞蚨祥、谦祥益买布现做,也不在家穿千层底布鞋,冬天也没人穿毛窝(棉鞋)。不舒服了也去医院,但是不去同仁堂找坐堂大夫;能用资生堂,就不用蛤蜊油雪花膏。洋字号代替了中华字号,洋货代替了国货,想起常四爷的话:“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鞋大衫,洋布裤褂……”(见老舍话剧《茶馆》第一幕)
我对老字号是留恋的,不论是逛老街还是看老照片,我喜欢看那些字号,看字号上的幌子和广告语。
每种行业都有幌子,幌子也叫招幌。《清明上河图》里就有幌子。民国时有个洋摄影家叫甘博,他拍了一通前门大街,照片里保留了许多老式幌子。最近见到街面上保存的老式幌子是在安阳老城区,一家过去的药铺,现在已成民居。现在幌子照旧,理发馆是用圆筒的三色转灯,东来顺还是用火锅,而茶叶铺吴裕泰,立了个抹茶冰激凌道具当幌子。
每种行业都有过去的广告语。那种用词不上书本,只相当于民间俗语。典雅,内敛,模拟对联或四六句,它化自古人的思维方式。现代人能模拟文言,但难模仿过去字号的习惯用语。《尚书》之所以难懂,也是用了上古时期的口语。
那些广告语连带字号名,都是用书法字体雕刻在砖石上的,也不乏民国书法家。旧京有位书法家叫张伯英,前门外的字号,大半出自他手。而天津有位书法家叫华世奎。他们大多是这样写的,比如一家药铺,在一间门面的上部有女儿墙,从右往左分别是:自办各省,地道药材,照□批发;下一排,右起是泉香桥井,左起是春满杏林;中间是字号:同□堂。
又有一家杂货店,上下联是:各种槟榔加工改造适口精良,奇品名烟批发各省与众不同。横批:槟榔□批发。
又一家叫福兴居的饭馆,来得干净利落:福兴居饭庄包办南北酒席内设旅馆。那个饭字写的是“飰”,用了个很少见的异体字。
如今不少广告语连带字号名都铲掉或抹平了。当一个字号,手艺不是原来的,经营不是原来的,氛围更不是原来的,那也无从谈承传了。
我看阿胶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买卖,用巨大的金属罐密封熬胶(过去也是用锅熬制,用棍子慢慢搅拌),凉凉了切成“山楂片”来卖。没法统计阿胶多送人还是自己用,反正放在锦盒里,拿得出手。
东阿能有个现代化的字号,一直兴旺着,难得。
三
自家称呼自家的字号,习惯叫“柜上”。我想起很多柜上的故事,也有些其他字号的故事。夏天我去过一趟福建,确切说是闽西,有个地方叫永定,土特产是土楼。从土楼群中钻出来,我们来到一个小村,村里的文物叫虎豹别墅,是胡文虎、胡文豹家族的产业。
胡文虎这个人,是与陈嘉庚并称的大慈善家,听名字就很江湖气。他出身江湖郎中家庭,文化不高,却混迹江湖,仗义疏财。他有个残疾兄弟叫胡文豹,兄弟感情颇深,他一直照顾兄弟,一向是虎豹并称。他开创的品牌是万金油、八卦丹等,在民国时畅销一时。万金油成了一个词,现在还在使用。
同样是医药,还有个相对小成本,但一时爆款的东西:北京长春堂的避瘟散。民国时日本的袪暑药人丹一时流行。人丹的包装上是个留着日本胡子的男人(有个词叫人丹胡)。那正是人们在心理上抵制日货,但表面上不得不用的阶段。北京长春堂的老板孙崇善(人称孙老道)抓住时机,顶着人丹发明了避瘟散,避瘟散的包装是个打坐的年长道士。避瘟散本着能治虎列拉(霍乱),也本着民族情绪,在民国时非常畅销。后来便完成使命,退出舞台了。
四
老字号的制度与现在不一样,它是伙东制和学徒制的混合体,浸透了中国家庭伦理。伙东制是东家出钱,请一位山西人当掌柜的,也便是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和CEO。旧京时期,山西人善于经营,多是请他们来做。这制度讲的是规矩、人情和伦理。东家没分家时,整个大家庭都靠这个买卖来吃饭,全家的钱便是柜上的钱。另一个制度是学徒制。学徒在字号里干活,用不着上学。多是十几岁跟着做学徒三年,学手艺成后便出徒,但多数徒弟会留在柜上继续当伙计,这样二十年下来,即便是个伙计,也能在乡下买房子置地了。
作为一家字号的伙计,在过去并不容易。伙计肯定会为字号服务一生(也不会干别的)。但学徒的时候,多是受难受气的三年,多是伺候师傅一家,受尽委屈。老舍先生的《我这一辈子》,里面写到当巡警的主人公是裱糊匠学徒出身,开头几章写尽了学徒之苦。“能挺过这么三年,顶倔强的人也得软了,顶软和的人也得硬了……一个学徒的脾气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被板子打出来的。”但作为东家,徒弟太老实了意味着笨得要死,而如果太聪明了肯定会干活偷手,保不齐卷铺盖跳槽。唉,东家也没有余粮啊。

⊙ 何大草· 手持利斧的齐白石
我的祖父念了几年私塾,念至十二岁起,在前门外的鼎仁当铺(这个字号名得家里的说法,并未考证)学徒三年,学成了便回来干自家的买卖,跟着曾祖学习照相。问家里人,为什么去当铺?答曰:当铺吃得好,不挨打,条件在各种铺子中算好的。
我们侯家经营过三个字号:德容、爱翠楼、松竹林,一个是照相馆,另两个是酒楼;另外在一些别的字号里有点股份。可不到一年里,伯祖父和曾祖父先后殡天,家里没多久就卖了三进的小院,从南锣鼓巷的黑芝麻胡同,搬到我现在居住的北新桥,这是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事了。原因是欠的债还不上,家里没人挑大梁。待我出生时,家已穷得窗纸都糊不起了。这仨字号干了起码有四十年,公私合营也有六十年了。我总是在想象祖父、曾祖父、叔伯祖父们如何辛苦地管事,他们上上下下地忙碌着。我不忘家中的字号,它们养育了祖先也养育了我,否则我不会被生到这个世界上。
五
过去北京人的生活,是与字号绑定在一起的。北京人习惯请客或收徒弟,去鸿宾楼;做买卖开张去东兴楼;考试中了去泰丰楼(在南方可去状元楼);而有好事了,去致美斋;纯属聚会雅集,来同春园或同和居……去哪个饭馆,请谁,吃什么,与人的生活绑在一起。“头顶马聚源(帽子),脚踩内联升(鞋),身穿八大祥(八家大绸缎庄,都是山东孟氏家族经营),腰缠四大恒(指四家银号的银票)”。过去的生活,不能不用老字号,而现在模式都变了,老字号用不用,都不吃劲了。
当然,老字号不用了,会换作新一轮的洋字号。护肤品是兰蔻和雅诗兰黛,家居是宜家,吃饭是肯德基与金拱门,穿运动鞋要耐克或彪马,衬衫要托米和阿玛尼,而太阳镜都要雷朋。西洋字号不题匾额也不写对联,生生地少了文人的财路。为了这些西洋老字号,中国人活得多累啊!千辛万苦攒足几年的钱,千方百计找出国的机会,再从国外背回来。那所谓的奢侈品,就为了个牌子。
原先,我们的老字号消费的群体很稳定,稳定到能不用现金,多是在年中、年关时才结账,体现的叫品牌忠诚度。熟识的买卖人,谈事多是君子协定,不必签合同,完全靠口头。一说就这么定了,就这么执行,现代社会不一样。过去是人情社会,是一个道德社会,现代是契约社会。契约可以撕毁,但道德与人情不能违背,就像中国的礼教。
其实,老字号最终面对的,是社会和消费者的变化。以前阿胶是有钱人用的,比如生孩子的妇人为了补营养才用,而现在普通人也用得起。过去人活得好好不会送人参,都是人落了炕快不行了,送上人参熬汤,再硬撑一段。不像现在有了西洋参,没事嘴里含着。就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字号也能到国外大卖,要看我们怎样经营。比如马应龙是研制药膏的,研发的眼药和痔疮药都极为好用,被美国人捧为灵丹妙药。我希望阿胶同样广泛地走出国门,卖给劳苦大众,卖给原本不信中医的人,让好东西恩济所有的地球人。
愿所有的字号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