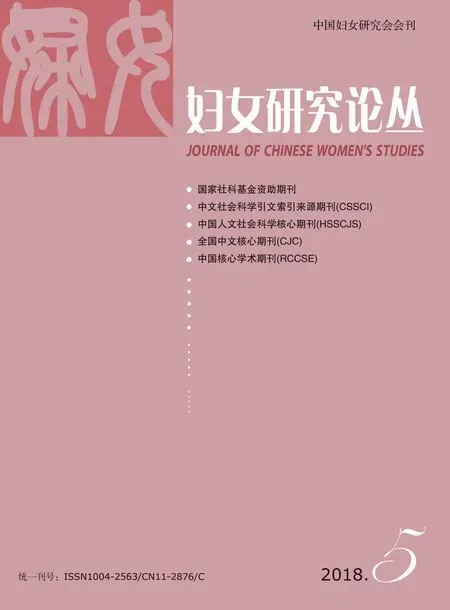《申报》影评中的“肉感”女体修辞演进与早期电影(1925-1935)*
马聪敏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从“人体”到“女体”——《申报》中的“肉感”与女体修辞
《申报》中首次出现“肉感”一词,是在1911年8月25日第36版小说栏目刊出的丑情小说《动物之爱》(二)中[注]此文的译者之一王钝根,于辛亥年即1911年8月24日为《申报》创编《自由谈》;此文的另一译者翼仍,时为《申报·自由谈》“海外奇谈”的栏目编译。两人于创办《自由谈》的第一日即辛亥七月初一日《申报》第三张第四版刊出同译的丑情小说《动物之爱》第一章;于辛亥年七月初二日即1911年8月25日《申报》第三张第四版刊出《动物之爱》第二章,首次出现“肉感”一词。:
所谓学生者,类皆情窦初开,易生肉感。一见小白菊雪白之肤、妖媚之态莫不心醉神迷。争投其拙诗陋文,以博美人之青。复摄小白菊之靓影,归而置诸座右。是可见小白菊当时殊为社会所倾倒也[1]。
《动物之爱》讲述巴黎欢场女子小白菊,从爱慕者红橘郎处得一红蛋,以为其无甚用处,遂将之赐予乞丐,孰料其中包有不菲钞票的故事。《动物之爱》中“肉感”一词的基本含义,指肉体上给异性以诱惑的感觉。其所配插图,对“肉感”的具体视觉形象做了呈现。细读该文插图中的“肉感”,可以明显看到,“肉感”首先与女体相关,而其所表达的女体的视觉形象具体是指:胸部浑圆突出,腰肢纤细健康,臀部肥美而坚实,一双长腿笔直而优美,身体丰腴,富有曲线美,皮肤雪白,体态婀娜妖媚,充满女性魅力,可给异性带来微妙的、神秘的、兴奋的感觉和感情等。
中国古代汉语中并没有“肉感”一词,作为完整词语,“肉感”的意义自近代以来方才获得,并且可能受到晚清以降东瀛文体的影响[注]“肉感”一词在日语中的词源及词义演变的相关内容,由笔者友人日本琦玉女子短期大学宫泽真一教授提供。。“肉感”一词日语中有两种发音方式,一种读作にっかん[nikkan],另一种读作にくかん[niku kan]。前者多用于口语,后者多用于书面语。其形容词形式“肉感的”读作にっかんてき[nikkan teki]或者にくかんてき[nikukan teki]。古代及中古日语词典中没有这一词条,日语词典对于“肉感”一词的词源及其第一次使用的确切引文也没有明确说明。作为一种艺术理念,在江户时代末期如北川歌麿的浮世绘[Ukiyoe]作品中就可看到体态更为丰满、更为感官的女体形象,但作为一个确切的概念和术语,“肉感”一词出现于现代日本的明治时期,如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7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东京版朝刊的广告页中,刊有由中村不折制作的名为《肉感美——历代浮世绘美人集》的木版彩色印刷、一套七枚的画片广告。再如1909年10月6日,《朝日新闻》东京版朝刊中,田边尚雄在“近世の学艺”栏目中发表《容姿の美学》第二讲《衣服の作用》,以简笔图画的形式对比了日本女性与欧洲女性的身体曲线美。身着日本传统和服的日本女性,其身体曲线隐藏在和服下,而欧洲女性身着连衣裙,脖颈细长,胸部丰满,腰肢纤细,腿部细长,更有魅力。1913年8月20日,《朝日新闻》东京版朝刊第6版,标题为《肉感的舞俑》的两张图片,表现了一位男性正在与他的女性舞伴跳舞。此时,“肉感”一词在日语表达中,已经有了性的魅力、性的诱惑的意义。有岛武郎[Arishima]在其写于1919年的小说《或る女》中,用女性眼神中所传送出的“肉感的な温かみ”形容女性的一种对于异性的吸引力。织田作之助[Sakunosuke]在其写于1946年的短篇故事《世相》中,也用“肉感的な女”与潇洒和摩登并置,说明女性的魅力。在现代日语中,“肉感”一词在形容女体时,通常表示女体的性的吸引力,但在与其他事物相联系时,则会失去“性”的意味,而仅仅表示其具有吸引力。有时也表达因为其所具有的真实的和重要的特质而具有的吸引力,如“肉感的饺子”等。
“肉感”一词在《申报》中甫一出现,所指涉的便是西洋女体形象,这与中国民族话语中早已熟悉的古代仕女造型相去甚远。明清以来,中国仕女画的发展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程式,其女体修辞主要是《诗经·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的婉约端庄与娴雅柔情。一方面,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以及第一批留学画家的归国,针对传统中国人物画缺乏解剖学和正常比例知识的批评变得颇为常见。传统水墨与西洋技法相结合的新绘画层出不穷,其女体修辞在服装、现代用品以及商业符号的包裹下,逐渐开始从传统仕女人物到时尚美女的形象转型。这一时期的女体修辞虽仍以柔弱为主,但身着新装、体态丰饶、婀娜多姿的女体之美已逐渐涌现[注]郑曼陀绘制的女学生月份牌,其背景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虽然表现新人,但仍没有摆脱造型羸弱的特点。徐青、郑曼陀两人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画《秋色横空人玉立》。画面为一位少女漫步于溪水河畔,胜似闲庭信步。楷书竖写题识:“……轻躯鹤立越苗条。袖罗裙幅,新样最魂销。为有芝兰同气味,别饶环燕丰。”。另一方面,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共和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追逐和效仿“现代性”,其参照无疑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西洋女体修辞成为被追逐和效仿的对象,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肉感”一词在1911年至1925年10月前的《申报》中几乎没有使用,直到1925年10月7日即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七日的《申报》本埠增刊《陈抱一先生对于人体画之解释》一文中,方再次出现:
再说人体又因种种姿势及光暗的关系,他的美点都是不同。美的姿势每从最自然的动静中发见,所以绘人体写生的时候,模特儿的姿势最要自然。肉色的光泽在适度的光线下是极美的。人体上肉感的感觉若经过艺术家纯美的表现就成为艺术化的肉感美。观鲁娜亚儿(Renoir)的裸体画及迈煜儿(Majllol)(法国近代雕刻家)的雕像都漂着丰艳的肉感味。这肉感就是一种不能说喻的美。但是一点都没有卑俗的感觉。也可说就是艺术的神秘[2]。
“肉感”一词在《申报》中的再次出现,其背景与人体画、人体写生、人体模特儿所引起的波澜有关[注]李叔同于1914年在浙江第一师范高师图画手工科使用人体写生。1915年刘海粟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专)开始雇用男孩做模特儿。1916年,美术院开始使用男子全裸模特进行教学。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院因为展出人体习作而受到攻击。1920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并使用女性模特儿。1925年到1926年期间,刘海粟在学校使用女人体模特引发的“模特儿事件”达到高潮。人体写生问题甚嚣尘上,人体画遭到报纸文章的攻击或者直接被查禁,以至于1925年8月24日,江苏省教育会议通过了禁用人体模特儿的提议。1926年官方判定上海美专暂缓使用人体模特儿,并对刘海粟处以50元罚款。。在人体写生被一般无识者群相骇怪,尤其是女体艺术的合法性问题带来巨大争议和风波的时候,时任上海图画美术院西画系教师的陈抱一先生[注]陈抱一(1893-1945),曾留学日本研究美术十余年之久,兼通英文和日文,大量涉猎各种艺术书籍,举办展览、组织艺术团体、开办艺术学校、创办杂志,其丰富的艺术活动与实践使其成为西方艺术进入中国的不可忽视的历史见证人。发表《女性肉体美的观察》一文,对人体写生和人体美的相关问题做了具有权威性的、让“误解者读之当可释然”的回应。此文认为“充溢着肉体美的生命是滋灌人类的永远的‘灵泉’”[2],在需要对“肉感”做权威解读的时候,适时地建构了“肉感”即“在适度的光线下的肉的光泽”、与“卑俗”无关的“艺术化的肉感美”“神秘的肉感美”的含义,并通过数例表现肉体美的绘画及雕刻作品,如意大利画家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巴洛克时期的画家鲁本斯的《海伦娜》、西班牙画家戈雅的《裸体的玛哈》、意大利画家乔尔乔内的《野外奏乐》《入睡的维纳斯》、法国画家莫奈的《奥林匹亚》以及雷诺阿的《沐浴中的少女》、雕塑家罗丹的裸像等,说明艺术化的“肉感美”的视觉形象。
陈抱一的《女性肉体美的观察》一文,在发表时改名为《陈抱一先生对于人体画之解释》,“女性肉体美”等同于“人体画”,与同时期“人体模特儿风波”的代名词是“女人体模特儿风波”、“裸体画”的代名词是“裸体妇人画”、“人体艺术合法性”的代名词是“女人体艺术合法性”、“身体的审美价值”等同于“女性身体的审美价值”的潜台词是一致的。肉感,作为近代艺术对于人体美的要求,本没有性别之分,但女体特别是妙龄丰盛的女性的肉体逐渐取代了人体,成为“肉感”所指涉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对象,这一“窄化”的过程,尽显男性权力中心社会在女性裸体与淫秽之物以及情色诱惑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文化传统,也显示了男权社会对女体的围观、凝视和聚焦的视觉关系。
二、《申报》影评中“肉感”女体修辞的艺术现代性获得
《申报》中与电影有关的“肉感”,最早出现在傅彦长发表于《申报》1926年6月30日第15版关于电影《伏德维尔》的影评文字中:
卡尔登影戏院近来所映写的伏德维儿(Vaudeuille)是近代艺术思想已经有了表现的凭据。这是在上海研究艺术的人所极应该欣喜的事。近代艺术思想最重要而且是最剌激的字只有两个,就是动与肉[3]。
此处的近代艺术思想之“近代”,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艺术界对于近代艺术进行重新认识的一种审美的精神标示,在含义上与艺术的“现代性”有相通之处。其基本立场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反抗与决裂以及对全新的中国艺术的呼唤与诉求。如刘海粟的呼吁:“……大家来做一个艺术叛徒!能够破坏,能够对抗作战,就是我们的伟大!”[4](P 575)再如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形艺社”的展览会宣言:“我们要打倒一切传统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新艺术,我们要建设为全人类的艺术……”[注]“形艺社”是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西洋画、图案画和中国画系学生组织的一个学生社团,校长林风眠参加了这个思想激进的社团的活动。1927年4月11日,《晨报》登载了“形艺社”展览会宣言。在傅彦长看来,“动”之成为“近代艺术思想最重要的两个”字眼之一,其中一个含义是指活动影戏之表现动的特性使其成为最具近代品格的艺术形式之一。《伏德维尔》(Vaudeuille,又名VarietéJealousy)一片中冬园(Wintorgarden)所表演的各种舞蹈、武技、猫狗小戏、转椅子、转脚踏车之类的杂耍综艺,尤其是剧中主人公在秋千架上表演杂技的段落,以及其中所包容着的一切近代生活,其令人目迷神眩的视觉观感,让评论者直呼其表现了确非活动影戏不可达到的“极动的艺术思想之表现的能事”。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随着影戏事业的风起云涌,关于“影戏是什么”的回答,依然囿于影戏为戏剧之一种的观念,同时又将影戏概念还原为“活动映画”(motion picture),并用大量更具认识论意味的如对电影的“活动”摄制方法的介绍来丰富活动影戏的本体观。活动影戏的专业性内容,如胶片的属性、拍摄对象的明度、景物的摄取、景物的动性、摄影的范围、对象的距离、摄影的速度、对象的显隐、镜头前的彩虹光圈、自动的混合、黑幕上的重摄、遮盖法的重摄、间断的摄法、倒摇的摄法、突然的显露、摄影时的注意等诸多专业性、科学性和技术性的摄制方法得到强调。
“动”,一方面是指影戏由于其“动性”的科学性、技术性和专业性而获得的艺术现代性品格,这一艺术现代性品格的获得,是在对中国艺术固有传统的拒绝和决裂以及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的近代思想的受容过程中完成的;另一方面,“动”的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指艺术的“自动力”,即艺术的自我创新的能力,所以作者在文中对中国艺术缺乏自我创新能力发起了如下的批判:
生在近代而不知努力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想呵。他们如果是画家,决不会在大都市里面去寻题目寻印象,而一定要到那满处是坟墓的什么杭州的西湖之类的所在去寻题目寻印象。现在以影戏为艺术对象的人也仍旧尽在那里编什么城市是万恶、乡下是清雅的情节,老是这样地在那里说什么动与肉的罪恶,而不晓得近代所努力要表现的艺术思想只是动与肉的两个很剌激的大字而已[3]。
“肉”之作为“近代艺术思想最重要的两个字眼之一”,其焦点多在由活动影戏这一形式所带来的“肉感女郎”的视觉形象建构:
克拉拉宝女士,她宛然是一个近代纯真的都会女性。她的肉心燃烧着的是浪漫底烈焰,肉感丰富的最显著者是胸前耸起的两个乳峰,两只银星发出来的光是带着无限的Vampire的魅力,她那蓬乱的头发,就是她在青春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天真底特征。她那8字身,就是她在青春时代诱惑男人的一副带着无限美与力的身段……女性本来是伟大的,克拉拉宝女士所描写出来的女性,尤其彻底与深到。她在银幕上真是在罗曼主义的作品中的一个最好最优越的灵魂[5]。
和克拉拉宝一样的肉感女郎,如有着“棕黑色的双瞳、棕黑色的秀发、明媚的秋波、动人的微笑、曼妙的声音、莹洁的肌肤、高耸的双峰”[6]的慕兰·奥黛;“一双眸子与两片樱唇、胸部美、肉感与爱娇完全表现在银幕之上”[7]的桃乐丽丝·德尔里奥;“皆擅绝色,关于情爱的表演亦热烈而真挚”[8]的美人佛琪·樊丽、南珊·葛尤雪等。以都会的、浪漫的、充满美的异性魅力的女体影像修辞建立了“肉感”与艺术现代性所具有的伟大、彻底、深刻、优越之间的关联。
在笔者看来,“肉感”女体修辞的艺术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有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肉感”的女体修辞的近代性或曰现代性(mordernazation)的获得,并进而成为近代艺术的审美标准之一,是在与古老中国、落后中国的决裂中得到建构,并与其他现代性事物与现代性空间一起获得现代性合法权的。在影片《如此巴黎》(SothisisParis)中,“巴黎是现代的最新的巴黎,只要看片中无线电话和却尔斯顿舞的盛况即可知”[9];“舞场的柱子都是女子的足部,含有近代的意”[9];“无数的肉腿或在幕的上下或在幕的正中或在幕的两旁急动着摇摆着”[9]。“肉感”取得的“现代性”,与无线电话等现代性事物、现代化的巴黎和新的巴黎等现代性空间,因为都“含着近代的意”而得以相提并论了。
第二,在中国艺术场域内部,作为革旧立新的武器之一,不能忽视“肉感”的艺术现代性所具有的攻击性。作为近代语汇的“肉感”,在《申报》中第一次用来形容电影界的中国女性,是采子在《银台紫舞记》中形容南国著名舞星紫罗兰时所用。“夫肉感者多显露。灵感者每深切……紫姝体魄既健。舞术亦似习自西人者。殆已完全为一欧化美人矣。……内子颇以予意为病。谓予想像中之舞之女。系已为时人所唾弃之东方病态美。”[10]20世纪20年代,肉感与灵感的关系不再是重灵轻肉传统[注]就中国思想的主流来说,是言心重于言身的,儒家的“肉身性”因汉代天人感应的神秘阐释、宋明理学的形上规定、政制(治)共同体的钳制等,使得心性与身体的断裂、道对肉身的压制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中固有的地位结构,肉感凸现,有肉感方有灵感的灵肉一致的观念在大众媒体领域得到建构。
第三,“肉感”的女体修辞所特有的指向性:热情、主张自我、即任主观、没有羁缚等意义,在与其时的妇女解放运动相契合的同时,又以更先锋的姿态,与早期妇女不缠足运动、兴女学运动、女性参政运动所产生的新的羁绊划清界限,并进而与近代性或曰现代性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有了关联。
新艺术运动至少是含有“肉”与“动”的意义,充分的现世思想和充分的自由思想。至少要向礼教思想进攻,向宗教思想进攻,向山林隐逸思想进攻,向命运思想进攻,向吟风弄月红男绿女式的女学思想进攻[11]。
总之,在“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艺术现代性所应具有的反抗精神,集中体现在“肉”与“动”两个关键词上。“动”所表达的近代品格与“自动力”即创造力,“肉”所表达的“真美”与其开放性及自由精神,成为《申报》影评中“肉感”的女体修辞所具有的艺术现代性和审美自在性的主体含义。
三、《申报》影评中“肉感”女体修辞演进的三条路径
1928年9月30日《申报》刊登了《巴黎艳舞记》(又名《巴黎春色》)即将在百星大戏院开映的消息,《巴黎春色》之来到上海,其“肉感”依然带有攻击伪道德的“大肉感”的攻击性,但同时,该片在上海上映后,绝对禁止非成年的儿童观影,随之带来的对“肉感”的艳情化、奇观化、神秘化的侧重,逐渐成为流行趋势。“肉感”的含义逐渐向妖艳、奇妙、浪漫、香艳等“吸引力电影”的奇观因素上侧重。“肉感”的女体修辞路径有了不同侧重,形成不同线索,“肉感”的艺术现代性含义也逐渐发生偏离。
(一)商品的“肉感”与女体的消费主义修辞
“肉感”女体修辞的路径之一,是“肉感”一词在所指与能指的双重符码意义上与艺术之美越离越远,与“经济”“生意经”“投机生意”等含义却越来越接近的“诲淫”性质。看影戏,是近代生活之一种“化少许金钱的代价,在一二小时内,可以看到许多可歌可泣、悲欢离合或是滑稽可笑的人生缩影,是为了求精神上的兴奋、神经上的刺激”[12]。“肉感”之能达到“精神上的兴奋”“神经上的刺激”是毋庸讳言的,所以,“浪漫肉感”“诱惑刺激”“丰满的臀”“乳峰肉感”的号召性标语在营业不振时就尤其要作为生意经的依傍了。以“肉感”为生意经来标榜,是舶来片的妙招[注]如最具肉感的滑稽爱情巨片《春宵一刻值千金》;风流浪漫、富有肉感剌激的《风月宝鉴》;肉感而热烈的滑稽言情名片《骏马美人》;以“伦敦一大戏院作背景,穿插有戏剧、有丽术、有肉感的跳舞,……其情节亦复离奇曲折、兼香艳滑稽神秘之长,且富于刺激性的奇情巨片”《红宝石》;等等。,也是早期民族电影的法宝。早期民族电影中有大量的影片直接以“肉感”为噱头。如锡藩影片公司宣称重金摄成的肉感国术巨片《理想中的英雄》,片中有数十裸体女子表演天魔舞的镜头。《女侠白玫瑰》香艳浪漫之处有美女就浴、同性恋爱、姊妹争风等,俱富有肉感色彩。尚武、神怪、香艳名片《大破青龙洞》,有妙龄女子多人戏浴海中的镜头。影片《通天河》,取材于西游记中神怪、香艳、肉感的一段。张石川为“爱护国产片者意”,特拍摄《新西游记》第二集,情节有“K女士之迷人术、九花娘之勾魂法、小阿媛灌迷汤”[13],集香艳、浪漫、肉感于一炉。连以拍摄新闻影片为主的鹰目新闻影片公司,也与南洋某片商合作,开拍苗猺装束武术剧《蛮荒两朵花》,片中女演员的服装,以豹皮遮体、袒胸裸臀、极尽香艳肉感之能事。大中华百合公司之香艳肉感爱情影片《马戏女》,由周文珠、张文清主演,其中有神秘肉感之表演。《火烧七星楼》(又名《大闹玄清观》)中不仅有幻变及飞剑等设想奇特的特技,而且有香艳肉感之表演若干。1931年7月7日上海影戏公司但杜宇导演,殷明珠、王元春主演的《东方夜谈》(本名《人参果》)中有庆宴一场,祼美人从凤盒莲花中冉冉而出,载歌载舞,异常肉感。
最后的一节,幕启了,一个含羞的女郎,也许是操皮肉生涯者,她把薄如蝉翼的纱展开,一露这女性的秘密,就算了。同时,观众起了“轰”的一阵笑声……[14]
1933年下半年,中央为了体恤商艰,维持国产片前途,特发行一种“未通过国产片临时准许公映执照”,允许凡被禁的一切国产片,可以在6个月内(1933年6月15日到12月15日)放映。小制片公司出品的神怪、武侠、肉感影片重见天日,“肉感”影片有一短暂的回流。人英在《都市缩影》一文中详细描述了1933年下半年肉感电影回流的细节:
经过××路的中段,在一个扎起竹篱笆预备兴建电影院和跳舞场的场合,在外面钉起一块马口铁皮的广告牌,“心的安慰,性的安慰”,他是这样皇皇然的告诉我们。怪不得现在的电影,是没有什么教育意味,而专求香艳肉感的。跳舞场也不包含什么交际和娱乐,而专求性的发泄。我终至于莅然若失,或许这是一幅模糊的都市的缩影吧[15]。
不论是肉感影片还是歌舞团或游艺用肉感来吸引顾客,其原因都在于商业的凋敝不景气[注]现在内地各城市影戏院大都向关门停闭的路上走了,如成都,五家影院就有三家在本年十一月关了门,其余两家则因积欠省市医药捐在十二月被市当局勒令停业。汉口影院六家除世界一家尚能勉强维持外,其余倒的倒,未倒的也如风前之烛了。广州影院担负了五种捐税:戏饷、娱乐捐、娱乐印花、广告捐、营业税,因不堪担负,有全部停业的危机。即如遍地黄金的上海,影院营业也不大景气,有一轮戏院降而为二轮的,有以专映权定期包于电影公司的,至于内部极力紧缩,和想法节省广告费等,也都在影院老板的算盘内。见夏贞德:《一年来之中国电影》,1935年1月6日《申报》。。一旦中国影业出现衰落的景象,或是电影公司或影戏院的营业方面步入挣扎的境地,“出卖肉感”、走回“肉感经济”的老路是最有效的救市方式。
(二)堕落的“肉感”与女体的民族主义修辞
作为艺术美标准的“肉感”,在近代美术领域一直保持着该词语所特有的专业性。与美术领域不同,“肉感”一词的词义变化,在一·二八事变之后,逐渐走向“革命”的对立面。“肉感”之罪恶直指青年的堕落、艺术的堕落、民族的堕落与国家之将亡。曾经作为现代性审美标准之一的“肉感”也开始尽显其“现代性”之罪恶。
怎说不会亡国呢!现代的乐园中,处处都是亡国的现象:提倡着肉感作品,比着过去时代的八股文章,尤其流毒无尽。迷恋着歌唇舞腰,比着过去时代的三寸金莲,尤其麻醉一般青年的国民性!科学不进步,而炫于物质文明,人人都喜舶来品。比着过去时代,科学不进步,而人人尚能推行国货,尤其可怖而可危![16]
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陷入战争状态,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抵抗达一月有余。自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各业罢市御侮两月之久,并于1932年3月26日令各业开始复业。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影戏院也停市,后又复业,复业后,原来以“肉感”“香艳”来取悦观众而求满售其座的心理以及把电影作为“消遣品”及“玩意儿”的行为,逐渐被认为是足以使电影破产的“观念的错误”。而与“观念的错误”相对的,则是有着正确高尚的中心思想的“意识的正确”。虽然,作为一种号召的方法,“肉感”还没有完全失效,影戏院的广告上依然有大量香艳、肉感的字句,但其号召力逐渐乏力。“肉感”的“肉”,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准亡国奴的焦虑心态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肉感”成为口诛笔伐的焦点概念。
确然,东北在表现着肉感呢。死尸暴露在疆场上,十足地肉感,只可惜都市里人们没有看到罢了,以后我想登这类广告,最好加上“我们的肉感是货真价实,不信请到东北一看,方见言之不谬也”[17]。
一面是以“浓歌腻舞、现代的、空前的”为措辞的广告,一面是“这里没有大腿,不用肉感”的口号,国难期间,“肉感”与“没有肉感”的对立,观念的错误与意识的正确的对立,欧美影片与《生路》《重逢》《亚洲风云》《金山》等苏俄影片的对立,促成了中国民族电影的一种新觉醒。1931年,随着中央电影检查会采取严格主义,公映影片的数量锐减,客观上使得标榜“肉感”的国产影片受到斥责,得到肃清。同时,在意识与观念的领域,随着《狂流》《城市之夜》《三个摩登女性》的公映,尤其是既无爱情又无肉感但竟可以连映60天、观影人数达到22万人的《姊妹花》以及连映80多天、成为1934年最轰动影片的《渔光曲》的出现,既无爱情、也非肉感、又能卖座的国产影片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影片卖座的经济效应反哺“软硬之争”的观念之争,基本肃清了“肉感”对于1931年后中国民族影片的号召力。“意识正确”替代“肉感”,成为中国新兴民族电影的判断标准与号召力所在。电影公司在制片方针上也随之变化,在题材的剪取上,对小市民生活苦况的描写,对现实的有力揭露,成为一种争取文化上、营业上胜利的方法。如拍过《关东大侠》的月明公司投拍制作意识正确的爱国名片《恶邻》;天一公司自《青春之火》《吉地》《似水流年》《舞宫春梦》后,投拍意识正确而有力之《红粉铁血》《挣扎》等。
(三)意识正确的“肉感”与女体的新生活主义影像修辞
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对影片中的“肉感”以及“肉感镜头”的格外敏感与严格检查不同[注]浪漫肉感影片因为一直以来被认为其对世道人心的腐蚀性,所以在中央检查委员会的电影检查中,予以特别注意。覆衾共卧、狂吻、脱衣见脐及女子小腿镜头等均予以删除。国产影片中如“联华公司的《再会吧!上海》,删去接吻及化妆跳舞镜头;《神女》删去妓女与游客住宿旅馆的镜头;明星公司的《春之花》,删去台词“不是我有几个姨太太吗?全送给人家了,就是谁要,谁拿用”;《船家女》,删去歌词“无钱的卖身进妓院”;上海有声影片公司的《健美运动》,其中女子拔河与跳绳的镜头,因光线不佳,看似裸体剪影,被删去。文化影片公司的《中国健美的女性》,本已通过检查,在修剪后准演。但该片放映时,公司与影院老板出于生意经,“竟将已修剪之重要部分擅自加入,并利用教育影片名义,作不正当宣传,以蒙蔽观众,引起社会不良批评,情节甚为严重”,结果被罚款并禁演。见《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议事录》(1936年6月13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1936年第3卷第6期,第76页。,20世纪30年代各种影戏小报的广告或者篇目上,还常常用“肉感”吸引眼球。如“谭雪蓉肉感出现”[18]、“热情肉感女郎黎灼灼”[19]、“梁赛珊的一个肉感镜头”[20]、“陈燕燕乳房公开”[21],等等。但事实上,这里的“肉感”也仅仅是一种宣传标语,其实广告宣传得再怎么香艳欲滴,而其时的影片中,“肉感”的表现也已经无伤风化了。“肉感”的“无伤风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针对“肉感”和“肉感镜头”的严格检查,使得电影在经过审查后自然过滤掉了不良含义;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裸体运动、健美运动在德国、美国发源,电影《回到自然》《健美运动》将德法美各国的裸体运动和体育大众化运动介绍到中国国内,银幕上新生活信徒们那种自由、天真、活泼、康健的健身强体方法得到传播,契合了新生活运动的主题。
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一般同胞,个人都能做健全的现代国民。要做健全的现代国民,第一就要有强健的身体,有了强健的身体就有了强健的精神,有了强健的精神,就可学会一切强国的本领,有了各种强国的本领自然可以保卫国家,发扬民族,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永远适存于世界”[22](P 41)。健全社会的实现,不仅需要健全的男子,而且需要健全的女子。于是在新生活运动的号召下,“肉感”的女体影像修辞呈现出自然的(natural)、康健的、富有生活力的意味。正如《到自然去》中黎莉莉所唱的那样:“草编裙,皮做衣,哪怕风雪雨;陆擒豺虎海斩蛟,杀兽有宝刀。早撒网,晚耕田,工作夕阳边;优者胜利劣者败,携手到自然。”此时,《人间仙子》《健美运动》《国色天香》《蔷薇之歌》等中国式歌舞片的拍摄,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其“肉感”更多的只是标语,而无实质性的“肉感”,进而言之,代之的是一种意识正确的“肉感”,有深刻意义的“肉感”。如但杜宇的《人间仙子》,“广告上见满堆着肉香、粉味,便以为是一出在一种简陋的组织之下饶有美国华纳风味的出卖肉感的影片而已”,但“全片并没有甚么肉感”[23]。“虽是一样有着千百条肉感的大腿,但它却暴露了富有者追求女性的丑态,它暴露了人生的虚伪,它写出了少女在社会上立足的不易,它……实含有很深刻的意义。”[23]健康的体魄、健美的形象、健全的人格,正是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也是现代国民形象想象的重要发展。
四、“肉感”女体修辞的意识形态工具作用
正如皮埃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所说,电影是“书写”现实语言的符号体系[24]。电影使用形象符号所完成的以及所记述下的“肉感”一词的文化流变,其实也是对那段流变的现实的符号化解析。在美术中的与人体美相关的“肉感”,其词义相对固定,少有演变。而在作为大众媒介的电影中,“肉感”一词的文化建构,反映出的是一个时代文化心理的转移轨迹。“肉感”在中国早期电影中女体修辞路径的变化,交织成“肉感”一词的意义生成和其文化史建构的复杂样貌:代表了时代方向、天赋的、带有解放和先锋意义的具有近代性和现代性的被呼唤的“肉感”;表现真与美,带有艺术性的美的“肉感”、艺术的“肉感”;带有“危险的愉悦”的商品化的“肉感”、诱惑性的“肉感”、堕落性的“肉感”;反时代的、站在革命对立面,尽显现代性罪恶的错误的“肉感”、被诅咒的“肉感”。“肉感”的文化史建构,呈现出多条演进轨迹。一方面,“肉感”的女体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修辞逐渐使其走向其含义的对立面,所指逐渐剥离并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呈现出能指与所指的剥离和漂移状态。从“x”到“反x”的单向的不可逆轨迹,即所指的内涵却逐渐剥离并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是独特而又具有典型性的。另一方面,“肉感”的女体新生活主义修辞继承了艺术现代性的余脉,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所指的本来含义。其多条路径所形成的交缠和模糊的地带,呈现出“肉感”与妇女解放、现代中国想象等诸议题的复杂联系。
“修辞学在其全盛时期既非一种以某些直觉方式关注人们语言经验的‘人文主义’,也不是一种仅仅专注于语言手段之分析的‘形式主义’……它不把话语和作品仅仅视为进行美学沉思或无限解构的文本对象,却将它们视为与作者和读者、演说者和听众之间的广泛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的活动形态,脱离其植根的社会目的和状况,它们就多半不可理解。”[25](PP 257-258)修辞,就是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指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社会意识,更主要的是指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指存在于共识中的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各种虚假观念”[26](P 15)。意识形态的实现借助于修辞的展开过程,修辞,是意识形态工具,也是意识形态的同谋。
“肉感”女体修辞背后固然有不同的阐发背景,但这一概念被引进后的遭遇和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其主因是时代风云变幻造成的意识形态导向的变化:共和初期,意识形态的全面危机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再造来化解。其时“新学”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进入,与旧学形成尖锐对立,中西、新旧各种思想理论和学说相互交锋是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社会精英追逐和效仿所谓“现代性”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主流方向。1915-1927年,中国政治动荡不安,大一统政治被打破,出现权力和权威真空,意识形态论战在以往的政治和权力的空间外有可能涉及资源和资本的再分配。抗战初期,社会情绪和主流政治转向民族主义。而20世纪30代中期的新生活运动则显示了国民党作为统治阶级一直在试图寻找的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意识形态与价值信仰系统的努力。“肉感”女体修辞所遭遇的“复杂样貌”,“肉感”的不同命运:被呼唤、被利用、被诅咒、被批判、被抛弃,恰恰是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修辞重构。
修辞,是意识形态的同谋,也是意识形态的破坏者。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的实现借助于修辞的展开过程,则克服意识形态的手段也应是修辞手段[27](P 5)。罗兰·巴特认为应该在文本和符号中保持两条边线:一条边线聚集着文化、历史、句子等意识形态之物,另一条则是异端、新物、身体等审美之物[28](P 16)。“肉感”这个被利用的字眼所承载的女体修辞,其所具有的自在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现代性(真美、创造力、自由精神),恰恰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文本和符号中的两条边线之一,在意识形态边线的缝隙、断层和断裂处破坏与对抗意识形态。本文以“肉感”这个颇具现代意味的概念为例,可以看到修辞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是怎样具体发挥作用的——无论哪个时代,修辞都具有如此功能。作为被意识形态利用的概念,值得不断指证的是,这个概念在“被利用”的时候(无论被褒还是被贬)对“肉感”的实际承载者女性本身造成的误导和伤害,也间接地呈现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