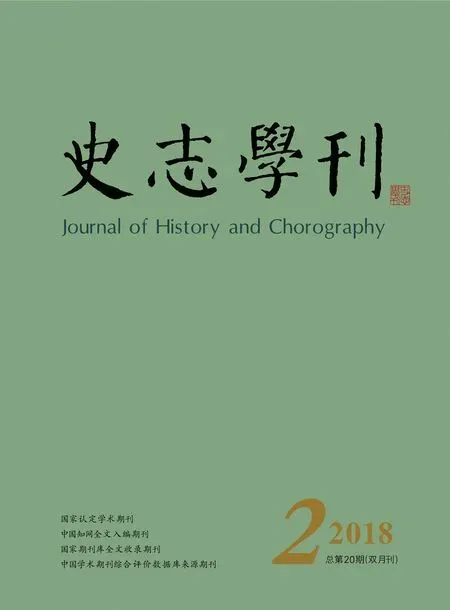宋太祖迁都洛阳之议新探
李大旗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汉唐至宋,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南迁,作为国家权力核心象征的都城也不断向东迁移。“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为每个王朝或政权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1]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M].中华书局,1996.(P180)。宋代后周而有天下,以后周旧都汴京为都城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随着宋在南方疆域的不断拓展及北方辽国的日益壮大,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这一看似毫无疑问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借郊祀之名提出要迁都洛阳,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最终未果。这次迁都之议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及其后果对于北宋国运的发展及多都制的最终形成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探析北宋政治生态状况的一个重要起点。
关于这次迁都之议,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较早地撰文对宋太祖欲借郊祀而迁都洛阳的过程进行了专门分析,将其中止的原因总结为在兵制上持有不同政策和态度的晋王赵光义及其周围势力的反对[2](日)久保田和男著,赵望秦等译.五代宋初的洛阳和国都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3).。王永太则在对宋初迁都洛阳相关史料的来源及可靠性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与久保田氏提出商榷,认为晋王反对迁都的动机并不存在,迁都的中止和定都开封的根本原因在于漕运的现实状况,是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迁移的必然结果[3]王永太.宋初迁都洛阳的考辨及其意义[J].中国史研究,2005,(2).。马强在回顾了整个唐宋时期的定都和迁都之议后认为宋初定都开封顺应了唐宋时期国都东迁的历史发展趋势,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北宋朝廷中一直存在迁都的呼声,开封军事地理形势上的先天缺陷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4]马强.唐宋时期关于定都与迁都之议[J].人文杂志,2009,(1).。除了以上专门系统的讨论之外,个案性的城市研究和通识性的断代史著作,如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5]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6]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M].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余蔚《宋史》[7]余蔚.宋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等,对于宋太祖迁都之事也都有提及。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或者侧重于对史实及其影响的描述,或者侧重于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及对迁都未果原因的分析,而较少涉及宋太祖提出迁都的具体原因。笔者认为,从宋太祖迁都的动机这一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同前人不一样的认识。同时,对于史料记载和迁都未果的影响及目前学界已经做出的有关宋太祖迁都原因的解释等方面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和商榷的余地。因此对此一事件做一重新探析,以求达到深化认识北宋历史发展过程的目的。
一
关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欲迁都洛阳的史实,《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为:
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迁,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几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7)[M].中华书局,2004.(P369)
针对这段史料记载,久保田和男和王永太在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辨析,此处不再做过多探讨。只是,前者认为此段史料的记载基本值得信赖,并由此指出迁都之议背后有宋太祖与晋王的权力之争。而后者则认为宋太祖是采纳李怀忠的阻谏才放弃迁都的,史料中的晋王之谏应是出于杜撰,并非历史事实。笔者认为,两者分歧的重点在于李怀忠的阻谏到底是如上记载的“上亦弗从”,经过晋王再谏以后宋太祖才放弃迁都,抑或如《宋史·李怀忠传》所载他的反对意见一经提出,宋太祖便“嘉纳之”[2](元)脱脱等.宋史(卷 260)·李怀忠传[M].中华书局,1977.(P9022)。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宋太祖欲迁都洛阳的动机上来。
宋太祖为什么想要迁都洛阳呢?根据上面所引史料,第一重原因是“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迁移都城,修造宫殿、城池、官署等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从起居郎李符所陈的“八难”中就可以看出,迁都事关重大,且十分不易。王朝时代虽然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但若单凭感情用事就提出迁都之事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这点不会是宋太祖欲迁都的出发点,更不会是主要原因。《长编》记载的第二重原因“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则在宋太祖与晋王的对话中出现,因事涉杜撰,暂留下文讨论。《宋史·李怀忠传》则载宋太祖欲迁都洛阳的原因为“爱其地势得天下中正”[2](P9022),这是第三重原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爱”是出现在“上幸西京”之后,即宋太祖在郊祀的过程中临时起意想要迁都,这与《长编》所载的两重原因中宋太祖早有谋划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要确定第三重原因是否就是宋太祖欲迁都的真正动机,就要首先解决迁都之想确实是宋太祖临时起意吗?
按《长编》载开宝八年(975)十月“遣庄宅使王仁珪、内供奉官李仁祚与知河南府焦继勋同修洛阳宫室,上始谋西幸也”[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M].中华书局,2004.(P348)。开宝九年正月庚辰,“诏幸西京,将以四月有事于南郊”[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7)[M].中华书局,2004.(P363)。从此两条材料只能看出宋太祖有行幸洛阳并在洛阳举行郊祀的意愿,尚不能说有迁都之念。但是,宋太祖在位16年(960—976),亲行南郊祭祀4次,前3次都是在开封进行,此次却要大费周章选择在洛阳举行,其动机确实值得推敲。久保田和男认为,后梁太祖、后唐庄宗都曾在洛阳郊祀之后留都于洛阳,宋太祖很有可能效仿他们,就好比他效仿后周太祖黄袍加身一样,是借郊祀之机,行迁都之事。因此,这两条材料所示也不能排除迁都为早有预谋的可能性。随后,开宝九年正月末“浚洛水”[2](P364),这一举动十分值得玩味。虽然宋一立国,就明确“汴都仰给漕运,故河渠最为急务”“岁调丁夫开浚淤浅”[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M].中华书局,2004.(P6),但是此前都只是对开封周围的汴河、五丈渠、闵河(惠民河)等漕运价值较大的河流进行疏浚,而对贯穿西京,漕运价值不大的洛河进行疏浚尚属首次。随即,宋太祖“诏发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桥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4](元)脱脱等.宋史(卷 94)·河渠四[M].中华书局,1977.(P2336),“穿掘民田,通于巩,入黄河,欲大通舟楫之利,辇运军食于洛下”[5]张齐贤撰,俞钢整理.洛阳缙绅旧闻记(卷5)·石中获小龟[M].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M].大象出版社,2003.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将开凿漕渠之时系于三月末,可见李焘并不能确定漕渠开凿的具体时间。但是同卷记载三月丙子,宋太祖已经从京师出发前往洛阳郊祀了,那么凿渠之事究竟是在郊祀之前,还是郊祀之后呢?据此处张齐贤载“太祖皇帝将幸西洛,命修大内,督工役甚急,兼开凿漕河”,可知凿渠之事正在郊祀之前。(P200)。如果说选择洛阳进行郊祀不能说明宋太祖有迁都意图的话,那么对于洛阳的漕运困境进行治理则毫无疑问有这方面的考虑。王永太将宋太祖迁都中止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封比洛阳更具漕运优势,而很明显宋太祖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整顿洛阳漕运正可以说明宋太祖有意让洛阳在此方面的定都优势与开封比肩。因此,笔者认为开宝九年郊祀之后太祖欲都洛阳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种有计划的安排。所以,《宋史·李怀忠传》中所载宋太祖郊祀之后,因“爱其山川形势”,才“有迁都意”[6](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 16)·武臣·李怀忠[M].中华书局,2012.(P488)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二
如果宋太祖是郊祀之后临时起意想要迁都,经过李怀忠的阻谏随即放弃是有可能的。但是,就以上分析可知宋太祖迁都洛阳是早有筹划,并且在宫室、漕运等方面做了准备,那么《宋史·李怀忠传》中所载宋太祖在听闻李怀忠阻谏以后便迅速“嘉纳之”就值得怀疑了。下面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看看就李怀忠本人的身份及他的建议内容来说到底有没有扭转圣意的可能。
据《长编》载宋太祖有迁都意以后,最先上书劝谏的是起居郎李符。据蒋复璁考证,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符是晋王的“藩邸之股肱”,但根据他在宋太祖迁都事中与晋王的配合及后来在太宗朝秦王廷美被贬房陵等事中的行为推断,他应该是晋王的外围关系[7]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A].宋史新探[M].台北正中书局,1966.。是这样的吗?据《长编》载李符早先知归州,“转运司制置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等他“秩满归阙,上以京西诸州钱币不登”,于是开宝五年(972)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转运事”,并且以“李符到处,似朕亲行”八字赐之,“令揭于大旗,常以自随。符前后条奏便宜,凡百余条,其四十八事皆施行着于令”[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M].中华书局,2004.(P288)。可见李符是受到宋太祖一手提拔而成的官员,而且宋太祖对其极其信任。在开宝八年(975)征讨南唐的过程中还让李符“赴荆湖调发刍粮”,负责后勤重事,事成之后“赐金紫”[1](元)脱脱等.宋史(卷 270)·李符传[M].中华书局,1977.(P9275)。至开宝八年九月时,朝廷还接纳任京西转运使李符的建议“发和州三县丁夫,凿横江河以通粮道”[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6)[M].中华书局,2004.(P346)。而开宝八年十月时“上始谋西幸也”[2](P348),在这种“始议西迁”的情况下,任职京西转运使,对西京实际状况比较了解的李符“上书,陈八难”阻谏宋太祖迁都的行为,不能够说与太宗朝他受赵普指使去上言责贬秦王廷美一样是受了宋太宗的指使。而且,在洛阳郊祀之后,朝廷还“以调发军储有劳”改“京西转运使、起居郎李符为比部员外郎”[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7)[M].中华书局,2004.(P371),可见李符在郊祀前后始终是受宋太祖信任与器重之人。至于太宗朝他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正像《宋史·李符传》中所评价的那样,是“好希人主意以求进用”的结果,而不能说他在太祖朝就已经为晋王所指使了。
那么,回到李怀忠的话题上,备受宋太祖信任和器重的李符,在宋太祖刚有迁都想法的时候就提出系统的八种反对迁都的理由,宋太祖尚且“不从”,李怀忠的建言就能让已经做了多种准备,迁都几要决定的宋太祖改变心意么?按《宋史·李怀忠传》,宋太祖“掌禁兵时”,李怀忠“隶帐下为散都头”“乾德中,授东西班都指挥使”,在开宝二年(969),宋太祖征太原的过程中才以英勇异常“授散指挥使,迁富州团练使”[4](元)脱脱等.宋史(卷 260)·李怀忠传[M].中华书局,1977.(P9021)。在开宝九年郊祀时,李怀忠任“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是禁军的首领之一。无论《长编》还是《宋史》本传,对李怀忠的记载都比较简单,其一生中只有两件事载于史籍,一件即攻打太原城的战功,一件即为劝谏宋太祖迁都成功,可见其并非深受宋太祖器重的朝中枢要之人。李怀忠和李符相比,一个是只凭武功和资历占据高位的武将,一个是深受重用“似朕亲行”的文官。众所周知,宋太祖立国以后,提倡文治,重视文官的治国意见[5]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J].史学月刊,2005,(7).,李符的意见尚且不从,何以能从李怀忠?另外,从李怀忠所谏的内容来说,漕运与府库都可以概括进李符所陈“八难”之中,更何况宋太祖已经在漕运方面做了准备,李怀忠所谏说服力并不强。
那为什么《宋史·李怀忠传》等史料中记载李怀忠阻谏迁都确实成功了呢?据王永太分析,李怀忠劝谏太祖成功的史料应源自《三朝圣政录》《三朝宝训》两书[6]王永太.宋初迁都洛阳的考辨及其意义[J].中国史研究,2005,(2).(P96)。《三朝圣政录》为“嘉州判官石介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凡十九条。始君道英断、谨惜名器,终戒贪吏。每篇末自为赞,以申讽谕”[7](宋)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三朝圣政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330)。而《三朝宝训》一书的性质从王永太分析中所引的“臣今月初九日入侍经筵,进读《三朝宝训》”[8](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0)·论屯兵漕河大要[M].中华书局,1988.(P266)也可以看出,同《三朝圣政录》一样是一本展示祖宗圣明、臣下英勇的书籍。而李怀忠在“群臣莫敢谏”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不可谓不英勇,宋太祖听从臣下意见果断放弃迁都的想法不可谓不圣明,可如果英勇进谏的结果是“上亦弗从”,如何成全君明臣勇的书写主旨?况且李焘在《长编》中对李怀忠阻谏迁都一事已经自注“李怀忠为节度使,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冬,此时但领富州团练使。《三朝圣政录》称节度使者,误也”[3](P369)。《三朝圣政录》一书中连李怀忠的权位也进行了夸大,更可见其不实之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史·李怀忠传》等有关李怀忠阻谏迁都成功的记载并不是确实可靠的。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李焘在修《长编》时也看到了《三朝圣政录》,却为何将其阻谏的结果记载为“上亦弗从”呢?这正说明了李焘并不认同李怀忠能够阻谏成功,抑或是他参阅了更多其他的史料才做出了这样的记载。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宋太祖迁都洛阳是早有谋划,《宋史·李怀忠传》中所载宋太祖是郊祀之后,一时兴起“爱其地势得天下中正”才欲迁都洛阳,并且听从了李怀忠的阻谏而改变圣意是并不可靠的。那么,回到宋太祖为什么要迁都这个问题上来,就只有《长编》中所载的第二重原因比较可靠了。但是王永太分析认为,第二重原因所载的宋太祖与晋王的对话是杜撰而来。如果此段内容确属杜撰,何以对宋太祖迁都原因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下面来分析晋王劝谏迁都事属于杜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长编》中李焘自注说“晋王事据王禹偁《建隆遗事》,《正史》阙之”[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7)[M].中华书局,2004.(P369)。那么王禹偁的记载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建隆遗事》早佚,王永太引南宋晁公武、王明清对于此书的评论和李焘在《长编》中对此书注释认为,《建隆遗事》乃是托名之作,舛误甚多,因此书中所载晋王劝阻迁都事也不可信。但是,北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中却收录了《建隆遗事》中的晋王劝谏迁都的相关全文:
开宝末,议迁都洛阳。晋王言:“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于洛,恐水运艰阻,阙于军储。”上省表不报,命留中而已。异日,晋王宴见,从容又言:“迁都非便。”上曰:“迁洛未已,久当迁雍。”晋王叩其旨,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晋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晋王出,上谓侍臣曰:“晋王之言固善,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2](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 7)[M].中华书局,1983.(P66)
李焘在《长编》之中所采用的就是这段文字的后半部分。此段史料首尾贯通,有理有据,就本身来说很难判断是否出于杜撰。虽然李焘对《建隆遗事》一书的真伪持怀疑态度,但是他却采用了这段史料,可见李焘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家有自己的判断。另外,在王称《东都事略》卷28《李怀忠传》中亦同样将晋王劝谏迁都事系于李怀忠阻谏之后,可见王称对于晋王劝谏之事也是认可的。而且,《东都事略》中所载与《长编》并不完全相同:
太祖幸西京,有迁都意,怀忠乘间言曰:“汴都岁漕江淮米四五百万斛,赡军十数万,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迁都洛,臣实未见其利。”会晋王亦以为言,太祖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之故事,以安天下。”晋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太祖不应。晋王出,太祖谓侍臣曰:“晋王之言,若从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乃不过迁,遂还京师[3](宋)王称.东都事略(卷28)·李怀忠传[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193-194)。
或许王称并非引自《建隆遗事》,有另外的史料来源也未可知。一个反面例子就是在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中亦记载的相关内容就与《长编》完全相同[4](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太祖圣政[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43),很明显是袭自《长编》。四库馆臣评价《长编》与《东都事略》说“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王)称与李焘、李心传之书”[5](宋)王称.东都事略[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23)。两位史家均认可晋王劝谏迁都的史料,可见其价值所在。虽然南宋时即有人指出《建隆遗事》一书为托名之作,但是距离《建隆遗事》成书更近的北宋邵伯温却明确记载其书为王禹偁所作,而且“自叙甚秘,盖曰:‘吾太祖皇帝诸生也,一代之事皆目所见,考于国史或有不同。’”[1](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 7)[M].中华书局,1983.(P64),指出其价值所在。退一步说,纵然此书为托名之作,但它的成书时代距离宋太祖时期较近则是无疑的,北宋中期就已经广为流传,而且就连批评此书的晁公武都说“世多以其所记为然”[2](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上)·建隆遗事[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197),其内容绝非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定然有所依据。久保田和男的研究中对于晋王劝谏一事史料的真实性也并非完全认同,但是他分析认为这些史料背后反映出众所周知的宋太祖与晋王的权力斗争问题,可见久保田氏也是认同这些史料存在的合理性的。
另外,迁都之事关乎重大,开宝九年议迁都之时,太祖皇帝所倚信的谋臣赵普已经于开宝六年(973)因为为政过专,“廷臣多疾之”[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4)[M].中华书局,2004.(P304),受到宋太祖的怀疑[3](P303)而罢相[3](P306),退出了中央决策群体。而晋王赵光义就成了当时朝中仅次于宋太祖的重要决策者,而且自始至终他都是宋太祖信任和倚重之人,所以晋王不可能不参与迁都之议。反过来说,前文已经分析宋太祖迁都洛阳是有计划有准备的,郊祀之后,几乎就要决定迁都之时,也只有像晋王这样“重臣”才有改变圣意的可能。从这个层面上讲,晋王劝谏迁都史料的存在也是具有合理性的。
四
前文已分析《长编》所载宋太祖迁都洛阳事始末,特别是其中关于晋王劝谏之事是比较可靠的。那么根据史料记载宋太祖迁都的原因就只剩下“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一条了。但是,有学者也注意到了太祖欲迁都的动机问题,并且认为另有他因。前文已经提到,久保田和男指出这段记载虽然值得怀疑,但是却能够反映出宋太祖与晋王的权力斗争问题。因此,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在宋太祖的重要谋臣赵普离朝之后,晋王便乘机迅速扩大自己在开封的势力,至开宝九年太祖与晋王的权力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宋太祖迁都的真正原因正是想要“另起炉灶”,洗刷内外人事,重新培养自己的势力,但是最终因为自己在决策上已被“孤立”,所以失败。并且分析指出宋太祖在郊祀过程中所做的种种行为,包括晋升皇子德芳的权位,借洛阳宫室修建有功之名对德芳的岳父焦继勋进行升迁奖赏等都是为了给皇子“立名分、培植势力”,加紧与晋王进行权力斗争,而迁都更是他使出的与晋王斗争的“奇招”[4]余蔚.宋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P22-24)。笔者认为,迁都之议能反映出权力博弈是对的,但将权力斗争总结为迁都的动机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郊祀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太祖与晋王并非如想象中那般水火不容,太祖对朝廷的控制也并非有心无力。一件是开宝九年六月“上以晋王光义所居地势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门,至其第,遣工为大轮,激金水河注第中,且数临视,促成其役”[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7)[M].中华书局,2004.(P372),并且在七月戊辰还再一次“幸晋王第,观水入新池”[5](P373)。另一件是开宝九年八月丙辰,宋太祖“诏分兵入北汉界”,大规模发动第三次对北汉的进攻[5](P375)。前者是太祖对于皇弟的关心,后者是太祖对于朝廷控制力的展现。笔者分析,之所以有学者要将迁都的原因与太祖和晋王的权力斗争联系起来,是由于后来太祖的突然去世和太宗的登基给人留下一贯的二者斗争激烈的印象。有了这样的印象以后,将“迁都”一事也看作是二者权力斗争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真的迁都之议是双方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举措,而且后来李符在太宗朝的重用与他在迁都一事中立功有关[1]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A].宋史新探[M].台北正中书局,1966.(P90),那么在更为关键,迁都几于决定之时站出来阻谏的李怀忠却在太宗朝并未发迹。这也可见迁都并非是因权力博弈而起。
那么迁都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正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宋太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乃至非要用迁都来解决呢?这里有两重意思,“去冗兵”的想法及“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的叹息,是针对北宋冗兵的状况而言的,而“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则是对都城的选择而言的,而这两者正反映出北宋在整个立国环境上的焦虑。宋代后周以后,立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南方政权一一被兼并,就连实力最强的南唐也于开宝八年(975)十月被平定,但乾德二年(964)、开宝元年至二年(968—969)宋太祖两次伐北汉,都因为辽的插手而败退[2](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 12)·平北汉[M].中华书局,1977.。他深知北方不能平定不仅冗兵不可去,而且都城开封也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后晋开运三年(946),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相州节度使张彦泽受契丹命,率先锋二千人”便攻入了开封,后晋灭亡[3](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 85)·晋少帝纪第五[M].中华书局,1976.(P1123-1124)。虽然后周显德三年(956)正月周世宗曾“发丁夫十万城京师罗城”[4](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16)·周世宗纪第三[M].中华书局,1976.(P1539),但是开封毕竟无险可守,靠数量众多的禁军来拱卫又势必会造成冗兵的后果。裁撤冗兵就很难保证后晋之祸不再重演,不裁冗兵天下民力又必然逐渐耗竭,遵循汉唐经验,先迁都于距离开封较近又有险胜的洛阳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却被以李符和李怀忠为代表的臣下及皇弟晋王所否决了。宋太祖开宝九年八月对于北汉的征讨,也可说是迁都未果后改变策略,采用消除北方威胁的方法来应对这种立国焦虑的一步措施。只可惜北汉还尚未平定,宋太祖就突然去世,使得这种焦虑一直延续下去。
结语:都城、党争与国运
事实上,虽然宋太祖迁都未果,但此后北宋朝廷中一直都存在呼吁迁都的声音[5]马强.唐宋时期关于定都与迁都之议[J].人文杂志,2009,(1).。其中宋仁宗时期一次目前少有学者论及的迁都之议对北宋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景祐三年(1036),备受宋仁宗信任的重臣孔道辅向皇帝建言“迁都西洛”。宋仁宗就此事询问权知开封府范仲淹的意见,范仲淹认为“国家太平,岂可有迁都之议。但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然彼空虚已久,绝无储积,急难之时,将何以备。宜托名将有朝陵之行,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闲,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8)[M].中华书局,2004.(P2783)。这本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建议,但是当宋仁宗将此建议与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进行商议时,吕夷简却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将它贬低得一无是处。这引起了范仲淹的极大愤慨,于是他先是向宋仁宗呈上写明官员升迁次序的《百官图》,并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6](P2783),指责吕夷简专权。又写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臣下”四篇论奏[7](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7)[A].(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等校点.范仲淹全集[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P152-158)呈上,还向宋仁宗建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也”,都是明喻暗指吕夷简蒙蔽圣听[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8)[M].中华书局,2004.(P2784)。虽然范仲淹此前身为谏官,在明道二年(1033)废除郭皇后事上就与吕夷简结下了嫌隙[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3)[M].中华书局,2004.(P2648),但是这次因为对迁都的政见不同,二人彻底决裂。吕夷简闻知范仲淹的种种指责后大怒,在宋仁宗面前哭诉说“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3](元)脱脱等.宋史(卷 314)·范仲淹传[M].中华书局,1977.(P10269)。两人交相论奏,争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范仲淹被贬知饶州。当时殿中侍御史韩渎为了迎合吕夷简的意思,请得宋仁宗同意“以仲淹朋党牓朝堂”[1](P2784)。而后,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都因为范仲淹求情而被贬黜,“自是朋党之论兴矣”[3](P10269)。
王夫之评价宋代的朋党之争说“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4](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中华书局,1964.(P86)。正是这次因迁都而引起的争议开启了整个宋代党争的序幕,自此以后朝中政见不同者多以“朋党”指责对方,各方因于利益或意气之争而互相倾轧,不仅枉耗政治精力,也极大地阻碍了以后各种有利于国家改革措施的推行。范仲淹改革的中止、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西夏战争的反复等无不与此有重大关系,最终断送了北宋的国运。同时,正如宋太祖所担忧的一样,开封都城的地理位置不好也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郑樵评价宋都开封说“臣窃观自昔帝王之都,未有建宸极于汴者”“盖其地当四战之冲,无设险之山,则国失依凭,无流恶之水,则民多疾疠”“宋祖开基础,大臣无周公宅洛之谋,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难,岂其德之不建哉,由地势然尔”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都邑略·都邑序[M].中华书局,1995.(P561-562)可谓公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庆历二年(1042)在宋辽关系不稳的情况下,因为“景祐中,范仲淹知开封,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朝中有“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请”。但吕夷简却认为“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两者交相论奏,结果是促成了北宋大名府北京的建成[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6)[M].中华书局,2004.(P3260),最终完备了北宋“四京”的多都制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