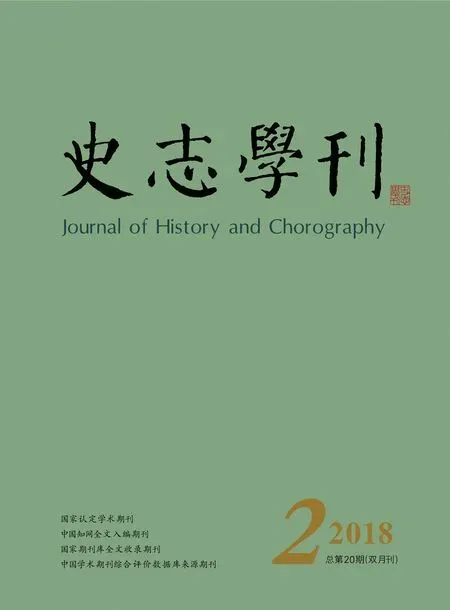晋宋之际的皇权回归与门阀余响
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2488)
东汉以降,随着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士庶界限日益明晰。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以品第取士,进一步加剧了士庶分流,遂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士庶格局,此为门阀政治之先声。司马氏代魏,惩于曹魏亡国之际孤弱无援,大兴宗王政治,然矫枉过正,宗王权势过盛,反而成为中央朝廷的潜在威胁。永嘉南渡,东晋复立,门阀政治时代由此开端;刘裕造宋,则象征着门阀政治时代的终结和传统皇权的回归。不过南朝时期门阀势力犹在,仍与回归的皇权进行着不懈的权力争夺。
一、东晋时代的门阀士族与皇权
(一)士族门阀化与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汉代采用察举、征辟等选官机制,通过对选官权的掌握,汉代官僚勋贵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形成一个个支系庞大的政治集团。东汉中后期,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通过世代传承家学的方式,累世公卿,世居高位,形成世家大族。在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士族势力虽然遭到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不过仍然表现出坚韧强劲的发展势头,并最终消灭了东汉的宦官势力。有惮于士族在与外戚、宦官集团斗争中展示出的强大社会号召力,曹操当政时曾颁布命令禁止朋党:“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异部,更相毁誉。……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1]陈寿.三国志[M].中华书局,1959.(P318)此外,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欲破除士族的入仕特权,抑制士族力量。然而当时士族影响力之大,即便是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借助士族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士族的实质性抑制也就无从谈起。史载:“(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三国志》卷10《魏书十·荀彧传》)曹丕当政,为借助士族之力取代汉室,遂取陈群之议,广泛推行九品中正制。唐长孺先生以为,汉末大姓、名士为魏晋士族的基础,九品中正制为士族服务,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中华书局,1983.(P53)。可以这样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实质是曹魏皇权向士族的妥协,此制推行进一步加剧了士族在官员选拔上的话语权,为巩固士族提供了政策保障。此后,曹魏代汉,曹魏的宗王政治徒具其表而已。《袁子》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魏氏春秋》载宗室曹冏上书曰:“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闲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三国志》卷20《魏书二十·广平哀王俨传》裴松之注),整个国家实际掌握在士家大族的手中,曹魏政权亦卒为士族所取代。
司马氏作为世族的代表立晋代魏,对于已经门阀化的世家大族,西晋皇权给予了足够的特权优待,以此保障世族门阀的基本利益,可以说,门阀的最终形成即在西晋,且当时士庶之分已经成为主流观念深入人心,森严的等级制度亦由此确立。为适应士庶之分产生的新的教育需求,晋武帝于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2]沈约.宋书[M].中华书局,1974.(P356)又,“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太学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3]萧子显.南齐书[M].中华书局,1972.(P145)可见国学与太学成为区分士庶的重要手段,国子学的创立也成为门阀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4]张旭华.试论国子学的创立与西晋门阀士族的形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P10-14)。不过,西晋门阀穷奢极欲、清谈误国,为西晋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晋卞壶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此此。”(《晋书》卷70《卞壸传》);桓温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98《桓温传》)。西晋亡后,晋元帝南渡,在江南士族的支持下重振晋室,东晋之世遂成为门阀士族时代。
(二)汉晋间皇权政治之进退
由东汉至东晋,是皇权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段,此间皇权与士族的斗争是一个波澜起伏、形势多变的漫长过程。东汉建国之初,刘秀采用三公制而未恢复丞相制,以尚书台为行政中枢,带有明确的集权思想[5]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190)。而尚书台的主要职能就是制约三公、抑制官僚士大夫阶层,防止其权势过盛危及皇权,君臣之间的博弈最终表现为皇帝私人掌握的内朝与外朝之间的争夺。事实上,以内朝对抗外朝的思想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即有先例可循,东汉时期正是通过内外朝双轨并行机制,皇权始得超越士族,实现独尊。
不过皇权独尊的现实前提和弊端是:依赖外戚或宦官来保证内朝的正常运转,以此对抗士族掌握的外朝。可以说,东汉的中前期,在皇权的掌控下,内朝、外朝的两大集团相互制约,形成一种难得的政治均势,这种政治均势成为皇权昌盛的有力保证。
然而,即便在皇权的授意下达成,这种政治均势和政局平衡依然无法长期持续,原因在于官僚士大夫群体与外戚、宦官集团注定无法兼容共存。面对外戚、宦官掌控的政治排斥,士大夫阶层通过“清议”的方式来影响选官仕进,弱敌强己。以名士郭泰为例,“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1]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P2227)汝南名士许劭与许靖“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1](P2235)清议之风盛行,自然引致外戚、宦官集团的反击,两大阵营的矛盾空前激化,此后遂有恒灵时的“党锢之祸”。“党锢之锅”破坏了三者之间的政治均势,外戚、宦官坐大,皇权则随着士大夫集团的没落,外戚、宦官集团权势畸重而被无限削弱,终致亡国。
不过士族门阀化的步伐却并未因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而止息,经过曹魏时期的蓄势休养,士族门阀的崛起已成为魏晋之际的必然趋势。西晋逆势而为,恢复宗王政治,其国遂亡;直到晋室南渡,晋元帝始在江左士族的帮助下,重整旧山河。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晋建立在南北各阶级协调的基础上,南北各阶级正是通过东晋建立而实现了利益趋于协调[2]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黄山书社,1987.(P157)。不过,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下,政权已经实际掌控在门阀士族手中。东晋时代皇权已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P27)。东晋皇权之暗弱,达到空前的地步。
二、晋宋之际的政治新格局
(一)传统皇权的回归
东晋后期,门阀政治格局下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政治均势随着后者的逐渐衰落被打破,历时百余年的门阀政治亦因此走到尽头。
淝水之战谢安隐退,是东晋门阀政治由盛转弱趋势开启的象征性事件[3](P292-293)。作为东晋时代最后一个执掌朝政的门阀士族,以王恭为代表的太原王氏在晋孝武帝伸张皇权的诉求面前,应付乏力,终致覆亡。东晋政治局势亦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机,出身次等士族的刘裕掌握了北府兵的控制权,他先后平定桓玄、北伐南燕、南定卢循,声望日隆,功高震主。义熙八年(412),刘裕罪状刘毅,发兵讨之,毅自缢而死。至此,江东已无任何势力可以与刘裕抗衡,刘裕成为东晋后期的实际领导人,打破了门阀士族把握朝政的惯例,开创东晋百年未有之变局。综而言之,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司马氏皇族已经腐朽,皇权亦无可能在此基础上振兴,刘裕遂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并承担起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重任,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与统治秩序[3](P257-301)。刘裕功业已定,人心所向,此后的禅代则如水到渠成,众望所归矣。
东晋元熙二年(420),晋恭帝行禅让之礼,刘裕正式登基为帝,标志着经历百余年的门阀政治之后,传统的皇权政治终于正式回归。刘裕作为开国之君,有着超乎常人的集权意识,早在造宋之前,就注意控制方镇势力,扬州、荆州、徐州等江东强藩皆由刘氏子弟镇守。宋立国之后,方镇冲要皆为刘门宗室,此为宗王政治回归之前声。刘裕死后,这一传统被刘宋政权继承,“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弟居之。”[4]沈约.宋书[M].中华书局,1974.(P1798)可以说,刘裕一手重建了宗王政治,欲以此来保障刘氏基业常青、江山稳固。
刘裕初死,徐羡之、谢晦等顾命大臣杀死少帝刘义符,迎立刘义隆,此为宗王政治全面施行之际,门阀势力的最后一次反扑。元嘉三年(426),宋文帝下诏征讨徐、谢集团,诸人皆死之,经过此番动荡,南宋的宗王政治终于稳固下来。
有此度重臣废立的前车之鉴,宋文帝更为坚定严格地推行宗王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宗王政治下的南宋朝廷也确实一扫门阀政治的陈腐气氛,开创出“元嘉之治”的太平气象。不过宋文帝身后,孝武帝等人以年少而登大宝,于方镇宗王而言,再无武、文之际的家长权威,地方诸镇便屡生叛乱。宋孝武帝为减轻宗王的威胁,采取分割强藩、异姓方镇取代同姓方镇、幼王出镇等方式对方镇格局进行调整[1]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J].历史研究,1997,(4).(P35-51)。然而,孝武帝此举削弱了宗王力量,导致异姓势力崛起,刘宋旋即为萧氏所取代,与此不无关联。萧齐建国后同样推行宗王政治,不过亦因无法克服皇权与宗王政治之间的矛盾,最终无法逃脱与刘宋相似的结局。
(二)寒人集团的崛起
门阀政治时代,士庶之别泾渭分明,深如鸿沟。这种区别不仅反映在交往、婚姻等社会生活中,在官职任选上也有所体现。清贵文翰之职为清职,多由士族出任;事务冗繁之职为浊职,多由寒人任之。
此所谓浊职,除武将兵家外,实为文法吏职,多繁剧庶政,这种清庶之辨早在汉时已可见其端倪。中国古代成熟的公文制度大体形成于秦汉时期,从秦汉时开始,帝国的行政运转已经离不开公文以及掌管公文的文吏[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汉时儒生集团对文吏及繁琐的公文工作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夷鄙之态,与晋时官员任选的清浊之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由于公文系统的高度发达,无论秦汉魏晋,文吏与浊职皆已成为帝国行政系统内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唐长孺先生指出,东晋门阀士族时代,虽然士庶之别几乎不可逾越,不过贵族亦不能完全把寒人排斥于政权组织之外[3]李延寿.南史[M].中华书局,1975.(P91-97),个中原因正在于此。
晋宋之际,传统的门阀政治正处于瓦解边缘,刘裕以强有力的手段恢复皇帝威权,彻底改变了东晋以来的政治格局,这种时代剧变决定了寒人集团崛起的必然性,寒人集团于此风云激荡之际也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进取态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也正是借助于寒人集团的鼎力协助,才能够完成摧毁门阀政治、重建皇权政治的功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南朝时期门阀政治虽已成明日黄花,不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但仍保留着旧有的思维定式和认知传统,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这实质是其对与皇权结盟的寒人集团的戒备和对抗[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P327-329)。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寒人集团在晋宋之际的强势崛起。
如前所述,秦汉以降,寒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且无可取代,为实现皇权回归,早在东晋时期,孝武帝、司马道子就曾尝试借助寒人力量来对抗门阀[3](P105)。但是直到晋末宋初,双方才真正达成战略同盟,获取皇权支持的寒人集团迅速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四面出击,从各个方面瓦解门阀政治的立足之基。
可以说,由东晋至南朝,除了江山易主、政权更迭,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推动并实现了门阀政治向传统皇权政治模式的转换。在这样的历史大进程中,蓄势已久的寒人集团因势利导,进取有为,成为一支足以左右全局的重要政治力量。
三、南朝门阀余响与皇权政权之争
(一)门阀势力的余响
如前所述,由晋入宋,东晋门阀政治已经让位于皇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门阀士族的终结。一方面,门阀势力依然在许多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制约皇权的回归与张大;另一方面,南朝门阀政治持续表现出对庶族寒人集团的排斥意向。对于皇权和寒人的政治态度,表明东晋门阀政治在南朝的余响犹在,且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南朝政局的发展走向。
门阀政治余响的具体表现是在皇权回归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强调士庶之别,努力维护高门大户的尊崇地位。宋文帝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上尝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王球属琅琊王氏,为王导曾孙,门第高贵,当此之时,尽管王氏已不复旧日荣耀,不过仍然当即推辞,“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1]李延寿.南史[M].中华书局,1975.(P630)可见,以南宋皇权之盛,欲以皇帝一人之力,急切间弥除士庶之别,犹未能逮。宋孝武帝时,士族王僧达以赴皇室之乱,得孝武帝赏识,“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2]沈约.宋书[M].中华书局,1974.(P1952)然以未偿所望,意甚怏怏。此后孝武帝亲自召见他,王僧达“傲然了不陈逊,唯张目而视。”孝武帝叹称:“王僧达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僧达闻其言,慨然而曰:“大丈夫宁当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1](P573-574)时孝武帝母路太后侄孙路琼之为黄门郎,盛服诣之,僧达言其祖曾为王门驺人旧事以折辱之,甚至“遂焚琼之所坐床”[1](P574)。由此可见,南朝皇权回归之后,门阀士族仍以高门自许,无视天子威权;强调士庶之别,路琼之虽为清职,然而仍然无法获得传统门阀的心理认同。凡此种种,南朝门阀与皇权斗争之烈,可见一斑。
面临门阀士族的此种态度,南朝皇权亦不甘示弱,宋齐诸君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化皇权,努力把门阀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以期最大限度地消除门阀士族的余响。通过对东晋、宋、齐三代曾任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左仆射、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八种重要职官的身份进行量化统计,南宋士族门阀占比为总数的64%,仍高于半数,不过这一数字已经比东晋下降了15%,南齐时期这一数字继续下降至55%,与此相比,宗室外戚的占比则在稳步回升[3]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P109-112)。
由此可知,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余响犹在,而降低门阀士族的社会影响力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实际上,传统门阀士族直致梁末侯景之乱,始被消灭。在此之前,尽管权势空间被不断压缩,但仍以独特的方式存在并持续地发挥影响。
(二)南朝皇权与寒人集团的战略联盟
刘裕以次族而居大宝,欲在门阀政治的基础上重建君臣秩序和皇权政治,无疑其路漫漫、道阻且长;而在面对门阀余响的问题上,南朝皇权与寒人集团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因此,南朝皇权与寒人集团结成战略同盟,共同对抗门阀势力,成为当时形势下的必然选择。清人赵冀称:“然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中华书局,1984.(P254)。从寒人角度来说,南朝寒人的社会地位虽因门阀政治的终结而有所改观,但实质性改变发生于宋孝武帝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皇权与寒人结盟的深化期。“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2](P2302)皇权与寒人的结盟的态势,也几乎贯穿南朝始终:“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4](P173)皇权与寒人结盟,最直观的反映是南朝寒人在国家权力中心的构成,比之东晋有了极其明显的变化:曾任录尚书事一职的寒人比例由5%提升至21%;曾任尚书令一职的寒人比例由0提升到8%;中书令一职,寒人比例由0提升到7%[1]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P229)。
此外,寒人执掌机要成为寒人集团崛起的又一例证,此种趋势则在典签和中书通事舍人两职权势日重的变化中得到体现。中书通事舍人与典签原皆寒门小吏,宋齐之际却因获得皇权的支持权势畸重,甚至凌驾于方镇宗王之上。典签负责监察宗王门阀,几为一步登天之势:“宋氏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蕃,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闲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2]李延寿.南史[M].中华书局,1975.(P1933)与典签职能异化相应对的,是中书通事舍人地位的显著提升:“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版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3]萧子显.南齐书[M].中华书局,1972.(P972)时人乃称:“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2]
可以说,寒人出任中书通事舍人,表明寒人已经进入帝国行政的权力中央,此亦为皇权最为彰著之处;典签之权重,则表明皇权政治复兴,皇权的力量已经触及帝国的各个角落。
四、结语
晋宋之际,南朝门阀士族通过强调士庶之别,排斥皇权、抑制寒人等方式,来维护传统的政治格局;宋齐皇权虽比之东晋的暗弱有了极大改观,但亦不能真正创建起中央集权制度。不过在面对门阀余响的问题上,皇权与寒人集团表现出一致性,双方结盟协力,努力在东晋门阀政治的余响中构建新的政治格局和君臣秩序。皇权与门阀之争成为南朝政局的主流格调,寒人集团的崛起则是这一斗争的衍生品,南朝政局最稳定的时候便是三方力量形成均势之际。然而南朝皇权过度倚仗寒人,造成寒人集团权势畸重,又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均势,并激化了内部矛盾,南朝政局多动荡不安之秋,与此不无干系。直到侯景之乱,传统门阀势力始成绝响,不过南朝政局亦已千疮百孔,难复昔日荣光,南朝于丧败之余,为北朝所灭,业已成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