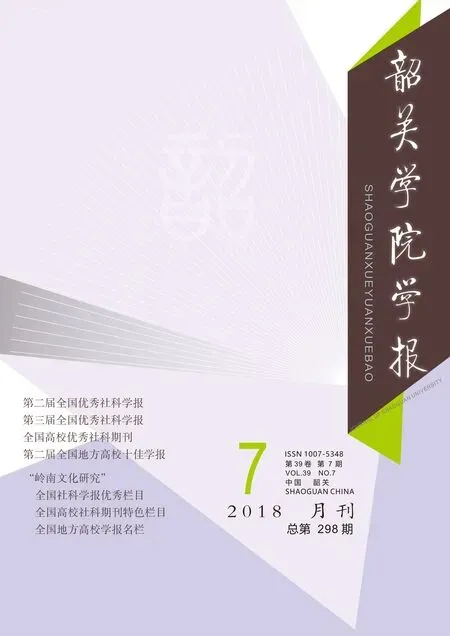王培孙对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校辑的文献价值
金建锋
王培孙(1871—1953),初字培荪,后字培孙,名植善,以字行,上海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办育材书塾,从事教育救国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育材书塾先后改名为育材学堂、南洋中学,自任堂长、校长,提倡新式教学。王培孙既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又是一位藏书家。王培孙收藏古籍四十余年,而王氏先人又藏书颇富,皆藏于南洋中学图书馆,后王培孙把所藏图书捐献给国家。
王培孙不仅收藏古籍,而且对一些喜爱的古籍进行校辑。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就是王培孙倾力校辑之作。杨为星指出:“特别是王培孙在三个蓝本的基础上,……故应是目前最好最全的一个版本。”[1]319王启元说:“王先生所辑《南来堂集》,以其搜罗、考订之精,为苍雪诗集流传诸本中之至善本,顾廷龙先生所编《续修四库全书》及纪宝成氏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皆取此本影印,即可见其版本价值。”[2]由此可见王培孙对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的校辑是得到学界肯定的。王培孙对《南来堂诗集》的校辑对研究苍雪大师和《南来堂诗集》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试就此展开论述。
一、有助于厘清苍雪大师的生平事迹
释读彻(1588-1656),俗姓赵,初字见晓,号苍雪、南来等,云南呈贡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高僧和诗僧。苍雪大师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钱谦益《苍雪和尚塔铭》、圆鼎和空《滇释记·苍雪传》、西怀了惪《贤首宗乘·苍雪传》等,但是这些资料毕竟不成系统,生平事迹脉络不清。陈乃乾编次《苍雪大师行年考略》(简称《考略》)有助于梳理苍雪大师的生平事迹,陈乃乾云:“庚辰孟秋,王培孙先生以所注《南来堂诗》付印,俾予雠校,循诵数过于苍雪大师之事迹,粗知梗概,爰依年编次写为一卷,其同时法侣诗友之可考者附焉。寒家自兵燹以来,箧藏尽散,索居孤岛,希借无门,今撰此编不胜疏略之憾云。海宁陈乃乾。”[3]4庚辰年即 1940 年,陈乃乾于战争期间,在孤岛上海和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犹能编出《考略》,实属可贵。一般而言,编撰某人生平事迹是为了达到知人论世、知人论学,姚光《序》评价云:“海宁陈君乃乾助先生(先生即王培孙)搜录校订复辑《大师行年考略》一通以附之,于是而读《南来堂集》者,不仅可想见大师之禅机气概,且如读明清之际诗史焉。”[3]1由此可见,陈乃乾的编次是王培孙校辑的组成部分。陈乃乾《考略》的编次,以“以事系年”、“言必有征”原则,对文献资料加以梳理汇集,必要处进行考证,以按语说明。陈乃乾考证精审之处值得称道,因为他能把苍雪大师生平事迹资料、寺院志、交游诗文和苍雪诗文等相结合,做到诗史互证,所引用的一些文献资料即使现在也颇难寻获,如《明河二愣大师无住迹》等。关于苍雪大师生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三《僧徒之外学第八》在引用袁枚《梅村家藏稿》卷五八“苍雪师,云南人。与维扬汰如师生同年月日……”后,有言:“按苍雪丙申闰五月卒,年七十,见《有学集》换三十六《苍雪塔铭》,汰如崇祯十三年卒,年五十三,见《初学集》六十九《汰如塔铭》,同年月生之说有异词。”[4]315陈乃乾《考略》云:“按师与汰如生年月皆同,集中赠汰公诗同年月日长,时丁丑还同拜五旬可证也。近年陈援庵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独谓师生万历十五年,不知何据?”[3]5陈乃乾的考证以《南来堂诗集》中诗人诗文为依据更有说服力。但笔者查阅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苍雪彻传》,未言及苍雪生年“师生万历十五年”,可能是陈乃乾误记。苍雪生年的错误来源于钱谦益《塔铭》所误记“年七十”。后来陈垣纠正前说,《释氏疑年录》卷十一云:“苏州中峰苍雪读彻,云南赵氏。清顺治十三年卒,年六十九(一一五八——一六五六)钱谦益撰塔铭,《有学集》三六。”[5]392所以王培孙校辑《南来堂诗集》收录陈乃乾《考略》等,有助于厘清苍雪大师的生平事迹。
二、有助于更全面和深入研究苍雪大师和《南来堂诗集》
王培孙对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的校辑内容主要有:其一是卷首,王培孙请友人姚光、周凤庠各序一篇、王培孙《校辑缘起》、友人陈乃乾《苍雪大师行年考略》等。其二是《南来堂诗集》正编,有卷一至卷四,其中卷三分为上下卷。王培孙于正编后辑附遗文四篇,补编诗歌四卷。对于正编和辑附内容,王培孙有校勘考证。其三是附录,附录卷一为“本集旧序凡例”,即收录有关《南来堂诗集》蓝本的序文、陆汾本凡例、录诗评论等;卷二为“南来事迹记述”,即收录有关苍雪大师的一些传记、塔铭、诗话等;卷三为 “中峰前后概况”,即收录一些有关中峰寺的碑记、中峰大师的塔铭、游记等;卷四为“诸家酬唱汇录”,即收录苍雪与诸师友酬唱之诗歌汇编。附录中部分篇章王培孙有校勘考证。由此可见王培孙对《南来堂诗集》的校辑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极尽网罗,大凡经眼过有关苍雪大师和《南来堂诗集》的文献资料皆予收录,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培孙的校勘考证,可谓说是用力之勤。王培孙的校辑嘉惠了学术界研究苍雪大师和《南来堂诗集》。其一,王培孙的校辑大大扩充了《南来堂诗集》的内容。现存《南来堂诗集》有两个刊本,一个是1914刊印,底本是云南图书馆藏本,共有正编四卷,收录苍雪诗376题,计623首;一个是1940年刊印,王培孙校辑本,此本是在云南图书馆藏本四卷基础上形成,增加了补编四卷,就苍雪诗而言,收录669题,计1048首。两相比较,王培孙辑录的诗歌就增加了400多首,更不要说对诗歌的诸多考证。其二,王培孙的校辑大大丰富了苍雪大师和《南来堂诗集》研究。虽然此书命名为《南来堂诗集》,但是王培孙还是收录了四篇重要遗文,如《寄徒三和书》之后收录对此文评价云:“知空和尚曰:‘苍老人此书叙情则感慨悲壮,脍炙人口,论道则策进机宜,直切勤勉,世出世法,纤毫必备矣,可三读之。’康熙壬午九月十六日常乐晚学比丘圆鼎访录。”[3]79我们由此可窥知苍雪大师的为文为学为人之风格一二。更有甚的是附录四卷,对《南来堂诗集》的情况、苍雪事迹、所住寺庙中峰寺的情况和与苍雪大师酬唱之士人衲子的收录,大大丰富了后人对苍雪和《南来堂诗集》的全面研究。
王培孙对《南来堂诗集》中265个诗题做了考证和注说,这是王培孙对深化苍雪大师和《南来堂诗集》研究的贡献。姑举一例,卷一《赠北禅寺熙达(达一作远)掩关》,王培孙校辑:“百城烟北禅讲寺在齐门内,崇祯间天童密老人憩时出天童养病于此,值诞日众请上堂,有法语勒碣砌壁,十四年三峰汉禅僧结制,时文文肃公护持十七年,三昧律师说戒,刻有北禅同戒录。按熙达无考,惟北禅寺为当时高僧弘法之地,则知熙达渊源有自耳。”[3]18此可见三点:一是对字的同异处理,比如有近似字等列出。二是对相关文献的辑录,此类居多,一般诗题中人物、地名、时间等考证,涉及到的典籍、塔铭、传记、游记、方志等一一原文摘录列出。三是王培孙的考证,有史事依据按依据言之,无则存疑等。事实上,王培孙校辑的诗题很多篇幅颇长,文献来源清楚,考证精良,采用了传统的校雠方法即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理校法。
三、有助于考辨《南来堂诗集》的源流
一般说来,对诗文集的整理研究,择其善本而用之。王培孙校辑《南来堂诗集》可以说是如此。我们可以从《校辑缘起》看出王培孙的苦心孤诣。以《校辑缘起》来看,王培孙有三个校辑本,获得先后顺序为:其一是得云南刊本四卷,讹脱过多,不可卒读,投置箧中者久矣。文中虽未言明具体时间,但从文意来看,应是最早获得。此本简称云南本。其二是癸酉(1933)清明,时以钱琴一先生约偕游虞山,参观常熟图书馆,见钞本《中峰苍雪大师集四卷》,录自常熟瞿氏者,得馆长陈敬如先生许可假归。此本简称常熟本。三是丙子(1936)季春某日,邮差送来吴门潘圣一先生赠书一册,即《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钞》残本下册。诗为吴江顾有孝茂伦选刊,分上下二卷、外篇一卷,外篇为关于佛事之作。今存下卷及外篇,已佚其所选之半。此本简称顾茂伦选刊本。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培孙分析和校勘三个校辑本,因为梳理清楚它们的关系可谓是至关重要。王培孙的论述为:首先,常熟本和云南本互勘,常熟本诗多于云南本者几十之四,且讹脱处二本不同而不妨于互勘。二本均冠以陆汾序文凡例及募刊小引,其序文康熙十七年作,距苍雪示寂二十余年。诗集当时讹脱之多在陆汾时已然。其次,云南本据正脉后述得自洞庭东山,后述作于雍正元年,距陆汾考订又四十年余年。再次,据陆汾凡例以乙酉至丙申示寂诗为第三阶段,而云南本罕见乙酉后诗。最后,至顾茂伦选刊本则陆汾正脉等皆不述及,殆所未见可知流传之少。惜佚首册致刊书之序例及年月俱无可考,然在二本互勘后遇此残册裨益已匪残。且此册中为二本所无者又得多首,不特讹脱之赖以校正。
正是基于《南来堂诗集》源流的考辨,正式形成了王培孙校辑本的内容和体例安排,即以云南本为底本,常熟本及各选本所有辑为补编四卷;云南本讹脱依钞本及各选本改正,为了增加准确性,王培孙还去寻求常熟本的瞿氏所藏原钞本进行校改,更有疑处只得存疑;等等。王培孙对于云南本和常熟本原陆汾凡例等附录在卷一为“本集旧序凡例”,便于后人详解原貌。上述诸多校辑工作,体现出王培孙的文献功力之深,可以说王培孙不仅是一位藏书家,而且是一位文献大家。
四、有助于深化和延伸苍雪大师与交游人士的研究
王培孙特别注重《南来堂诗集》中与苍雪大师有交游人士生平事迹的辑录,因为苍雪大师是明清之际一位忧国忧民的诗僧,李舜臣云:“苍雪的这些兴亡诗虽不像吴梅村具有‘诗史’性质的歌行体那样描绘宏大广阔的社会现实,但其中流露出来的深沉的亡国之思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亦能折射出当时僧人的心态。”[6]所以王培孙云:“南来适际明清易代,集中共酬唱者一时高僧古德名臣硕儒与夫特立奇行之士,表而出之,足增是集之价值,故就诗题之有可考证者笺注于下,作笔记观可,作诗话观亦可,惜参考书之供给不多,借阅匪易,尚有无从考证者,不无遗憾。”[3]3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王培孙校辑对古人的崇敬之心,而且可以看出他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奉献精神。
王培孙不仅在诗题下对所涉及的与苍雪大师交游人士生平事迹的辑录,而且放开视角,附录专辟卷四为“诸家酬唱汇录”,收录苍雪大师与诸师友酬唱之诗歌汇编。一般而言,对文学家的研究,交游人士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因为交游诗文的留存,可以为文学家的研究留下非常重要的文献线索。如吴伟业《丁亥之秋,王烟客招西田赏菊,逾月苍雪师亦至,今年余既卧病,同游者多以事阻,追叙旧约,慨然赋此》:“露白霜高九月天,匡床卧疾忆西田。黄鸡紫蟹堪携酒,红树青山好放船。秔稻将登农父喜,茱萸遍插故人怜。旧游多病难重省,记别苍公又二年。”[3]150从诗题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苍雪大师和吴伟业的重要生平事迹,即丁亥(1647)秋,吴伟业、苍雪大师和王烟客等一起赏菊。从诗文看,丁亥秋赏菊,吴伟业等人是好友相聚,热闹非凡,心情十分愉悦。二年后即己丑(1649),同样是秋天登高赏菊之时,吴伟业自己卧病,好友们因事受阻,聚会无成,表现出他的感伤心情和与苍雪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是一首展现士僧交游的诗歌。众所周知,在四库全书和电子检索版等书籍文库未出之前,学人要收录交游人士诗文颇有大海捞针之感。所以,王培孙诸多辑录和附录有助于深化和延伸苍雪大师与交游人士的研究。
五、余论
王培孙对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的校辑是校辑本的典范之作。王培孙的校辑方法和体例是值得后人借鉴的。从方法来说,王培孙首先是尽量收集版本,其次是校勘版本,再次是收集相关文献进行辑录和考证。从体例来说,王培孙的安排是:友人序文二篇(评价苍雪《南来堂诗集》的价值和意义),校辑缘起 (交代校辑情况)、《苍雪大师行年考略》(知人论世、知人论诗)、正篇四卷(主要诗作)、遗文四篇和补编四卷(校辑遗文遗诗)、附录四部分(校辑相关杂录),可以说收罗广泛,考证精审,条理分明,层次清晰,安排得当。
王培孙对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的校辑是王培孙爱国情怀的体现。“余(王培孙)二十年来暇,每披阅明清间诗,就选本中读苍雪诗而好之。”[3]3“上海培孙王先生竺志文献,尤喜浏览明清间诗文,于鼎革时事固多识而明辨之矣,得大师之作而酷好之,因发愤为之校辑。”[3]1那么王培孙为什么喜欢苍雪大师诗歌呢?也许正如吴梅村云:“其(苍雪)诗之苍深清老,沉着痛快,当为诗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其《金陵怀古》四首,最为时所传。师虽方外,于兴亡之际,感慨泣下,每见之诗歌。”[3]143就是说王培孙深处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心中兴亡之感不言而喻,苍雪大师之诗正契合王培孙所感,所以王培孙喜爱苍雪大师其人其诗,特定时期对《南来堂诗集》的校辑倾注了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