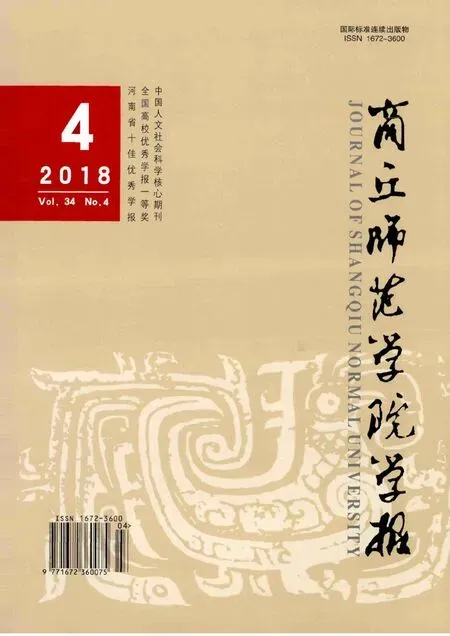社区矫正顶层设计的理性批判
——以修复性司法为视角
吴 何 奇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上海200433)
一、研究的背景
社区矫正,也被称为社区制裁或基于社区的刑罚。人类最古老的法典的第一段,就对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予以了暗示,那就是对公民的保护以及对罪犯的惩罚①。在早期刑事司法的范畴中,人们认为,通过对罪犯的隔绝与约束,能够实现犯罪的控制和减少。然而,19世纪中叶,居高不下的重新犯罪率侧面反映出,单纯着眼于对罪犯的报复并不能实现减少犯罪的目的。
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在社会化方面的探索与实践。通常认为,行刑社会化的启迪,源自于一个名为约翰·奥古斯都(John Augustus)的波士顿制造商和兼职社会工作者的实践。1841年,奥古斯都造访当地的法院后,使用自己的积蓄和他人的捐款对一名被指控为酗酒者的罪犯开展了机构外的矫正工作。凭借着数周后令司法者满意的出色的矫正效果,奥古斯都的尝试推动马萨诸塞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缓刑法令的地区[1]。
修复性司法最先由美国学者巴尼特提出[2]。这一司法理念的创设是为了化解冲突,进而修复被害人与犯罪人所在社区的安全[3]。在传统刑事司法的思维进路中,能否实现报应是区分刑罚能否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然而,社区矫正所秉持的刑罚理念、所奉行的实践模式与报应显得并不相容。实践中,社区矫正所提倡的个别化处遇所带来的诸多弊端更是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它的认同感。
问题在于,监禁刑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弊害,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刑罚理念的转变将刑罚实践的注意力从罪犯的单一要素延伸到对被害人的保护、修复破碎的社区关系的层面上。这些思想的涌现,推动了刑事司法的创新,一种被认为其重点在于“修复”,修复由加害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而不单纯是惩罚罪犯的司法理念开始流行。基于该司法理念所具备的特征,理论界称之为“修复性司法”。贯穿于这一司法理念的是三个核心要素:加害人、受害者以及社区。现代刑罚的发展与关于人的科学的产生、发展和运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在予以罪犯痛苦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对人的解放,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使罪犯得到人道的尊重,进而提升人格,实现生命价值的重塑,把国家对罪犯的强制力所伴随的痛苦限定在有效防范犯罪行为的限度内。这一研究范式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修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在刑罚观的理性建构中予以贯彻。相关学者基于公平正义的立场,通过对传统刑罚观内容的考察,认为传统的刑罚手段不仅不能达到真正的公平正义,也不可能达到特殊预防和综合预防的目的。有鉴于此,刑罚的设置与运作不应仅仅考虑国家与罪犯的立场,还应将刑事司法的关怀更多地给予受害人与社会,修复罪犯对受害人、社会的创伤,追求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的实现[5]。在这一视角下,结合域外社区矫正的实践情况,当代社区矫正的处遇方案被赋予了“监督”“释放”以及“制裁”三个层面的内容②。这也是域外社区矫正在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的猛烈批判后涅槃而来的发展进路。
在以修复性司法的视角审视我国的社区矫正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修复性司法的本质进行澄清。简单地认为修复性司法是被害人运动的产物,进而得出其本质中不具有报应、惩罚内容的观点值得商榷。
二、修复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运行机制契合修复性司法之肯定
修复性司法提倡通过对冲突的化解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进而维持社会的秩序。笔者认为,对冲突的化解是修复性司法的手段而非目的,这一司法理念所致力于构建的是社会的“和平”,只不过基于主体的不同而体现出多元的价值选择。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的和平?换言之,如何维持社会的秩序?这就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来实现正义,即对正义的修复。正义的内涵难以界定,就像是普罗透斯的脸,千变万化。但在刑事司法领域,对于正义的理解至少存在这样一个共识:被害人得到应得的赔偿,罪犯(加害人)得到应得的惩罚,即查士丁尼编撰的罗马法中所宣示的——“得其所应得” (“Giving each man his due”)。修复性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的区别体现在手段的不同以及价值选择的数量上的差异,但从本质来看,对于犯罪的回应,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差别。简单地说,以修复性司法指导刑罚的实践,不代表对刑罚所具有的惩罚性的丢弃。基于这一立场,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对于修复性司法的引入以及本土化实践才具有现实的意义,与之相关的讨论才具有展开的可能。
如上文所述,理论与实践皆证明,仅仅实现报应或是预防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成为评估刑罚是否正当的依据。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宽严相济是标榜刑罚合理性的最有力说辞。就此而言,修复性司法所体现的多元价值选择较之于传统刑事司法价值倾向的一元性,更适合引导刑事司法的改革。需要承认的是,近几十年来刑事政策思想的嬗变深受修复性司法的影响,而在刑事司法的改革进程中,修复性司法对于犯罪的惩罚、“预防及控制”的实践导向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上,修复性司法所提倡的价值诉求与社区矫正的具体运行存在很高程度的契合性,如重视对社区内的有效资源展开链接就是两个命题均应有之义,二者都倡导教育矫正和监督的目标。但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于修复性司法所提倡的关注被害人的核心诉求在社区矫正具体适用中往往得不到体现。笔者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承继了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大部分内容,而体现修复性司法内涵的实践只有少数组成部分,不仅没有突破传统刑事司法的藩篱,反而混淆了公众对于社区矫正的本原的认知。
(二)本土法治环境中对“社区”认同度的缺乏
结合自2003年起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具体实践,我国已有五种类型的社区制裁方式: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6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来看,国家对前四种社区制裁予以了立法上的肯定,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统称为社区矫正人员,已对其实行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的社区矫正活动,却对于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不置可否。某种程度上,这是立法文件中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从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的进一步排除。
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是否应当适用社区矫正,理论界、实务界的看法莫衷一是。2003年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2009年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都将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的监管纳入社区矫正的工作范围。但根据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及2012年两高两部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具体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罪犯不再被视为社区矫正的对象。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的监督管理以及教育矫正依法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工作予以监督。实践中,适用缓刑、假释等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中也存有附加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形,这就意味着,对于上述人员的监督管理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但对上述人员“政治权利”的管理则由公安机关承担,这势必会为工作的对接带来困难。此外,鉴于公安机关本身就担当重任,在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以及教育矫正方面,难免不如人意。而参照《意见稿》的要求,将上述人员的社区矫正全权交由公安机关负责,必然造成地方公安机关的超负荷运转。
结合实践,由于社区组织、社区工作者以及志愿人员的能力仍停留在一般的水平,财政保障、相关立法的缺位等因素的制约,让立法者以及公众对“社区”在刑罚执行工作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缺乏认同。就立法者而言,构建社区矫正刑事政策的目标在于规范非监禁刑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升刑罚执行的效果,以帮助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顺利进行,最终预防并减少犯罪。新出台的《意见稿》也将其主要篇幅用于规制社区矫正的决定机关以及社区矫正机构的具体实践,却罕见引导社区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细致规定,对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定位、福利待遇的保障也缺乏清晰的阐述。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引导的行刑社会化改革,尚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内部调整,而不是权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转让。一定程度上,这与修复性司法所倡导的通过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参与进而促进冲突的解决、维持社区的安全的司法理念相背离。就公众而言,传统的报应思想依旧深入人心。公众志愿支持社区矫正的意识还很淡薄,社区力量对社区矫正的支持仍处于起步阶段。现实中,公众不仅不热衷于社区矫正的相关活动,更排斥将罪犯置于社区中开展刑罚所给自身以及社区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推进社区矫正的深入发展,应当注意到,维护公正的秩序的确是政府的责任,但建立公正的秩序却是社区的责任。然而,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却缺乏认同“社区”的自信。虽有社区之名,但仅有矫正之实,或许抑制了监禁刑罚的一些弊端,却与社区矫正功能的完全发挥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社区矫正中对被害人的关注度依然羸弱
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较之于传统的刑事司法活动,修复性司法的发展与贯彻有助于降低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被害人的恐惧和愤怒。在介入修复性的案例中,只有少数被害人仍未摆脱负面因素的影响。作为对传统刑罚路径的突破,社区矫正的具体实践中理应给予被害人更多的关注。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刑事诉讼法》一定程度地保证了被害人作为诉讼过程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但有关刑罚执行的立法却没有明确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的权利。与传统刑事司法理论不同的是,修复性司法尝试整合犯罪行为所致的破碎关系,追求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和解,并以全面的方式关注被害人的诉求。在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下,参考相关的立法文件,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依然是以“犯罪人中心”的思路予以设计、实践,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被害人的参与。然而,被害人是犯罪行为最直接的作用对象,赋予其参与社区矫正的权利显然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即使在最早引入修复性司法概念并付诸本土化实践的少年司法领域,基于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而将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信息、矫正过程予以封存和不公开的做法尽管具有理论、实践的双重支撑,但对于相关的被害人而言,这阻碍了该群体的参与,并不利于相关破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处遇空间的相对开放,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行刑社会化。就对被害人所受损害的弥补而言,物质上的伤害或许可以通过赔偿来抚平,但内心的创伤并没有借助社区矫正的实施而得到更好的修复。
三、修复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适宜补充的顶层设计
(一)修复视角下社区矫正的理论逻辑
修复性司法秉持的修复正义的理念着力于解决冲突和修复损害。一方面,它鼓励那些造成损害的人发自内心地承认他们所做的行为的不利影响,并给予他们直接参与赔偿与弥补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为那些遭受伤害的人提供了通过参与修正损害或损失的权利进而肯定司法实践的正义性的机会。
在修复性司法的语义下,以忏悔自身罪行为基础的再社会化是矫正罪犯的核心。依据这一刑事司法理念,相比国家或政府,让罪犯承担修复损害的责任更具有说服力,因为被害人以及社区所遭受的破坏通常源于罪犯自身的行为。修复性司法强调,在修复破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应当包含“赋权,诚实,尊重,参与,自愿主义,愈合,恢复,个人责任,包容,合作和解决问题”等内容;在刑事司法中,提倡人道主义的同时实现社会正义。无论是报应刑、预防刑还是兼顾二者的修复性刑罚,正义的回归都被视为刑罚的要义。作为对刑罚人道化的解读与贯彻,社区矫正制度中理应摄入修复性司法所传达的观点。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的设计中,社区参与、对被害人的重视在相关立法中相对真空,亦如上文所述,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进路存在与修复性司法的理论逻辑相偏离的现状。因此,笔者认为,明确规定具有社区、被害人参与的实践模式,加深对被害人诉求的关注,是社区矫正顶层设计中应有的内容。
(二)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应肯定社区的力量
在实践应用方面,应肯定社区在刑罚实践能够发挥的作用。社区矫正较之于监禁刑罚的优势,首先体现在通过社会化的行刑模式,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体以置身于社区和社会这个正常的发展环境中的方式,反思加害行为对他人乃至社区、社会的不良影响。社区乃至社会,是各类权利义务关系的集合,犯罪是对合法权利义务关系的侵犯,也就是对社区、社会的侵犯,是“社区自己的失败”,因为它没有为加害人提供机会去实施对社区有益的事情。因此,在矫正罪犯的过程中,特别是社区矫正的具体实践中,社区不仅仅充当一个矫正罪犯的场所,更需要借助其各方面力量,在谴责罪犯那些有害社区的行为同时,引导公众参与到罪犯的矫正中来,重视该群体的成长、生活技能、工作技术、社交能力等方面的传授与培训,重塑社区矫正在促进罪犯再社会化问题上的优势。
另一方面,作为行刑社会化的根基,社区同样有助于被害人群体通过社区给予的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持,愈合因犯罪行为造成的创伤。借助社区的力量,充分调动居委会、村委会的资源,开展诸如针对被害人的“危机热线”、提供具有临时避难性质的“安全之家”等活动,可以考虑通过相关立法的形式纳入社区矫正的具体实践之中。
(三)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应体现对被害人的关注
国外学者对于适用传统刑罚以及修复性刑罚对被害人的影响展开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参与具有修复性内容的刑罚实践,被害人对罪犯的恐惧和愤怒程度大大降低。具有修复性内容的刑罚实践为罪犯和被害人提供了互动与交流的可能,被害人能以此加深对罪犯的理解,同时,也令罪犯直观地了解到自己的行为对于被害人的负面影响。如果被害人的意识直接传递给罪犯,受害者的意识将最有效、有力地提高罪犯对罪行的反省。现实中,被害人通常会有非常具体的个人问题,他们宁愿直接向罪犯提出,因为只有罪犯知道答案。然而传统的刑罚实践不能也没有提供其与罪犯直接沟通的前提。具有修复性内容的刑罚实践可以通过对话让被害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反过来,让罪犯明白他们做错了什么,造成了被害人多大的痛苦,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行为(无论是否有意)(潜在的)后果的严重性,有助于成为警醒以防止刑满释放的罪犯在将来继续使用暴力。
在社区矫正中,重视被害人的参与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这为罪犯帮助、赔偿、弥补被害人提供了机会。通过相关立法的设计,肯定罪犯帮助被害人的积极意义,给予他们因从事上述有益行为而得到决定机关、执行机关的最宽大的刑罚。如提前结束社区矫正、封存相关罪名、犯罪记录等,帮助罪犯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被害人对罪犯的谅解更能够体现刑罚正义的实现。通过立法设计,将被害人对赔偿、弥补的满意度作为评估罪犯矫正效果的依据。通过加害方与受害方的参与,融合和平衡被害人和罪犯的需要。家庭小组会议(FGC)在英国的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中逐渐成熟。借助会议,治愈被害人的那些由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恢复受上述行为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鼓励那些对罪犯或罪行有直接利益的人通过会议的参与,在社区乃至社会中包容罪犯。重视被害人的参与需要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提高对被害人的关注,在域外的经验中,被害人的参与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可以达成创造性成果,并被认为是一个更有成效的方式。
需要重申的是,在修复视角下强调社区矫正的修复性不等于背离刑罚的本质,社区矫正的顶层设计仍需要体现刑罚的惩罚性,中间刑罚的模式值得借鉴。一方面,对于那些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的罪犯,在适用社区矫正前的阶段,可规定一定期限的监禁刑罚予以威慑,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公众对于报应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我国的相关法律文件中仅仅规定了社区内执行,实践中,往往忽视了风险境况以及不同群体需求的转变。通过与风险评估制度的结合,灵活地分析对不同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效果,对于不适宜继续社区刑罚的采取收监执行的方式,更有利于最大化的实现社区矫正的现实效益。
注释:
①汉谟拉比法典:“…to bring about the rule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land, to destroy the wicked and the evil-doers; so that the strong should not harm the weak…and enlighten the land, to further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②“监督”(Supervision Programs),是对于人身危险性较轻的罪犯,通过社区服务以及罚金等形式,在给予罪犯适当的惩罚的同时,让罪犯对被害人的补偿更易落实。“释放”(Release Programs),具体实践的内容包括中途之家、狱外工作以及探视程序等, 旨在以这些措施拉近罪犯与社会的距离,从而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制裁”(Punishment Programs),是对“释放”的补充,针对的对象是那些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的罪犯。例如,家庭监禁、电子监控等方式,通常认为,这些措施兼具机构性处遇以及社区处遇的特征。此外,还设置了震慑缓刑(Shock probation,又称休克缓刑), 对于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罪犯在适用社区矫正之前,首先进行一个短期的羁押,以达到对罪犯的威慑,同时也符合民众的意愿。
[1]吴何奇.兴起、修正、进阶:社区矫正的发展逻辑[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3).
[2]Barnett, R..Restitution: A New Paradigm of Criminal Justice[J].Ethics, Vol.87(1977).
[3]Daniel W.Van Ness.New Wine and old Wineskins: Four Challenge of Restorative Justice[J].Criminal Law Forum,Vol.4(1993).
[4]苏力.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对法学的贡献[J].比较法研究,1993(2).
[5]孙华璞.公平主义刑罚观之提倡[J].法学,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