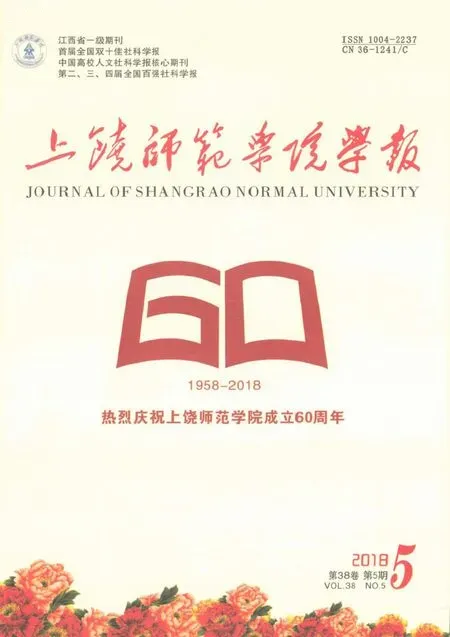走出中哲史:对阐释学的一点看法
(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34)
“走出中哲史”,是指中哲史研究需要“走出来”,既要更广泛地了解其它学科研究成果,更要走进世界哲学研究的潮流之中。进一步说,不要局限在哲学(哲学史)来讨论阐释学,更不能局限中国哲学来讨论阐释学。
这里,笔者谈三个问题,可能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或由于猎涉不广而存在理解错误,请诸位专家学者帮助笔者释疑解惑。
一、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阐释需要注意的问题
1991年,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将自1987年之后多次来华讲学的文稿编成《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一书,该书出版后他就赠送笔者一册。笔者曾撰写了一篇名为《哲学的反思 严肃的抉择》的书评予以介绍,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1]。成先生介绍了西方分析哲学、诠释学的要义及流派,别开生面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与范畴加以新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思维模式,企望中国哲学摆脱目前困境,迅速走向现代化。此后,国内有不少学者运用阐释学的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取得一批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阐释中国古代哲学应当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历史场景,即要注意分析这些思想家所说的话原来意思是什么,存在什么缺陷,拥有什么价值,而不能直接用现代概念来“直接衔接”,否则就会违背历史主义的原则。笔者认为,研究古代哲学,许多概念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使其获得“新生”。不能新瓶装旧酒,而是要老树开新枝。
这里以第一代新儒家研究为例。第一代新儒家学者是在“五四”之后,中华民族遭遇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这批真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企望从民族文化的宝库中寻求出路,来应对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儒家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与时代价值的。应该承认第一代新儒家在西学泛滥于中国之时,他们有维护中华文化的勇气, 非常值得赞赏。但是,第一代新儒家毕竟采取的是文化保守主义,过于执着传统文化,总体上对西学采取排斥态度,因而与世界潮流并不是同轨共进,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对第一代新儒家需要予以理解其文化心态,需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有些论文讲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关系或有过当,如袁宏禹“现代新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会通”提出“通过儒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新儒家也将儒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融通,通过马克思主义使儒学现代化”(《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类似论文还有一些,如姜彦华“新儒学助推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人民论坛》2017年第9期),朱兰、但家荣“论儒家文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语文建设》2015年第12期)。这些学者提出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会通、契合的观点,实际上是上世纪90年代新儒家研究中某些观点的延伸。。遗憾的是,学界确实还有一些全盘肯定、言过其实的评论。其实,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它产生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远古陆续走来的儒家思想家们,他们的思想不可能直接为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服务,他们某些值得我们汲取的思想精华,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过程,这一过程自然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其中包括以阐释学的理论对儒家思想作出解构并进行现代性建构。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将儒家们的某些概念、观点的原意弄清楚,然后考虑好转换成什么层次上的概念与构建怎样的理论体系,这样才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例如,《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2]。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儒家强调以礼治国,二千多年来,礼仪已经成为中华先民尊崇的生活方式,礼义也成为中华先民追求的精神价值。但是,上述“义”是指封建专制主义下的道德践履,是强调封建伦理纲常的践履,与当今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需要将“义”转换成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从而使国人能修身立德、行礼律己,成为道德高尚、礼仪优渥的“君子”。
正由于此,笔者不同意对中华传统文化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将其神圣化,容不得半点批评;也不同意抛弃中华传统,全盘西化。中华传统文化只有在脱胎换骨,进行现代性转换之后才会焕发青春,如果将其神圣化、固态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也就变成“千年僵尸”了,不会有什么活力可言,更不会适用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提倡读经、国学不是坏事,是让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传统,可以让国人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但将其视为恢复或弘扬中华文化的唯一手段,则会背离了当今社会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时代精神。因此,没有必要身穿古服、口诵古经、行用古礼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实质弘扬出来。这就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助西方现代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加以阐释,经过“现代性转换”,将其可以转换的精髓发掘出来,从而构建起新时代的可与当代世界文化对话的中华新文化,既让它真正具有“中国血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性”意义。
二、阐释学的三个层次
按照一般解释,阐释学又称诠释学,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阐释学被广泛地运用在哲学、法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学中。一般认为:有关阐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今形成诸多流派。其实,阐释学并不神秘,中国古代亦有之。在中国,原始的“阐释学”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存在了。
在笔者看来,阐释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疏释字词等概念,第二层次是阐释文句,第三层次是阐发意义。前两个层次是语言文字的层面,而第三层次则达到思辨的层面。这大概是东、西方都存在的。笔者从中国角度来试加论述。
从阐释角度来看,中国字词的阐释当以《尔雅》为始,再往后推一些,那么许慎《说文解字》也是很重要的著作。许慎另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惜已失传,当亦是解释字词为主的著作。《说文解字叙》称:“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3]《说文解字后叙》:“闻疑载疑, 演赞其志。次列微辞,知此者稀。”[4]也就是说,由于古今字型、字义不同、制度相异,因此后人往往不晓其意,故有必要通过字词解释来了解其旨,深明其义,做到“信而有证”,这样才能演绎出正确的观点。
第二个层次可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刘氏在《文心雕龙》中说:“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5]237此将“解”字作“释”字解,即互文,两字同义。这里的“解释结滞”是指解释文中不明之义,也就是刘氏所说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5]448。章即彰,“释名以章义”是指从解释名物入手达到了解其涵含之义。“征事以对”,即指引证事例来作对应解释。如《史传》中称孔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因此著《春秋》“睿旨幽隐”[5]141,故左丘明为《左传》而释其旨。此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将《左传》作为解释《春秋》之作,实际正是“解释结滞,征事以对”的注脚,此从字词文句的解释引申到事件的“核实”,进一步阐述事件,使读者明了事件真相,初步接触到“阐释”问题。
如果仅停留在上述两个层面,那么只能说是了解篇章内容而已,难以进一步阐发其内在意义。在中国古代,确实还有更高层次的阐释,这进入第三个层次,它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格义、六家作代表。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指出:“东晋以来,教理之疏讨日益繁密,于是华人渐自辟门户,辩论遂兴。陈隋之际,乃颇多新说,而宗派之分以起。”[6]汤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魏晋时期般若学分为两大流派,一是“格义”,一为“六家”,对佛教概念、教义的阐释各有不同。僧睿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虽曰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7]“迂而乖本”,是僧睿批评“格义”歪曲佛教本义,也是就阐释不符合佛教经义;“偏而不即”,是批评“六家”阐释偏颇不合佛教真谛。其实,“格义”是运用中国古代原有的名词、含义,特别是采用了老庄哲学的名词、概念来比附佛教名词和概念,进而阐释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的精义,是适应魏晋玄学流行之后的历史现状的,因为这样的阐释能使中国僧人比较容易地掌握思辨性比较强的般若性空之学。如朱士行等人翻译了《放光般若经》[8],其中般若学的事数(名相)概念不易弄清,如分析构成人们心理与物理现象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五蕴即组成人身的五类东西:色(组成身体的物质)、受(感官生出的苦、乐、忧、喜等感情)、想(意想的作用)、行(意志活动)、识(意识);十二处是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处、身处、所触处、意处、法处这十二处;十八界是指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所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及意识界。,用中国固有之名词、概念来作阐释,就比较容易理解它们的内涵,从而掌握般若学之真谛。可见,无论是格义还是六家,都是运用阐释的方式来解读佛教经义,他们从较低层次的字词解释入手,进而揭示佛教性空之义,初步具备了后世阐释学要求的从本体论高度来理解文本的特性。其实,当时名僧道安对格义也极不满意,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9],但他又感到佛教的概念确实不易弄清,于是采用折衷的方法来处理,他一方面批判格义派,同时也允许其高足慧远讲道时采纳老庄的概念来进行疏释,使人触类旁通。事实上,由于中印文化背景不同,理解自然会不同;佛教经义不用相应词义来解释,是难以使当时中国人接受的。
当然,中国古代这种阐释,不能等同现代西方的阐释学,从学术理论水准来说,它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中国古代的阐释却具有现代阐释学的某些因素则是毫无可疑之事,尤其是三个层次问题,东方、西方大概不外乎此。
三、“读经”与“解经”
所谓读经,指字词句文义疏释;解经,是指从思辨高度来阐释经中所包含的意义、价值。读经是基础,解经是目的。
其实,每个时代的“读”经都差不多,因为我们不能离开经典原文和作者原意来随意加以疏释。在读经上,只存在对“经”文理解的正确与否,对其蕴涵着的意义掌握与否。但“解”经则不同,因为解经需要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而作出新的阐释。在中国古代,面对同一经典,每一代知识精英对它的阐述则会随着时代条件变迁而变化。孟子解读孔子思想不可能与荀子一样,而董仲舒、郑玄、王肃、孔颖达、二程、张载、朱熹乃至王阳明对孔孟的解释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孔孟思想正是在这一代代学者的不断阐释中演化着,而演化的结果便是这些后代精英们的思想而已。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些不同的解释,才推进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换句话说,作为我们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与阐释,自然应当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重新加以阐释,发掘其可以转换成符合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因素,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进入现代世界文化之门。
读经还是解经,都需要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精神而努力。这虽是一句老生常谈、令人生厌之话,但笔者认为还是要说。笔者这里讲的“他山”,除指现代西方学术(当然包括哲学)外,还指国内其它学科的研究。现在大家都十分关心世界学术潮流的变化,西方学者的著述、理论大量被介绍进来,给国人以启迪与借鉴,因而促进了国内学术的迅速发展。因此,“走出”中哲史,就需要“走进”世界学术研究之中,了解世界学术——尤其是哲学的发展变化,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回眸中国古代哲学,加以研究,吸取营养,那么我们必然会取得更多令人兴奋的成果。
从与国内其它学科关系来说,哲学史界一些学者确实与国内其它学科的交往不是太多,学术层面的交流乃至交锋更为少见。对其它学科的发展、成就了解不够,这至少限制了个人的学术视野,严重者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笔者主要是研究历史的,曾经研究过朱熹,现在研究礼制,涉及到许多经典著作,但在阅读同行相关研究中,确实发现了一些研究对经典释读不正确的情况,有臆断之嫌,那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其理论推导也必然会出现重大失误。其实,只要稍微关心一下相关研究,许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走出中哲史”是祈盼更多地进入其它学科的领域,了解他们的研究信息,掌握他们的研究动态,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而促进中哲史研究的不断进步。
“走出中哲史”,就是祈盼哲学史界的同仁们共同努力,摆脱固有的研究思维,打破思维定势,扩大学术视野,更多借鉴与吸纳其它学科乃至世界各国最新的学术成果,将中哲史研究放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来考虑,放在世界哲学的范围中去加以比较,以创新精神来构建并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理论体系,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为世界哲学史作出我们的贡献。
——关于海德格尔的“那托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