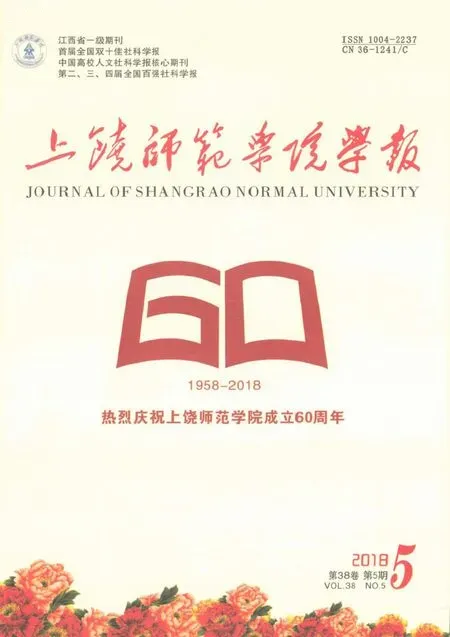观点与话语:理学家朱一新汉宋比较的近代性特征
(1.浙江海洋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2.浙江海洋大学 经管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浙江义乌人。曾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及广州广雅书院山长,为近代著名理学家。清同治八年(1869),朱一新入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师从著名汉学大师俞樾。诂经精舍由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创建,成为19世纪浙江考据学中心。诂经精舍奉许、郑木主于堂,其学风完全属于汉学性格。朱一新在诂经精舍两年,受到的是考据学洗礼。理学家不废考据,乃他日后常要表达的一个观点。例如他对于朱熹的推崇,其中也包含了对朱熹重视考据的深刻认识。他说:“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朱子言:‘考证别是一种功夫,某向来不曾做此。’自谦之词。今读《语类》随举一事,无不通贯,非精于考证者能之乎?”[1]116而朱一新本人也非常重视考据的作用,认为“小学训诂,治经之始事,而经义非仅止于斯。训诂既明,乃可进求大方之所在耳。”[1]143此与乾嘉学者“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但作为理学家的朱一新,最终在覃思考据与义理的分际时,强调义理“从考据中透进一层”,是为治经之终极目的,因此考据与义理又不纯是先后关系,亦为粗精关系,表里关系,上下关系,终始关系,故朱一新以理学家视野来作汉宋比较,其观点与话语之新颖性至今仍对我们有莫大启发。
一、汉宋之别,乃学问与学术之别
在分析朱一新汉宋比较之前,我们先要了解朱一新对汉儒与汉学家、宋儒与宋学家等两组概念的区分。根据曹美秀的研究发现,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每以‘汉儒’称汉代学者,以‘汉学家’称乾嘉学者,而且遍搜《无邪堂答问》,这两个用词都不曾混淆”[2]170。与此相应的是,朱一新还将宋代学者称作“宋儒”,而将清代研究宋儒的学者称作“宋学家”,在《无邪堂答问》中,朱一新对汉儒、宋儒和汉学家、宋学家是作了严格区分的。换言之,汉儒、宋儒与汉学家、宋学家的区分,又在学问与学术之分。而学问与学术之分,其标准便是有无宗旨,这是区别学问和学术的标杆。
朱一新先引《明儒学案质疑》中对明儒好立宗旨提出的批评云:“明儒各立宗旨,互指辨驳。其实静中养出端倪固善,随处体认天理亦善;致良知固善,慎独亦善。但实言之而实行之,岂有不善者?”然后,他加以反驳说:
乾嘉以来,学者多持此论,实非也。天下无有两是之理,正当别黑白而定一尊。苟徒假圣贤一二言以佐其说,则何者不可附会?析理未精,姑为此调人之言,乃乡愿学问耳。古来有不实行而可为学者,谓明儒务立宗旨,不务实行,此近人矫诬之说,明儒果如是乎?(明惟隆万时,士习多空疏恣肆,岂可以赅前后?)宋学之有宗旨,犹汉学之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学术者,心术之见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圣贤无不于此致慎焉。《论语》一书名言“仁”,“仁”即圣门之宗旨。《孟子》七篇言“性善”,言“仁义”,“仁义”、“性善”即《孟子》之宗旨。其它诸子百家亦皆有之。惟其有心得而后有宗旨,故学虽极博,必有一至约者以为之主,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六经无一无宗旨也。……汉儒谓之“大义”,宋儒谓之“宗旨”,其揆一也。故不合于六经大义者,不可以为宗旨。谓明儒宗旨有善有不善则可,谓无不善则不可。[1]13-14
根据有无宗旨的标准,在朱一新的学术谱系中,除汉代学术以外,他常要将“宋、元、明、国初”学术作为一个序列来加以表述,究其原因,皆因此序列学术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好立宗旨。换句话说,此四阶段学术都为宋学范畴,故他要将宋、元、明、清初作为与乾嘉相对的另一面来看待。宋代程朱之为学,其宗旨为大家熟知。此以明代而论,自明初曹端以“太极是理”为宗旨,薛瑄以“达于性天”为宗旨,吴与弼以“自治力行”为宗旨,胡居仁以“主敬”为宗旨,陈献章以“洒落自得”为宗旨,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王守仁以“致良知”为宗旨,王龙溪以“先天正心”为宗旨,钱洪德以“后天诚意”为宗旨,以及黄绾的“艮止”之旨,季本的“龙惕”之旨,邹守益的“戒惧”之旨,欧阳德的“动静体用合一”之说,聂豹的“归寂”之学,罗洪先的“主静”宗旨,王时槐的“透性研几”之说,胡直的“心造万物,察外无理”之说,李材的“止修”之学,王艮的“良知现成自在”之学,罗汝芳的“赤子良心”之学,耿定向的“不容己”之学,焦竑的“知性求仁”之学,李贽的“童心”说,罗钦顺的“气上认理”说,王廷相的“太极道体”之学,高攀龙的“格物知本”之学,刘宗周的“诚意慎独”之学等等*以上所举,参考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各学者、各学派无不有自己的论学“宗旨”,这是明代学术的鲜明特色,也是对宋学的深刻继承。因为明代学术好立“宗旨”,故被清代汉学家批评为“空疏”,对此朱一新认为这是近人的“矫诬”之论,不可轻信。
他认为不言宗旨,不可与言学术。回顾先秦时期,孔子言“仁”,子思言“诚”,孟子标榜“仁义”;两宋时期,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颐的“持敬”、朱熹的“理一分殊”,陆九渊的“心即是理”,无不有宗旨。他说:
有学问,有学术。……吾辈生汉宋诸儒而后,六经大义已明,儒先之宗旨即可取以为我之宗旨。由是而进窥圣贤之门径,庶几不误岐趋。近人以训诂为门径,此特文字之门径耳。圣贤道寓于文,不通训诂不可以治经,即不可以明道。然因文以求道,则训诂皆博文之资。畔道以言文,则训诂乃误人之具。[1]14
很显然,在朱一新看来,训诂之学为“学问”,宗旨之学为“学术”,六经大义,经汉宋诸儒的发明阐释,已有相当成熟的显扬,故遵循汉宋诸儒所立宗旨,进而得窥圣学门径,已成为学而不歧的通衢,这体现了朱一新鲜明的宋学立场,以及对宋学的张扬和抬升。由于宋学属于学术范畴,而汉学属于学问范畴,二者高下,不辩自明,所以他说:
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己,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故圣贤必斤斤于此。[1]14
又说:
学术之发于心术者至微,其关于天下者甚巨。[1]5
如此看来,朱一新所谓学术,即道术。道术坏天下坏,“故圣贤必斤斤于此”。而训诂之学,不过博文之资,其利害无涉于道心人心,不过文字的门径而已。
基于宗旨的治学理念,乾嘉学者治学虽以实事求是为圭臬,但朱一新认为,汉儒所谓的实事求是与近人所倡实事求是有所不同,他说:
汉儒所谓实事求是,盖亦于微言大义求之,非如近人之所谓实事求是也。然此皆求知之事。知之而不能力行,虽望见其门,犹不得入,而可以训诂自画邪?[1]14
简言,汉儒之实事求是为求真理,而近人之实事求是乃求真知(客观的知识),但倘若求得真知而不能力行践履,仍然不免于徘徊在圣学门外,画地为牢。因此,他接着说:
惟能寻绎践履,故训诂为有用,并非说《尧典》二字三万言而后谓之训诂也。[1]14
训诂只有与求道两相结合,方为有用之说,而以三万言释“尧典”两字,只是为训诂的训诂,实不足道。因此他批评道:
训诂本易明,其不明者,人自凿而晦之,即间有难明之处,于道之大端固无害也。乃借圣人正名之言,以自张其说,天下后世其可欺乎![1]14
这种现象,在乾嘉的汉学家那里时有表现,此可谓训诂之末流。需要指明的是,朱一新批评训诂之弊,并非要彻底排斥训诂之学,他仍然肯定训诂作为文字之门径,其作用不可低估,故又云:
圣贤道寓于文,不通训诂不可以治经,即不可以明道。[1]14
但凡事物皆有正反两面,训诂之学亦然。因此要正确对待训诂的作用,如前所引,倘“因文以求道,则训诂皆博文之资”,如果“畔道以言文,则训诂乃误人之具”。训诂的工具性质,决定了使用训诂这一工具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否,以及将训诂导向何处。要么成为“博文之资”,要么成为“误人之具”,但无论如何,就训诂之学本身而言,仍为治经者所必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为学不能溺于训诂,因为“第终身徘徊门径之间,而一进窥宫墙之美,揆诸古人小学、大学之教,夫岂具然”[1]4?因此,朱一新依次设计了为学的三个门径,其云:
夫训诂者,文字之门径;家法者,专经之门径;宗旨者,求道之门径。学者苟有志于斯,阙一不可,而其轻重浅深则固有别也。[1]14
“家法”,指汉儒治经之专门之法。在朱一新设计的三个门径之中,“宗旨”之学显然居于顶端,因为它是“求道之门径”,仅此排序,亦可见出他对宋学的推崇。由是,朱一新的汉宋之分,其实不是简单的将汉宋进行二元切分,而是更进一步探讨它们内涵上的差别及其此种差别在为学等级上的意义。
二、汉宋诸儒,于大旨固无不相合
要之,朱一新鲜明的宋学立场,以及对宋学的张扬,是建立在宋学与汉代学术对接前提之下的,他说:
博考宋、元明、国初儒者之说,证以汉儒所传微言大义而无不合。[1]14
他特别强调宋儒之说与汉儒之说“无不相合”,意味着从学术角度看,汉宋之分根本就是不能够成立的。乾嘉学者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接续汉儒传统的学者,而朱一新认为真正接受汉儒传统的不是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们,相反是他们一直排斥的宋儒。
在《无邪堂答问》里,朱一新常将“汉宋儒”合言并称。如他认为“汉宋诸儒大旨,固无不合”[1]116,既是“固无不合”,当然就不应将汉宋之学作人为的切分,他又说:“吾辈幸生汉宋诸儒而后,六经大义已明,儒先之宗旨即可取以为我之宗旨,由是而进窥圣贤之门径,庶几不误歧趋。”[1]14在他看,六经大义已明,其实是汉宋诸儒前仆后继,连续地、层累地阐发的结果,因此汉学家强分汉宋,固设门户,引来朱一新的强烈批评:
学士大夫矜言复古,其说愈精而愈琐,至宋儒辨晰心性之旨,乃以其涉门户也而疑之,然则论学必屏程朱,说经必宗许郑,非门户欤? 夫非许郑、程朱之果歧,人自歧之也。[3]
汉宋诸儒如前所引,“固无不合”,而乾嘉学者却由于一味推崇许郑,而不断排斥程朱,人为地在汉宋之间筑起一道隔带,这就是朱一新为何常常要将“汉宋诸儒”合称的深意所在。那么,朱一新所谓汉宋诸儒“固不无合”的理由又如何呢?从大的方面看,他举例说:
汉宋诸儒之治经,亦无不求其端于天。《易》言卦气、消息,《书》言洪范、五行,《诗》言五际,《春秋》言灾异,汉儒所谓性与天道者,类如此。虽非尽六经本旨,要其师承,远有端绪,亦圣门之微言也。……周张二子崛兴宋代,乃作《太极图说》《通书》以明《易》,作《西铭》以明仁,作《正蒙》以明诚。诚与仁亦夫子赞《易》之旨也,其言与汉儒虽异趣,而其阐阴阳之蕴,探性命之原,则无不同,视董生尤加粹焉。[1]154-155
虽然汉宋诸儒学术各有异趣,但从总的原则来看,“亦无不求其端于天”,其阐述阴阳之理,探索性命之原的大方向是相通的,因此强分汉宋,固为门户,实在是大可不必,他说
六经大旨,灿若日星,汉宋巨儒,阐发殆尽。后人患不能读,不患不能辨。辨生于末,学纵有所得亦不过补苴罅漏,况琐屑穿凿之纷纷乎?董、郑、周、朱遗书具在,曷尝有局于末道遁于虚之弊?学者胡不捐门户之见,熟读而深思之?[1]157
只有捐除门户之见,熟读而深思,方能看到汉宋诸儒治经的特点,他说:
汉宋诸儒解经,一字一言,必还经之本义。笃信谨守,宁阙毋妄,故可宝实。……程朱可师法者多矣。[1]118
而与之相反的是,“近人但哓哓辨古方之真伪,而并其言之精粹者,弃之如遗,岂非颠倒刺谬乎”[1]118?他因此批评乾嘉学者,与程朱相比,“学识不及其万一,而动欲以己之意见治经,自伪古文之说行,此风曰炽,名为卫经,实则畔道。古书中名言精理,弃若弁髦,而反搜罗谶纬,旁及杂说以示博,岂谶纬杂说果胜于古文《尚书》乎?多闻阙疑,圣有明训。吹垢索瘢,锻炼成狱,纵能得情,亦是酷吏。此事为不己,有关心术,非儒者所宜为也”[1]118-119。古文《尚书》辨伪,是清代汉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朱一新却认为即使古文《尚书》是伪书,但其中的名言精理早已成为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血肉不可分离,因此古文《尚书》的思想价值仍是涂抹不去的。他斥汉学家之辨伪为“酷吏”,虽然有严苛之嫌,但立足思想史的链条形成,古文《尚书》则是其中不可忽缺的重要一环。汉学家虽精于考据辨伪,但常常囿于识力不深,故未能将学问上升到学术层面,这就是朱一新所言汉学家学识不及程朱之万一的缘由。
既然如此,如何正确深刻地把握宋学、深入理解宋学,既是摆在汉学家面前,又是汉学家不愿面对的问题,所以他要说“程朱可以师法者多矣”。深究起来,最值得后人师法的便是程朱“学术正而虑患深”,“此则为万世学者计”[1]30的学术精神。
学术有为一人之学术,有为一时之学术,有为一世之学术,亦有为万世之学术(所谓为“万世开太平”是也)。那么,程朱的这种学术精神,导源于何处呢?朱一新认为直接自于孔孟,其云:
“仲尼之门,羞称五霸”,为万世学术计也,不如是,则道不尊。“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为一世人才计也,不如是,则道不大。管子天下才,而孔识器小,孟斥功卑,《春秋》之法为贤者讳,而又责贤者备,此物此志也。[1]103
为万世计的学术,是超越一人之功、一时之功、一世之功的学术。五霸之功,非谓不大,但仲尼之门羞称;管仲之功,非谓不大,但孔孟二人讥贬。此并非孔孟不重事功,而是他们不为事功所缚,企图超越事功层面“为万世立一行之久远而无弊端之标准”[2]185。
三、阐发义理,从考证中透进一层
朱一新对宋儒推崇的同时,当然兼及对汉学家的批评,在方法论上体现了破汉立宋的特色。朱一新认为,清代汉学家中除了戴震等少数学者略涉宋学藩篱之外,“其它可言学问,不可言学术,古人于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学不逮古之征也”[1]4。可见在朱一新的批评武器里,“学问”和“学术”这两个概念常常用来区分汉学和宋学标准的。为学的圆融之境当然是二者相合,这一点古人是做到了的,但今人多分。此所谓“今人”,即指乾嘉学者而言。虽然戴氏能够互通,但毕竟是少数派,更何况戴氏对于宋学本身有许多误解,并非本质意义上的互通。因此,朱一新对于汉学的批评,其主要的立足点是学问与学术不合,亦即谓学问未能摆渡到学术之境,这成为乾嘉学者的最大缺憾。二者不合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分穷经与致用为二事,故他先从古人的明体达用说起:
古之儒者明体所以达用,宁使世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之不足用于世。故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其有不合,则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求之。周公夜以继日,仲尼铁挝三折,圣人且然,况学者乎?圣贤垂训,莫非修己治人之理。降而九流之言,百家之说,亦无不以明体达用为归。所学有浅深,斯所言有纯驳,识之限于天者无如何,学之成为人者宜自勉矣。[1]4-5
学术的境界当然是“以明体达用”为指归的,学问则不然,他批评汉学家“琐碎穿凿,自谓能振汉儒之坠绪,不知此特汉博士之所为”[1]4。而真正的汉儒是“不求实是而能远绍微言,兼通大义,夫岂如汉学家所云乎?”[1]4故他告诫汉学家说:
古未有不躬行实践而可为学者,亦未有不坐起行而可谓之学者。故班史讥不学无术,学术之发于心术者至微,其关于天下者甚巨。[1]5
学术于天下有大用,而“汉学家乃分穷经致用为二事”,故朱一新感叹道“浅学所未闻也”[1]5。语气中透露出对乾嘉学者的极度不满。
对于汉学家的批评,朱一新还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在比较考据和义理二者时,他认为义理要高出考据一层,其云:
宋学不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1]116
客观地看,朱一新其实并不反对考据,他虽为理学家,考据功夫其实也不弱。理学家不废考据,是他常要表达的一个观点。他对于朱熹的推崇,其中也包含了对朱熹重视考据的深刻认识。他说:“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朱子言:‘考证别是一种功夫,某向来不曾做此。’自谦之词。今读《语类》随举一事,无不通贯,非精于考证者能之乎?”[1]116而朱一新本人也非常重视考据的作用,对于考据与义理之关系,他还有很通达的见解,其云:
小学训诂治经之始事,而经义非仅止于斯。训诂既明,乃可进求微言大义之所在耳。[1]143
小学训诂是治经的基础,但治经不能永远停留在小学训诂阶段,而当在此基础上,朝深处更进一步,即求经典之微言大义。当然,在求经典之精意过程中,必须遵从以下原则:
治经者当以经解经,不当以经注我。以经注我,纵极精深,亦未必圣贤本意,况易入于歧趋乎?[1]47
探求义理,不能脱离经典,更不能以经注我,这与前面所引“汉宋诸儒解经,一字一言,必还经之本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进一步申言:
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训诂名物,典章制度,无不讲求。倾群言之沥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诵,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1]47
朱一新见识超出一般宋学之处,在于他强调义理的同时,不偏废考据,同时明确反对凿空武断的议论,更反对新奇之说,其云:
学问之道,愈平常则愈精实,愈精实则愈繁难。人情畏难而就易,厌故而喜新,故新奇之说易行,尤易误聪明子弟。周秦诸子理昭趣博,可谓新奇之至,而其誃倚于一偏,不善读之,则易坏人心术。[1]47
就朱一新对义理的“覃思”而言,他主张“精实”之论,而非“新奇”之说,因为后者“易坏人心术”,故发为议论,必须审慎。在我们知道朱一新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考据与义理关系,以及他对义理本身所框定的原则之后,结合他前面提到“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的观点,可见他总体上是将义理作为治经的终极追求来看待的。因此相较于考据而言,义理为“精义”,考证为“粗迹”,义理为上、为精、为指归。由此他总结道:
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愈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识何以长?在乎平心静气以读书。一卷之书,终身抽绎不尽,通之于身,验之于事,而学识由此精焉。学者囿于凡近固不可,骛于新奇无不可。圣贤所言,莫非人情物理。训诂、名物,岂足以尽六经?即进而窥微言大义,亦当于切近者求之。必欲驾乎古人之上,斯近名之习中之,而凿空武断之病纷纷起矣。[1]47
考据属于“学”的范畴,议论属于“识”的范畴。义理得之于识力,故比考据要更“透进一层”。学而无识,愈学愈愚,此对乾嘉汉学家有含沙射影之意。事实上,朱一新就常常喜用一个“识”字来对汉学家作出评价。如他比较郑、焦和汉学家之区别,就是以“识”作为标准的,其云:“郑、焦未尝无一得可取,渔仲尤有心得,特其以后世之例诋诃古人,故格不相入耳。国朝诸儒者斥渔仲甚力,然学识终在诸儒之上。近时史学惟钱竹汀为超绝,其精审视渔仲固远胜之,而孤怀闳识,亦不逮渔仲远甚。”[1]40又如朱一新批评惠栋治汉《易》的“寡识”,讥讽之辞,近于刻薄。除了他认为惠栋未得“汉儒家法”的原因之外,引起朱一新批评冲动的更深层次原因还于惠氏之学“流于礻几祥小数”,他说:
理可知而数难知,儒者治《易》,穷理以尽性可矣。多谈象数,复不得其本原,琐悄穿凿,甚无谓也。[1]4
可见惠栋治《易》不仅在于是否遵循汉儒家法问题,更主要是偏离了儒家治《易》的基本立场,即对于义理之学的追求。
由此而导出朱一新对汉学家治学不言“心性”的又一批评。《易》书有“性道”,而惠栋治《易》走象数之路,故未得窥圣学门径。其实自西汉起,学者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惠栋未得闻,除了“寡识”之外,当然还与他压根就不重视义理有关,这其实是汉学家们的一个通病,朱一新说:
西汉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多明大义,然精微要眇之说,宋儒固亦甚多。其言心言性,乃大义之所从出,微言之所由寓。汉学家独禁人言之,则无论《周易》一书专明性道,即四子书中,言心性者何限?[1]116
汉学家禁止言“心性”,在朱一新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群经之中,莫不蕴含性道。他指出:
子贡谓性道不可得闻,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后,学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借口此言以文浅陋,则六经几可删其半矣。[1]117
不错,子贡是说过“性道不可得闻”的话,但此话不可作为汉学家掩饰自我寡识的一个借口,否则,治经而不覃思性道,则六经有一半以上要删除了。他接着申言之曰:
《韩诗外传》云:“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恶,适情性,而治道毕矣。”……故理好恶者,《大学》絜矩之事;治心术适性者,《大学》诚正之事;原天命者,《大学》顾諟明命之事。古之儒者,言治道若此,安有去心性之学而可言治道者乎?[1]117
朱一新论及汉学家不言“心”,似乎越批越来气,他甚至认为他们连王学末流都不如,其云:
虽然王学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则目自能视,耳自能听,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无所与,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诃以为释氏之说。古人惟恐心不灵而时省察以养之,近人惟恐心之或灵而事事窒塞以仇之。务使如顽石然,一无知觉而后已。呜呼!误天下后世,而骛于口耳相率为破碎无用之学者,非此言欤![1]124-125
心性关乎治道,而治道乃学术终极目标,这便是他特别强调义理要高出考据一层的原因所在。
四、学思相合,宋学胜于汉学之由
朱一新认为对于义理的追求,认为必须要做到学问与思辨并重,他说:
《孟子》谓“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问学”。盖德性尊,大体立,而后学问有所附丽,破碎支离,固不足以言学也。陆象山以此为宗旨,本不误。误在主张太过,而欲以六经注我,则流弊甚大。圣门教人学问与思辨并重,故无罔殆之弊。……去思以言学,近儒乃始有之。[1]125
朱一新尊崇程朱与批评汉学家,主要在于思学相合与否,这仍然反映了他关于义理为考据更进一层的观点。“去思以言学”,实质对汉学家最终的学术成就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为此朱一新也感到惋惜,其云:
近儒乃倡实事求是之说,鼓动一世六书、九数、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类,多卓然名家,惜乎其不善用所长耳。[1]116
所谓“不善用所长”,盖指汉学家为学,仅止于学,而未及思,故未能最大程度发挥其治学的效果,这确实是可惜的。这又由此而导出他对汉学家批评宋儒的反批评:
后儒或疑穷理为支离,谓非下学所能。或疑穷理为惝恍,谓非圣门所急。不知“大学”者,大人之学。旧读“大”为“泰”,古者十五而入太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穷理者,事事有条理之谓,凡天下国家之事,皆吾身所当为,即皆吾心所宜知。知之而仍累于物欲,是意不诚也;为之而不得其条理,是知未至也。天下有无理之人,无无理之事,事之无理者,必其不能通行者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斯可措诸天下而咸宜,俟诸百世而不惑,夫岂有支离惝恍之失哉?[1]148
“穷理”语出《周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颢认为天理为人心所固有,只是气禀所限,人欲所蔽,而使本来的理变得昏暗了,因此要穷理尽性,最终之目的是要复其初。朱熹作《大学·格物补传》,一方面继承程颢关于理为人心固有的先验论思想,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只有“即物穷理”,才能使内心本来之理显明。朱一新此论大抵从朱熹“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来,并具作了更为客观的阐述。他之所谓穷理,倒不是为使内心本来之理显明,而是要寻绎到一个“措诸天下而咸宜,俟诸百世而不惑”的事物发展规律,若此,汉学家诃斥“穷理”为“支离惝恍”就是无知的表现了。他于是接着批评道:
近人惟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学,所以可贵者,以其本末兼尽也。小小抵牾,岂能尽免?后人虚心以订之,可也;肆口以底诋之,不可也。明中叶后,乃诋为“支离”,乾嘉以来,又诋为“惝恍”。同一程朱,何以相反至于如此?亦适见诋之者之无定识也。孙夏峰言:“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当泻;姚江没,而天之虚病当补。”窃谓夏峰之言未尽确,若汉学家乃正当泻者耳![1]83
由汉学家溺于器数,又导出朱一新对于他们治礼而攻义理的批评,其云:
圣门诲人曰博文,曰约礼,文谓《诗》、《书》、六艺之文,《礼》则三百三千。今人终身治之不能尽,何以谓之约?盖礼有文有本。忠信者,礼之本也。《礼器》云:“忠信礼之本也,义理之文也。”文非徒器数之谓,习其器数,而仍归于义理,乃可谓之文。近儒治《礼》,而力攻义理之学,盖不读《戴记》。[1]155-156
他认为治礼应将习其器数和精思义理相结合,“以措诸用,而非摭拾细碎”[1]157,如此《礼经》大旨,灿若日星,方能阐发殆尽。“苟徒索诸虚而不知征诸实,是为无用之学;异端以之泥于器数之末,而不知性道之原,是为无本之学,俗儒以之”[1]157。
由此而又导出朱一新对宋儒穷理之功其实与圣人约礼之旨无异的辩护,这可谓是他对汉学家批评程朱穷理为支离而进行反批评的总结,其云:
大抵博文约礼分先后,不分缓急。当博文时,即有约礼之功,非俟读尽天下书而后约之以礼也。古者多言礼而少言理,以礼乐之事,童而习之,有迹象之可循。圣门以下学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则言理居多,仍与约礼之旨无异。盖《礼经》残缺,古今异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宫室器服,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与之言理,则愚夫妇可与知;能与之言礼,虽老师宿儒,或不能通其义。古人制礼之精意,何莫非由天理而来?故礼有文有本,其文之委曲繁重者,非后世所能行,亦非愚夫所能喻,则不得不举礼之精意言之。汉学家以是攻宋儒,未之思也。[1]145
因为往古礼书具在,人人皆识其器数,有迹可循,有礼可依,但却怕他不晓其义,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倘若失其义而陈其数,则为祝史之事。可见礼之精意,本来就是由古人讲起来的。当今礼乐之书残缺,大小礼数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这个时候更要举礼之精义宣教,让人明白古人制礼,亦由天理而来的道理。所以朱熹认为读书穷理,即博文约礼,语虽殊而意则一。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程朱学术之所以为正宗的理由,其云;
朱子教人读书,而读书必归于穷理。于二陆之直指本心者,则虑其过高,而失下学上达之旨;于东莱之多治史学者,则虑其泛滥而贻玩物丧志之讥。至明季及乾嘉以来,而其言无一不验,故择术不可不慎,程朱所以为圣学正宗者,此也。[1]144
由是而又导出朱一新对汉学家诋朱熹小学为浅陋的又一次反批评。汉学家之小学,眼里只有六书,而宋儒所谓小学,则意欲恢复古貌,以趋近三代圣王设立痒序之教的本意。如吕氏《童蒙训》云:“后生学问,且须理会《典礼》、《少仪》、《仪礼》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1]76由此看来,宋儒设计的小学,并不排斥六书,但同时增加了洒扫、应对、进退等内容,因此更加合符三代小学之遗法。所以他批评“近儒诋朱子小学为浅陋,大谬不然”[1]76。由诋朱子小学为浅陋,汉学家继而又批评宋儒不重考据,故从训诂角度言,他们认为唐以后书可以不读,对此朱一新反驳道:
近儒谓训诂、名物,当求六朝以前书,是也;其谓不读唐以后书,则非。此特读书减省之法,非真读书人语也。[1]116
汉学家不主张读唐以后书,实际上就是针对宋儒不擅训诂、名物而言,这个看法其实是带有偏见的。以朱子而论,朱一新云:
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朱子言:“考证别是一种工夫,某向来不曾做此。”自谦之词。今读《语类》随举一事,无不通贯,非精于考证者能之乎?[1]116
当有弟子问及朱子《论语集注》于训诂多不明引,表示“异哉”之时,朱一新回答道:“训诂则博采众家,融以己意,悉著之,将不胜琐屑也。未知其例而率讥之,谬矣。”[1]127朱一新的看法在当时并不孤独,与他同时而较早的陈澧《东塾读书记》,多记朱子亦曾从事考证。陈澧还特别引朱熹《答孙季和书》云:“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他评论道:“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其持论不偏如此。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4]可见朱子重考据,是作为治学之基本功来要求的。
汉学家重视考据,是其所以为汉学家的本色所在。但他们在诋朱熹同时,其自身考据亦屡有所失,由此而导出朱一新对汉学家考据不精的批评。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汉学家对《大学》“明明德”的训释,让朱一新感到非但没有获得确解,反读到他们“借训诂以伸私说”,其云:
《大学》“在明明德”,郑《注》谓“显明其至德也”。“至德”即“明德”。“显明”训上“明”字,故下文注:“谓皆自明明德也。”语意炳然,更无疑义。段懋堂乃援《尔雅》“明明、斤斤,察也”之训,广引诸书,证成曲说。其言与西河《大学问》略同。(西河实用李恕谷之说,而段氏又暗袭西河,汉学家如此类者不少,须分别观之。)而下文“欲明明德”、“皆自明也”二语,绝不可通。反谓孔《疏》误会郑《注》之意,可乎?近儒借训诂以伸私说,不顾上下文义,动欲以此律彼,乃治经之大患也。[1]148
段氏谓孔颖达不得其读,反不知是自己证为曲说。汉学家知识的出错,也许是一时疏忽,但对于许多与思想史相关概念溯源而出现的错误,则可能是因为对学术史缺乏了解而出现误判,如朱一新对汉学家认为“虚灵”二字出于道家,就有不同看法,其云:
近人以“虚”、“灵”二字出于道家,不可以状心体。然则心体固当实同而蠢乎?《大戴礼·天圆篇》:“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诗·灵台篇故训传》:“神之精明者称‘灵’。”《说文》:“灵,巫以玉事神”。此制字之本义,引申之则为“神灵”之称,安得据许书以纠古文《泰誓》、《礼运》?“四灵以为畜,”孔疏谓此“四兽”皆有神灵,异于他物。[1]83
从文字学角度看,《说文》释“灵”,是为求此制字之本义,但作为一个思想史的概念产生,则“灵”仍出于儒家经典,并自有儒家思想的精义所在。由对思想史概念的溯源,导出朱一新对汉学家斥朱子学为禅学的反批评,其云:
朱子注《论语》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近人亦斥为禅学,不知《周官·师氏》郑《注》云:“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郑君已以德属诸心矣。[1]148
汉学家推崇许郑,贬抑程朱,他们批评朱子以德属心,附入禅学,殊不知他们最为尊崇的郑《注》里早已说过“在心为德”的话,所以这个批评是无效的。又如朱熹引郑《注》“相人偶”的解释,而汉学家不知,朱一新批评道:“郑君之说,朱子早取之,而近人反执此以攻宋儒,可乎?”[1]32朱子不仅反对入禅,而且他还恐他人易入于禅,汉学家完全是误解了朱子。朱一新力辟宋儒与禅学无涉,理至精密,辩之甚详。
当然,正如朱一新将乾嘉汉学置于学术史洪流中来看一样,我们倘将朱一新也同样置于整个学术史发展的洪流来看,他的出汉入宋,亦无非是晚清学风转变、思想转变的一个典型案例。正如钱穆所谓:
此则非在汉学风气已衰,人心向厌之后,不道此。不仅章实斋时绝不如此说,即陈兰甫著书,亦尚不如此说也。即此可见当时汉学颓波日衰日落之处,而鼎甫主张所以转换学风以开此后之新趋向。[5]544
很可惜,这种转变因为他的早卒而最终未能修成正果,故钱穆仍将他视为“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学者”[5]546。
纵观近代浙江理学,主要代表有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伊尧乐、应宝时、黄方庆、陈居宽、朱一新等。与清初比较,这时候在浙江理学集团内部,出现了两个方向的融合趋势:一是,对于朱王的界限分别已经不再执着。如会稽学者宗稷辰尝言:“朱子之学,由闽而递传于浙。吾道之昌于越,自尹子证人之学始,至刘子而证人之学成。故尹犹大春也,刘子犹大冬也。若紫阳则博文而道舒,姚江则守约而道敛,犹之夏发荣而秋落实焉。至于冬,而天地之性于是乎毕见,万物之理于是乎备昭,学统之全,与岁功等。”[6]宗稷辰将自己的家塾命名为四贤堂,就已经看出他融合朱、王的学术趋向。二是,对于汉宋的判鉴已经趋于调和。汉宋兼采无论在经学领域,还是在理学内部,都成为浙江学术的主潮;前者以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为代表,后者成绩最为突出的就是义乌朱一新,可见汉宋兼采已成为晚清浙东学术相当成熟的风气了。支伟成之所以将朱一新、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徐时栋以及陈澧等划入“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序列,就是缘于这种浙东学术内部性格长久以来的养成。朱一新虽然学出诂经精舍,为汉学大师俞樾的门生,但是他最后变成了一位理学家,此即所谓的“出汉入宋”。朱一新这种学术倾向的转变,照常理是不可理喻的,但如果我们通读《无邪堂答问》和《佩弦斋文存》《佩弦斋杂存》的相关文章,就会发现朱一新其实是一个具有学术史整体眼光的学者,而且他的这种眼光,已经超出了同时代人许多,因此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但他毕竟还是从旧学术到新学术的过渡性人物,因此他最终只能成为浙江乃至近代理学的殿军。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