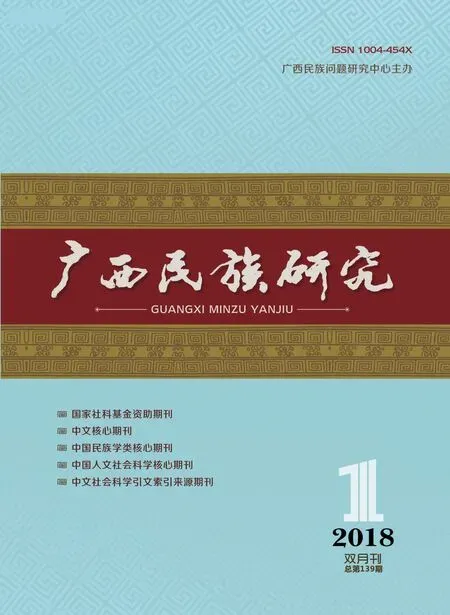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与资源税扩围*
王玉玲 胡颖欣 赵晓明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资源税列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六大税种之一,提出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2016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提出在“适度分权”原则下,逐步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对水、森林、草场、滩涂等开征资源税;赋予地方适当税政管理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根据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提出方案建议。“适度分权”原则下的资源税扩围改革开启。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税权高度受限,“适度分权”原则因此备受关注,被视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税体制的重要举措。
“适度分权”原则对民族自治地方①由于税权的特殊性,本研究所论“民族自治地方”指5个民族自治区。具有重要意义。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治理要实现从中央支配到地方自主,[1]“适度分权”是关键环节。坚持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领域中“适度分权”,不仅可改变以往以经济利益补偿换取政治稳定的思路,也是使自治权向经济性自主权发展,避免其特权化、特殊化的关键。[2]
我国资源税最早可追溯至周代的“山泽之赋”。古代对资源征税较宽,既包括山海园泽之税,也包括各类矿税。清朝开启近代资源税的征收,《大清矿务章程》规定,开矿要缴纳矿界矿产出井税。民国时期,矿产资源税和盐税并行。新中国建立后,实行矿产资源无偿取得制度,矿产资源税取消,仅保留了盐税。1984年,《资源税条例(草案)》颁布,征收范围为原油、天然气和煤炭。1992年,铁矿石纳入征收范围。1993年,资源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7类,取消了盐税。之后,这一征收范围长期保持稳定。
学术界普遍认为,限于7类的资源税征收范围过于狭窄,在资源日益稀缺和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扩围势在必行。征收范围过窄带来两种效应,一是替代效应,即选择性征税人为造成资源产品税负不公,鼓励用不征税资源替代征税资源;二是收入效应,国家放弃了部分资源产品的税收权利,还鼓励过度使用不征税产品。资源税扩围有利于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实现税制的绿色化转型。[3]
民族自治地方牧区、半农半牧区面积占全国比重为75%,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占全国比重分别为42.2%、51.8%,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总量为66%。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作为资源富集地区,民族自治地方是资源税扩围的重点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管理和保护本地区自然资源的权利。权利需要落实为权力才能发挥作用,但由于我国税权长期集中,地方税权受限。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实践看,除了西藏自治区资源税立法[4]外,其他地区的税收立法基本是空白,地方税权虚置。“适度分权”原则的提出为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的充实提供前提,完善资源税权,实现资源税有序扩围,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集中税权”到“适度分权”原则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税权原则不同,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因之变化。税权可分为税收立法权、管理权和收益权。税收立法权是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权力。税收管理权指税务机关依据税法,进行以税款征收为核心的管理所行使的权力。税收收益权是获取并使用税收利益的权力。在经历了“集中税权”“合理分权”后,“适度分权”原则拓展了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
(一)“集中税权”原则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1984-1993年)
1984年,资源税开征。1985年3月,《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将资源税收入70%划归省级财政,30%划归各地市财政。虽然地方财政分享资源税收入的30%,但税权集中在中央。对此,中央也一再加以强调。1988年12月,《国务院关于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指出,国家税法必须统一,税权不能分散,统一税法的原则必须坚持。1991年,《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管理报告》,要求坚决维护税法统一性、严肃性,坚持依法治税,“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这是“集中税权”原则的首次提出。这一原则在1991年4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再次明确,要求按照“统一税政、集中税权、公平税负”原则,理顺税制结构,强化税收管理,严格依法治税。
“集中税权”原则下,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地方资源税权受到限制。唯一的例外是西藏,1989年10月,《西藏自治区资源税试行办法》颁布,自1990年1月1日开征资源税,税目为铬铁矿产品,按照30—40元/吨由资源所在地税务机关从量定额征收。分成比例为自治区50%,地市50%,地县分成办法由地县协商确定。可见,西藏拥有包括税收立法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完整资源税权,是我国这一时期地方税权的独特标本。
(二)“合理分权”原则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1994-2015年)
1993年12月,《资源税暂行条例》和《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发布,盐税并到资源税中,资源税征税范围扩大为7类,“普遍征收,级差调节”。海洋石油企业资源税归中央,其余资源税归地方。作为分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此次资源税改革遵循分税制改革界定的税权原则,即“合理分权”原则。这一原则来自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
“合理分权”原则下,资源税分权的内容体现于1993年《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2011年,《资源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修订,表1中的①内容有所变化,②③④内容基本不变。

表1 “合理分权”原则下的地方资源税权
基于表1中①“对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有色金属矿原矿,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或者暂缓增收”规定,这一时期,地方开始行使税收立法权。以水资源为例,1996年,海南省将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作为资源税税目。1997年,国家税务总局《资源税几个应税产品范围问题的解答》中对此确认,明确矿泉水等水气矿产属“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民族自治地方中,广西对矿泉水和地热水立法征收资源税。
“合理分权”原则下,中央对西藏的特殊税收管理体制延续。1994年7月,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西藏实行分税制,赋予“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特殊政策。除关税、增值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外,征收其他中央税和共享税的具体办法,由自治区政府作出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地方税种的开征,税目、税率的确定和减免税的权利仍由西藏自治区掌握,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资源税立法权、消费税开征权下放地方。西藏仍保有完整的资源税权。
总体看,这一时期中央对“合理分权”比较慎重,并未赋予除西藏外的其他地方较充分资源税权。表现在:首先,有限的税收立法权都在严格的前提限定下。且2011年的修订,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或者暂缓增收”改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表述上淡化了地方税收立法权。其次,税收管理权内容有限,只有纳税地点区域内调整权。第三,税收收益权受限,只有重大损失的减免权。
由于限制地方资源税权,中央政府为应对资源价格变化,不断分省区调整资源税额,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调整包括:2004年和2005年,内蒙古、宁夏煤炭资源税先后调为2.3元/吨;2006年,广西、内蒙古煤炭资源税分别调整为3元/吨、3.2元/吨;2009年,新疆煤炭资源税调整为3元/吨。这种调整对民族自治地方体现为税收收益的变化,并非税收收益权的明确。与此同时,与资源相关的“乱收费”不断滋生,以宁夏为例,2005年,煤炭资源税为2.3元/吨,同时收取森林补偿费10元/吨、煤炭补偿费30元/吨等,规费负担是资源税额的33倍。[5]究其原因,税权缺失导致的资源税收入低、无法弥补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恢复等成本是重要原因。这促使2016年资源税改革“清费立税”和“适度分权”。
(三)“适度分权”原则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2016年至今)
2016年,新一轮资源税改革提出“适度分权”原则,明确在不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秩序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内容见表2:

表2 “适度分权”原则下的地方资源税权
“适度分权”原则下的地方资源税权涵盖了征收范围、计税依据、税目税率和税收优惠等。从性质看,则包括了税收立法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在税收立法权上,中央政府保留了包括批准、核准和备案在内的监督权,保障地方资源税权与中央资源税权不冲突。税收管理权和收益权也较表1明显扩大。
综上,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经历了“集中税权”“合理分权”和“适度分权”3个阶段,从历史纵向比较看,目前处于地方资源税权最充分的时期。最核心的地方资源税权体现在资源税扩围上。民族自治地方是资源税扩围的重点地区,要用好“适度分权”原则,完善资源税权,实现资源税有序扩围。
三、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基本制度框架
(一)扩围基础: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权
充实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包括划分、行使和监督。其中,划分可分为纵向和横向划分。[6]139-141纵向上,“适度分权”原则划分了扩围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立法权,将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扩围的税收立法权应保留在自治区级,不可层层下放,以保障其规范行使,有效监督。横向上,“适度分权”原则以省级人民政府为扩围的立法主体,这与授权主体是作为中央行政机关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一致,对于民族自治地方以税收地方规章立法推进扩围,具有促进意义。长期看,伴随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推进,授权立法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变为《资源税法》,民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主导资源税立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制定地方资源税法规,有序扩围资源税。资源税扩围中,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立法权的核心原则是不抵触原则,即不得同中央政府的资源税立法原则和内容抵触,与中央立法不冲突。这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要严格在授权立法范围内行使立法权。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立法的监督十分必要,要采取国务院批准这一事前监督方式。
优化税收管理权。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管理权主体是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资源税扩围初期多为相关资源的“费改税”,因此,地税部门与之前收费机构的协作是优化税收管理权的首要。以水资源为例,可借鉴河北省地方税务局经验,采取水利核准、纳税申报、地税征收、联合监管、信息共享的征管模式,即水利部门核定企业取用水量并向纳税人核发《取用水量核定书》,纳税人持《核定书》到地方税务局申报纳税,填写《水资源税税源登记表》,相关信息录入征管系统,征收税款。税务机关和水利部门要协调配合,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和协商机制。
保障税收收益权。税收收益权是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行使的结果,对地方政府至关重要,是其履行职能的保障。税收收益权不只是税收收益,是因为权利可以带来固定预期的收益回报,受国家法律保护。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要求“清费立税”,在此背景下,保障税收收益权就尤为重要。
(二)扩围前提:正确定位资源税职能
目前,资源税职能被界定为“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在此职能下,“资源税”实为“调节级差收入的资源租”,混淆了“租”与“税”。调节级差收入并非税而是租的职能。将资源税职能限定为级差调节,不仅不利于优化资源税制,且导致国家凭借所有权应获取的资源租流失。
本研究认为,资源税的职能主要包括矫正负外部性和收入职能。矫正负外部性是主要职能,收入职能是次要职能。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应基于两个职能并正确处理其关系。
负外部性包括当代负外部性和代际负外部性。当代负外部性是资源在开采、生产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代际负外部性是指当代人开采使用资源,导致后代无资源可利用;而后代缺乏对当代资源开发投票权,资源权利无法通过市场价格体现,代际补偿要通过体现国家政治权力的资源税实现。开发水、森林、草场等对导致代内负外部性,即因资源开发利用污染或破坏周边环境,例如,水能资源开发会带来泥沙淤积、河流改道、鱼类洄游通道受阻、候鸟栖息地改变等,森林过度砍伐和草场过度放牧会带来局地小环境改变、土壤退化乃至沙化、沙尘暴等。若土壤彻底沙化,森林、草场无法恢复,则会形成代际负外部性。矫正两个负外部性,是水、森林、草场等资源税的核心职能。应充分认识到,这些资源既具有资源价值,更具有生态价值,在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下,生态价值更加重要。资源税扩围唯有明确并坚持矫正负外部性这一职能定位,才能保障有序扩围,不会“竭泽而渔”。
资源税的收入职能从属于矫正负外部性职能。现有水、森林、草场等资源财政收入形式为各种收费,资源税扩围的实质是“费改税”。短期内,由于税收征收刚性高于收费,资源“费改税”会带来财政收入增加。①从河北省水资源税征收看,2016年7月1日开征到2017年第一季度,水资源税收入11.74亿元,比2015年全年资源费收入总额还多2亿多元。按月均收入算,水资源税比水资源费高88%。参见王晓洁等:《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成效、问题及建议》,载《税务研究》2017年第8期。长期看,由于资源稀缺和环境保护要求日高,资源税扩围广度和深度扩大,带来税目增加、税率(额)提高,资源税收入增加,收入职能凸显。但收入职能不是主要职能,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不应是为获取税收收入,否则,就背离了“适度分权”原则赋予的地方主体性,也不利于民族自治地方可持续发展。
(三)以水资源税引领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有序扩围
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应采取渐进思路,有序推进。借鉴河北省经验,最先扩围水资源税,逐步到森林、草原、滩涂等。原因在于:
首先,水资源税具备较好征收基础。目前,除了宁夏,其余4个自治区都征收水资源税,最早的广西1997年即开征。之后,不断调整和优化,已经积累了相应经验,具备开征基础。见表3。
其次,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税亟待完整化。表3显示,只有广西对地下水征税,其他是对地热和矿泉水征税。对地表水则都征收水资源费。水资源税呈现碎片和缺失状态,亟待通过资源税扩围,实现水资源税完整化。
第三,从资源保护的紧迫性看,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税应尽快推出。表4显示,2015年,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宁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5个自治区人均用水量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人均用水量的4.58倍,民族自治地方中,内蒙古、宁夏和新疆都低于全国平均值,宁夏只有0.13。水资源使用形势严峻,节约用水要求紧迫。

表3 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税

表4 2015年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情况
表5是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除了特殊行业外,其他的都非常低。且如此低的标准仍不能实现应收尽收。水资源费调节水资源使用、保护水资源的职能弱化。
综上,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税亟待推出,扩围要从水资源税开始。之后,逐步扩大范围,在对现有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等“费改税”基础上,实现森林、草场资源税的有序扩围。

表5 民族自治地方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单位:元/立方米)
(四)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后税收的归属和使用
资源税扩围对象的水、森林、草原等,目前都有相应收费,其归属和使用见表6:

表6 资源收费归属与使用
由表6可见,现有资源收费的归属各不相同,有中央与地方分成的水资源费,有全额缴入地方国库的草原植被恢复费,还有按照收取单位不同而缴入中央或地方国库的森林植被恢复费。而现有资源税是除了海洋石油资源外,其他归属地方政府。这样,初期以“费改税”实现的资源税扩围后,其收入归属就需要明确。从河北省水资源税试点方案看,水资源税延续水资源费的分成办法,仍按1:9在中央与地方间分享。若照此办法,则草原植被恢复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改税”后,都要延续之前收费的归属。一个资源税下会因税目不同出现4种甚至更多归属方案,这必然带来税收收入体制的混乱。因此,资源税扩围初期,为稳定中央与地方既有财力,可考虑复制相关收费的归属方案。但长期看,应将不同税目的资源税收入归属统一。基于前面对资源税矫正负外部性核心职能的分析,而此职能主要由地方政府履行,因此,民族自治地方扩围后的资源税应与现有资源税归属保持一致,归属地方。
现有资源收费的使用原则上都为专款专用,“取之于水,用之于水”“取之于草,用之于草”“取之于林,用之于林”。而现有资源税并未明确专门用途。本研究认为,应将扩围后的资源税调整为特定目的税,用于地方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资源税使用中,向基层政府倾斜。
(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优秀青年人才科研专项”和2017年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之理论经济学学科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1]熊伟,等.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治理:从中央支配到地方自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2]陆平辉.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问题解构与协调对策[J].宁夏社会科学,2016(6).
[3]黎江虹,黄家强.中国税收征管法修订新动向:理念跃迁、制度创新与技术革命[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4]王玉玲,等.西藏资源税立法:历程、评价与改进[J].地方财政研究,2013(9).
[5]寇铁军,高巍.资源税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及未来政策构想[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3(6).
[6]王玉玲.民族自治地方税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