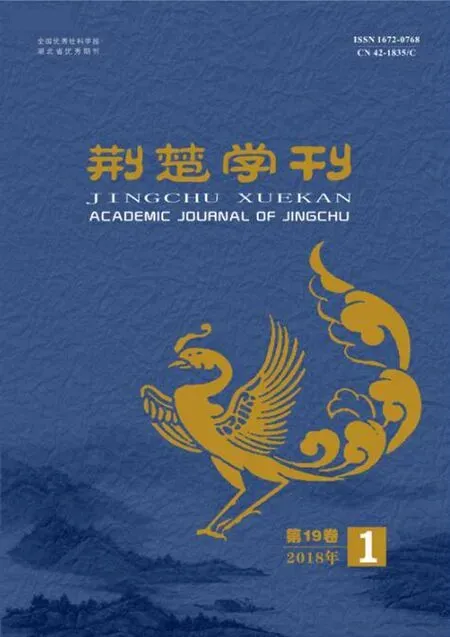屈骚对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的影响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楚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历史上的楚国,枢要之地在湖北,屈原的故乡也在湖北。明清时期,湖北治域逐渐形成,楚文化对当时湖北文学的影响也鲜明起来。研究楚文化对后世文学发生的影响,从明清时期的湖北入手自有其典型性。
洪武九年(1376),明朝设立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基本囊括两湖地域,其中洞庭湖以北即湖北,将湖北今境除了英山、建始二县之外的所有区域,首次纳入同一高层政区。湖广虽为统一政区,但八百里洞庭事实上将之分隔为湖北湖南两个区域,统一施政,多有不便,所以某些业务的有限分治时有发生。尤其是正德五年(1510),“以大湖(洞庭湖)中分南北”,设置南北巡按御史二人,分按湖北、湖南。(参《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癸亥”)这个官职是省级配置,湖北与湖南分省已显苗头。虽然基本独立的湖北政区要到康熙三年设置,然而,期间有关行政、司法、科举、粮政、民族、军政等方面南北分理之策,多有出台。据张建民先生在《湖广分省问题述论》中考证:嘉靖十五年(1536),以湖广地广,粮务浩繁,诏添设湖广布政司督粮参政一员。(参《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四》)万历二十八年(1600),设置偏沅巡抚(湖南巡抚的前身),万历皇帝称:“偏沅用兵原是湖广巡抚之责,朝廷念其地广难遍,特设经理以分其劳。”自此大湖南北分督兵饷。(参《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四》)万历四十一年(1613),湖广分南北,始各增提学一员。(参《明史·卷六九·志第四十》)顺治十年(1653),湖广境内湖南、湖北各设屯道,分区主持屯田之事。(参方裕谨《顺治年间有关垦荒劝耕的题奏本章》自《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第25页)这些分理之策本身显示了两湖各自独立成为一种文化地理趋势,客观效果上也使得湖北成为了一个机能文化区,具有文化发生学的作用。大量文献显示,在湖北走向分治的过程中,楚文化在湖北文人身上形成浓郁的区域文化意识,楚文化和屈骚鲜明地影响着湖北文学。本文拟谈谈屈骚对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的影响。
屈骚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其入人之深,幽眇深曲,难以言说。本文既然单论湖北,就不求全面,但求证据明了,甚至尽量用明清时期湖北文人自己的言论来说话,希望揭示当时的湖北文人在有意识地状态下怎样受到屈骚的影响。
一、屈骚对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袭取体貌
宋人黄伯思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楚辞。”(《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这是从楚辞的外观风貌着眼的。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受屈骚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这类显性层面。
湖北文士们常以与屈赋相关之名命题自己的诗作。如在《湖北文征》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类的标题:明代沔阳欧阳谦的《沧浪集》,蕲州顾天锡的《隐骚》,蕲水李元莹的《楚诗》,孝感沈宜的《楚声》;清代孝感熊賜履的《些余集》(熊氏自注云:曰‘些余’者,犹骚音也。见熊賜履《些余集序》),麻城梅坼的《续骚草》,阳新费墨娟的《感怀辞仿骚体》,等等。
在诗歌句式方面,湖北文士们全方位学习屈赋,如:
澧有兰兮人其人,沅有芷兮物其物。(孙树瑜《屈公祠赋》)
智人远虑兮,反不若蚩蚩者之安愚而守拙。(费墨娟《感怀辞仿骚体》)
这些句子,从字数上看,有通篇四字句,有杂言句;从语气词上看,有“兮”字句,有“些”字句;“些”字位于四言诗偶句之尾;“兮”字有每句用的,有间句用的;有用于句中的,有用于句尾的。
从用词方面考察,文士们常常在创作中直用或隐括屈赋篇名。如:五峰田信夫的诗句“山鬼参差迭里歌”(《澧阳口号》其二);其同族田宗文的诗句“故里已拚渔父约,天涯堪作白头吟”(《陈广文裁甫不赴汉中归武陵有赠》),“寻芳过楚泽,取醉吊湘君”(《登遇仙楼寄玄璞子》);江陵汪嗣圣作楚歌《告狱中白骨》有句云:“自古国殇,为雄傀些”;归州孙树瑜的楚歌《屈公祠赋》有句云:“每望阙以兴思兮,惟涉江而永叹”,“既搔首而问天兮,岂解寸心而愁断”,“撷芳草兮绵长,思美人兮抑郁”,等等。其中的“山鬼”、“渔父”、“湘君”、“国殇”、“涉江”、“问天(天问)”、“思美人”等都是屈赋中的篇目。
至于屈赋中其它的词语,在文士们的作品中就更是俯拾可见,如“洞庭风叶下,不见雁南飞”(五峰田九龄《秋风》),“客鬼轻残蜕,骚宫重楚魂”(公安袁宏道《泾阳驿见王子声壁间韵,怅然有怀》),“我所思兮在螺洲,下有长江万里之清流。生平濯缨爱此水,誓将归筑沧江楼”(监利王柏心《螺洲吟》)等。结合上面的句子,“洞庭”“落叶”“楚魂”“沅澧”“沧浪”“濯缨”“楚泽”“雄傀”等,都是屈赋中常见的物象或意象。特别是蕲州顾天锡的《隐骚》,主旨是叙述和慨叹明末故乡蕲州所遭受的兵燹,通篇词语和主要意象大多仿效屈原的《国殇》,如:“肃杀窞兮亥气弇,戾士坎兮木先憯。……神灵怒兮鬼夜泣,雷填填兮雪霰集。长矢抨兮短兵接,崇墉堕兮震轰配……”,不仅词语物象袭取《国殇》,而且句式、意境上,亦得《国殇》之神。
(二)继承特定的意象
在屈骚中,有一类意象尤为湖北文士们所青睐,那就是“香草美人”,如“芙蓉渚外骚人径,杜若洲边处士家”(田九龄《改岁感忆兆孺师却寄》);“东风二月杂香起,缘岸芎间白芷”(王柏心《螺洲吟》),上述诗句中“兰”“芷”“芙蓉”“杜若”“芎”“芳草”等,都是这类意象。屈赋中的“香草美人”是具有比兴功能的意象。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为显著的艺术特点,也是《风》《骚》的优秀传统,而且与《风》比较而言,《骚》的比兴更发展,不仅连类取譬,而且递进为象征之法,更添一种曲折、深沉、含蓄之美。王廷相云:“《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1]所言正是此意。司马迁言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屈赋中的“香草美人”象征屈原高洁的品质和忠君爱国思想。这些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意象运用,成就了屈赋的魅力。明末景陵邹枚在《郢中白雪记自序》中谈到屈骚对楚国后世文学惠泽时,云:“江水之清,清到于今;玉露之洁,洁到于今;香草之美,美到于今;而吾郢之异人复生焉。”[2]强调屈骚中美人香草传递的精神激励和培养了楚地后世文学。嘉庆时通城吴寿平曾作自放诗《续琵琶行》,自题其后云:“于戏,碧海青天,羁愁莫诉,美人香草,骚士寓言,又谁知之?”[3]认为自己有屈子那样的襟怀和苦闷,屈子托之以香草美人,自己托之以《续琵琶行》,用心如此,有谁知之?突出的正是屈骚中香草美人的传统对自己创作的启发。
正是由于屈赋中的香草嘉木蕴含着动人的魅力,楚地的香草嘉木便成为湖北文人关注和称颂的重要文学对象。如:清朝黄陂范轼作《三楚草木颂》,清朝孝感武东澍亦作《三楚草木赞》,二作都以十二首四言诗分别对所选的十二种名卉珍木予以赞颂,诸如兰、蕙、桂、菊、杜若、芙蓉、蘼芜、丹青、柏等。武东澍在《三楚草木赞》序文中说:“楚自屈子作骚,草木弥著,词人衔其华实,童蒙拾其香草。”“昔江淹居闽作《草木颂》,不揣固陋,窃效其体,取见于前记者若干种赞之,以继屈子之后。凡已见于《离骚》者,不与焉。”[4]可见是继骚而作的。其中的《柏》诗云:
木贵冬荣,黛饶夏色。高节久彰,苦心谁识!香叶菴霭,青柯攒植。阴附云霞,独全贞德。
这类作品比德于木,赋予更多的嘉木以美德,就是要将屈赋的香草美人象征传统发扬光大,更好地泽被后人。
屈赋中,还有一类与香草美人密切相关的意象,即鬼神。楚地巫风盛行,鬼神信仰,源于地理,根乎民性。屈原在笔下构筑了一个缤纷的神话世界,那里的神鬼,既具有灵性,更具有人情。屈子思绪飞腾,纵横奔逸,构筑了一幅幅神秘、浪漫、诡谲的瑰丽图景。湖北文人,也明显追求着这类的意象和意境。袁中道云:“楚人之文……直摅胸臆处,奇奇怪怪,几与潇湘九派同其吞吐。”[5]道光时监利王柏心的《田父逢列仙行》,写田父与群仙对话,主题与楚辞《渔父》相仿佛。其中写遇仙场面云:“道遇蓬莱仙,云衣垂翩翩。田父往问讯,子何来田间?答云紫府拘束久且疲,玉山禾熟不疗饥,上清真诰读尽三万卷,太乙藜火难为炊。后来秦萧史、王子晋,亦有金华牧羊儿,纷纷少年子,道成饱且嬉。骑麟翳凤凰,出入盛威仪。”思绪飞动,把场面写得缤纷灵动。又如,光绪时沔阳黄福在《黄鹤楼赋》中描写黄鹤楼的一段:“秋江涌月,倒影流黄。洶涛喷齿,匹练凝霜。金宫银闼,罗幌高涨。忽水落而石出,澹西爽之斜光。燦琼霙于秘殿,拂櫺槛以轻飏。……百灵闢噏,变态溢洋。贡媚权奇,顾盼徜徉,集四序之瑰璚,涵万籁之铿锵。”作者以奇特的想象,将黄鹤楼边大江的景色交错写出,昼夜晴雨,鳄鲸灵怪,声光变幻,纷纷呈现,瑰丽而诡谲,令人目不暇接,魂悸魄动,体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风采。
(三)继承多忧善怨的抒情特色
嘉靖时兴国吴国伦云:“予读《楚辞》,而知楚之人善怨,其天性哉。”“夫离骚,自怨生也。”[6]认为楚人天性多忧善怨,文学上的典型便是《离骚》。其实,说多忧善怨是楚人的天性,自有其道理。楚文化自来就与儒家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中原文化有所疏隔,受儒家的以理抑情之侵入不深,因此,楚人的文学创作常常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自由挥洒感情,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情感抒发,即所谓多忧善怨。
崇祯时孝感沈宜曾与其伯兄有过一次争论。他说:“伯兄出而遭妒,化而为诗。”“先生之诗,胎息三闾。”“大抵先生之诗感乎物境,发乎性情,情至韵深,自能动众,而间有露怨悱本色者,先生欲乙之。宜曰:‘否否,三百篇中氓蚩巷伯诸诗,何尝不明写胸臆,直指谮人。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安睹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乎!且夫峭直而善怼,磊砢而多风,亦又与楚辞近也。’”[7]87(沈宜《伯兄荼庵诗集序》)指出伯兄在官场贤而遭妒,其诗又从屈骚之中生长而出,发乎深情,难免怨悱。其自编诗集时,因感不合怨而不怒的儒家规范,欲予以斧削。沈宜则坚决主张保留,认为怨悱是诗的本色,《诗经》中已经出现,《楚辞》就更普遍了。虽是一次小小的争论,但显露的恰恰是“哀怨起骚人”这一创作传统在湖北文人创作中的顽强生命力。
多忧善怨、情词激切,其实质是文学创作对儒家诗教规范的突破,对真情的追求。万历时蕲水郭士望在《蕲上社初集序》云:“宇内博士家,无不高楚人才分者。”其原因便是“人不破绽,定非真人;文不破绽,定非真文。”[8]指出楚人的才之高,文之真源自真人,而不是完人(不破绽)。那么真人为什么会写出真文呢?万历时夷陵雷思霈进一步指出:“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9]并且认为,作为楚人的袁宏道正是由于“但任吾真率而已”,方能与古人抗首,自铸伟词,成就楚人在明代文坛上的辉煌。这种看法是深刻的,袁宏道确实主张“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而且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抒情的峭露。袁宏道在谈到公安派的创作心得时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其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景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斎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乎?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10]指出楚风“劲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离骚》一经,屈子“忠而见疑,洁而蒙污”,有不堪之情,发辞哀而至于伤,是自然之理;公安派的诗歌,真情所致,发语张露,故其诗可传。如袁宏道的《逋赋谣》:
揭露赋税沉重,民生凋敝,矛头直指当时朝廷和万历皇帝,真可谓胸胆开张,酣畅淋漓。屈子有诗云:“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两相对照,其情之张扬,哀而伤,怨而怒,何其相似乃尔。
这种真情创作,往往同时就是创新。嘉靖时沔阳陈文烛在《少泉集序》中评价京山王格的诗歌创作云:“余每读‘哀郢’‘怀沙’之章,‘垂老’‘无家’之叹,‘不才’‘多病’之咏,千载而下,使人沾襟。倘所谓楚人之深于怨乎。先生抱器丁年……乃引迹江澨,灌园艺蔬,濩落终身。”“(其诗)情属景生,神在象外,如元造播物,色相种种。一物之中,生意俱足。其文丽而则,正而不迂。苕发颖竖,离众绝志,而奇气横逸,不可控驭。”[11]认为王格如同屈原那样,怀忧怨之深情,则奇气横逸,不可控驭,因此创作出新鲜活泼的诗作来。如王格的《谒申大夫祠二首》(其一):
古庙隐孤汀,遗风千载馨。伍员覆楚国,七日叫秦庭。社稷心犹赤,江山草又青。过门惭下马,未勒颂功名。
作品鲜明地表达了对申包胥和伍员的爱与憎,也寄寓作者对楚国深深的依恋和叹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王格的诗信口矢笔。《四库全书·万姓统谱·卷四五》称其诗“多幽愤不平之意,而卒归于和厚,犹有三闾之遗风焉”。良有以也。这在尺模存拟的七子时代,当然是有新意的。
(四)继承屈赋的现实主义精神,记录时代巨变
风骚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具有相通的可贵文学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政治绝不是身外之物,文人自身也绝不可能做个闲吟的逍遥派,现实主义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创作精神。湖北文士们认为,在湖北诗歌史上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最典型地表现在屈原和杜甫(祖籍襄阳)身上。他们经常将屈、杜连类而举,如:嘉庆时汉阳易元善在《汉南诗约序》中云:“(汉阳人诗),或摘艳三湘,瓣香屈宋或读破万卷,接武少陵。”[12]光绪时孝感丁宿章在《〈湖北诗征〉凡例》中云:“虽生不同时,庶几楚国先贤,襄阳耆旧,时深景仰焉。”[13]皆屈杜连及,风骚并举,属意美刺,关注现实。说杜诗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容易理解。其实,屈骚同样有着鲜明的现实性。刘知几云:“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14],指出并赞赏屈赋与《诗经》同样具有诗史的属性。
屈杜的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引导了湖北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特别是在政昏治乱、国破家亡之际,屈杜的这种诗史精神更是启发着湖北文人用诗歌记录时代巨变。沈宜在给自己的诗集作序时说:“三户夏五之乱,可为痛哭流涕者矣。”“语曰:杜诗如史。又曰:子美一生愁世乱,史官失职,身其乱者志之诗。时事可知矣。”首先指出屈杜诗歌对国家动乱的记录,接着说明自己的诗集“起癸未夏讫甲申春,始乎乱,卒乎烬也。骨肉凋零,鸿飞露溘,风烟余息,饮痛荆榛。听其声如嫠妇之夜泣,如征人之晨起焉。其事则剧寇骄兵,其诗则史。盖自元至正甲辰后,楚国之乱,未有是也,则亦江汉汝坟之别调也。虽燕台醉梦中,魂魄犹思楚焉。未能忘楚,题曰《楚声》。”[7]86在屈杜引导下,沈氏有意识地用诗歌记载楚地明季所经历的张献忠之乱,并将诗集命名为《楚声》。光绪时沔阳黄福在给汉口诗人舒虞笙的诗集作序时说:“盖楚风始于江汉,雄于屈宋,盛于杜孟”,强调了楚地屈杜的诗歌传统。接着说:“舒君虞笙……变革以来,(其诗)尤多拊时感事之作。”“虞笙其有《小雅》伤时,《离骚》幽怨之意乎!”[15](黄福《粪心室诗集序》)指出舒氏诗歌创作在“今环海交通,全球多故”的清末变革之际,尤多拊时感事之作,祧承骚雅精神。
在这种现实主义写作中,诗人表达对时局危殆的深切忧患,浸透着鲜明的屈骚情结,体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如,明清之际杜濬的作品主要表达的便是自己作为一位遗民诗人的亡国沉痛。他的《龚宗伯座中赠优人扮虞姬绝句》云:
色散准则关系式隐含了液体射流表面波增长率与表面波数之间的关系。采用穆勒方法,可以对色散准则关系式求取数值解,并绘制出表面波增长率随表面波数的变化关系曲线图。图中曲线的最高点为最大表面波增长率点通常称之为支配表面波增长率(dominate wave growth rate)其所对应的波数称之为支配波数(dominate wave number)表示液体最不稳定的状况,也就是最容易碎裂的状况。因此,稳定性分析就是研究液体两侧气液流速比之差液流韦伯数 W el、欧拉数 E ul、雷诺数Rel 、气流马赫数 M agj等因素对曲线图以及的影响。
年少当场秋思深,座中楚客最知音。八千弟子封侯去,惟有虞兮不负心。
“楚客”是作者自称,作为虞姬的知音,在八千子弟中许多人降汉封侯的反衬下,深切地表达自己作为一位遗民诗人的亡国沉痛。
二、屈骚对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产生显著影响之原因简论
(一)崇拜屈原
屈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杰出的诗人,加之他又是楚国这样一个大国出色的政治家,在挽救祖国的政治危机过程中表现出崇高的人格精神,因此被后世文人视为榜样,甚至被偶像化。因为屈原的故乡——秭归,所以屈原的偶像化在湖北表现得尤为突出。且看几则材料:
雍正时归州学使凌榆山捐修屈原祠,归州拔贡向治在《凌学使捐修屈公祠碑记》中云:“其(屈原——引者)在三楚,固为第一流人。历乎九州,亦属无双国士。”“当年建庙江滨,潜德比乾坤之寿。蒸尝世及,大节争日月之光。然余韵流风,洵足廉顽立懦。”[16]
清初公安诸生龚三捷呈请本县乡贤祠崇祀屈原,他在《请崇祀屈原于乡贤祠文》中云:“屈公生于荆而遂志于长沙,楚乡之贤未有能先之者,若得洒一笔之波澜,举千载之旷典,使楚属乡贤俱得崇祀屈公”,则“三楚幸甚,天下后世幸甚”[17]。
清朝后期黄冈举人刘溱在任武昌府教授时,主持重修三闾大夫庙,他在《重修三闾大夫庙碑》中云:“先圣后贤,若合符节,此我三闾大夫遗庙千年,独能受腥焰俎豆之供,而永为江汉雎漳之望也。”[18]
这样的文章在湖北有很多,在历代《归州志》中最为集中。他们认为屈原德行文学,彪炳楚地,崇祀屈公,“尤足垂世教而励末俗”、“生其乡,被其遗芳余韵,类皆洁廉贞之行,猎文艺之薮也”[19]作为楚地后人,道德文章必然受其沾溉。这种观念,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信仰。
(二)皈依屈骚
屈原是屈骚的核心,屈骚是楚辞的核心,湖北文人对以屈骚为核心的楚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湖北文士们好读屈赋,格外关注屈赋。如袁宏道“凭将野意酬君子,饱食西窗读《楚辞》”(《食笋,时方正月》),五峰田霈霖“《离骚》聊自展,一读一悲吟”(《甲申除夕感文怀》其九),其同族的田宗文不仅爱读楚辞,还将自己别业命名为“楚骚馆”,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楚骚馆集》。仅仅明清时期,史籍见载的湖北人所写的屈赋研究著作就有十三部,而郭维森先生在《屈原评传》中提及的同期楚辞类著作总共也不足三十部,足见鄂人对屈赋的偏爱。
湖北域内的才士,常被时人冠以“楚中二杰”“楚中三才子”“楚四君子”之类的连称。湖北文士交游唱和,常带有鲜明的楚骚人意识,如崇祯十三年十六位楚地(鄂湘两地——作者)诗人“同集秦淮”,在南都结红雪诗社。湖北文人经常在一起,展开仿骚创作活动,如嘉庆时天门熊士鹏在与汉阳雷楚材一批才士交往时云:“吾与(雷)南翘诸君,皆楚人也,亦安能不操钟仪之土风哉!”[20](熊士鹏《汉南诗约序》)甚至连隆、万时期的诗坛盟主王世贞也羡称:“莫怪相闻多楚调,秋风自傍楚人多。”[21]湖北文人互赏仿骚创作,正如顺治时孝感熊賜履在《些余集》所言:“楚人好楚音,固其性然。”[7]264
文士们还编辑湖北地域的诗作,并以与楚骚相涉之类的词命名。如:明代江陵雷叔闻编《郢里阳春集》;清代蕲州汪蘅编《楚中风雅》,江夏王一宁编《楚风两朝诗选》,汉川张清标编《楚诗选》,蕲水李见璧编《宏圃楚诗》,等等。
(三)继骚而作的责任感
生活在湖北这块土地上的文人,受到屈赋的感召,形成了继骚而作的常态创作心理。
明清之际黄冈杜濬在《楚游诗序》中说:“(士)所游之地(楚地——引者)乃屈原、杜甫之乡。……然则士之过乎其间其安能无言耶?”指出大凡游楚之士,受到屈原、杜甫的感召,没有不动诗笔的道理。接着他写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楚人的创作体验:“故欲言又岂易耶!余垂老不归,故乡之事日新月异,然无由得知,其得知传闻者,挂漏不足据,往往自伤。又时用自幸,无屈、杜二子之才而百倍其穷,藉使得归而不能为其骚与诗,何如不归藏拙之为愈也。”[22]杜濬,即茶村老人,黄冈人,倜傥高才,有鸿鹄志,累困科场,值明末动荡,遂避地金陵,专意为诗,穷居茅屋,甚者不能举火。此处杜濬的意思是,自己以垂老之年客居他乡,无由知晓故乡的变化,往往自伤。但想来也有一丝庆幸,因为对于故乡先贤屈、杜来说,自己穷困过之而才又不及,如果回到故乡,就一定要写出骚诗;但才笔不能胜任,倒不如不归乡的好。在文坛上被灵均遗芳、继薪火、发楚声、张楚军,成了湖北文人的责任和写作的基本心态。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湖北文人,崇拜屈原,皈依屈赋,对屈赋的传承和发展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有意识地继承屈赋的传统和精神,形成引人瞩目的仿骚写作现象,为明清诗坛画出一道亮丽的风景。明清时期,专制思想和统治进一步强化,作为正统的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其创作总体上呈现出因循守旧的状态,在唐宋诗风之间兜圈子。湖北文人的仿骚写作,不仅丰富了明清诗坛,而且给诗坛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屈赋对真情的崇尚和对情感自由表达的追求,破除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激发了与王阳明、李贽思想解放相呼应的公安派、竟陵派的诞生,正是这一脉活水,流经清末与“西风”东渐相呼应的“诗界革命”,最终汇成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滚滚洪流。
[1]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M].台北: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213.
[2]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五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388.
[3]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26.
[4]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十三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337.
[5] 袁中道.珂雪斋集·淡成集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5.
[6] 吴国伦.甔甀洞稿:卷三九[M].道光十年桂芬斋木活字印本.
[7]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六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8]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四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321.
[9] 雷思霈.潇碧堂集:序[M]//袁宏道.潇碧堂集.万历三十六年,袁叔度书种堂刻本.
[10] 袁宏道.序小修诗[M]//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87.
[11]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二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508.
[12]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八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325.
[13] 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M]//《湖北诗征》凡例.光绪丁氏泾北草堂刻本.
[14] 刘知几.史通·内篇卷五·载文第十六[M].四库全书本.
[15]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十二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186.
[16] 沈云骏.归州志[M]//向治.凌学使捐修屈公祠碑记:卷九.光绪八年刻本.
[17]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七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412.
[18]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十一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415.
[19] 范德炜.兴山县志:序[M]//伍继勋.兴山县志.同治四年刻本.
[20]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文征·第九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56.
[21] 王世贞.寄魏顺甫·卷四八·四部稿[M].明刻本.
[22] 杜濬.楚游诗序·卷二·变雅堂文集[M].康熙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