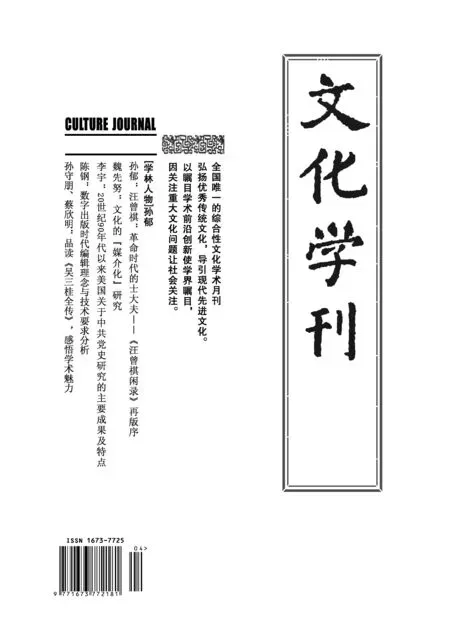基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分析职业流动与性别分层
王瑞祥(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隐含的“男权主义”逻辑共同加剧了女性职业不平等问题,女性的职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职业流动与性别分层一直都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职业流动方面,国内研究文献较多,研究者大多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代际角度探讨影响职业群体流动的因素,较少引入或关注性别变量的影响,但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性别因素的重要性并展开了研究。性别分层领域,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些改变,表现在从原来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考察,到近年来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问题,如职业的性别隔离与男女性收入上的差距。
由此,将职业流动与性别分层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事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职业流动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分层
格伦斯基认为,社会流动可以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被人类活动创造的、修改的任何变化而导致的从一个社会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1]它有两种基本类型: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简言之,水平流动就是在同一社会阶层之间的移动,而垂直流动分为上升和下降两种形式,它所表示的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转换。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目前,关于职业流动的研究已有很多,这里笔者侧重于回顾有关职业流动中性别差异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层研究,对没有或者较少涉及性别因素的职业研究不做过多表述。
张文宏、刘琳于2013年从社会网络角度探讨了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问题。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社会网络能够有效提高男性和女性现职地位获得的可能性,相比于男性,信息和人情资源的使用更有助于女性实现职业流动。[2]吕晓兰、姚先国于2013年使用2008年农民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他们指出,家庭和工作是导致男女性农民工在收入效应上存在差异的关键因素。在工作方面,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工作原因主动流动倾向,但所获得的收入回报不及男性;在家庭方面,女性农民工的后续收入水平因其家庭原因主动流动的影响反而下降。[3]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问题。佟新在2010年对中国特色市场化的经验研究发现,市场化下的女性不仅面临着性别间的分化,也承受着女性内部的分化,市场化使得女性内部的分化愈发复杂。[4]吴愈晓、吴晓刚在2009年研究了城镇中的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职业的性别隔离依然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女性比例越高,平均收入水平越低,但这一情况仅限于体制内,对体制外的收入分配没有影响。[5]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首先可以看到,大多数职业流动研究都试图引入一个或者多个变量,进而通过数据分析其对职业流动的影响程度。其次,关于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分层问题,研究结论大多表明了教育变量对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形成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度,但对于教育是如何导致男女在职业流动中形成性别差异的,现有研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鉴于此,本研究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尝试建立一种分析框架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二、分析视角: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布迪厄的阶级分析工具——资本、惯习与场域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阶级的分析有独特的研究取向。布迪厄认为,阶级指的是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
在这里,布迪厄提出了三个关键概念:资本、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认为,处于社会空间的个体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会对社会资源展开争夺,包括各种符号资源(如信息、关系)和物质资源。他将各种资源看作“资本”,并将之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简单来说,经济资本指个人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指个人依靠社会网络累积起来的资源总和;文化资本是个体所掌握的文化符号,如知识、言行举止和各类证书。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对个人的社会化产生累积性作用,从而提升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根据资本的分类,布迪厄构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范畴,提出了场域概念。刘欣指出,布迪厄所说的场域是一种社会关系构型,它强加在每一进入该场域的个体行动者身上,是权力分配的结构,任何个人欲获得利益,必须进入相应的场域。[6]为了解释不同阶级的人在相应的场域内所产生实践的差异,布迪厄引出了“惯习”这一概念加以论述。布迪厄指出,惯习即一系列社会性建构起来的“性情倾向”,是个体将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内化的产物,表现为个体行动者下意识而持久的思维、知觉和行动,由于阶级处境的差异,因此不同阶级的个体产生的惯习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布迪厄的阶级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阶级的形成及实践提供了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借助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本研究的职业阶级含义与布迪厄的界定一致,即“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职业位置,受到相似职业条件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阶层与阶级概念上的区别,学术界依然未达成共识。有学者,如李春玲、吕鹏认为对于分析社会分层来讲,两者概念的区分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明确阶层或阶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7]
(二)职业结构中的性别分层形成机制
对于这一机制的形成原因,必须将之放于教育场域与职业场域的关系中加以理解。家庭和学校是个体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其中学校作为一种社会体制下的教育机构与个体职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职业发展的限度和方向。表面上看,学校作为一个中立性的教育机构,强调男女之间的机会均等,在必要时采取一些干预手段以保证教育资源在两性之间的合理分配,让学生都认识到职业发展的前景只与个人的努力程度相关,跟性别无关。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一致,在社会空间下,学校作为教育场域的主要实践场所也受到了性别文化的形塑作用。一方面,学校教育有其特殊的运作逻辑,它看似中立实际却依附于权力场域,而这种权力的形成一直受到主流性别文化的熏陶。在中立性的掩饰下,学校教育将隐含的性别文化以符号的形式源源不断地向学生进行灌输,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性别观念,产生接受这一文化的“主文化个体”。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使得性别文化的再生产在个体层面得以延续。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性别文化经由学校教育场域的运作将这种不平等的性别符号施加在女性身上,形成了所谓的“符号暴力”。
另一方面,这种形塑作用也引发了职业场域中的性别分层,导致职业阶级关系结构的再生产。经由学校教育塑造的“主文化个体”,会将性别文化内化为自身的惯习进入职业场域。在惯习的约束下,两性在职业场域中的实践实质上是个体在传统性别秩序及“男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行动的延续,致使在职业场域中形成了性别分层现象。此外,通过学校教育机制的稳定运行,分层体系所包含的阶级结构关系的再生产得到保证(见图1)。
以上分析隐含的前提是个体都能够在学校接受教育。事实上,在入学前,女性就面临着传统文化观念的排斥,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性别观在一定程度上淘汰了不少女性,给男性留下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不仅不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只能在家“相夫教子”,被迫接受对男性的从属地位。尽管目前女性的教育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依旧偏低。

图1 教育场域与职业场域的关系
(三)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分层结果分析
职业结构的性别分层现象带来的最直接结果是女性职业流动的不平等。从横向看,教育场域所塑造的职业结构如规章制度、职场网络及工作环境更有利于男性的职业流动。在现实工作中,用人单位不招女性,处于同一职业等级的女性收入不及男性等性别隔离现象十分突出。从纵向来看,两性的职业流动难易程度不同,相比于男性,女性成功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几率不高。一方面,由于职业结构特征本身的不平等,女性处于相对较低的职业阶级,需要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女性受困于“以家庭为主”的传统观念及市场经济体制隐含的“男权主义”逻辑设置的阻碍,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容易遭受歧视而不得不放弃向上流动的机会,专心为家庭服务。
同时,女性内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中的众多因素如户籍、年龄与性别相互组合,加剧了女性内部的分化,具体表现在女性因所处的体制、职业等级和时代上的差异,发生的性别隔离状况不一致。此外,仇立平、肖日葵于2011年开展的研究表明,父母的文化资本对子女的教育和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父母的文化资本存量越多,子女受教育程度也越高,子女进入更高的职业阶级也相对容易。[8]这告诉我们,除了市场体制本身,家庭的文化资本也是影响女性间分化的重要因素。家庭积累的文化资本越多,处于该家庭的女性越能在职业场域中减少代价,规避风险,更容易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建立“教育—职业”的二元分析框架解释了职业结构中性别分层的形成,并分析了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
综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于理解职业结构中性别差异的形成具有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刘欣认为,布迪厄在论述惯习概念时提到的心智结构的内化过程十分模糊,没有一个清晰的交代[9];朱伟钰指出,布迪厄依然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困扰,他所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缺乏变化[10]。事实上,这些批评都深刻地反映了很多宏观理论的弊端所在。
另外,关于教育究竟是人力资本还是文化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有什么不同,学者们意见不一。林南指出:“被一些人视为人力资本的教育,都可以被另一些人视为文化资本。这不仅仅是对教育的不同感觉,它们代表了理论解释中的基本分歧。”[11]仇立平、肖日葵认为,将教育看作人力资本无法察觉社会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家庭背景、家庭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深层次影响。[12]结合本研究来看,将教育纳入文化资本旨在说明教育对职业结构的塑造是一种社会建构,强调教育发挥着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教育视为文化资本是很必要的。
[1]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二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94.
[2]张文宏,刘琳.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研究——一种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3,(5):53-75,243.
[3]吕晓兰,姚先国.农民工职业流动类型与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分析[J].经济学家,2013,(6):57-68.
[4]佟新.劳动力市场、性别和社会分层[J].妇女研究论丛,2010,(5):12-19.
[5]吴愈晓,吴晓刚.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J].社会学研究,2009,(4):88-111.
[6][9]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观察,2004,(3):44-45.
[7]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M].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7.
[8][12]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1,(6):121-135.
[10]朱伟钰.超越社会决定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J].社会学研究,2006,(3):87-96.
[11]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