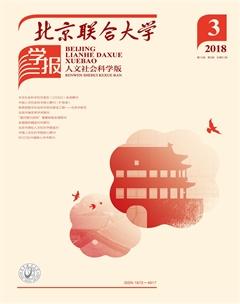大学章程性质的法理透视
陶好飞 徐雷
[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大学章程作为高校的核心法律文件,在“依法治校”中的重要地位开始显现。但对于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学界仍存在争论,由此造成的实施困难,影响了其实效性的发挥。本文评析了学界较流行的“契约说”“自治规则说”“法律说”三种观点,认为应从外延视角、法律位阶视角、特征和价值视角入手,以“大学内部‘宪法和外部‘权利宣言”“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软法”的定位,来综合评价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
[关键词] 大学章程;法律性质;法律位阶;软法
[中图分类号] D922.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8)03-0109-07
大学章程作为“依法治校”的核心法律文件,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支撑。在我国,章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先后将章程明确为高校设立的必要条件。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加强章程建设、完善治理结构”作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目标[1]。2012年《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制定办法》)出台,详细规定了大学章程的内容、制定程序、核准机关等要素,对章程的规范化提出要求。2014年,教育部制订了《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工作规程》(以下简称《核准规程》),要求“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在年底前完成章程起草工作。至2016年,全国本科高校章程已完成起草核准工作,基本形成了“一校一章”的格局[2]。在此之后,进入了以成文章程为依据,推进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健全高校章程实施机制的新时期。但总体来看,学界对章程的效力范围认识不明,对其法律性质的探讨未达成共识。实践中,已出台的章程实效性不高,价值也未得到普遍认同。只有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才能克服众多理论和实践困境,促进章程的有效实施,进而发挥章程规范、指引的最大功用,为现代大学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一、大学章程的内涵及合法性来源
大学章程最早诞生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其源头为教皇或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意在使大学身份合法化,可类比为办学执照或政府批文。[3]经过历史的洗礼,发展到今天,西方的大学章程已分化出多元的称谓,如Charter、Statute、Ordinance、By-law、Constitution、Legislation、Regulation等。实际上,任何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含义均应视文件内容做具体的考察,甚至多个文件组合在一起才表示大学章程,如美国耶鲁大学章程(The Yale Corporation By-laws)中,就包含Charter、Bylaw、Regulation三种表述[4],英国的大学也有Charter、Statutes、Regulation共用的情况。而在我国,大学章程则有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组织大纲”“组织规程”,台湾地区的“组织规程”,香港地区的“大学条例”,大陆地区的“章程”等多种表述形式。
大学章程名称的多元性,是造成目前对其内涵认识含混不清的重要原因。应该说,任何一种称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具体含义应当纳入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脉络中考察。Charter(特许状)出现的历史最为久远,其作用类似于大学的设立文件,由权力机关授予,是大学成为独立法人机构的标识;Statute、Ordinance(章程、条例)则是大学在逐渐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形成的,多是大学自行制订的基础管理制度、规则的集合;而By-law、Constitution、Legislation、Regulation(董事会规则、议事规则)则出现于近代,多侧重于大学权力机构的议事规则,或内部机构运行的规程。实际上,完整意义上的大学章程至少应包含三重内涵,首先是大学获得合法身份的记载或授权,体现章程对大学内部、外部的约束力;其次是大学运行管理的实体规则,保证大学顺利达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功能和使命;最后是大学决策治理的程序性规则,使公私权力混杂的大学,权力运行和责任分配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这样理解,大学章程是对大学所拥有的合法身份、运行管理的实体性规则、决策治理的程序性规则的书面固化。
大学章程之所以合法,首先来自于法律授权。大学章程的演进历程告诉我们,缘法而治是其发挥实效性的重要保证,无论是中世纪的特许状,还是现代大学章程,其效力都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授予,缺乏法律赋权的大学章程无法实现“法治”与“权利”的共生共荣。其次,大学章程的合法性还来自于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核是公民的公共协商,反映为参与者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和集体理性反思。大学章程“既是政府治理工具,又是公共自治规则,涉及多类主体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和保障,具有公共性、契约性、包容性和开放性”[5],因此各利益主体经过博弈和集体决策而达成的共识构成了大学章程的主体部分,这为其发挥效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二、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学界观点述评
大学章程历经千年发展,样态纷繁复杂,客观上增加了把握其法律性质的难度,观点上的论争在所难免。目前学界对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契约说
持该说的学者认为,大学章程是学校办学各方以各自意思表示为基础,共同协商后达成的关于权利义务的合意。但因所借鉴理论及对契约主体认识的不同,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民事契约说”,认为大学章程是大学内部制定的,是内部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议,“具有民事契约的性质”[6];另一种观点是“行政契约说”。该说认为大学章程是举办者(政府、社会)和办学者(大学、大学成员)共同制订的契约,尤其对于公立大学的章程,是“政府与公办高校签署的一份行政契约,通过契约明确政府与公办高校的权力和职责”[7]。
本文认为,大学章程虽有合意性,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契约。首先,“民事契约说”缩小了大学章程的内涵,违反了缔约主体平等原则。该说把大学章程的制定范围仅限制在大学内部组织成员,忽略了除大学及其成员以外,还有作为举办者的政府,作為利益相关方的投资者、校友等,都是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此外,民事契约以缔约主体地位平等为原则,而在章程制订过程中,政府享有对章程的核准权,处于明显的行政优益地位,显然与民事契约的平等原则相悖。其次,“行政契约说”并不适合中国的现状。行政契约的概念,目前只在理论上获得认可,在立法上尚不明确。姜明安教授将其定义为“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一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8]。从普通法国家的行政法著述看,政府合同(行政契约)一般与商业有关[9]。在大陆法系国家,区分行政契约的意义在于将管辖权置于专门的行政法院,从而排除普通法院管辖。而大学章程的内容与商业性质的行政契约具有较大差异,我国也没有类似德国、法国那样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设置。此外,在成立要件上,行政契约是行政主体的主动性行为。而大学章程是大学设立的必要法律文件,以高校提出申请为前提,“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大学章程的审核,实际上属于行政法上的行政许可行为”[10],是依申请而为的被动行为。章程并非高校与行政机关达成的行政契约。
当现代大学由单纯的学术共同体向复合型的公共组织转化,并在公私两个法域发挥作用时,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也随之表现出复杂的样态,现从如下三个不同角度切入进行探讨。
(一)从外延角度考察,章程是大学内部“宪法”和外部“权利宣言”
章程是大学法人成立及具有独立人格的基石,是学术自治的基础,是隔离行政干预和办学自主权的“防线”。在制订阶段,章程主要体现出协商性。制订章程是校内外利益主体达成合意、相互博弈的过程。章程权威性的重要来源是多方合意,立约各方必须具有相应的发言权,合意内容必须体现各方的诉求,并得到对方的认可。各方合意达成了,章程的权威也就树立了。在实施阶段,章程则具有了强制性,约束效力开始显现。即使参与各方在达成合意时地位并不平衡,但在章程核准生效后,其效力所及的范围是平等的,所有利益主体及其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均平等受到章程的约束,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均按照章程所厘定的边界确定。
此时,在大学内部,章程是不折不扣的“宪法”,居于“最高法”和“纲领法”的地位。它不仅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原则的内部法源,还体现了大学内部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是大学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关于大学价值和利益的分配契约。[16]校内任何规章制度都必须以章程为直接依据。师生员工的行为,都应以章程作为指导准则。另外,章程还有一个重要功用是填补法律漏洞,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章程的预先规定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违反章程的行为,如果没有同时违反国家的法律,可以由大学自行解决。
就外部关系而言,章程是大学立校治学的“权利宣言”。“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边线的地方才休止”[17],章程是划分大学与外部势力,尤其是与政府行政权力边界的界碑,它对外宣示大学的权利和义务,力求达成大学与外部的平衡,保证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这要求政府放权,允许不违反法律和政策、适合学校实际、较为具体化的条款载入章程,彰显大学的办学特色;还要求大学敢言,在遇到行政权力非法干涉时,敢于拿起章程,宣示办学自主权,对行政权力说不,使政府的归政府,大学的归大学。
(二)从法律位阶角度考察,大学章程属“行政规范性文件”
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大学章程是类似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但并未明确该文件的性质,介绍时多使用“自治性规章”等模糊性字眼一笔带过。究竟大学章程是法律、法规、规章抑或是一般规则?本文认为,大学章程应定位为“行政规范性文件”。
首先,大学章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法。有学者根据《制定办法》第23条《制定办法》第23条规定,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的章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其中本科以上高等学校的章程核准后,应当报教育部备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的章程由教育部核准;其他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章程,经主管部门同意,报教育部核准。,以及教育部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的“信息类别”属性为“部门规章”[18],认为大学章程是教育部的部门规章,具有强制行政法律效力,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大学章程的核准、审查、公布环节,确实与部门规章有类似之处,如均由部务会议决定,由行政机关发文公布等。但二者的区别也显而易见:大学章程制定的主导权在大学,而部门规章制定的主导权在相关行政部门;部门规章通常以“部令”形式呈现,在部门公报或者国务院公报和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有关报纸刊登,并报国务院备案,大学章程显然难以满足上述条件。此外,除教育部直属高校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举办的高校,其章程由省教育厅核准。教育厅发布的核准书自然达不到地方政府规章标准。若非要把教育部核准的章程认定为部门规章,会陷入同样是高校,只因所属部门不同,章程的法律效力存在高低之分的窘境。
其次,大学章程是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教育部《核准规程》第10条规定,“经高校确认的章程文本,由部长签发《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予以发布”。教育部公布的章程核准书中,也载明“核准书所附章程为最终文本,自即日起生效”。除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外,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如湖北省教育厅的《湖北省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工作规程》中,也规定“经高校确认的章程文本,由廳长签发《湖北省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予以发布”。这均是对我国大学章程行政规范性文件性质的确认。
大学章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位,并非对“去行政化”要求的背离。过去大学章程被束之高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无法摆脱校内文件的身份,法律位阶过低,治校作用没有显现。尤其是在行政权一家独大的今天,外界往往忽略大学章程的独立性,将其等同于一般校内规则。如果不从价值定位、核准公布程序上进行“拔高”,仍采取以往大学制定、自行公布、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形式,难以提高公众对章程权威性的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虽不是行政立法,但显然比普通校内规定规格更高,规范性更强,约束范围更大,尤其是由国家和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公布,扩大了关注和知情范围,突出地向外界公示了大学和政府间的合意,划分了二者的权责边界,使政府或其他机构对学校的过度行政干预丧失了法理基础。这有利于确立章程的权威性,确保“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去行政化”原则,在既定规则的约束下,真正得以贯彻实施。
(三)从特征和价值的角度考察,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应定位于“软法”
“软法”这一术语最早来源于国际法。1994 年西方学者弗朗西斯施尼德(Francis Snyder)为软法的概念作了一个被认为较为准确精练,从而也被大量引用的界定,即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19]。在我国,软法通常被定义为“在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主要是由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方式形成的、并以柔性的或者非正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功能和作用的法律体系”[20]。学者们认为,软法的特征在于,第一,软法规则的形成主体具有多样性。既可能是国家机关,也可能是社会自治组织或混合组织等,当然,后两者形成的规则需要得到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国家认可;……第三,软法一般不规定罚则,软法通常不具有像硬法那样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更多的是依靠自律和激励性的规定;第四,软法通常不具有国家强制约束力,而是依靠制度、舆论导向、伦理道德、文化等软约束力来发挥作用[21]。
大学章程的法律特征与软法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首先,从制定主体看,大学章程由政府、大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商制定,符合软法的主体多样性特征。而且大学章程的制定由大学主导,不同于由立法或行政机关主导制定的“硬法”;其次,從制定过程来看,章程制定各方以对话、协商、开放为特征,较多运用脱离强制命令色彩的软性协商手段;再次,从内容来看,大学章程一般不规定具体的罚则。与宪法类似,章程作为一校运行的根本大法,更多的是对学校及相关治理主体权利义务的事实性叙述,带有确认性和鼓励性,并非重在体现制裁性和惩罚性。因此,章程中鲜见惩罚性条款,而多见宣示性的“学校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等表述。最后,从效力来看,大学章程的约束力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强制性特点,而更多地表现出基于大学精神而产生的认可性约束力。[22]对内,如果大学成员违反了基本权利义务,学校可以根据章程规定,适用校内规章制度中的相应罚则进行处理,但该约束力的直接来源是大学的自治传统和特别权力关系,而非国家强制。对外,如果行政机关违反了章程义务,大学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章程的作用是提供二者权利义务划分的依据,但约束力来源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而非直接源于大学章程本身。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大学章程与软法的主要特征高度一致,可以说,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就是软法。
软法的兴起,源自现代公共治理发展的推动。同样,我国大学章程的梳理和重构,也是在公共治理理念推动下,摆脱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其价值诉求在于规范大学内部运行与管理,协调大学内外部关系。明确大学章程的软法性质,有利于理顺大学内部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推动各种力量通过有效互动,生成一种创造性的“自发秩序”,以构筑开放、民主的自治性治理结构,推动大学管理模式的转变,实现章程规范大学内部运行与管理的程序的价值诉求。此外,大学章程作为软法,有利于实现大学外部权力的合理分配,是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硬法的有益补充和导引。其补充作用体现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只能就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的、重大的问题做出规定,不可能顾及每一所大学的特殊性,这就为大学章程的软法规则留出了发挥空间。大学可以在章程中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可行的治理方案,充分体现办学特色,并由硬法提供法律保障,以类似于“司法解释”的形式,增强硬法的可操作性。其导引作用体现在,大学章程因其开放、灵活的特点,对相对僵化的硬法具有导引和推动作用,促进其不断完善和全面,使硬法的制度安排更重视衔接与呼应,更贴近实践,更注重实效。
最后,还应该看到,深化大学治理改革,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硬法和软法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既要重视大学章程的重构和实施,克服“软法偏软”的弊端,更要注意总结和归纳,把先进经验写入法律,解决“硬法不硬”的问题。应借助大学章程实施的契机,把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提上议事日程,进一步明确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明确教育行政机关和大学的关系,明确违反章程时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大学章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加快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王维坤、张德祥:《我国民办高校章程文本表达现状研究——基于105所民办本科高校章程的文本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7期。
[2] 孙霄兵:《推进大学章程实施 提高高校治理水平》,《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19期。
[3] 刘冬梅:《章程视域下的大学治理法治化》,《教师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
[4] 张冉:《美国大学章程的类型化分析及其对我国高校章程制定的启示》,《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9辑,第278—293页。
[5] 董柏林:《协商民主视阈中的大学章程合法性建构——基于大学章程制定与实施的理性反思》,《高教探索》2017年第4期。
[6] 杨德齐:《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之困及其解决——基于与公司章程之比较》,《学术交流》2012年第4期。
[7] 周光礼:《从管理到治理:大学章程再定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8]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349页。
[9] 余凌云:《论行政契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
[10] 陈学敏:《关于大学章程的法律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1] 米俊魁:《大学章程法律性质探析》,《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1期。
[12] 刘文杰、吴跃文:《论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教育探索》2013年第8期。
[13] 杨向卫:《大学章程:软法还是硬法》,《陕西教育(高教)》2014年第3期。
[14] 米俊魁:《大学章程法律性质探析》,《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1期。
[15] 湛中乐、徐靖:《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
[16] 罗泽意、何蓉:《大学章程制定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讨》,《高校教育管理》2016年第3期。
[1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页。
[18] 教育部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45号(西北工业大学)》,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144/201412/182092.html。
[19] 黄学贤、黄睿嘉:《软法研究:现状、问题、趋势》,《公法研究》2012年第1期。
[20] 梁剑兵:《“软法律”论纲——对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一种界分》,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6558。
[21] 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2期。
[22] 王韦丹、史万兵:《大学章程与治理法治化重考——基于软法的视角》,《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statute, as the core legal document of universities,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ule of law. But for the legal nature of university statute, there are still argumen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resulting in the difficulties of application,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views of “contract theory,” “rule of autonomy” and “legal theory,” which are popular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university statute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the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document” and the “soft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tensi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gal hierarchy,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alue.
Key words: university statute; legal nature; legal hierarchy; soft law
(責任编辑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