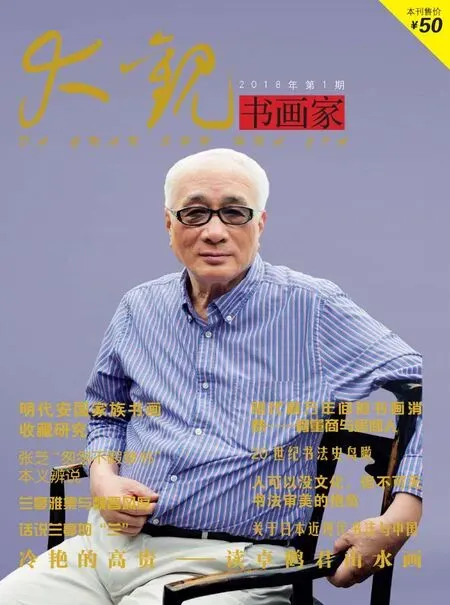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 灏
转型时代的前瞻意识是一个双层建构。
价值取向危机
所谓文化取向危机,首先是指基本的道德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动摇。大约而言,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可分两面: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与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这两面在1895年以后都受到极大的冲击,造成二者核心的动摇,甚至解体。
精神取向危机
任何一个文化,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多是自成一个意义世界(universe of meaning)。这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一些基本价值与宇宙观的组合。这组合对人生与人生的大环境——宇宙,都有一番构想与定义,诸如宇宙的来源与构造、生命的来源与构造,以及在这一环境中生命的基本取向与意义。这组合我们称之为意义架构。前节指出,传统儒家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在转型时代受到严重挑战,这代表传统意义架构的动摇,使中国人重新面临一些传统文化中已经有所安顿的生命和宇宙的基本意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由之产生的普遍的困惑与焦虑,就是我所谓的精神取向危机。
这一精神层面的危机是转型时代思想演变中比较不为人注意的一面。但是当时许多重要的发展都有它的痕迹。转型时代初期,知识分子很盛行研究佛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发展我们不能完全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去看,它不仅是对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的回应,它也是传统意义架构动摇以后,人们必需对生命重建意义架构所作的精神努力。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这些人之走向佛学,都与这种取向危机所产生的精神挣扎有关系。五四时代人生问题引起激烈讨论,胡适提出“人化的宗教”,周作人提出“新宗教”,这些思想的发展也应从精神取向危机这个角度去看。
文化认同危机
中国人自从19世纪初叶与西方接触以来就发现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与从前中国自认为是“天朝”或华夏中国的世界很不同的新天地。因此中国人在认知上很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一种对这新世界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借此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新的世界伫,相对于世界其他文化与国家作文化自我定位。因此中国人在这方面作的思想挣扎与摸索一部分是发自于一种文化自我认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认同感里面强烈的情绪成分或心理深层需要。前面我指出转型时代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发生动摇,而就在同时,中国进入一个以新的西方霸权为主的国际社会。顿时由一个世界中心的地位降为文化边缘与落后的国度,自然产生文化失重感,群体的自信与自尊难免大受损伤。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霸权不仅是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的。就因为如此,这霸权不仅是外在的而且也已深入中国人的意识与心理深处,而内化为一种强烈的情意结。一方面他们恨西方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深知与帝国主义同源的西学也是生存在现代世界的需要,是“现代化”的要求,是一种现实理性的驱使。这自然造成中国人内心思想的困境与心理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这也是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于50年代提出的问题。列文森也许夸大了这情意结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中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是转型时代出现的认同危机的一个基本环节。
文化认同的需要在转型时代普遍的散布,不论是出自中国人情绪的扭曲或发自文化自我定位的认知需要,都是当时取向危机的重要一面,不可忽视。但是在讨论文化认同取向时,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这一问题,因为就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文化认同取向方面所作的挣扎与他们在价值取向以及精神取向方面的困惑与焦虑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只有把这三方面作综合的分析,才能看到当时取向危机的全貌。
(二)新的思想论域
前文提及,转型时代制度性的传播媒介促成了公共舆论的产生,这种舆论内容极为驳杂,各种问题都在讨论之列。但就在这纷繁驳杂的讨论里,逐渐浮现一个思想论域。称之为思想论域,是因为这些讨论有两个共同点:(1)使用新的语言;(2)讨论常常是环绕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例如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形式,革命与改革的途径,新时代的人格典型,等等。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随之而来的讨论,常常都是从一个共同的主体意识出发。
谈到转型时代报刊杂志所使用的新语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词汇。这些词汇主要来自西学的输入。它们有的是由西文直接翻译过来,但很重要的部分是转借日文的翻译,因此日文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蔡元培手札
但是新的语言不仅表现于新的词汇,也表现于新的文体,这方面的主要变化当然是由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虽然这两种文体不无文法上的差异,但最重要的分别还是在整个文章结构和语句的形式。就文章的整体结构而言,文言文是受一些传统修辞上的限制,例如起、承、转、合的规律以及所谓的抑扬顿挫法、波澜擒纵法、双关法、单提法等等。至于个别的语言形式,首先我们必需认识,文言文是一种非常简化的语言,有时简化到像电报的语言,因此语意时常是很不清楚的。同时,文言文的语句结构又受到其他一些修辞上的限制,例如用典、语句的长短整齐必需合乎所谓典雅的形式,而白话文则不受这些文言文的形式与规律的束缚,因此能比较自由地表达个人的论理或抒情的需要。

熊十力手札
不可忘记的是:在转型时代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虽然那时代的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黄遵宪、刘师培等人已经尝试用白话文,白话文真正普及是1917年文学革命以后的事。在此以前,报刊杂志使用的仍然是文言文,但常常是一种新体文言文。这种文体可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为代表,就是所谓的“新民体”。梁启超后来对他当时的文章有过这样的评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夹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当时使用新文体的还有林纾,他翻译西方小说时所采用的文体,虽是文言文,但并不严格地沿用桐城派古文文体。钱锺书说:“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辞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所谓收容量很宽大,就辞汇而言,是指它采取不少白话与新名词,就语法而言,是指它带有了许多欧化成分.因此,所谓新文体是一种解放的文言文,也可说是一种比较接近白话文的文体。
总之,转型时代的新思想的散播是与新文体(不论是白话文或新体文言文)的出现分不开的,正如同中古时期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无法与白话文翻译佛教经典分不开的。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两次受外来影响而形成的思想巨变都是以新语言为背景。新语言的出现固然重要,但不能代表思想论域的全面。我不同意时下一些学者认为思想可以完全化约到语言层次。我认为,要了解一个思想论域,我们必需同时考虑使用新语言的人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转型时代知识份子的主体意识。
当时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最重要一面,当然是笼罩那个时代的危机意识。要认识这种危机意识,我们首先需要把它摆在它产生的环境脉络中去看。所谓环境脉络,不仅是指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危机,也是指当时的思想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同时需要把这危机意识放在传统思想与“西学”交互影响的脉络去看。只有把当时知识分子对这两种环境——政治社会环境与思想环境的回应合而观之,我们才能透视这危机意识的特徵。
根据上面的观点,当时的危机意识的最大特征,毫无疑问是它特殊的三段结构:1.对现实日益沉重的沉沦感与疏离感;2.强烈的前瞻意识,投射一个理想的未来;3.关心从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应采何种途径。现在就这三段结构作进一步的说明。
对现实的沉沦感与疏离感。当时在转型时代散布的不只是对国家社会迫切的危亡感与沉沦感,而且是激进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与疏离感。在转型时代以前,激进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只有零星孤立地出现。那时的主流思想仍然希望在传统的思想与制度的基本架构内对西方文化作适度的调节,这就是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的论点。1895年以后,文化自我批判意识由“用”进入“体”的层次,由文化边缘深入核心,认为当前国家社会的危难反映了文化核心部分或整体的腐烂。这种激进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与疏离感在转型时期日益深化与扩散,常常与政治的危亡感互为表里。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这是一种强烈的前瞻意识,视历史向着一个光明的远景作直线的发展。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称这种前瞻意识为“未来之梦”,它首先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生活在帝国主义压迫的阴影下,自然热望变作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透过新的传播媒介在转型时代作空前大规模的散布。因此,由甲午到五四,民族国家观念是对未来理想社会展望的一个核心成分,但它却不是唯一的成分。因为,除此之外尚有另一个重要成分,那就是以大同理想为代表的各种乌托邦主义。现代史家常常不正视这种思想,但是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与心态而言,乌托邦主义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因为它曾出现在转型时代的每一个主要阶段或思潮。就以转型时代初年的维新改革派而论,一方面有梁启超鼓吹民族主义的文字,另一方面也有康有为的《大同书》与谭嗣同的《仁学》散布乌托邦主义。就辛亥以前的革命派而言,一方面有邹容与陈天华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不仅在孙中山的思想伫已经浮现,它在革命派左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伫尤为突出,当时这一派报纸如《新世纪》《天义报》与《衡报》都充满了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的思想。
五四时代的思想也复如此。谈到五四思想,现代史家多半强调五四时代的民族主义。其实,当时世界主义的盛行决不下于民族主义。文学家朱自清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正是北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思想气氛时,曾经提醒大家五四运动的思想常常超过民族主义,而有浓厚的世界主义气氛。这种气氛我们可以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这篇文章中所强调的一段话为代表:“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庭、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五四时代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思想就是从这种世界主义的信仰兹生出来。
因此,转型时代的前瞻意识,大致而言,是一双层建构。当时知识分子所瞩望的常常不仅是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由现实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当时人对现状的失望与反感以及对未来的热望,使他们非常关心如何由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转型时代持续不断对改革与革命的激烈辩论,最能反映这途径问题在当时思想界的重要性。当时其他一些被热烈讨论的课题,例如中西文化的关系、主义与问题的比重、民主与自由的意义也都与这途径问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途径问题可以说是危机意识的三段结构的凝聚点。

俞平伯手札
更进一步去分析,这三段结构反映一个历史理想主义的心态。大约说来,这心态有下列的特下:1.这理想主义态是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中的理想主义的合产物。它一方面认为理想与现实有极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相信这差距可以克服,透过现实的转化,可以使现实与理想合而为一;2.这个世界观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因为它是建筑在一个新的历史观上。这个新的历史观主要是由西学带来的演进史观,把历史看作是朝著一个终极目的作直线的演进;3.同时这理想主义涵有一种高度的政治积极性,一种强烈的政治行动倾向。我们可称之为以政治为本位的淑世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来自传统儒家的经世思想,认为知识份子应该有一份顾炎武所谓的“救世”情怀,投身政治,以改造污浊沉沦的世界。这是一种充满政治积极性的使命感,表现于我们大家常常听见的一些话题,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等等。重要的是这种政治积极性与使命感隐含了一个对人的主观意识与精神的信念,认为人的思想与意志是改造外在世界的动力。因此反映一种高度的人本意识;4.这种人本意识与方才提到的演进史观结合,使得演进史观在中国往往含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与西方的历史演进观很不同,因为在西方这种历史观常常带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意识,相信历史发展的行程有其本身的动力,因此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与行为而向前发展。这种史观对于人的自动自发的意志与意识是一种限制与压抑,甚至否定。但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对演化史观的了解却与西方很不同。一方面他们接受历史向前直线发展的观念,因而常常有很强烈的历史潮流感;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认为这历史潮流会排斥人的自动自发的意识与意志。相反地,他们常常认为历史潮流只有透过由人的意识产生的精神动力才能向前推进,这或许是受传统天人合一宇宙观不自觉的影响。因为后者相信,天的意志只有透过人心才能显现。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历史潮流代替天意,同时保留了传统对心的信念,其结果是一种近乎主观意识决定论的观念。我们可称之为意识本位的历史发展论;5.理想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演进观结合,使人觉得这世界观所展现的价值与理想不只是人的主观意识的投射而且是植基于宇宙的演化与历史潮流的推进。因此传统思想模式中的应然与实然的结合,宇宙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得以在转型时代以一个新的形式延续。上述五点,简略地说明了转型时代的危机意识所隐含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加上前面提到的新语言,构成一个新的思想论域,在当时逐渐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