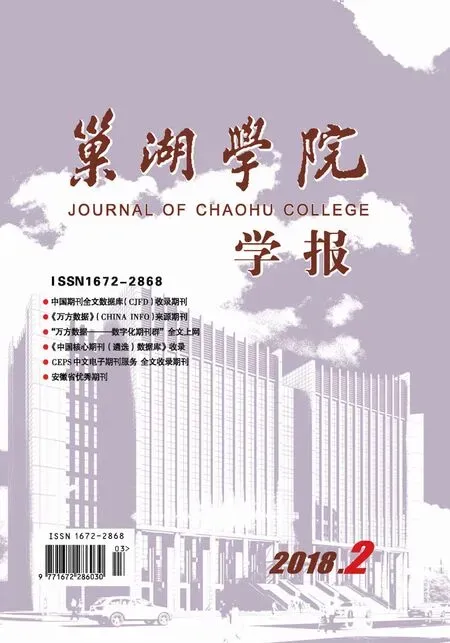从(嘉庆)《无为州志》看无为地区人口及赋税变化
任晓雯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无为县今属于安徽省芜湖市,地处于安徽省中南部,南临长江,北依巢湖,气候温和湿润,境内多平原、丘陵,自古为鱼米之乡。隋开皇元年设置无为镇,这是无为地区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建制,元至元二十八年始设无为州,隶属庐州府,明清沿袭,基本未变,直至民国元年取消无为州,改设无为县。关于无为地区的地方志最早于宋代纂修,然而大多亡佚,明清二代为无为地区编写志书的也大有人在,但“相比之下,《无为州志》是现存无为旧志中内容最为详实、编纂体例最为严谨、最具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的一部志书。”[1]
这部志书由当时知州会稽人顾浩、抚顺人宁贵承修,司主事吴元庆编纂,再集合当时学正、学训、贡生、举人、廪生、增生、附生、监生等一批饱学之士四十余人,历时一年编纂而成,嘉庆八年刊行。全书共三十六卷,外加卷首一卷,记载了清无为州的地理沿革、人物、职官、武备等内容,其中卷七、卷八为《食货志》,分别记述无为州的户口、民赋、芦课、卫赋(屯丁)、盐法、仓储、蠲赈、优恤、物产等内容,对研究清前中期无为州的经济状况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根据(嘉庆)《无为州志》中所统计的户口赋税等数字,再加上其他地方志材料,对清前中期无为州官方统计的人口及赋税进比较分析。
1 无为州人口变化
1.1 人口数字变化及原因
(嘉庆)《无为州志》卷七《食货志》的第一部分《户口》就对自清初到嘉庆初年无为州可考的人丁和户口数做了详细记录,详见下表:

表1
顺治五年至康熙十二年的户口人丁数字是据颜尧揆修、杨交泰纂的 (康熙)《无为州志》而来,详细记录了户数和人丁数,未记载增长人丁数,表格中关于康熙元年至十二年的增长人丁数为笔者计算而得。自康熙十六年开始,所记载的数据资料是根据常廷璧修、吴元桂纂的 (乾隆)《无为州志》而来,“只书审丁,不纪编户”[2],而且只有增长人丁数,这在人口数字的统计中容易产生错误。所以自康熙十六年开始,只有增长人丁数,实丁口数为笔者计算而得。这里先分析一下(嘉庆)《无为州志》中记录的数据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根据上表可知,到康熙五十年,无为州人丁数为53426丁,但据《无为州志》记载,顺治五年的丁口数为46474丁,逃亡丁口数为13014丁,实际人丁33460丁,每丁征银一钱,共4647.4两,逃亡人丁的丁银平摊到原额田地内兼征,也就是说即便现无为州内只有33460丁口,也要承担46474人丁的丁税。而“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五十年,节次编审人丁,增徭银二千一百七十八两九钱,除抵补缺额扣除田赋外,计溢额人丁八千七百七十五丁,增徭银八百七十七两五钱。”[2]丁银在顺治五年所征徭银4647.4两的基础上增加877.5两,共5524.9两,每丁征一钱,所以到康熙五十年,无为州应共有人丁数55249人,比表格中所统计的53426人丁数多1823人。又康熙五十一年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以后征收丁银皆以康熙五十年人丁数为准,即55249丁,优免乡绅进士举贡生监丁银共249丁,即每年征收丁银人丁数55000人,征收丁银5500两,外加每钱耗银一分,除正银5500两外再加耗银550两,共6050两。从这里来看,人丁数目的统计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征收丁银的数目来推断的,至少(嘉庆)《无为州志》得出康熙五十年无为州的人丁数目是55249这个结论便是根据征收丁银数量推断而来。
第二,这里所说的人丁数应该指的是纳税单位,不仅仅指成年男性。尽管,按《清史稿》所记载:“凡民,男曰丁,女曰口,男十六为成丁,未成丁亦曰口,丁口系于户。凡腹民计以丁口,边民计以户,盖番、回、黎、苗、瑶、夷人等,久经向化,皆按丁口编入民数。”[3]根据《清史稿》的这段话,十六岁以上的成年男性才叫作“丁”,而女性和未成年男性皆为“口”,“丁口”即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人口总额。而(嘉庆)《无为州志》中统计人口数字用的都是“丁”,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表示的是十六岁以上成年男性,可是根据几组记录了户数与丁数的数字来看,这里的“丁”不可能仅仅表示成年男丁。顺治十四年,户数为6937户,丁口为35285丁,平均每户5.087丁;康熙元年,7352户,38420丁,平均每户5.226丁;康熙六年,7615户,42433丁,平均每户5.572丁;康熙十二年,9236户,42270丁,平均每户4.577丁;嘉庆六年,共计137617户,723200丁,平均每户5.255丁。通过这五组数据,可以看出自顺治至嘉庆不论人口与户数如何变化,一户都大约有五丁左右,而这五丁若都是十六岁以上成年男性,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至嘉庆六年,摊丁入亩政策已经行使多年,丁税全面取消,仅仅统计丁数已经没有了税收上的意义,又因,自乾隆六年起,统计制度基本定为统计口数,即含大小妇男在内的全部人口数,到嘉庆六年无为州也应该实行了这种统计方法,但(嘉庆)《无为州志》中仍记载:“嘉庆六年,本州现册计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一十七户,共七十二万三千一百丁”[2],仍用丁表示。以上可证,(嘉庆)《无为州志》中关于“丁”的含义已不同于《清史稿》中的表达,至少到嘉庆年间,它已代表总人口数,在此之前,应该表示纳税单位,而在清朝,不仅仅是十六至六十岁的成年男性需要纳税,也就是说(嘉庆)《无为州志》所统计的丁数不仅仅是成年男性丁额。
第三,根据(嘉庆)《无为州志》所记载的人口数据,可知顺治初年,由于战乱等原因,人口死伤逃亡数达到原数额的四分之一。此后人口数开始稳步增长,至康熙二十一年为48091丁,已超过原额的46474丁。在康熙十二年,无为州人口数减少了163丁,对比前后几年人口数千的增长,这个数字有些奇怪。无为州在清朝隶属于庐州府,庐州府下辖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巢县以及无为州,查阅(嘉庆)《庐州府志》卷二十户口部分,将整个庐州府历年人口增长数与无为州相对比,列表如下:

表2
由表2可知,康熙十一年,整个庐州府在康熙十一年人口增长数为6290丁,而之前的康熙六年庐州府增长12213丁,之后的康熙十六年增长11133丁,相较之下,整个庐州府在康熙十一年增长人数皆不多。根据(嘉庆)《无为州志》卷三十四《集览志一:禨祥》记载,在康熙六年到十二年间,无为州多自然灾害:“七年戊申六月十七日地震有声,景福寺塔顶坠,民间庐舍倾倒甚众;九年庚戍大水圩田尽没;十年辛亥旱;十一年壬子春大饥秋有获”[2]。康熙十二年人口增长数为负值应与这几年自然灾害频发有关。
第四,由上表也可看出,自康熙三十年后,不论是庐州府还是其下辖的无为州,人口的增长速度皆放缓,无为州的人口增长数从每五年数千人跌至几百人,庐州府则由原先的每五年增长数万人跌至两三千人,两组数据在各年份基本能达到一一对应。那么在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五十年,为什么无为州乃至整个庐州府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慢呢?也许是因为在清初由于战争造成过多伤亡,以及大量难民逃亡,人丁锐减,无法统计,经过顺治以及康熙三十年间的休养生息,百姓渐渐回归故土,登籍造册,康熙三十年后所增加的人口基本为正常出生人口,便远远不及前几十年的人口增长规模了。但不论如何,康熙三十年后所记载的增长人丁数极为不准确,特别是乾隆年间的增长人口数,乾隆三十一年增长26丁,乾隆三十六年查增长23丁,更为不可能,因为“钦遵康熙五十二年恩诏,以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2],在乾隆年间,人口应该大量增长才符合实际,绝不会每五年只增长二十余人,且康熙以后的人口具体数字过于缺乏,难以说明问题。
查阅(嘉庆)《庐州府志》关于无为州人口数据,雍正以前记载:“无为州,原额人丁四万六千四百七十四丁,顺治五年审除一万三千一百四丁,节年审增二万一千九百六十四丁,实在人丁五万五千四百二十四丁,内优免人丁二百四十九,当差人丁五万五千丁,每丁科银一钱,滋生人丁一百七十五丁。”[4]其中顺治五年审除“一万三千一百四丁”应是作者抄误,当是一万三千一十四丁,与(嘉庆)《无为州志》中所记载逃亡丁口数13014相符合,也才能得出当差人丁五万五千丁,据此也能推断 “实在人丁五万五千四百二十四丁”的数字是根据所纳丁银推算而来。查阅《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关于无为州人口数据,记录与此数据一字不差,可见光绪年间续修的《庐州府志》人口数字也是来源于(嘉庆)《庐州府志》。雍正及以后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3
上表是根据(嘉庆)《庐州府志》关于无为州的人口数据(此数据与《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完全一致),另外摘录了关于庐江县的人口数据,因为在清代,庐江县与无为州同属于庐州府,且庐江县与无为州地理位置相临,人丁原额相近,另查钱荣所修的(光绪)《庐江县志》,卷三户口部分所录入的人丁数与(嘉庆)《庐州府志》所记载的庐江县人丁数完全一致,除了乾隆四十一年,(光绪)《庐江县志》记为15518丁。这里以(嘉庆)《庐州府志》为准,因为只有以65518丁为准,距嘉庆六年实在人丁323483丁才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嘉庆)《庐州府志》记载的关于无为州的人口数据相对而言较为准确。由上表可看出,无为州在雍正年间的人丁增长数额极小,庐江县在雍正年间的数额增长也相当有限,查原文:“雍正四年,合肥县增人丁二十一丁,舒城县增人丁一百六十六丁,庐江县增人丁七百八十三丁,无为州增人丁二十六丁,巢县原额人丁二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丁,无滋生;九年合肥县增人丁二十四丁,舒城县增人丁一百七十三丁,庐江县增人丁九百五十六丁,无为州增人丁二十丁,巢县原额,并无滋生。”[4]庐州府下辖的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无为州、巢县在雍正年间的人口增长数额都较小,可见无为州在雍正年间官方的人口统计结果上并无太多增长,而在乾隆六年记录实在人丁达454102丁,康熙五十五年官方给的数字结果是55249丁,二十五年间多出了接近四十万人,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大约为87.91‰,这个数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二十五年中,除了雍正十三年没有任何人口数字统计外,其他年份都大致按照五年一次记录了人口增长额,但将这些年人数增长额相累加,远远达不到乾隆六年高达四十五万的人丁数,那么在这二十五年间官方的统计数字上为何存在这么大的差异?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乾隆五年十二月,“令各督抚于每岁仲冬,除去流寓人等及番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总数与谷数一并造报”[5],于是,自此,人口统计不再按丁计算,即不仅仅指纳税单位,基本指代了除去流动人口外的总人口数,统计面远远扩大,而且乾隆六年的户口统计工作应该比前二十五年要细致得多,无为州的实在人丁达到四十五万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庐州府下辖的五个州县在这年都没有记录增长人口,只誊抄了实在人口,应该是由于增长人口过于庞大,不便记录的缘故。
再由表三可看出,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激增,无为州增长了十六万余人,庐江县也增长了六万余人,再看庐州其他县:“四十一年合肥县增人丁二十一万一千六百七丁,舒城县增人丁五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丁……巢县增人丁一十八万九千九百五十七丁。”[4]可见乾隆四十一年,不仅仅是无为州,庐州府各辖区人口皆高速增长。康熙皇帝下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人丁不再成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于是乾隆三十七年废除了人丁编审制度,《无为州志》中记载:“三十七年奉文永停编审,每五年仍以户口报部,自是之后,节次造册详报。”[2]人丁编审原是为了征税便利,现在不需要凭借人丁数额进行征税,田亩早已成为了唯一的征税标准:“雍正六年,丁随田办,多则丁增,少则丁减,尽则户不存,无当丁之累,益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咸,乐生户口所以日蕃欤。”[2]不用再交丁税,人口日益增长,但又取消了人丁编审制度,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迫切希望知道具体的人口数字,“借以验海宇富庶丰盈”[6],于是乾隆四十年十月下令,令原先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的保甲制度来进行具体的人口数字统计:“现今直省查保甲所在户口人数,倶稽考成编……朕以时批阅,既可悉亿兆之概,而直省编查保甲之尽心与否即与此可察看。”[5]乾隆皇帝如此严厉地令各省督令保甲查核具体人口数字,各地官员不敢怠慢,尽心竭力地查核具体的人口数字,这便使得乾隆四十一年无为州以及庐州府人口统计数值大为增长,乾隆四十一年统计的人口数量结果也较以往各年统计结果更加精确,除部分经商的流动人口外加一定的不可避免的隐漏人口外,这个数字大致能够覆盖当时无为州的全部人口数,以后历年的人口增长数额应当可以视为是无为州的人口自然增殖数。
1.2 人口数字变化分析
从以上三幅表格以及分析可以看出,在顺治康熙年间官方统计的无为州人口数字由于征收人丁税的需求,所能代表的只能是纳税单位,虽然它不仅仅如字面意思上只表示16—60岁的成年男丁,但也远远不到当时无为州的全部人口数。并且这个数字由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统计条件的落后、人口隐漏严重等原因,离实际纳税人丁都有一定差距。甚至由于统计人丁数过于繁琐,官员一般会根据所征收的丁银来推测具体人丁数,这在无为州康熙五十年所统计的人丁数字中可明显体现。虽然我们不能够根据顺治康熙年间统计的人口来推断当时无为州的总人口,但自明末至康熙年间,这些数字的性质一致,即都是纳税单位,所以可以将这些数字归纳在一起,对当时无为州的人口数做一个定性分析。自明末的四万六千余丁,到清初统计逃亡一万余,只剩下三万多丁,统治者采取各项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及战乱结束,天下太平,流亡人口纷纷返乡,到康熙十六年基本恢复到明末的人口规模,在古代,人口的多少基本能表示当时的繁荣程度,所以可以说在康熙十六年,无为州已基本恢复到明末的经济水平。
到康熙五十年以后,因为每年的丁税额已经固定,雍正年间普遍推行摊丁入亩,以土地税全面取代人丁税,丁银取消,每五年一次的人力物力耗费巨大的人丁编审便没有了太大意义,地方官员对人丁的统计便更加疏忽怠慢。清高宗实录大学士九卿会议御史苏霖勃的一段上奏可很好地体现出清查户口的艰难:“户部议行岁查民数之事,止可验生息之番,难据作施行之用,盖向例五年编审,只待按户定丁,其借粜散赈,皆临时清查,无从据此民数办理。且小民散处乡僻,若令赴署听点,则民不能堪,若官自下乡查验,则官不能堪,仍不过委之吏胥而已。况商旅往来莫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多未便清查之处,请降旨即行停止。”[5]乾隆皇帝素对调查人口一事颇为重视,即便如此,仍有大臣直接上奏叙述调查人口的种种艰辛和不便,更不用说康熙五十年后及雍正年间地方官吏对人口的统计了,只是此时每五年一次的人丁编审制度还未取消,官方统计数据上还需登记,但记录的无为州每五年一百丁甚至几十丁口的数字实不可信。
乾隆年间由于加大了对人口审查的力度,并且乾隆皇帝更加关心总人口数而不是局限于纳税人丁数,所以乾隆年间统计的人口数较以前更为准确,而且更加接近于当时无为州的总人口数。尤其乾隆四十年后,令各地保甲严格审核人口并上报,所以自乾隆四十年后,无为州的人口数据源更加真实可信。通过这些数据也可看出无为州的人口到了乾隆嘉庆年间进入了迅速增长阶段,到嘉庆六年达到七十二万多人,此时处在康乾盛世的后期,社会稳定,农业技术也较为先进,农产量较以前提高,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迅速增长。
2 无为州赋税变化
2.1 无为州赋税种类及变化方向
据(嘉庆)《无为州志》记载清前期无为州赋税种类繁多,赋税共包括民赋、卫赋、芦课和盐法等等。
这些赋税之中,尤以民赋部分最为繁杂,大到漕粮、丁银、官员俸银,小到马草料工食银、造黄册纸张银、岁考生童文卷茶饼银等等一一记录在案,无一不需征税。民赋也是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在无为州的各项赋税中占最大比例,在(嘉庆)《无为州志》的记载中也耗费了最多的笔墨。清初,按照明朝的赋税制度进行征税,税收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地税和丁税两种,再加上其他各种琐碎的课税,如“现办本色物料”下有:“额办银珠”“增办银珠”“增办白麻”“额办桐油”“增办桐油”等;“随漕起解折色银”下又分为“漕运船料旱脚银”“江水脚米银”“本色三分芦席银”等等,各项大小赋税种类不胜繁冗,达数百种之多。为减轻农民的负担,康熙五十一年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将丁银数额固定,雍正元年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亩中征收,到乾隆元年基本实现了全面取消人丁税,以地税取代丁税,雍正二年实行“耗羡归公”政策,给予官吏养廉银,使财政收支更加透明。清朝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简化税收项目,在(嘉庆)《无为州》志中经常能看到“豁免”某某税的字样。赋税的减轻是促使清朝中后期人口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
卫赋是指对军屯粮食以及丁银的征收,原先无为州共八卫:江宁左卫、江宁右卫、江宁后卫、横海卫、江阴卫、镇南卫、广洋卫以及鹰扬卫,后来广洋卫并于含山县,鹰扬卫并于巢县,无为州只有六卫。六卫原额共有军丁7602人,其中4616名军丁领田纳粮,不需交纳丁银,另外2986人交纳丁银,实在交纳丁银者859人,每丁征银三钱,协济银五分,六卫共征粮一万一千余石,征银一千五百余两,另有加津银、漕船火药银等款项,但比民赋款项要简单得多。据卫赋也可看出,作为军事组织的卫所制度,到了清朝完全丧失了其军事职能,而代以八旗、绿营兵。“卫所内部的‘民化’、辖地的行政化过程加速”[7]。但通过(嘉庆)《无为州志》卫赋一项的征收来看,卫所的行政化过程还是相当缓慢的。到嘉庆年间,无为州的八卫还剩下六卫,征收丁银每丁三钱,远高于普通百姓的每丁征银一钱,卫所内的士兵不再承担军事职责,完全变成了屯田性质,成为国家的屯丁,直到清末,才完全废止。
芦课是一项特殊的赋税,明清时期,适宜耕作的农田早已开发利用完毕甚至被过度开垦,但这一时期人口又在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的速度增长,农田粮食产量之间矛盾突出。适宜耕作的农田越来越少,但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迫使江南、湖广、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民把沿水域边缘的荒地进行开垦,这些荒地由江沙淤泥形成,生态环境恶劣,被称为芦州。芦州在农民辛勤地改造下,土壤肥力日益提高,被开垦成芦田,清朝统治者对这些芦田进行征税,便称之为芦课。无为州位于长江中下游,境内芦州广布,达三千多顷,远大于安徽境内其余州县的芦州面积,自然成为征收芦课的重点州县之一。对芦州的征税又按照土壤肥力、土地好坏的不同分成密芦熟田、稀芦地、草地水塘、水荡、上地滩、下地滩等,征收课税从每亩四分到一厘不等起科,泥滩不起科。这说明到清中后期,无为州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对芦田的管理已经相当成熟。《无为州志》记载,在无为州内征收的芦课正银和水脚银共九千五百余两。
《无为州志》对盐法的记录,所费笔墨不多,除了各朝规定一盐引有多少斤盐的变化,以及每斤盐课银多少外,重点介绍了食盐的行销路线以及行销路线的变化。庐州对食盐的运输,以前为陆运,现在为水运,还记述了水运的便利及采用水路运输后食盐销量的增加:“庐州府属从前陆运时,每年仅销一万余引,自改降运,逐渐多销,近年竟能销至两万余引。”[2]另外还记录了官盐与私盐的竞争情形:“陆运时,牛户偷去盐斤,掺入沙土,私贩之盐较好,以至官盐不行,今江运一直到岸,并无掺和,民食好盐,私贩不无利,不禁自止,是以官盐畅销,玆据庐州。”[2]私盐的贩卖在历史上一直屡禁不止,令各朝统治者异常头疼,贩卖私盐在任何时代都是违法行为,在某些朝代甚至被判死刑,但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人口增多,对食盐的需求量增加,以及食盐产量的日益提高,对私盐的禁止便没有以前严格,在庐州地区甚至产生官盐私盐销售激烈竞争的情形。对此也可看出,到清朝中后期,庐州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整体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和繁荣。
2.2 无为州赋税特点
无为州赋税的发展方向大致是渐渐减轻,赋税种类趋于简化,这也是整个清朝赋税变化的基本方向。再根据无为州自身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境内多芦州的特点,比别的州县多芦课税,芦课税到清朝中后期对其管理日益成熟,自有一套成熟的征税细则。卫赋,以前叫作“屯政”,在明朝的时候是一项重要的税收,明朝实行卫所制,“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钱”是其宗旨,但后来卫所制逐渐衰落,到清朝无为州只剩下六卫,军丁越来越少,只作为屯田征收一定的丁税与地税。由于对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贩卖私盐的商人越来越多,量也越来越大,政府对贩卖私盐的管理越来越宽松。
3 小结
无为历史悠久,《民国无为县小志》中载:“无为,古扬州之城,为巢伯国后属。楚敬王二年灭于吴,至秦一统,始隶中原,三国六朝尤为争雄之地,厥后为军为路为州,兴替更迭,随朝而异。”[8]如此悠久的历史,再加上其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地理位置,对无为地区的研究也可以增进对其他地区的了解。而关于无为的地方志是我们了解其历史的最好读本,这其中又以(嘉庆)《无为州志》为最。(嘉庆)《无为州志》中所记载的人口数字虽不准确,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定量的分析,但可给我们带来定性的分析。我们可据此推断出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无为州的人口稳步增长,到乾隆嘉庆时期增长速度尤快,且乾隆四十一年及以后所统计的人口数字基本可以视为当时无为州的总人口数,当然实际人口数要超于这个数字。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清朝无为州的税负趋向于简化和减轻,这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人口与赋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1]魏舒婧.(嘉庆)《无为州志》述略[J].巢湖学院学报,2013,(4):8-12.
[2]顾浩,吴元庆,等.嘉庆无为州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8、89、89、410、89、89、90、108、108.
[3]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80.
[4]张祥云.嘉庆庐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19、319-320、320.
[5]清高宗实录:第 10 册[M].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931、255、930.
[6]清高宗实录:第21册[M].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254.
[7]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2):15-22.
[8]民国无为县小志[M]//顾浩,吴元庆,等.嘉庆无为州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