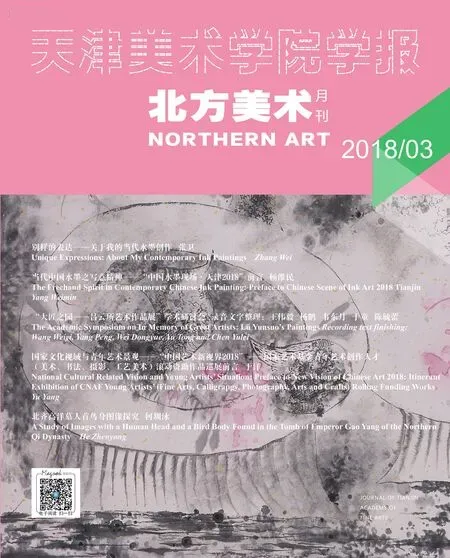浅析中国古代女性审美情趣的演变
王胜男/Wang Shengnan
对于美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中国历代女性的审美不仅取决于女性爱美的天性,更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如阶级、种族、生产力等,既有不同时代的审美特殊性,也有在传统观念下积淀的共性。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女性审美处于萌芽阶段,生殖和生产的能力是女性美的重要评价标准。“形容女性美有一个字:‘好’,但那更多地带有生殖崇拜的色彩,认为女性之美主要在于其生育子女的功能。”[1]此时女性的审美特点为“丰乳肥臀”“阔肩厚背”。到了先秦时期,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审美观念也随之产生变化,从生殖崇拜转变为更加关注身体本身。《诗经》中对庄姜容貌美有这样的描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位美人有着纤细如柔荑的玉指,凝脂般白皙的肌肤,身材高挑,牙齿整洁,额头方正,蛾眉弯细,嫣然巧笑的酒窝,含情脉脉的美目,使得她美得无可挑剔。除了从容貌上描写女性的美,对女性心灵深处的内在品性也有所描写,如《诗经》开篇《关雎》写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什么样的美人使得君子朝思暮想,“辗转反侧”?这里的“窈窕”不似现在身材婀娜多姿的意思,“窈”表示美心,“窕”表示美状,指女子心灵仪表兼美的样子。对女性内在美的侧重,在两汉时期达到一个高峰,这离不开汉代统治者尊奉儒家思想的原因。
魏晋时期思想高度解放,随着玄学与佛教的流行,时人的审美思想实现自我化,最大程度地释放了对美的感受和追求,甚至出现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主要对象的现象。这个时代对于男性举止仪态的品评蔚然成风,“在‘竹林七贤’的‘林下风气’影响下,飘逸风雅之美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审美情趣”[2],后世称之为魏晋风度。受这个时代整体精神风貌的影响,多才善辩、气质高雅自然成为魏晋女性美的标准。《世说新语》记载:“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3]当桓温的夫人南康公主提刀找李氏兴师问罪,破门而入时,只见李氏正对镜梳妆,长发乌黑直拖地面,皮肤白皙温润如玉。面对公主,李氏表现出国破家亡,亦不愿苟存的愿望,其“我见犹怜”的姿容以及淡定从容的气质深深感染了公主,李氏表现出的气质也正是当时社会追求的美感,此后公主待李氏如同姊妹,并成为妻妾不嫉妒的美谈。
除了文学作品,绘画也记录了古代女性的审美倾向。《资治通鉴》记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4],这种“细腰”的审美倾向,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存在,从画家顾恺之的作品中可见这种审美偏好(图1)。“魏晋人士的审美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审美转向了道家审美,充满了创新意识和个性色彩……魏晋的审美缺乏一种壮丽健美、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充满着柔弱和纤细的风格。”[5]

图1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
纵观古今,女性对于审美与时尚的追求主要体现在着装与打扮上,古代女性的审美在其妆容上有着明显的表现。早在汉代,女性就将红色颜料涂抹在嘴唇上,并且轮廓画得很小,“樱桃小口”逐渐成为古代女性美的基本格调。到了唐代,女性妆容样式有所丰富,但对唇妆的审美依旧是“朱唇一点桃花殷”。唐代政局稳定,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经济繁荣,建交国家众多,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此时的女性美相应地呈现出雍容华贵的景象,即以胖为美。此外这种审美还和统治者血统有很大关系,唐代贵族中有鲜卑族血统,崇尚武力,因此对健硕、丰腴的体态更为偏好。唐人把女性的丰腴视为妩媚,女皇武则天容貌为“方额广颐”,方额头四方脸,长相端庄、富态甚至有些英气,故而唐太宗赐名武则天为媚娘,这与唐时女人以胖为美、崇尚阳刚大方的审美标准是十分相符的。
“蛾眉”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妆容,张祜有诗“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描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怕脂粉污损了自己原本的天姿国色,只淡淡扫出娥眉朝见玄宗的场景。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图2)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宫廷女性的姿容,宽额圆脸,体态丰腴婀娜,服饰明艳华丽,以朱砂色为主。加之高耸的发髻,轻透的披帛,显得雍容华贵,落落大方,也充分体现了“盛唐气象”。正是在国力强盛的背景下,形成了唐代女子热情开放的性格,受胡风影响,衣着上尽显女性的柔媚性感。而在妆容上,亦是绚丽多彩,唐代女子妆容精致,步骤顺序与现在妆容一样烦琐(图3)。从唐代的仕女陶俑中,更可以直观感受唐代女子在浓墨重彩下所形成的别样妖娆。

图2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 纵46厘米,横180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代统治者尚文,文人、士大夫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男性对女性美感的把握也被文人审美意识所左右,奠定了喜好典雅、平淡、内敛的基调。宋代居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宋代理学不惜以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代价,来建立符合男权规则的礼教社会”,其中最为刺目的,莫过于对“三寸金莲”的审美喜好,不仅在精神上实现对女性的绝对统治,在肉体上也予以压迫。
宋代女性的妆容与唐朝相比,显得要清新淡雅,在当时称之为“素妆”。“桃花妆”在宋代深受女性喜爱,这种妆容最初起源于南朝寿阳公主,“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6]。汪藻“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黄庭坚“珠帘绣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柳永“寿阳妆罢无端饮,凌晨酒入香腮”的诗句中都所表现。宋代女性妆容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创新,北宋皇后在原有的面靥、鹅黄、斜红的位置饰以珍珠,我们在皇后像中可以见到,珍珠在当时相对难得,故而这一妆容的盛行也如昙花一现(图4-7)。苏汉臣《妆靓仕女图》(图8)中所描绘的女性,“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瘦小娇弱,带有一些削肩,体现出男性对女性“温婉”的期待,也体现出宋人更倾心于纤巧、柔弱的女子,这也正是宋代女性审美的标准。

图3 唐代妇女化妆顺序图(出自《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图4 仁宗帝后像

图5 徽宗帝后像

图6 钦宗帝后像

图7 高宗帝后像

图8 宋代苏汉臣《妆靓仕女图》 纵25.2厘米,横26.7厘米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女性美为“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慢步走,勿乍手,要笑千万莫张口”[7],可见清瘦的形体、精致的五官以及含蓄内敛的气质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审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林黛玉“泪光点点,娇喘微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种对病态美感的喜好,正是明清人的审美标准。对宝钗的描写是“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白皙的肌肤、明亮的眼眸、红唇皓齿、蕙质兰心是当时美丽女子的象征,同时也是各个时代对于女性美感要求的共同之处。曹雪芹有诗“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模仿曹植《洛神赋》描写警幻仙子的美丽,明眸皓齿,樱桃小嘴。在白居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苏轼“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岑参“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等诗词中,都可见对美丽女子嘴唇红润小巧的描写,如樱桃模样,娇嫩迷人。历代女性在画唇时多不将嘴唇涂满,以唇形中间部分为主,其余部分用妆粉遮盖,以此突显女子的韵味(图9)。
总的来说,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女性的审美情趣多不是自发的,一是以男性审美为前提,二是受宫廷审美影响。正是对男性的迎合,使得女子不断创造出更为有新意的妆容,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这些审美情趣以及妆容种类对我们仍有借鉴作用。如当下最为流行的咬唇妆,便是对古代女性唇妆的一种延续,其目的都为了修饰唇形以表现出“樱桃小口”。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新时代女性的审美不再仅局限于“女为悦己者容”,而是较之古代有一种更为健康的方式。不同的时代背景产生不同的审美标准,古代女性审美情趣的演变,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社会的缩影。对镜描眉梳妆,其实也在行古人之事,释放爱美天性的同时,又令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

图9 历代妇女唇妆样式图(出自《中国历代妇女妆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