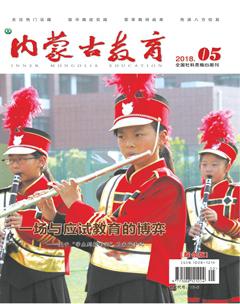专家?专家!
曹权
最近连续聆听了几场专家的讲座,很不舒服。
专家自己编写了一套教材,学校要推进以这套教材为核心的校本阅读,专家要进行专门的阅读指导。在专家莅临学校之前,教材已经发到学生手里了,所以,在听到专家要亲自为他们举办讲座的消息时,学生尽管对这套教材的价位心存不满,但对专家讲座这件事还是满怀期待的。
讲座开始了。
首先是作为主持人的学校某位领导代表学校对专家及其教材的评价——无非是专家是这个领域最牛的,教材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价位是同类书籍最低的,我们的学生认为如此低的价位是不可思议的,等等——大意如此。但学生已经开始反感了,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学生问过:“这套书这么贵,我们能不能不要?”现在,面对主持人慷慨激昂、真假参半的演说,学生在台下议论纷纷:
“教辅书哪有按原价卖的?笑话!”
“这套书网上书店的价格便宜得多!”
“他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
……
直到这时,我相信,学生对专家的讲座还是充满期待的,因为,当话筒终于交给专家的时候,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但他们再一次失望了,因为专家浓重的地方口音,使他们几乎听不明白专家在说什么,再加上会场的音响效果和通风条件不太好,几百人挤在一起,天气又热,当他们努力尝试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失去了耐心,有的开始写其他学科的作业,没带书包的学生开起了小会,甚至,在讲学的过程中,一度需要有专人维持会场秩序。就在这种闹哄哄的情况下,讲座进行了近三个小时。
为了给专家挽回面子,主持人又进行了近半小时的现场采访,刚才还在写作业、开小会的同學有不少被“砸中”,他们都给专家的讲座做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和极高的评价,如“灵魂的洗礼”“精神大餐”“满汉全席”等等,他们当然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主持人的表扬。
这样的讲座,连续举办了四场,场场“被爆满”。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专家所讲的内容有些还是很不错的,如关于艺术的高雅与通俗,生活中的雅俗共赏,关于阅读的迁移,等等,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我听了也很受启发——但学生没有我的阅历,尤其是他们日常接触的语言,除了当地方言就是普通话,听其他省份的方言,对他们来说的确很困难。加之这位专家个性超强,把中国从古代到现当代的许多名家名作,一概斥为“垃圾”“下三滥”(这几句话学生都听懂了),这和学生一直以来接受的文学教育是直接抵触的,所以学生不买账,也在情理之中。
我在这里不想对这位专家的活动再做过多的评价,我只想就学校邀请专家讲学的目的和如何发挥专家的作用,再做一点探讨。
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计划地邀请在某些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来学校讲学,学习他们先进的理念和做法,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活动的指向,必须是有益于教育,有益于教学,哪怕只是务虚,也应该让人们看到一个努力的方向。像这次的活动,即使在教学方面有一定的益处,能够给教师以有益的启发,但从组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在教育方面,传递给学生的,却是满满的负能量——因为四场讲座主要是面向学生的,教师主要是以组织者的身份参加的。场地、音响的缺陷,给学生树立了做事粗枝大叶、漫不经心的典范;为了让学生接受教材的价位,给学生提供了制造谎言的标本;为了给专家挽回面子的打圆场式的现场采访,更是先逼着学生当场说谎,再热情洋溢地鼓励说谎;一场学生并不买账的讲座,能连续举办四场,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到场,则直接让学生领教了权力的至高无上!事后,活动的组织者还把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归罪于任课教师事先没有在学生中广为宣传,没有把专家“神化”,如此高论,令人不寒而栗!须知,对专家的“神化”,必然对应着对学生的奴化!如果我们在学生人生的起步阶段就让他们学会面对名人只能无条件地跪拜,那么,他们即使掌握了先进、高效的阅读技巧,又有什么意义?而且,我们不遗余力地推进阅读活动,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跪着读书吗?
事实上,在第一场讲座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之后,完全可以进行补救,当然,这种补救的前提是坦诚与平等。作为主持人,可以和学生坦诚交流,专家讲座的哪些内容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作为当事人的专家,也可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探讨,对于自己存在的问题,承认就是了——比如“垃圾”“下三滥”之说,不论从哪个角度评价都是站不住脚的,何必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抱残守缺?这里也涉及到“平等”的内涵——学生与老师、专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学识方面,价值观方面,他们是学生,与教师不在一个层次,与专家更不在一个层次,学术方面的争议,可以拿出来与学生共同探讨,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甚至泄愤,对已成定论的、彰显共同价值取向的人和事进行的攻击谩骂,就没必要与学生“共享”了吧?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学生传递怎样的教育或教学的因素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家辈出的时代,各路专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创立”的或“拼凑”的理论。尤其在教育教学方面,今天张教授来了,主张一种模式;明天王教授来了,又提倡另一种主义;李教授主张训练,赵专家倡导活动……而且,这些专家教授的理论无一例外地都在所在学校取得了“成功”——高考的高分率、名校率大幅提升。于是,我们就今天推行张教授的模式,明天贯彻李教授的主义,都是提升到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的高度推进的,天天教改,年年教改,半年一种模式,一年一种主义,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拥有什么,需要什么,只要有专家教授的名头,只要在高考中创造了所谓奇迹,就一概来者不拒。我想,每一种模式、主义的产生,首先是基于倡导者所在学校的特定实际的,未必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可否认,其中肯定能体现教育教学的某些共性,但更多的是彼时彼地的个性。不考虑自身的实际,一味地“拿来”,看似好学,其实不值得提倡。我们似乎太过相信“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训,而没有考虑,对别人先进的东西不加选择、不加改造地使用,“变”亦未必“通”!目前,高等教育已成普及之势,我们还把培养精英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忽视了更高比例的普通学生的需求,方向、目标错位,这样的“变”更不可能“通”!
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说:“第一种人是自己不爱动脑筋,思想和行动老是学别人,包括学父母、邻居、牧师以及自己心甘情愿奉为师表的其他的人。他们只图省心省力,不肯认真思考和检验。”(转引自约翰·杜威《我们如何思维》,新华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27页)迷信专家的、好学的、试图通过各种模式创造奇迹的教育工作者,当引以为戒。专家的主张一定有其独到之处,但不加选择、不加改造地穿别人的“鞋”,又怎能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