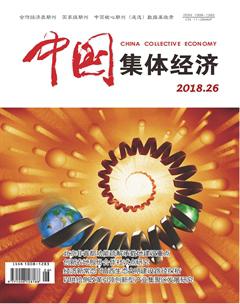浅析印度环境法庭的司法能动性
袁菲菲
摘要:印度,作为较早引入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得到创新发展。印度法院通过发挥司法能动主义创设了书信管辖制度和多样的救济方式等,并且其判决执行效率也是令各国羡慕,当然有权力,无约束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为此文章通过对于印度环境法庭司法能动主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印度环境法庭;司法能动性;绿色环境法庭
一、印度环境法庭的简介
(一)立法背景
1984年发生于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市的工业化学事故导致2.5万人直接死亡,55万人间接死亡。除此之外,还导致20多万人残废的悲剧。该事故的发生让印度开始重视环境问题给社会带来的严重问题,遂于1986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1989年、2000年颁布了《危险废物管理与处理细则》、《噪音污染规范与控制细则》等关于污染防治和控制的环境立法;1991年颁布了《公众责任保险法》、《公众责任保险细则》等关于环境救济的环境立法;1995年、1997年颁布了《国家环境法庭法》、《国家上诉权力机构法》等解决环境争议的环境立法。至此在印度形成了层次齐全、错落有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其中《国家环境法庭法》颁布多年后,没有有效任命审判成员、环境法庭也未设立;《国家环境上诉机构法》并没有催生出国家环境上诉机构,立法目的没有实现,这两部立法成了摆设。由此,为了满足国家对于环境法庭的需要,印度议会于2010年4月30日通过了《国家绿色法庭法》废除了上述两部立法。
(二)绿色法庭的相关制度
在《国家绿色法庭法》中规定,设立国家绿色法庭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国家绿色法庭主要是由三类固定成员和一类非固定成员组成的。其中固定成员包括庭长、审判成员和专家成员,任期均为五年;非固定成员主要是特邀专家,法院认为审理的该环境案件较为特殊且有必要依职权邀请一位或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关于绿色法庭的地区设立,印度法院将新德里作为常驻地,在此基础上将金奈、博帕尔、普纳和加尔各答这四个城市作为常设地。
印度环境法庭主要有两类管辖权:一类是民事案件管辖权及执行权;另一类是行政审查权。而由于缺乏相关经验的指导或者由于曾经未有相关法庭有此做法使得刑事管辖权从法庭的权限中被剔除,该法规定印度最高法院是所有受害者的上诉法院。在印度,环境法庭被赋予“政策制定”权,对于相关环境问题依此权利制定框架方案,并可对其进行管理和适时的修订(但是这些政策制定只限于对污染企业的转换或关闭,损害赔偿等方面,不同于行政决策权)。同时,国家绿色法庭还被授予依据案件事实和情况创建新理念。
关于印度环境法庭的程序规则,该国案件审理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但在现实的环境案件审理中,从案件的受理到审理以及案件的调查取证,均实行的是职权主义,由法官主导,赋予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合作式的诉讼程序大大提高了法庭审理案件的效率。
二、印度环境法庭司法能动性的应用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印度法院司法能动性的运用
1. 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
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是1988年,M.C Mehta律师就恒河水严重污染的问题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以公共妨害为诉因的公益诉讼。在该诉讼中,原告不是沿河居民,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该律师的诉讼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不被侵害,遂确认了原告起诉资格,并将该案定性为公益诉讼。随后经过一系列这方面案件的审理,最高院确立了“充分利益”原则。至此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告并不要求必须是自己的权利受到了直接损害或者与该诉讼有其他相关的联系,只要满足“充分利益”标准,起诉时为善意,就有可能被受理。这一标准的提出放宽了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创立了书信管辖制度
1983年7月位于印度北方邦臺拉登市的一个环保组织给最高法院寄了一封信,诉称非法经营的采石场行为对该地带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请求最高法院判令停止这种行为。按照传统的法律程序,该行为不会被视为启动诉讼程序的行为,但是最高法院开创性的将其视为正式的令状申请,并以此认为该原告提起了相关的诉讼,遂对被告采石场进行了调查。该案标志着印度环境公益诉讼书信管辖制度的正式建立,该制度是最高法院发挥司法能动性对传统诉讼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该制度满足了弱势群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有利于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维护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
3. 创造了多样的救济方式
在恒河污染案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并没有积极地配合判决的执行工作,于是法院自行成立执行监督机构。该机构主要是由法院的行政人员或者社会上热心公益的积极分子所组成,他们定期对判决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向法院做出报告,以确保法院判决的持续有效执行。再如前文所提到的台拉登采石场一案中,最高法院责令关闭破坏环境的采石场后,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对这一地区今后的采石场选址情况进行监督,确保之后建立的采石场不会破坏环境。同时,发布临时命令也是最高法院为了减轻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损害而采取的十分有效的临时救济方式。
(二)司法能动性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公益诉讼资格最为宽松,不仅确立了公民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同时制定了书信管辖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保障了公民的环境权但是也带来了滥诉的风险。例如曾有一原告诉称Jhunjhunwala石油厂和精炼加工厂违法排污导致当地土地和水受到污染,并引起了流行病的发生。后法院在审查中发现,原告与被告存在矛盾,并初步证实这两家工厂遵守了相关法律和污染控制委员会的命令。遂被驳回起诉。从这一案例我们看出存在一些个人或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公民诉讼制度和书信管辖制度,喊着公益诉讼的口号,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一现象不仅会给法院的工作带来不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背离了建立环境公益的意义。
悉数在世界上司法能动主义被运用的淋漓尽致的是印度法官。由于在印度司法能动主义出现在方方面面,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开始遭到各方面的质疑。比如,恒河案中,最高法院为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在判决中命令教育机构开设环境保护的课程,指示相关行政机关开展“环境情节周”的活动。该判决内容超出了司法权的支配范围,更像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虽然,这些内容有利于环境保护,但也让我们对最高法院的职权产生疑惑。 有些印度法学家对此产生了疑惑,认为法院已经超越了最初的职能范畴成为了国家的治理机构。
三、对我国环境法庭司法能动性的启示
(一)提高我国诉讼裁判的执行效率
在印度,宪法赋予了印度法院判决执行的权威,将公民遵守法院命令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使得法院的判决的执行相对顺利,就算在一个案件中存在一些利害关系人没有参加法院程序,也不会影响法院判决的执行。但是,在我国,由于宪法未明确授予此种权威以及国情的差异,我国法院的判决的执行力存在很大问题,大多是执行难、效率低。根据我国现存的问题:政府部门体系庞杂,现实中关于环境问题的执法往往会涉及到两个以上部门的合力才能解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多部门一起执法,将导致扯皮等问题,影响执行效率及效果,不利于有关环境裁判的及时执行。同时结合环境诉讼的专业性较强的特征,我国应该根据国情,适当放开一些专业社会组织代替政府部门完成相关领域的法令执行。以此,将我国符合条件的环境诉讼裁判交给更为专业的社会组织执行监督(社会组织由政府授权,受政府监督),进而提高我国环境诉讼判决的执行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其次,由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不同于普通诉讼,生效判决的执行是对公共环境权利的保护。由于其具有公共性和紧迫性,当原告代表国家或公众的意志提出公益诉讼并胜诉后,法院在判决生效后应主动执行生效判决,对于不配合或者不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生效判决的主体进行严厉的惩罚和打击,强化对国家整体环境利益和社会公共环境权的保护,提升环境公益诉讼判决的权威,预防公众环境损害事件的发生。
(二)坚持法院的归法院,政府的归政府
环境公益诉讼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透过印度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法院过多的行使其司法主动性,导致其逾越权限干涉行政和立法事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城市固体废物污染案的申请人曾经说过,她最不想看到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的那一天。因为只要法院尚未结束审理,“敬畏和服从”就始终存在,行政机关也就不会放松对环境的治理职责。在德里汽车污染案的审理过程中,尽管最高法院总共发布了一百多项指令,但是以科学和管理中心(CSE)为代表的环保组织依然认为由行政机关独立履行环境治理职责还不够成熟,最高法院“需要发挥更多的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公众对于行政机关的极端不信任,于是寄期望于法院。但是,最高法院持续介入判决执行是不正常的,与有关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职责司法不得干预相违背,违反了有关司法与政府的职能分配理论。这一行为显示出最高法院触角涉及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领域,模糊了三大机构的权力界限,不利于一国的治理。我国应从中汲取教训,严格遵循法院的只能通过司法审判的方式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由此可见,在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时,要遵守严格的限度,不能挤兑行政机关履行其职责的自由空间,保障行政机关职权不被受打压,以合理、合法、合规的立法、监管和执行机制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三)创新多样的救济制度
印度最高法院運用司法能动性,创新了多种多样的救济制度,这些救济制度具有灵活性,并能保障判决执行的有效性,以此增强判决的可操作性,发挥保障公民环境利益的作用。在我国也有一些地方环保法庭提出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性,创新多样救济制度的想法。贵州省清镇市环境保护法庭也在相关环境诉讼判决中运用了多样的救济制度:如对于滥砍滥伐的行为,采取补种树苗并照料树苗生长成树的救济手段。相较于通常的罚金的处罚方式,这种救济方式更能实现建立环境诉讼制度的目的、更为直接的弥补环境损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有些人认为,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法官这方面的权利,并且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救济制度也没有此种救济方式,这很有可能是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导致“法官造法”现象的出现。这种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过于拘泥于现存的制度不利于法律的发展,也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发展,将会导致法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唯一能解决这一担忧的方法就是适度放开、加强监督。法官在创新救济方式时应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和诉求做出判决,可听取其他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向公众公开判决结果,并接受公众和法律的监督等方式限制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于合理的状态。适当的放开步子,给我国法官一些自由,有利于推动我国环境诉讼制度的发展。现阶段,我国环境诉讼制度正处于摸索阶段,应给予法官这种权利去创新多样的救济方式以适应我国环境保护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建勋,蔡守秋.印度《绿色法庭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2).
[2]吴卫星.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启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05).
[3]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