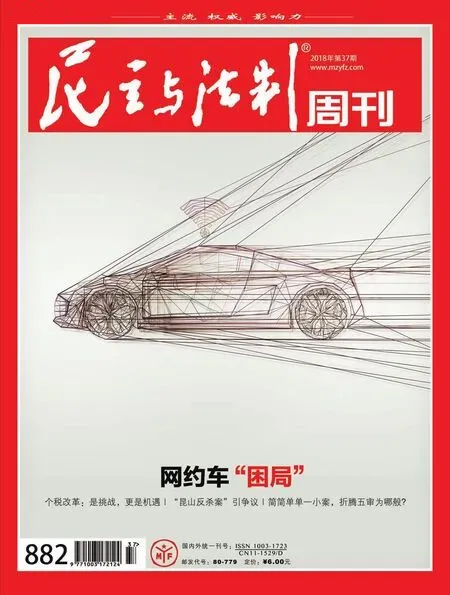回归创新:网约车市场的真正出路
本社记者 张志然

>>视觉中国 供图
“师傅您看,我刀揣兜里了,这儿还有一罐防狼喷雾和电击棒,我都随身带着呢……我现在开着直播,一直到下车都不会停,如果掉线,朋友会马上报警……我练柔道三年了,今年还学了自由搏击,参加区里比赛还拿奖了……”
这是近期网上流传的姑娘与网约车司机师傅对话的段子。与之相似的是很多女性乘客将自己滴滴顺风车的个人资料改成男性,并用上极为男性化的个人签名和头像。“暴躁老兵”“龙的传人”“战狼”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乘客名称出现在平台上,标注多为“散打冠军”“常年练武”等,职业多为汽车修理业。
这些夸张搞笑的现象折射出的却是一个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现实背景:网约车平台近几个月已发生两起恶性事件,受害者均为女性。
网上对网约车的声讨和议论已经渐渐平息。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除了让女孩儿们都武装到牙齿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网约车政策两次收紧
2018年5月3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将严格执行“京户、京牌、许可证”制度。实际上,这项制度2016年就已经通过。此次规定提出,非法营运将处3万元以上罚款,被抓到两次,暂扣驾驶证三个月,被抓三次则扣半年驾驶证。
7月1日起,这项规定正式执行。6月30日,零星执法行动就已出现,很多司机干脆不跑车。7月1日当天,大规模查车开始,很多司机“中招”,打车难的情况再次出现在北京。7月2日,有网友打车排队人数竟达到167人。因为叫车困难,近日已有一些网友使用App叫货车将自己当货物运送来代替打车出行。
网约车政策的收紧,与之前发生的恶性事件不无关系。这也引发了舆论对滴滴和网约车铺天盖地的讨伐。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总裁柳青发布道歉信,并且发布实施七大整改措施。9月5日,交通运输部等十部委人员及相关专家组成的检查组进驻滴滴公司,对重大安全隐患、影响公共安全和乘客人身安全等问题进行系统检查。其他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包括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曹操专车、易到、美团出行、嘀嗒、高德顺风车在内,都要接受为期半个月的进驻式全面检查。自9月7日起,上海网约车平台也将迎来新一轮监管。上海执法部门将持续多日对滴滴公司在上海的数据接入情况及对不合法合规的驾驶员及车辆的清理情况进行检查,督促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交通运输部以及多个城市的运管部门分别约谈滴滴。仅8月底两天内,滴滴就接到了12个相关部门的约谈。8月27日,贵阳市运管局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严查司机人证情况,不得再新接入未经许可的车辆和人员,滴滴平台必须停止接入非贵A车辆,并加快清退已接入的不合规车辆和人员。8月29日,成都市交委要求,滴滴加快人证、车证办理,立即清退不合格的车辆驾驶员……
然而,看似“铁腕”的措施换来的结果却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看到的。9月8日,成都滴滴司机向媒体展示的一段视频显示,近20名男子围住了租赁公司的经理。路边,还有十多辆白色标致车打着双闪。司机们要退车、退钱。突如其来的监管,让跑滴滴变成一件不划算的事:为了在成都办车证,必须多花一倍的钱上营运保险,一年就多出近1万元保费。
据了解,很多司机买不起车,就签租赁合同,用挂靠在租赁公司的车跑滴滴。这些车都是营运车,车证齐全。但办户籍证需要居住证,居住证又需要社保。因此这群地位最低、基数最大的“对公”滴滴快车司机,就成了淘汰的对象。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出租车数量“绰绰有余”。按照此前住建部设计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大城市每万人拥有出租车不低于20辆,201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万人,出租车6.6万辆,每1万人拥有30.4辆出租车,远高于标准。
然而,有媒体曾经测算过,如果在北京的打车高峰期要实现运力均衡,至少每辆车每小时要接3.5单,这就意味着北京出租车数量至少要再增加四倍才有可能满足。
而网约车平台却有足够的大数据和激励措施来协助解决问题。滴滴去年年底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目前其平台司机50.7%在线时间仅两小时内,更多是补充高峰期弹性运力。对网约车一味的声讨和整顿,很可能把网约车市场的活力彻底扼杀,变成下一个出租车市场。如何避免这种怪圈,是很多专家学者关心的问题。
如何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在一次研讨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支振锋指出,网约车监管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监管问题。我们身处一个现代的大型复杂社会,哪怕一个很小的新的问题,也能够带来一个体系化的困局、麻烦。网约车涉及的主体多、关系乱、利益很杂。而新的业态和旧的制度里面,本来共享经济就挑战行政监管,因为公共事业和商业监管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出租车定位于公共交通,网约车怎么定义?是公共事业还是单纯的商业?共享经济把私人民营的设施拿出来共享,有商用性质的话,会涉及非常复杂的行政监管。共享经济里面,是不是雇佣关系、劳动关系?一方面解决就业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劳动关系,受不受劳动法的保护?还有双向的安全问题,网约车提供者的车辆安全问题,还有乘客的问题。还有新经济和旧经济,如网约车和现有出租车的利益格局的问题。
支振锋表示,监管的标准要科学适度,安全标准不能降低,各个地方不能有自选动作,一定是必选动作。而涉及地方产业发展或者环保要求的,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涉及就业、城市的交通等,也属于地方立法的范围之内,但要经过更严格的审查。至于说为了保护本地或是为了保护出租车既有的利益格局的标准,如户籍标准,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都会面临质疑,对地方的网约车细则来讲就不合适。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要避免垄断。现在地方出租车公司高度的行政监管,对乘客不利。而如果全国都剩滴滴了也不行,这有一个反垄断的问题。另外就是算法治理,其定价和计算方式应该透明合法。
如果说支振锋是通过剖析网约车涉及的各方关系来指出出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常保国教授就是从公共政策出台的角度对网约车新政进行了考察并提出建议。
他表示,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关系到每个人。现在北京、上海出台的一些管理规定,总体来看,还是门槛太高了。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来说,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民主是落实到每个细节的,就像权利保护一样。制定过程中,应该要充分地让利益相关者参与。
“以北京为例,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是非常不够的,尤其利益相关者。在政策出台之前,很多没有北京户口的司机做网约车服务,以后他就干不了了。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问题,更涉及生活生存的问题。”常保国说。

>>视觉中国 供图
常保国还认为,要有充分的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能看哪个声音大,或者谁叫得欢就受到更多关注。其实,把听证会做好,做到货真价实,会节省很多立法政策方面的失误。公共政策出台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民主需要时间、需要成本,其中重要的成本就是时间的成本。从立法到公共政策,尤其地方政府往往一夜之间就出台一个影响我们很多权利的制度安排,甚至一个突发事件之后,一刀切,出台一系列的文件和政策甚至法规,往往是一种应急性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也会带来很多后患。“非典”期间,四天一个法规出台了,毕竟是极特殊的情况。总之,公共政策民主化涉及公共利益如何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相平衡的问题。作为一个城市来讲,不要光考虑本市的人的利益,立法者要站到更高的高度去考虑,公民权利的扩大和保障是国家利益的基础。
用出租车标准管理背离网约车的创新本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张效羽指出,目前网约车所面临的主要是要二次合法化。原因是,经过2016年七部委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至今网约车新政出台已近两年,全国已有超过200个城市发布了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然而据官方有关统计数字,要求的“京籍京牌”都能够达标的车可能仅占5%,能够满足一项的可能仅占10%。既然大部分车都难以达标,都是“非法营运”,是不是说明这个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门槛太高?既然大部分车都是“非法营运”,那现在是不是在对一种已经违法的行为进行约束?所以现在其实是“二次合法化”。
张效羽曾经开玩笑说:“如果都让北大的来当司机开车,那肯定安全。”可是,这其实已经背离了网约车的创新本质。对比出租车行业,本身其改革就困难,监管就严苛,难道说要把新兴的网约车又开回到出租车的老路上吗?这个质问看似尖锐,却把我们的目光引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互联网时代的新事物,是走过去的老路,还是给时代和社会带来真正的革命性的质变?
无独有偶,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网约车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的问题。能够多大程度上满足出行需求,决定了网约车是成功还是失败。互联网时代的事物应该是跨区域、跨行业、跨国界的,而目前网约车领域却是几百个城市各有各的管理。阿拉木斯说:“如果BAT(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产生时期,让他们每个城市都得登记一次,他们还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吗?”阿拉木斯让我们明白了,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新事物要采取包容、弹性、容错的态度,这样才能有创新的土壤。而互联网行业需要的是质变,而不是修修补补的量变。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金瑞指出,我们目前出现的问题说明了制度设计的不够精细。在他看来,网约车平台扮演的是一个供需撮合的角色,而国外已有的成型的租车模式并不适用于解决我们的网约车问题。原因是国外的租车都是停着的,而我们的网约车则是满街巡游的。现有政策中对户籍、车轴距的限制本质是对数量的限制,业态融合应该设法平衡出租车网约车的利益,政府应该利用平台公司的技术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增毅则将目光放在了司机的权益方面。一方面,政策要求司机本地户籍,这可能已经产生了就业歧视问题。而车辆限制不光让消费者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质疑。司机的工作时间过长、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因为与平台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仅为合作关系,所以也缺乏应有的保险。所以网约车平台上,数目庞大的司机群体的权益到底该怎么保障,谁来保障,也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网约车要创新,思考更要创新。新生事物产生了新的问题,新的问题自然要有新的解决方式。专家学者支招后,相信政府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好网约车带来的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