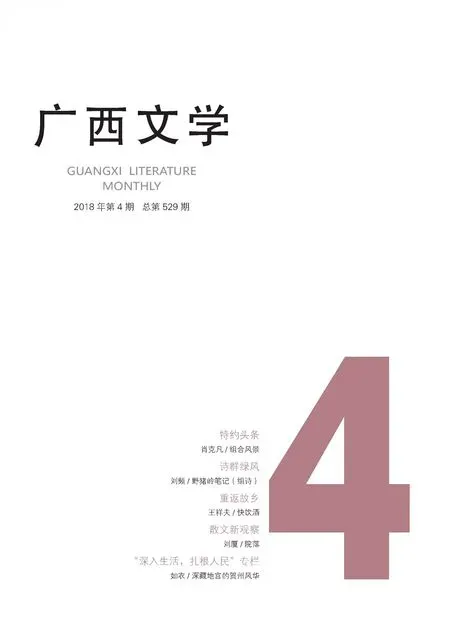深藏地宫的贺州风华
如 衣
(一)古人类时代
是宇宙洪荒的风云际会,是天地玄黄的深情孕育,是青山绿水的日夜守候。嘹亮的婴啼呱呱坠地,把沉睡的万物唤醒;坚定的脚步稳定铿锵,将厚实的大地踏响。湘桂平原缓缓打开古老的眼眸,在朝阳起落里注视着生命传承之初的乐章。
它,是生命的起点,文明的源头。
它是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龙潭角古人类洞穴遗址。
我特意选择了这样宁静温暖的清晨,缓缓靠近它,我怕惊扰了它。它掩映在如螺尖的重重峰峦之中,祥和又普通。
我站在它的正前方,等它醒来。
从这个角度远远望去,村镇的房屋错错落落、新旧交替。新的,是水泥小楼,外墙贴着瓷砖,形成颜色缤纷的图案;旧的,是灰瓦顶的青砖房,外墙被风雨侵蚀,斑斑驳驳。
天还没亮透,整个镇将醒未醒,有着如孩子赖床的娇慵。四周寂静,仿佛只有我的心跳。
天开一线,旭日东升,云层开始慢慢燃烧。那火苗,是先民们慈爱的眼眸,还是我心底燃烧的烈焰?
湘江与漓江千万年流淌不息,两江交接的上游,延伸出一片狭长平坦的平原,史称“湘桂走廊”。
湘江北去,漓江东流。
漓江流入贺州市昭平县境内,称为桂江。贺州就处在湘桂平原腹地,很早就有古人类活动的痕迹,是孕育古文明的摇篮。
天风浩浩荡荡,回响如歌悠远。
日升月落,亘古不变。太阳轻轻一跃,抖落烟霞,将光辉洒满湘桂走廊。然而仅仅是一道光芒转换,时间已逝十万年。
在龙潭角岩洞遗址内,2009年6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试掘,发现了古人类牙齿化石十七枚,并伴有大熊猫、熊、猫、牛、猪、猴、羊等动物牙化石一批,分布面积为一百平方米,据推测为距今约五万到十万年前的古人类洞穴遗址。该遗址证明了当时的贺州古人类已经在驯化或饲养牛、猪、羊等牲畜,这在湘桂走廊是非常先进、罕见的,就算在古人类记载史上也是起步较早的。从狩猎到驯养,在这边陲一隅,贺州古人类迈进的步伐已遥遥领先。
龙潭角岩位于清塘镇河东村委赤马村,洞深数十米,东北向,距赤马村约五十米,洞口在民国时被村民用石砖砌上,留有一门可供出入。
阳光落在老岩洞,植物青翠,风声细细。一条小径自山脚直通到洞口。
不曾想过先民究竟来自哪个遥远的地方,不曾想过他们长着何种模样,不曾想过触碰他们的遗物时会是何等心悸。十万年的青山绿水在蓝天下铺展,那个矗立的岩洞,阅过风霜、翻过岁月,最终积成缄默。一天天,一年年,岁月流淌成河,月光朗照成歌。静静的生活,默默地劳作,岩洞里进进出出的脚印展现着一个民族的顽强与坚定。正是这样一种苦而不怨、苦中愈强的精神,最终凝聚成潇贺文明,璀璨了华夏文明河流的波光,铸就了古老的东方世界的磅礴!
眼前的山峰鳞次栉比,好似海浪一般温柔中暗含万钧力量。线条起起伏伏,形状层层叠叠。而此时的龙潭角岩就是矗立于古人类历史瀚海中的一座丰碑,宣告生命终于来临。
日出月落,在天空划过的轨迹永恒不变,无声的光阴在流转。这里曾发生过多少精彩的故事,这里又有哪些艰辛的过往呢?风静默,树静默,山静默。我无从得知。
我走近岩洞口,抚摸岩壁,触手微凉。在今天,我能把手掌张开,与先民掌印重合,是怎样的一种荣幸啊!
发掘与见证,寻迹与追思。
那几个背脊袒露的汉子,手拿简陋棍棒与石块,潜伏在密草丛中伺机捕杀猎物;那个神情温柔的女人,侧脸的笑意映得岩洞光辉又温暖,她在轻轻拍哄着怀中哦哦细语的婴孩;那老者,在圈边苦苦思索,想必是在为圈中野性难驯的兽类伤脑筋了……

石铲
时光老去,岁月老去,人影也老去。只遗留下十七颗牙齿化石,成为永不消逝的坚固记忆。
我只能望着图片中的牙齿,试图在脑中拼接你微凸的额头,黑亮的眼睛,颀长的臂膀,还有和善的笑意。这一颗颗牙,啃食过野果、野菜、猎物的肉,也啃食过生活的苦难。饥肠辘辘,你无食物果腹,可曾绝望吗?冬天来临,你无衣裹身,可曾苦吗?风雨来侵,你只能借洞遮蔽,可曾冷吗?除了坚强,你别无选择。
尽管岩洞空空,你依然将生命之舟填满。用爱,用心,用毅力。于是,才有了我。
是怎样的一种汹涌泪水浸湿了心的坚硬,是怎样的一场撕心裂肺疼痛唤醒沉睡的记忆?旷野猎猎的回风,吹逝了先民渐远的足音;万年沉默的岩石,隐藏了谁的血泪?是谁,在这小小洞穴播种最初的文明?是谁,用身躯托起生命的图腾?是谁,让荒凉的土地接驳未来的流霞?
洞穴不为人所知,附近村庄的人仅仅懂得这里出过文物而已。十万年尘埃厚重,把它湮灭在其中。可透过贺州的外表,直达坚强、稳重的内核时,就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早已渗透到每一道古桥、每一片村庄,甚至每一个眼神。这一切的源头,不正来自洞穴吗?沿着时光大河溯源而上,洞穴光辉依然。

卷云纹青铜斧
洞穴里一定还留存着先民们的一脉灵魂,在默默地注视着这片大地和她的子民们。村庄恬静,稻苗青翠,鸡鸣犬叫……这一切,也一定是她护佑的结果。十万年的追忆是一种距离,很远,远到杳然无迹;也很近,近到掌印重合。
洞穴与贺州,这是一座山和一个城的对话,这是一个母与一个儿的对话。龙潭角古人类洞穴遗址,翠色青青,是一位沉静又伟大的母亲,衍生哺育了这片大地的子民。贺州,喧闹繁华,十万年光阴里依然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充满活力。一静一动,一个古老,一个现代。
在洞穴前流连,当心灵沉浸在缅怀与感恩的时候,先民们的形象已经在我的灵魂中永生。
天空一片蔚蓝色。先民的魂魄,已经张开翅膀从洞穴起飞,羽翼在纯净的云脚边滑过,最后高踞在白云之上、太阳之旁。天空那一抹澄澈的蓝,是先民们慈祥的笑意;那一缕云彩,是他们的眼眸。
眼眸里,会流下动情思念的眼泪;眼眸里,曾燃烧最初的文明光芒。在十万光阴里,这眼眸已是山川草木之情,是天地万物之心,是日月星辰之辉……
(二)旧石器时代
鲤鱼山安静地依偎在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怀抱里,两座石山相连,远看轮廓如同游动的鲤鱼,因而称为“鲤鱼山”。山脊淡抹白色的云朵,宛若初醒的远古母亲的温柔软语,飘啊飘啊,飘得心儿又醉又甜。
鲤鱼山遗址位于富川县富阳镇鲤鱼村东南面的鲤鱼山麓,距城约两公里,面积约十六万平方米。
该遗址地处富江东岸的二龙潭地下河与富江相汇的三角地带上,遗址由坡地和山腰洞穴组成,在离地面五十米处鲤鱼山山腰,有三个岩洞,呈“品”字形,洞口高一点八米,宽为三米,深为三十米,三洞内部相通,俗称“岔口岩”。岩口面向东南,洞口下的二龙潭地下水丰富,清澈甘洌,根据1979年国家水文地质普查成果资料表明:该水属于低矿化淡水,是比较好的人畜饮用水源。良好的地理环境,为贺州古代人类生产生活和繁衍生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山不变,水不变。自然的风烟冲洗着万年的记忆。鲤鱼山面前是一片开宽的田野,稻苗、玉米、番薯、花生,都在欢快地生长,叶色青翠养眼。更远处是富江,绕着弯流过。穿着蓝色土布衣裳的瑶族姑娘临水唱起了曼妙婉转的蝴蝶歌。歌的尾音拖得长长的,在江面飘起,在田野回荡,在鲤鱼山盘旋,然后穿越时间与天空的苍茫,与先民坚强的灵魂邂逅。
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岔口岩洞进行了试掘,发现文化层三层,分别为表土层、黄褐土层、黄色堆积层。表土层厚约三十厘米,在表土层下为厚约二十五厘米的黄褐土层,出土了磨光石凿一件、陶纺轮一件、人下颌骨一枚;在黄褐土层下为厚约三十五到五十厘米黄色堆积层,发现有碎骨化石、螺壳化石、零散陶片。经考证:该遗址的年代跨度为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这说明在约一万年前或更早,贺州就是古人类活动频繁地带,为当地进入新石器时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年年繁花盛放的季节里,一条巨鲤以它独立于世的姿态,游行在碧草之上、天地之间。它从远古的风雨中来,在鸿蒙开天中穿透岁月。这条吉祥的鲤鱼,游进了中国古人类长河的璀璨波光中,共同汇聚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与自豪。
当太阳又一次从鲤鱼山脊升起的时候,阳光下的富川恬静迷人,瑶族同胞用油茶、炸果、脐橙、瑶绣来欢迎四方游客,希望所有沐浴在阳光下的人们都能来分享这座古城的美丽。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热诚与辛勤,丰富着富川的内涵,铸成富川坚强的底色。
站在县城眺望,两公里外的鲤鱼山隐约可见,峰顶郁郁葱葱,令人心生清凉。凝望鲤鱼山,就是在凝望自己的精神家园、生命来处,内心是那么纯洁而宁静。鲤鱼山默默地注视着富川、注视着我们,用万年永恒的大爱守望着这片土地。
在对视中,心底的感恩与崇拜,已跨越万年时光之河。
“孩子,我永远爱你们。”和风吹拂,风中送来鲤鱼山的深情话语,带着母亲对孩儿的宠爱,一再抚慰我内心的伤悲。那些纠缠的愁肠百结、那些追寻的虚名浮利,已随风而去。
这里散发着母亲的味道,这是一种特别令人向往与眷恋的味道。这味道藏在山脊、岩洞、草木、花、微风,触手可及的安逸与依恋。宁静与怀念,足以让任何游子心醉心酸,几欲落泪。
这里是母亲的怀抱。当我踩着柔软的光阴走进鲤鱼山,伸手抚摸翠枝嫩叶、嶙峋岩石,是那么温柔又稳厚,仿佛母亲就在这里长久等待我们归家。一万年光阴似乎不曾存在,母亲在微笑迎接我们,她从不曾离去。
走在山间,任何一个转身或者回眸,都会让我跌入一万年前某段遥远又感动的回忆里。石凿开垦土地,种植粮食;陶纺轮唧唧转动,纺出温暖;陶器朴实,盛着生活的希望……
这些古朴亲切的物象,与今天的我隔了一道一万年的时间厚墙,世俗的尘埃被过滤干净,纯粹的思念被瞬间牵起。石凿、陶纺轮、陶片浓缩了贺州的古人类历史原貌,它们像是一个个阅历沧桑、收藏善良的精灵,无声地诉说着先民们的故事与传奇。
1974年富川县文物管理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察,在岩下坡地上采集有穿孔石铲、石斧、石矛头、穿孔石钺、石凿、陶鼎足、剑齿象牙化石等六十多件文物。石器式样多,磨制精致细腻、光滑圆润、线条流畅,见证着当时制作石器的技术已达到了领先水平。
石斧、石矛头、穿孔磨制石斧、穿孔石钺,在1995年均经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鲤鱼山遗址,是目前贺州发现的文化遗存和文化遗物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石器出,天地惊。
是谁打磨了石铲,在这片大地上锨开第一铲泥?是谁雕琢出石斧,劈开一条生活的路?是谁制造了石矛,用它一掷击碎生活的艰难?一万年来云和雨,厚重的历史,化为一道道石器上的智慧线条,成为让人感动的记忆。
今夜,银河倾洒,富江静静流淌,清亮的光辉自苍穹洒下,铺展在大地上。富川古城灯火辉煌。天地间一派人和政兴景象。
鲤鱼山静静地在月光下站立,慈爱的眼眸注视着身边的子民。一万年前如此,今天仍是如此。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她的母亲情怀。是她,用深情的步履丈量着一万年的坎坷;是她,用坚定的意志庇佑着子民的日日夜夜。
鲤鱼山啊,你能否告诉我,母亲的灵魂去了哪里?母亲经历了多少风霜岁月?饮下了多少人世沧桑?滑落过多少伤痛泪水?你能否告诉母亲,我很想很想她,她的孩儿很想很想她。
富江啊,你能否昭示我,那澄净如秋水长天的莽林,埋葬过多少先民的身影?夕阳下那辽阔的原野,又隐藏了先民多少开疆拓土的血汗?
茫茫苍穹,鲤鱼山有影却无声,富江有声却无语。没有人给予我答案,独遗我于这片大地,泣不成声。一头牛抬头向天,“哞”的一声,声音透过原野掠过天际。望向天空,我仿佛看见在风雨中用石铲、石斧、石矛头默默耕耘的先民们,他们以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贺州历史的光辉。
(三)新石器时代
山峦映衬着霞光,云彩牵引着梦想。岁月的轻烟在历史长河的波光中,氤氲了多少百转千回的动人故事?这一切,或许只有明月见证,或许只有流水知晓。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新石器时代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
李家村新石器遗址位于贺州市八步区,北边为贺江。遗址大体呈长方形,地势比较平坦,在遗址地面散布很多碎石片、大块石头断块,采集有通体磨光石锛、毛坯和石片,另还有方格纹夹砂软陶片。在局部断面地层中夹杂有较多石块、陶片等文化遗存,厚约九十七厘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所调查,推断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
在李家村新石器遗址、信都镇石福遗址、昭平县北陀乡立教村枫树坪遗址、富川鲤鱼山遗址、富川龙母寨二号东汉墓,出土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型制包括双肩石铲、双肩穿孔石斧、穿孔磨制石斧、斜刃石斧、磨光石斧、石矛、石镞、石钺。特别是其中的两件双肩石铲、一件石铲、一件穿孔磨制石斧、一件斜刃石斧、一件穿孔石钺,具有了当时极其高超的穿孔、开刃、打齿技术。这标志着贺州新石器时代的磨制技术领先于湘桂走廊。
这是一条闪烁着智慧的岁月之河,浪花托起一件件型制精美的石器,冉冉而来。它们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邂逅了先民们一双双温情的眼睛;它们在涛声明朗的贺江,与一岸幽香的禾稻对话。肥沃的土地,开始生长粮食、生长希望。
我在这些遗址一再流连,却无法读懂先民们留下的生命密码。在这些风护水藏的遗址秘境,我获得了一种从未体验的快乐,一种踏实的坚强在我心中渐滋暗长。遗址很简陋,石器也很简陋,折射出的精神内涵却是如此丰硕,它包含着一个民族对待苦难和挫折的豁达乐观。这份乐观,如同一束明亮而温暖的光,照亮了贺州远古先民们生存、发展、传承的艰难道路。
我来到李家村时,正遇上田野里一片一片的油菜花盛开。它们一块块地错落联结,连成一望无际的花海。芬芳随风飘送,金黄色霸气张扬,仿佛是大地给先民们的献祭。风过处,将先民的温馨叮咛一一送至。明丽耀眼的黄色如绸缎一般,从山脚开始铺展,直达贺江江畔。江水荡漾着繁花的色彩,云影、天光、花儿共舞。临江而居,这是先民选择的居住地,万年光阴流逝,依然那么美好迷人,那么盈盈如画。
贺江悠悠,流过先民的脚边,流过我的脚边。它波澜不惊地映照每一个人面容,仿佛早已参透了出世与入世。伫立贺江边听江水涛声,明白了江河山川从不曾老去,更换的,只是人的容颜,从先民到你我。
不时有白色的鸟儿翩然飞翔,小小的翅膀掠过江面,似是一个轻轻柔柔的亲吻,又似是一次天真调皮的戏弄。看江水泛起涟漪,水纹荡起要抓住鸟儿的小爪,鸟儿便飞走了。贺江不仅属于鸟,也属于鱼。鱼与鸟是一对冤家,一个仗着江水的保护敢于挑逗,一个凭着站姿的轻松敢于守候。
远处那头江中泡澡的牛,是裁判吗?
御风而行,飞临其上。这江、这田、这万物,是先民的灵魂还是语言?我多么渴望拥有那些鸟儿的翅膀与飞翔的姿态,那样就可以让思绪在天空与江水间畅行,让心灵追随先民的身影。
鸟儿翩翩,牵动我的感恩与追忆,于苍茫宇空接引前行的先民与后来的我。
先民们磨亮石器,就磨亮了坚强的信仰;打穿石器上的孔洞,就开启了通往未来的大门。有什么,可以熄灭生命的火把?有什么,可以阻挡不懈的追求?从一件件坚硬而线条圆润的石器上,印证出来的,是先民们永远向前的信念姿态,是供后人恒久膜拜的光辉人生。
件件石器,会勾起缕缕乡愁。它们古拙又智慧的型制,铺陈着遥远的岁月,带我们叩问生命的来处,慰藉和温暖游子的心灵。
细细观察石器,它们像来自一场遥远的梦幻,又像是一段段浓缩了的经年流转的传说。过去岁月里,它们在月光倾泻的山峦,深藏于神秘的洞穴与墓葬,任世易时移,始终不曾改变模样。它们收敛起沉静睿智的思想,沉默着风云变幻的过往,敞开着豁达宽容的胸襟,静静地度过百年、千年、万年。经历苍凉洪荒,倾听天风浩荡。今朝,它们来到我的面前,任我细细解读它们的传奇。
石器上的一刃、一孔、一齿、一肩,无声中透出的温暖直达心底。每一件石器带着力量锄向大地,拓土开疆的声音遥远又清晰。石器起落之间,是众所周知的寻常,又是众所不知的艰辛。石器扬起,挥动的是亘古不变的坚强;石器落下,锄开的是万千先民摇曳缤纷的人生。面对它们,不得不对生命有了全新的敬畏,不得不对生活有了全新的了悟。
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迈进,迈过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贺州,也进入了奴隶社会制度中的百越时期。
历史古籍将南方世居民族统称为“越”,因部族、姓氏众多,又称“百越”,所居之地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不同地区的世居民族又被冠以不同的称谓,苏浙称“吴越”,福建称“闽越”,江西湖南称“扬越”,广东称“南越”,广西及越南称“西瓯”或“骆越”。百越繁荣于商、周,汉初时被汉朝廷重兵镇压后消失,在史册的记载中只存在了一千六百年。
贺州曾史属百越,地处湘桂走廊上。
李家村新石器遗址、信都镇石福遗址、昭平县北陀乡立教村枫树坪遗址、富川鲤鱼山遗址、富川龙母寨二号东汉墓出土的石器,带着明显的几何印纹陶、有肩石斧、有锻石锛的特征,这些特征被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公认的是百越民族早期使用的典型器物。贺州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铲、石斧、石矛头、石镞、石钺无不打上了这一特征的深刻烙印。

穿孔石斧

穿孔石刀
这样辉煌凝重的开头,将演奏出怎样雄浑壮阔的乐章呢?又会将贺州带入何方呢?
(四)青铜时代
面对一件件文物,似蹚过一条时间的大河,感觉岁月可以触摸,可以遥望,甚至可以缩短。但细细读着文物上的斑迹,方惊觉岁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
我要如何才能读懂岁月刻烙在文物上的密码,走进它的心灵呢?
1996年在贺州市马东村发现了两座周代墓葬,出土器物全部为青铜器,有罍、鼎、甬钟、凤字形钺共八件。
2001年11到12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贺州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贺州市高屋背岭M122、M123进行发掘,共出土五十件器物。其中铜器四十八件,器形较多,有棺栓、矛、斧、剑、匕首、刀锯两用器、转角器、镦、锛、斧、钺、镞等。其中棺栓四件、铜矛一件、铜剑一件、匕首一件、锛两件、斧两件、钺两件、刀锯两用器一件、码角器一件、铜镦两件、铜镞三十一件。这两座墓出土的遗物种类主要是实用青铜兵器、生活工具及陶生活用具,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
从该批文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贺州的新石器时代制作工艺与青铜器技术的一脉相承。铜矛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石矛头惟妙惟肖;铜锛与新石器时代双肩石铲造型相同;铜斧与新石器时代双肩石斧的造型十分神似;铜镞与新石器时代石镞如出一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锯齿镞,边缘带有十分突出的锯齿状,这明显是由昭平北陀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带齿石铲演化而来,两者无论是从造型、手柄、齿状都极其相似。
从周代墓、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都继承了本地的石铲、石斧、石矛头、石镞、石钺的造型,说明这些青铜器就是贺州的本土先民铸造的。
新石器以坚决的姿态,把贺州带入了磅礴开阔的青铜时代,腾飞在青铜的妍美苍穹。
高屋背战国墓铜钺和马东村的凤字形钺均极具有创新特色。这两件钺与富川鲤鱼山新石器时代的石钺相比,只保留了石钺上半部的造型,下半部的刀刃部分却作了相当大胆的创新,变为宽口、敞开、弧刃,这样更轻便、更锋利、更实用。
这证明了贺州先民的创新意识,始终领先湘桂走廊。
一件件青铜器,曾经缄封于墓葬地宫中,它们静静地躺在那儿,等着我们走近发现,掀开这绝美的青铜大帷幕。道道纹饰是那般精美与繁华,它们的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使贺州的过往有了起转承合的传奇。面对它们,我一再词穷,因为不能仅仅用“美”来形容,它们,有着比外在更美妙、更深沉的内质。
一件青铜器是一首无声的艺术诗篇,打模、浇注、冷却,一道道工艺精心锤炼,凝成了青铜的躯体。我的目光缠绕着它们的弧刃、弦纹、立耳、捉手……是谁描绘了纹饰的精美?是谁浇注了躯体的圆润?是谁在使用它们时留下了指痕?青铜器虽无声,语言却无限。体悟青铜器,生命在净化,灵魂在升华。
青铜器,在墓葬地宫中沉睡两千年,今天重现盛世,它们汇集了贺州万物无穷的美丽,把缤纷辉煌的过往真实地呈现。有了它们,贺州就有了文化的根,有了记忆的落点。
它们将飞禽、走兽、碧水、酒香、音乐、力量、祈祷都藏纳其间,也将智慧的光华、生命的荣枯、人世的沉浮收归其中。青铜器,以永恒不变的坚硬,承载起思想深处的柔软。
我的身躯跟随着目光细成了一缕烟,轻盈腾飞。我绕到甬钟上的舞广、舞修、枚与壁,聆听到来自数千年前的音乐,它悠悠回响,缕缕不绝;我悄无声息地潜入罍,它敞口、方唇、短束颈,两侧有兽首耳衔环,我闻到了缭绕不散的酒香,听到宴会觥筹交错的喧哗;我贴近凤字钺,它方銎、弧刃,它劈向老树或侵略者,刃口闪过势不可挡的力量……
有了青铜器的加持,我发现我的内心变得如此丰富,心境如同大地一样开阔——原野苍茫,森林生长其上,贺江蜿蜒流过,耕田、种稻、饮酒、保卫家园……那些林间的小路叉斜纵横,是先民们匆匆忙忙的脚步,或砍柴,或打猎,或赶集。那急漩的流水,陡峭的岩崖,纠集的树藤,都不能阻挡先民的脚步,他们一掠而过。行行重行行。先民的面容不断变换,脚印不断叠加,踏出了贺州最壮美的青铜发展史诗。我飞翔在青铜的天空,更飞翔在自己的心境。
要怎样开阔的眼界、怎样高超的技艺、怎样深邃的智慧,才能将贺州的山水万物都装进这青铜的方寸之间?
青铜器在历史的天幕上闪烁熠熠辉光,光芒舞动间,五彩枫叶飘落大地,先民在篝火边载歌载舞,点燃了季节的灯火。风中静默的大桂山、瑞云山、姑婆山,像是阅尽风霜的智者。飘逸不定的流云,也在山头久久驻足。铜镜映照,照出先民在苦难中珍惜的诗意;铜矛与铜镦,组合出先民坚韧的力量。
我的目光停留在青铜器经年累积的铜绿上,停留在斧刃斑驳的痕迹中,停留在衔环叮当的回歌里,忆起了先民们风尘起落的简朴,念起了他们勤劳艰辛的身影。我抑得住内心的感伤,却抑不住眼眶中的热泪。
面对贺州这片大地与莽林,辛勤劳作,注定是先民们必定的、唯一的选择。钺、斧、锛、刀锯……是战天斗地的工具和见证。青铜钺,安装木柄,持以砍斫;青铜斧,是继新石器时代大量使用的石斧之后出现的砍伐工具;青铜锛是战国时期的农具,长条形,刃尖利,主要用于砍削木料;青铜刀锯两用器,这是贺州青铜器的创新之作,体现着先民们因地制宜创作农具的智慧,可砍可锯。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成了贺州大地最坚强的歌谣。
这支渗透着先民汗水的歌谣,歌声如水,处处遗留:滋润厚厚的泥土,变成禾稻的模样祭献出来;渗入石缝,化作清澈的甘泉流淌出来;从植物的根部流过,变成叶芽的形状绿出来;从岩壁上倾泻而下,化作清凉的身姿飘逸出来……
行走在这片大地,先民的歌声如天风荡涤,无处不在。
将心灵交付给这青铜、这歌声。在这样厚重的历史面前,我发觉自己渺小如一粒尘埃、一只蝼蚁、一片落叶。但凭借着青铜的光辉,让我渺小的生命也终得彻悟人生。
(五)青铜巅峰
我来到贺州沙田镇龙中村时已近傍晚。夕阳很美,道道余晖洒在大地上,有一种橘色的温柔,天地沉浸于一片浪漫的色彩中。龙中村是贺州千百个小村子中的一个,很普通,但又不普通。面前一条平坦伸展的水泥路把我带入龙中村的深处。
山峦小巧秀气,层层叠叠,似是一幅水墨画的远景。绕过一山,出现一村,再绕过一山,又出现一村,捉迷藏似的层出不穷。
溪水清澈,悠然流淌,不知来路,也不知去向。水中偶尔一片落叶“啪”的一声,荡起道道水纹。水中,白云与天光共舞,闪烁出疏朗的光影。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在溪边盛开,柔弱轻巧,如同精灵。
稻田平坦,一望无际,风儿撒着脚丫,一忽儿就从这边跑到那边去了,掀起了一波波绿色的浪。稻花又细又白,藏在稻叶间。
村居传出鸡鸣声,带着与生俱来的清新气质。我把脚步放轻再放轻,因为即将踏入的,是一个神圣的境地。可眼前溪声哗哗,水光潋滟,四面田园景色如画,又让我忍不住要开心笑出来。
贺州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有煤、铁、锰、钨、锡、铜、铅、锌、锑、钼、金、银等六十多种,主要矿产为钨锡矿、铅锌矿。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临贺县。《实用大字典》“贺”字条称:“贺,锡也。方术家谓锡为贺,盖锡以临贺出者为美也。”临贺县、贺江之所以取“贺”为名,是因为这一带盛产优质锡。贺州所产的精锡,敲之即发出清脆响声,誉为“八步响锡”。
青铜器是用铜、锡、铅,按适当配比,通过制范、浇铸、冷却、拆模、打磨而铸成。贺州盛产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铅,具备了制造本地铜器的便利条件。
经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领先于湘桂走廊的文明积累,并经潇贺古道受中原、楚地青铜文化的影响,再结合自身丰富的铜锡铅矿产资源,终于凝成了贺州大气厚重的青铜史诗,注定要登上青铜巅峰。
1991年7月,在贺州沙田镇龙中村东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一处岩洞葬,并出土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共出土器物三十三件,其中有十八件青铜器。青铜器有鼎三件、牺尊一件、铜鼓一件、铜罍一件、盒一件、龙头形饰件一对、兽头形饰件一对、箕形器一件、凤字形钺一件、环形器一件、钩形器四件、叉形器三件。墓葬的年代在战国时期。这批青铜器在器形和纹饰等方面,既有中原的风格,又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麒麟尊
龙中墓出土的这件铜牺尊很特别,尊形如一只体态圆润、神态温和的麒麟,被称为“麒麟尊”。麒麟尊背部有口,可由此处把酒注入腹腔内,口上有活动的盖,盖面浮雕盘蛇,蛇身饰三道鳞纹,居中蛇首高昂为盖钮,尊的头部形状独特,张头露齿,双目圆睁,有双角,圆柱形,尊的尾部有一直立攀附的小蛇。整体纹饰内容充满了浓郁的古越族文化特点。
它的出现,震惊了世人,精美得令人窒息。与中国过去出土的青铜鼎不同的是,它周身饰满了纹饰:双角饰蝉纹;鼻梁和鼻孔饰卷云纹,涡纹勾出;颈部饰云雷地窃曲纹;身部三组云雷地窃曲纹;背部是三道鳞纹;足部饰线浮雕的单层窃曲纹;尾部的蛇饰葵叶形凹鳞纹。纹饰交错,不厌其烦;线条流畅,不胜其美。
这岂止是一个鼎?这是匠心独运的一幅画!这幅画通过贺州先民的能工巧匠,制范、浇铸、冷却、拆模、打磨,最后凝固成青铜的传奇。
1995年,麒麟尊被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一致确认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国之重宝,举世皆赞。
麒麟尊身披青铜的精美衣袂,带领贺州青铜器登上了中国青铜史的巅峰极顶,留下了回响于历史天幕的绝唱。
蛇类喜居荫蔽、潮湿、人迹罕至的地方,杂草丛生、树木繁茂、枮木树洞、乱石成堆、柴垛草堆、古埂土墙,且饵料丰富的环境,都是它们栖居、出没、繁衍的场所。贺州地处湘桂走廊,山多、林丰、雾气重,正是蛇最理想的家园。
蛇与人,共享贺州这片美丽的家园,蛇成了贺州越人的图腾,他们将这种崇拜很自然地雕刻在青铜器上,成为百越的独特标记。
蛇,是麒麟尊的装饰主角。麒麟尊的背部有盖,盖面浮雕着一条盘着的蛇,蛇身平盘,饰三道鳞纹,道道精美;蛇首居中,头高高昂起,平伸出来的蛇头又作为盖钮,易揭易提,防止滑落,工巧别致,心思细腻。尊的尾部饰有一条直立攀附的小蛇,远看似是麒麟的尾巴,但此蛇与盖面之蛇相比又有变化,它直立,有角、鳞、爪,已演化成龙,正是龙图腾的最初雏形。
青铜器的身影在我眼前一幅幅展开,最后定格在麒麟尊温和妍美的面容上。贺州青铜器,不仅是一本精美绝伦的画册,更是一部记录人类开垦莽林大地的壮丽史诗。
麒麟尊出土于龙中村红珠(音)岩半山坡的岩洞墓内。此时此刻,夕阳的光辉温柔地笼罩着岩洞。是的,就是这样的黄昏,在贺州大地上照耀、陪伴了麒麟尊两千五百年。在村中流连,走在两千五百年前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烦。听从遥远的指引,回归初心。视线所及之处,处处是先民们的气息和痕迹。
我心已随先民远涉,从古人类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青铜巅峰一路走来,走进今天的盛世欢歌。回望生命来处,贺州的伟大风华,已在灵魂之上,在杂念之外,在星辰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