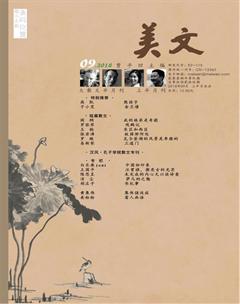汪曾棋,擦亮古的光芒

王国平江西九江人,供职于光明日报社。著有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负累也轻盈》,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年度银奖等。
一
《一辈古人》,汪曾祺写了三个人: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酱油、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醋,健步如飞,酱油和醋纹丝不动的习武高人靳德斋;研究《易经》,用蓍草算卦,算出某家丢失的戒指就在炒米坛子盖子上,却连十多岁的孩子也能感觉出来有些惧内的张仲陶;有一股英气,兼为撮合男女“好事”的“马泊六”,甚至自己也上阵,还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舒舒服服、无拘无束,彻底解放的、自由的卖菜农妇薛大娘。
“一辈古人”,这四个字,引人心暖。
向古人亲近,是现代人的梦想。只是,这个过程,何其艰辛。
山西诗人石头写有长诗,《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下雪的时候,来喝场老酒。”朋友热情邀约,诗人应下了,从太原出发前往长治,徒步,行程221公里。
一路行走,一地鸡毛:
往前出清徐,由太原界入晋中界。
路标显示离乔家大院8公里。
过牛家堡、大义、麻家堡、祁县经济开发区、张北。
此处路东有延寿寺。
再往前,张南,乔家堡,西观。
天黑下来。
这一趟,有多遭罪?
腿脚疼得厉害,连盖的被子都觉得是负担。几次一把掀去。
这疼痛非扎心,非钻心,非揪心,简直是要把心生吞活剥去,竟然忍不住叫喊出来。
在床上辗转无数,至零点,才入睡。
遇见的人有多惊诧?
叹息的——
昨晚吃面的那家饭店老板从对面进来,“唉,遭这罪干啥!”
逗乐的——
进去讨水喝时,店主问:“你受这苦作甚,你是和尚?”
气恼的——
老板娘说,“坐个车多好,你愣不兴兴的,走啥嘞。”
文字精简,“像破损的瓦片”。
诗人说,此次行走,要扔掉身上的眼泪与春风,要扔掉身体里的每个人,甚至身体里的自己,只留下一个最少、最小的自己,“一点多余都没有”。
“思”与“想”还是有的。指向的是古人:
208国道是条古道,许多村名都是什么堡、什么店。
很多古人应该走过。
——“今月曾经照古人。”
本想路上遇着一个破庙,露宿一次,感受古人风骨。
看来抵御不了这风寒,息了此念。
——“古来圣贤皆寂寞。”
诗尾,和盘托出:
徒步200余公里,来找朋友喝顿酒。我不想让古人小看。
诗有个副题,叫《兼致王维》。
201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刊出了《时代、生活与艺术表达——对“三晋新锐作家群”的一种观察》,稿子是我编辑的。作者杜学文提及了这首诗:
石头的长诗《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则极力张扬生命的意志与力量之美。诗人通过描写“自己”为了朋友的一顿酒,冒着大雪从太原徒步到长治的经历。这种似显琐碎的描写,是为了不让古人小看,也就是说,在今人身上,仍然具有古人的勇氣与毅力。
这类花名册式的群体性评点文章,以均衡用力为重,一个人只占一两行就可以了。现在对一首诗的阐述到了这个份上,已经超标了。
哪知作者意犹未尽,添上一句:
而古人,是多么伟大的古人,是曾经创造了多少人间奇迹的古人啊!
就报纸来说,原稿过长,添上的这句是作者“额外”塞入的“私货”,与全文风格似乎也不太搭,显得跳跃、突兀,按说是可删节的。但我在编辑途中,偏偏对这句悉心呵护,再三品咂,久久不忘。甚至武断,整个篇章的华彩,都落在了这句身上。也就是说,这一句就是这篇文章的“颜值担当”!
可惜,今人从内到外把古人的神色与风范给弄丢了。
1961年,汪曾祺写了《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其中有个丁贵甲,嗓子不好,唱起来不搭调,但还是好演戏,硬顶着上。这难坏了导演,就派他演个家院,也就是富贵人家的男仆,都是过场戏,还是演不好。而且台风也有点不妥,虽然穿了老斗衣,还挂了一副白满,但因为太健康、太英俊了,直直地站在台上,实在不像那么一回事。
鼓师小白很直白:
“你根本就一点都不像一个古人!”
不像古人,这似乎是当代人的宿命。
不过,似乎也不必过于焦虑。
“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这副楹联,悬挂在河北邯郸黄粱梦村吕仙祠的卢生殿门前。
既然成为古人是人之宿命,那“今人”应该想着怎样做一个好人。
二
黄裳在《也说曾祺》中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学问情况作了印象式的概述——
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请留意,“学问”二字,始终扣上了引号。
可是,这些人,在现今的人看来,是敬而仰之的。
他这么说,有自谦的成分,也有参照系的选择问题。
汪曾祺写《迟开的玫瑰或胡闹》,说唱花脸的邱韵龙是个很称职的二路。海报上、报纸广告上总有他的名字,在京戏界“有这么一号”,挣得也不少。比起挑班儿唱红了的“好角”,不是一个层次。但比起三路、四路乃至“底帏子”,他可是阔佬,“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再看推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黄裳给自己这代人定的比照对象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傅斯年,确实有点不妙。等于骑驴的,只想着跟骑马的比试高低,完全忘了回头这事。
他这么说,还有美化过往的思维惯性在作怪。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古时的“狂”“矜”“愚”也是好的,也是香的。
朱熹说:“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后之人则以石为玉而又炫之也。”
朱光潜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还说,“‘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
“古时”“从前”是光,是电,是唯一的神话。
“古”到何时?“前”到哪个地儿?是否有一条明显的界线?
周作人答:“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要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
对“古”的颂扬,隐含对“今”的冀望。因为,“现在”呢,不见骑马的,也不见骑驴的,推车的汉也没几个。
鲁迅小说《风波》里的九斤老太:“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俗语:一蟹不如一蟹。
三
《毋忘我》开篇,汪曾祺写:“徐立和吕曼真是一对玉人。”
读《世说新语》,常见“玉人”。荀淑有八子,包括荀靖和荀爽。皇甫谧《逸士传》云:或问许子将,靖与爽孰贤?子将的回答干脆:“二人皆玉也。”
还有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精理义,时人称为‘玉人”。
汪曾祺笔下是虚构人物,冠之“玉人”,但说无妨。魏晋名士,这么一群特异分子,称道他人为“玉人”,自然、贴切得紧。
古人对自己推崇的,溢美之词喷薄而出、铿然作响。张炜著有《陶渊明的遗产》,例举了后世诗家对陶渊明的仰慕。
欧阳修毫不掩饰:“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王安石说“结庐在人境”一诗,“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采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辛弃疾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再往上扬,直至“千古一人”才罢手。
再说王安石跟曾巩,上辈还有姻亲关系,两人一度很热乎,“举贤不避亲”。王安石夸曾巩很卖力:“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曾巩看王安石也是越看越欢喜,“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
不仅东方。
雨果曾经称赞大仲马是一个“超出法兰西疆界,在全宇宙播种文明”的作家。不知道是不是翻译有故意拔高的喜好,口气够大的。
当事人好像也笑纳了,并且遵从着东方古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行事路径。一次文学聚会,主办方准备了留言簿,让嘉宾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若君非您自己,愿为谁矣?”大仲马大笔一挥:“吾愿为雨果。”
在当下的文艺领域,设若这般评说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艺术家,实在令人受不了。——毫无节制的捧之上天,腻腻歪歪的甜言蜜语,被视为文艺领域的一则“公害”,划入典型的“捧杀”。
但古人好像不顾及这些,口吐莲花,潇潇洒洒。
是因为古人的人格魅力确乎有这么磅礴,还是因为今人越来越理性了?
其实,古人也是理性的。
為何说“二人皆玉也”?子将的理由是:荀爽外朗,荀靖内润。
“内”与“外”,占了一头即可,不必那么求全责备,赏月只赏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