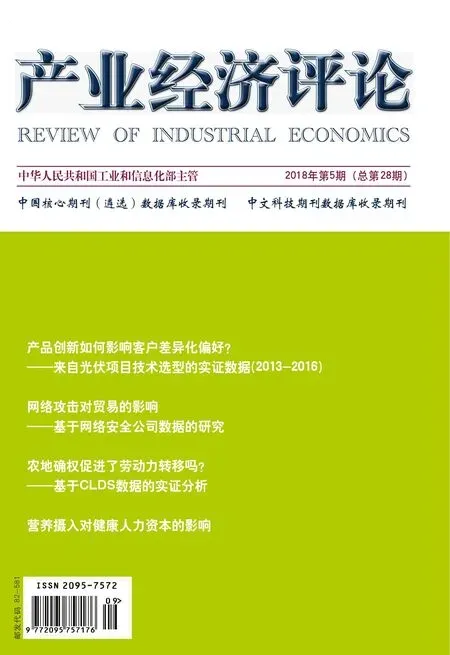农地确权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吗?
——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莉,金江,何晶,刘凯雯
一、引言
农地确权关系重大。一方面关系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关系到现阶段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对农地确权的改革力度一直在加强。2011年3月,农业部等正式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2013年中央又确定了105个区县为第二批全国确权登记颁证试点,更立下了“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目标。中央的农地确权改革虽有成效,但农户的承包地并未完成普遍的、有效的使用权界定。根据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微观数据,确权家庭3 341户,占全部有记录家庭的47%。农地确权改革需进一步深化。
农地确权影响广泛。一方面,农地确权影响农地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Janvry(2012)分析了1993年-2006年墨西哥土地确权运动,研究得出提升农业土地占有权的的安全性会增加土地生产性投资和促进土地租赁交易。另一方面,农地确权也会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农地集中到高生产率的农户手中,解放低生产力的农户,使其转移到亟待发展的产业。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下降,无法满足城市化的需要和非农劳动力的需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8》中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到2030年将达到70%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但是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比上一年减少了171万人;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显示到2030年,流动人口将骤减到1.5亿至1.6亿人次。总的来说,用工荒的出现和城市化率的目标都客观上要求更多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这就需要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农地集中到高生产率的农户手中,解放低生产力的农户,使其转移到亟待发展的产业。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村土地分割零碎,且各地土地小调整不断,使得农地风险无法降低,抑制农户土地投资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步伐。劳动力转移受到流出地、流入地、中间因素、个体原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大量研究关注流入地的影响,较少关注流出地的影响,而本文关注的农地确权是非常重要的流出地因素。确权是否对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有正向影响、影响有多大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文献评述和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第四部分围绕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就家庭、村居和地区的异质性进行拓展;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制度背景、文献评述和影响机制
(一)制度背景
以使用权证书的形式界定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确权的核心要义。农地为何要确权?这源于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民只能享用使用权、转让权和经营权,三级制的集体所有使得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更加模糊。“集体”概念界定不清晰,集体与农民关系不明确,导致农民不能成为产权主体、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虚设等产权模糊问题,为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带来了困难,严重削弱了村民的议价能力(张莉和魏鹤翀,2017)。而这些权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农地市场不断发展中确立的。
农地确权制度的演进要从建国之后说起。人民公社时期的高度公有化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革,赋予家庭农地的使用权。此后二十年内,中央不断加强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从地域扩大到时间跨度拉长,到确定法律保护,确权激发了农户对农地的更多投资,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但是确权的力度远远不够,许多政策也只是停留在字面,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1999年8月,17个省份只有38.3%的农民拿到了土地承包合同(叶剑平等,2000)。截止到2000年2月,对四个农业大省的调查发现,同时持有土地承包合同和证书的农户只有32.1%(杨学成等,2001)。
因而2000年后,中央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从2002年规定落实到县级到2008年确定土地承包关系永久不变。2009年的初期试点探索,农业部选择了包括四川、重庆、山东等在内的8个省份的部分乡镇。四川省成都市提出的“还权赋能”尤其值得借鉴。
“确权”的本质是在实测基础上,以使用权证书的形式界定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程令国等,2016)。2011年3月,农业部等六部门正式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此次确权的任务包括3个部分。一是确实权,在实测基础上厘清承包地的“四至”;二是定法律依据,建立注册登记管理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灭失等进行法律备案;三是颁证书,为农户对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颁证,提供正式法律表达。第一批在28个省份的710个乡镇、12 150个村确定了50个试点县,截至2012年底,已有1 642个村完成确权登记。
2013年确定了105个县为第二批全国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地区,更明确规定“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这也标志着确权工作在我国的全面开展。制度背景概要见表1。

表1 制度背景
(二)文献评述和影响机制
本文的研究与两类文献密切相关:一为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研究,二为农地确权影响的研究。
1.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放弃农业生产并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以获取更好的工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范晓飞等(2013)采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的微观数据,在比较优势的框架下发现预期城乡收入差距会促进劳动力转移。
其次,土地方面的因素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陈会广和刘忠原(2013)利用南京市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拥有卓越土地资源禀赋的农户更不愿意转移到其他产业;土地调整及放弃土地承包权意愿则显著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陈丹等(2017)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对劳动力暂时性的劳动务工转移有正向影响,但削弱了获得城市户籍的长期转移意向。然而游和远和吴次芳(2010)分析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后却发现,现阶段农地流转不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流转农地后更可能是离地失业或者滞留在农地。
还有文献认为消费方面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欧阳峣和张杰飞(2010)通过建立内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发现非农产品消费比重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另外他们还发现城市化水平提高会减缓农村劳动力转移,而迁移成本下降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
2.农地确权影响的研究
目前研究农地确权影响的文献大多关注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叶剑平等(2010)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8年组织的17省份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发现30年土地使用权不变政策的落实对农户土地投资、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以及农民地权稳定性的信心有显著影响。黄季焜和冀县卿(2012)基于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发现由于农地使用权确权提高了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从而激发了农户长期投资意愿。程令国等(2016)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的农户调查数据发现,农地确权使得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约4.9%,农地确权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土地流转,同时也增强了农地的产权强度,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出租价格。林文声等(2017)认为农地确权通过激励农户的农业生产、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价格、促进农村要素市场联动促进了农地流转。付江涛等(2016)利用江苏省三县(市、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农地确权有效促进了农地的转出,但对农地转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胡新艳和罗必良(2016)分析广东、江西两省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但对实际农地流转尚无显著影响。另外,也有一些文献认为农地确权对于农地流转并无作用乃至有反作用。一方面,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农地承包权的发展不同,政策往往难以贴合所有地区,表现出实践脱离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民需要的现象;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农村和农民被动接受政策,出现一些“被确权”“确空权”现象(李祖佩和管珊,2013)。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有其特殊意义,如生存保障、精神寄托等,农地确权会强化农户对农地的控制权偏好,进而促使其倾向于继续持有土地。再者,当农户对土地的情感和生存依赖程度较低时,农地确权会强化农户对农地的土地升值预期和“价格幻觉”,从而抑制其转出农地(林文声等,2016;罗必良,2016)。
农地确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研究也有一些,但是尚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Field(2007)发现为秘鲁的城市贫民提供土地确权使得家庭劳动数量减少而家庭外劳动力数量增加。Galiani和Schargrodsky(2010)却发现为阿根廷的城市人民提供确权虽然导致家庭规模减小,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供给却没有影响。Janvry(2012)通过分析1993年-2006年墨西哥土地确权运动,研究发现提升农业土地占有权的安全性不仅会增加土地生产性投资和促进土地租赁交易,还会导致人口从耕地村居流出。获得确权的家庭拥有流动家庭成员的概率比没获得确权家庭高出30%。本地人口下降4%但平均来说耕种土地没有减少,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杨金阳等(2016)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课题组”(RUMiC)在2008年-2009两年的农户调研数据,识别出两种关于农地产权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成本降低效应。结果显示,农地产权强化未必能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但是能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许庆等(2017)使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验证了农地确权能够促进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又促进了农地流转的决策和数量。
杨金阳等(2016)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区分农地产权的两种效应——生产率改进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成本降低效应,分析其对农业-非农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以及最终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农地产权强化未必能促进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能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如果城乡的资产分配状况不改善,仅仅依靠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差距难以有较大改观。参考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农村土地产权的强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降低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了强化农地产权是否鼓励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其中,农地产权对劳动力转移成本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一,在农户承包权没有完全保障的情况下,农户从事非农工作或进城后,可能担忧面临失去土地的风险;其二,由于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对农地产权的保护,土地流转的租金可能被压低,增加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这种情况以亲友间的转包最为明显。当农地产权受到初步保护时,农户会增加生产性投资,促使农业生产率上升,生产率效应大于转移成本效应,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农业部门。而当农地产权基本稳定后,土地租出收入上升,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成本下降,转移成本效应大于生产率效应,劳动力转移数量随之上升。
本文的研究贡献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运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研究农地确权对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影响,能够对近些年的农地确权进行政策效果评估。(2)对不同地区进行深入探讨,得出更丰富的结论,可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3)目前大量研究关注劳动力转移的流入地影响,较少关注流出地的影响,而本文关注的农地确权是非常重要的流出地因素。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
(一)估计方程

y表示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Certif表示家庭是否有农地确权即领取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xi表示控制变量,包含家庭和村居控制变量;iε表示残差。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的微观数据。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CLDS是在劳动力的流出地进行溯源调查,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样本选择偏误;该调查基于随机分层抽样方法,调查样本覆盖除港澳台、海南、西藏之外的全国29个省区市,以样本家庭户中年龄15至64岁的全部劳动力为调查对象。通过对中国城乡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村居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影响。
图1为2012年CLDS流动劳动力的流向示意图。CLDS对劳动力流动的记录精确到市层面,但是由于弦图难以包含250个市,因而本文选取省级层面进行绘图。CLDS2014问卷并未记录流出地,因此只作出2012年的流向图。两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省份之间的流入关系,线的粗细表示流入权重。未构成连线的山丘区域为省内流动。图中扇形边沿为各省份流入人口占全国流入人口的比重,其中广东、湖北、浙江、福建四个省流动人口最多。

图1 2012CLDS劳动力流向弦图
本文主要使用到CLDS2014的家庭调查和村居调查两份问卷的调查数据。家庭调查数据包含了每个家户成员总数、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各成员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等指标;本文的核心变量是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是否确权两个变量。其中有记录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家庭数据有4 839个;有记录是否确权的家庭数据有7 069个;确权家庭3 341户;无确权家庭3 728户。详见表2和表3。

表2 各省份2013年是否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除了核心变量外,本文在家户层面控制了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总收入、抚养比和男性比例;村居层面控制了村居地势、村居人均年收入、村居耕地面积(亩)、村居是否有初中、村居是否有医院、村居是否大中等城市郊区、村居是否有二三产业、村居实际居住人口等8个变量,详见表4。

表3 家庭层面描述性统计

表4 村居层面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5 基本回归结果
表4报告了确权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回归1我们仅考虑了确权对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确权使得更多的劳动力留在农业部门。回归2我们加入了家庭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总收入对数值、家庭抚养比、家庭男性比例等,核心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回归3我们继续加入村居控制变量,包括村居人均年收入对数、村居耕地面积等,确权的影响仍然存在。回归4在回归3的基础上加入省固定效应以消除各省差异,确权变量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总体来说,2013年我国的农地确权试点的生产率效应超过劳动力转移成本效应,农民在确权后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加大了农业投资等,农业收入提高,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也增多。
四、稳健性检验
(一)采用更加稳健的聚类标准误
White稳健标准误假定了任何样本间都不存在误差项的相关性,但实际情况却不一定如此,忽视这种相关性可能会导致系数标准误的低估从而出现不准确的显著结果。我们考虑了这种组内的相关性,并采用更加稳健的聚类标准误进行系数显著性的检验。估计中我们将标准误聚类到村居层面。
表6回归5是采用聚类标准误对确权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控制了前文提到的所有家庭、村居控制变量和省区固定效应虚拟变量,此时系数依然高度显著,证明确权的影响稳健存在。
(二)采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
我们采用“2013年家庭是否有从事农业活动”来代替被解释变量“2013年农业劳动力比重”,表6回归6和7采用probit估计,回归6使用稳健标准误,回归7采用聚类标准误。两个回归的核心变量都显著,说明农地确权对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是正向作用,对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是负向作用。
(三)采用不同的解释变量
接下来,我们用产权强度作为确权虚拟变量的替代,以降低样本测量误差。确权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产权强度,通过量化产权强度来进一步分析确权的影响。土地调整强度,取值为1、2、3,1代表村组内土地打乱重分(产权强度最弱);2代表村组内部分农户土地小调整(产权强度居中);3代表利用村里的机动土地进行调整(产权强度最强)。样本中共有2 335户记录了有土地调整,其中产权最弱的打乱重分的有603户,产权强度居中的部分农户小调整有1 382户,产权强度最强的机动土地调整有350户。
表6回归8中产权强度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加入了家庭控制变量和村居控制变量、省固定效应以消除各省份差异。说明当农地产权受到保护时,农户会增加生产性投资,促使农业生产率上升,生产率效应大于转移成本效应,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农业部门。考虑到两种效应的相关作用,我们也加入了产权强度的平方项,发现一次项依然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见表6回归9。说明随着农地产权的加强,劳动力先选择往农业部门流入,待产权强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才向二三产业部门转移,但目前生产率效应占主导。说明当农地产权受到初步保护时,农户会增加生产性投资,促使农业生产率上升,生产率效应大于转移成本效应,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农业部门。

表6 稳健性检验
五、模型的拓展:家庭、村居和地区差异
这一部分我们将引入家庭、村居和地区的异质性,着重考虑在不同家庭特征下,家庭对农地确权的反应是否相同,以及不同村居和不同地区中家庭的反应。
(一)家庭异质性
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家庭的异质性: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抚养比。
表7回归9我们引入是否确权和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交互项,两个主要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确权符号与基本回归中符号一致,确权与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交互项符号为负,说明随着家庭受教育水平上升,确权导致家庭更不愿意留在农地进行农业生产,而是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就拥有更多除务农以外的技能,能够获得比务农更高的收入。确权后,家庭的农地所有权得到保障,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得到解放,会比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更快地转移到二三产业。表7回归10显示确权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不变。确权与家庭抚养比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说明家庭抚养比上升,确权导致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抚养比越大,劳动力的负担越重,农业劳动的低收入不能满足抚养需求,劳动力倾向于向二三产业转移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承担家庭重担。

表7 确权与家庭异质性:受教育水平、男性比例、抚养比(交互项)
(二)村居异质性
我们通过村居人均年收入、村居耕地面积和村居是否有二三产业等方面来研究村居的异质性(见表8)。从结果来看,回归11中,确权和村居人均年收入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本地人均收入越高,确权后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数越多。回归12的确权和确权与耕地面积的交互项均显著,且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村居的耕地面积越多,本地确权后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户更多,确权带来的效果更显著。回归13中,村居是否有二三产业与确权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二三产业不会通过确权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
(三)地区异质性
本文根据东中西三个地区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份或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份或直辖市。

表8 确权与家庭异质性:受教育水平、男性比例、抚养比(交互项)

表9 各地区2013年是否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表10回归14、15、16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分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见,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确权对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影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上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确权率分别为36.51%、49.48%和61.27%,东部地区确权率比西部低了 24.77%。①http://www.tuliu.com/read-43990.html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是东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大,农民产权意识强,这使得东部地区常有土地争端,而且在土地调整或者划分时会出现矛盾,拖延确权的进度。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产权强度较低,确权工作的推行使得农地稳定性增加,农民增加农地投资,促使更多农民参与到农业活动中。

表10 东中西部确权对农业劳动力比重影响

(续表)
六、结论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产权强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双重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当农地产权受到初步保护时,农户会增加生产性投资,促使农业生产率上升,生产率效应大于转移成本效应,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农业部门。而当农地产权基本稳定后,土地租出收入上升,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成本下降,转移成本效应大于生产率效应,劳动力转移数量随之上升。实证结果倾向于认为,当前的劳动力转移数量是随农村土地产权强化而减少的,说明农地产权加强后,生产率效应仍然大于转移成本效应,劳动力更多地还留在农业部门。本文在控制了测量误差、家庭特征和村居特征等因素后,农地确权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还围绕家庭、村居和地区差异进行拓展。在家庭层面,家庭受教育水平和抚养比与确权的交互项都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抚养负担的上升,确权会使得他们更快地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就拥有更多除了务农以外的技能,能够获得比务农更高的收入。确权后家庭的农地所有权得到保障,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得到解放,会比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更快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家庭负担重的劳动力,在确权后更倾向于转移到二三产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回报。在村居层面,确权与耕地面积和村居人均年收入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村居的耕地面积越多,本地确权后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户更多,确权带来的效果更显著。在地区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确权对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影响显著。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是东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大,农民产权意识强,这使得东部地区常有土地争端,而且在土地调整或者划分时会出现矛盾,拖延确权的进度。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产权强度较低,确权工作的推行使得农地稳定性增加,农民增加农地投资,促使更多农民参与到农业活动中。
综上,农地确权关系重大,关系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影响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并且关系到现阶段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农地确权对于劳动力转移有双向作用,而我国现今的产权强度仍处于促进农民务农,对促进农民进城务工的作用不明显。在现今用工荒的压力和提升城市化率的目标下,应进一步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