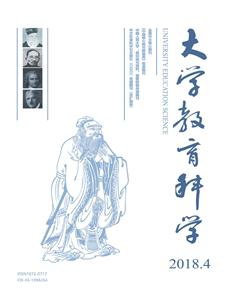家庭德育:为人一生的发展奠基
欧阳鹏 胡弼成
摘要: 民族的道德水平、价值观念,关乎其兴衰荣辱,关乎她每个成员的幸福指数。提升全民素质、解决道德困局最根本的途径即德育。家庭德育,为人一生的发展奠基。制度、价值观念、公共产品与财政支持等构成家庭德育的外部影响因素;家长的素养、儿童成长和家庭德育之客观规律从内部制约家庭德育的实施。威权型、控制型、反面型、暴力型、缺失型家庭德育形态为掣肘家庭德育功能发挥的典型困境。从国家、社区、学校、家庭四个层面搭建家庭德育的立交桥:完善制度和法律资源供给侧改革;保障相关基础设施完备建设和公共产品充足配置;加强家校横向联系,凝聚家校德育力量;调整对家庭德育的认知,规避错误的德育方式,从而为更好地发挥其对人生发展的奠基作用铺设一条康庄大道。
关键词:家庭德育;家庭教育;人生发展;德育误区;儿童成长;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4-0010-08
收稿日期:2018-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城市处境不利者社会流动教育归因及补偿机制研究”(BGA130041)。
作者简介:欧阳鹏(1991-),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法学、公共管理法治化研究。胡弼成(1964-),男,湖南长沙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长沙,410082。
一、德育问题须提上议事日程
一般来说,对受教育者施加关于道德、思想、政治的教育影响即德育,塑造儿童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德育的应有之义。德育的整体意蕴或部分内涵若被忽视,就将对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对学生个体生命之自我成全,产生负面影响。
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价值观念,关乎其兴衰荣辱,关乎她每个成员的幸福指数。但不可思议的是,它总是得不到实质上的应有重视。当我们对新闻报道中的恶性道德事件感到义愤填膺的时候,当我们亲身经历被身边的陌生人甚至熟人欺骗、算计的时候,当我们面临权力的肆意寻租、各行各业工作者只对上负责而不对其服务对象负责的时候,我们总是怒不可遏,继而悲观失望,问一个自己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这个城市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似乎善良总在限制我们的想象力。最后,当我们对这些现象见惯不怪的时候,我们就变得麻木、适应——毕竟生物都有适应环境的本能。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来到一个道德水平较低的地方,当有人恬不知耻地侵犯公众权益的时候,我们发现,竟无人站出来维权,甚至无人吱声。我们惊诧于公众之“一片沉寂”和“无限容忍”背后的原因。其实,久了我们就自然明白:蚍蜉撼大树是无助的、也是无奈的。高风亮节的人往往是孤独且痛苦的。即便他是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真的勇士”,即便他孤立地在“寒风中”站成了一根标杆、一个道德模范,对社会整体而言,他依然只有涓埃之力。不然,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仅靠几个“感动中国人物”或者“全国道德模范”就可以实现了。
于是,这种低劣的道德“常态”,既导致了人们对于丑陋脸孔、肮脏事件的“麻木”,麻木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论恶浊的事件有多需要他们去抗争,或身边的困境人群有多需要他们去救济或援助;又致使了大家对于社会、对于“所有人”的极度“敏感”,敏感到对这个世界极不信任——即便是朋友的善意相待,也要怀疑一下这善意背后是否存在不良的动机和居心。当他活在这样一个既胁迫他“麻木”又敦促他“敏感”的社会之中,他又何来幸福体验?他时刻战战兢兢:生怕该“麻木”的时候“敏感”,该“敏感”的时候“麻木”,两者一旦错位就令其失足成恨。为何文明社会的人可以单纯、真诚到白水鉴心?因为他的赤子之心未曾受过心怀不轨者的伤害、欺骗和染污。他对于社会的“信任值”还没有被摧毁得体无完肤,他轻易就能做到抱朴守真。所以,你别看他一把年纪了,却依然童心未泯,像个不经世故的孩子。
归根结底,道德问题要通过最根本的道德途径即德育来解决。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对道德水准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他在德育中言传身教,以期“大同”。由是,德育实则是一项很古老的人类活动,古老到至少两千多年前就被提及和重视。德育的精义,在《论语》等著作中俯拾即是。然而,为什么在物质文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果层出不穷的时候,现实的道德水平却依旧顿足不前甚至不升反降?观照历史,是不是现在我们对德育抓得还不够到位?这些问题耐人寻味。我们经常提到教育转型,但有时也当思考教育回归的问题,因为“往圣绝学”并未“俱往矣”,就德育而论,它们依然适切地为我们提供着灵感和启发。总之,只有高度重视德育的时代或社会,才可能充分激发稳步前进的内生动力,迎来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契机,创造能愉悦和润泽人心灵的、促进生命成长的、增加生命内涵的道德环境和文化生态。
二、“德”为人之魂,德育须由家庭教育奠基
家庭道德教育是指父母对子女施加的无意识影响或有意识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把一定的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品德[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教育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九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明确指出:“要注重突出家庭道德教育内容”,“家庭教育工作必须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原则”。立德树人,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重,通过正面教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从而达到塑造人、改变人、发展人的目的。“立德”与“树人”从实质上讲不是两个分离的过程,而是人才成长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方面。“德”是人的灵魂,育“德”就是要铸造人的灵魂。
那么,“铸魂”的德育为什么必须由家庭教育奠基?第一,家庭是一个新生命的起点,以父母为主的家庭成员是孩子不可选择的教育者。从生命伊始到接受学校教育之前,儿童接受的教育都由家庭提供。儿童在幼年时期与父母等家庭成员发生着最初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最初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心理特征、行为习惯,将最具深刻性和持久性。这种教育影响的先导性和深刻性会直接导致孩子对后续的其它教育影响具有強力的选择倾向。这就仿若一张白纸,第一次描摹、书写要比后发的添加或修改简单易行且效果鲜明得多。正如墨子所言:“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因此,家庭教育成为人一生所受的全部教育之实然奠基者。第二,这是由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幼儿时期的教育,因教育内容本身具有启蒙和奠基的性质,加上儿童的身心结构特点,使其较其它阶段的教育对人的道德发展意义更为重要、作用更加明显。第三,即使儿童入学以后,同时接受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依然是德育的主要载体:在学校因生师比等不可控条件限制,一个班数十位儿童接受数位甚至一位老师的教育影响;在家庭中,儿童受两个或多个成人的教育影响。第四,相比于学校德育(教育过程有阶段性和暂时性特点、施教者不断改变),家庭德育的效果和影响更具长久性、连续性、深刻性。无论何人,他都将离开学校,告别学校德育,但他永远无法“离开”家庭、“离开”父母,即使另立家庭,即使身在远方,与父母、长辈的感情交流也是永远割舍不断的[2]。第五,家庭德育的权威性(基于儿童对父母的依赖)、易感性(基于亲子血缘关系)、针对性(基于父母对子女“知子莫若父,知女莫如母”之足够了解)、潜隐性(基于亲子朝夕相处过程中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等,都使得家庭德育对儿童道德品质形成与发展产生无出其右的、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在家庭里,长辈们交往过程中的一言一行、父母对于孩子的言传身教、父母为孩子制定的孰可为孰不可为的家规等,都将或多或少内化成孩子的行为本能。许多家庭里都存在一种常态:随着孩子的成长,孩子的言行日趋符合父母的要求,孩子于成长过程中逐渐发现一种规律——一种怎样做能让父母满意,怎样做会让父母蹙额的规律。孩子的年龄越小,无条件接受长辈们的观念就越多——他们年龄太小无从反抗这唯一的教育影响,且他们经验浅薄还不会“曲意逢迎”或者“阳奉阴违”。由是,久而久之,在这种耳濡目染或潜移默化的氛围中,孩子把这种“技能”驾驭得非常娴熟,以至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成为“听话”的“好孩子”,成为父母世界的“附庸”。于此,不讨论这种“常态”之是非功过,本研究旨在说明家庭德育对于教育整体的巨大影响,以及家庭德育对于人终身的品行和观念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中语言的使用习惯对一个人从小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如果儿童在幼年时期接受家庭教育的语言为方言,即便后来学校教育以普通话为载体,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依然终生以方言为内部语言。家庭教育以方言为载体,导致受教育者一生都用方言认知、思考着世界。这个现象凸显了家庭教育对个体的道德品质塑形有着其它教育影响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换言之,语言载体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下面,就是家庭教育可以影响人一生的奠基磐石。
三、家庭德育优劣的主要制约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前,传统的中国家庭教育模式是宗法、家族供给模式:孩子的家庭教育供给主要由家族承担,承担的比例大小由“亲疏关系”决定,此“亲疏关系”如同“将石子投入池塘泛起的一圈圈波纹”[3]。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属于过渡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家庭教育社会化进程加剧,家庭德育虽说仍由家庭供给,但它受到的社会制约显著扩大,父母的德育态度、定位、方向、手段时刻受到外界影响。具体说来,影响家庭德育质量的因素包括内、外两方面:外部影响因素有制度因素、价值观念因素、公共产品与财政支持因素;内部影响因素有家长的素养、儿童成长和家庭德育之客观规律等。外部因素是家庭德育的影响条件,内部因素对家庭德育起决定性作用。
在外部影响因素方面,首先是制度因素。家庭德育受国家教育制度、政策、法律的影响,父母通常根据国家的制度标准和政策导向来供给家庭教育。譬如,当社会人才选拔机制以智育成果考察为中心(追求分数指标、学科成绩)时,对于德育这一很难量化考察其成果的教育,考试制度很少针对性地考核其成效。这导致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德育的忽视:家庭教育以智育的供给及评估为重心,以适应外在的制度环境。许多家长甚至认为,家庭教育即等同于辅导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学生放学回家仅仅是学习地点从学校转移到家里。孩子的节假日,也被父母安排的不计其数的培训班填满,孩子的身心因而得不到良好的劳逸结合。长此以往,儿童的道德发展滞后于学习成绩,“成才观”与“成人观”的矛盾日益凸显,孩子即使“成才”也难以“成人”。又譬如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后,许多家庭由于只能生养一个小孩,父母或祖辈们容易陷入“溺爱孩子”的误区:对孩子的言行无条件纵容、放任、姑息,而培育孩子的道德品质的责任则被束之高阁。
其次是价值观念因素。价值观念因素既有纵向的、世代相传的思想观念、教育态度、长辈期望、家庭文化等意识形态(譬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等级观念、亲疏观念、礼节观念等,且较注重集体主义和社会规范。很多家长深受这些文化传统的濡染,有意或无意地将这类意识形态通过德育传递给其子女);又有横向的、社会的、地域的、行业的、阶层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等。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譬如:书香门第与商业世家、南北地域文化差异显著的家庭,对孩子施加的德育影响可能会有霄壤之别。而父母所在行业或阶层独具的道德操守、思想观念、职业习惯、文化理念等,也将被父母带入家庭,参与家庭德育供给。譬如,父母甚至可能因为同事的只言片语而更改对子女的德育方式。
再次是公共产品与财政支持因素。家庭德育公共产品指的是国家或社会提供的、有益于家庭德育供给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产品。当下,国家对学校教育尤为关注和重视,并為之提供充足的资金投入、持续的财政支持。这成为近年来我国学校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师资建设到基础设施建设等诸方面的进展若火然泉达。然而,社会对家庭教育或家庭德育的关注度却明显不够,更遑论采取具体有效的扶持措施,仿佛家庭教育本是家庭内部事宜,与社会毫无关联,公共产品对家庭教育的输出和参与力度极为有限。其实,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一样,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家庭德育方面,家庭的作用和影响比学校更具深刻性。因家庭德育具有外部性(德育效果优良即具有正外部性,德育质量低劣则具有负外部性)等原因,国家、社会有必要、有责任对家庭教育提供相应的大力支持,如增加财政支持、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力度。由是,社会对家庭德育的支持力度就成为家庭德育的外部影响因素。譬如,社区为年轻父母提供家庭德育“亲子课程”,以提高家庭德育质量;地方政府扩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便更好地为亲子德育服务。
在内部影响因素方面,第一重要的是家长的素养。家长素养差异可导致不同家庭的德育质量相差甚远。父母的成长历程、社会阅历、性格特征等,对其教育孩子的方式有重要影响;父母之间的关系和谐度是父母能否提供适切的德育影响之要因;父母对于德育内涵和重要性的认知,以及父母对于这种认知的一致性,是父母协同提供优质德育影响的关键保障;父母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学历层次,则涉及德育的实施方式,影响德育的传递效果(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更常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关怀和支持,更少地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如虐待、忽视、惩罚等[4]);父母自身的道德水平,则是家庭德育的根本前提。值得一提的是,比起父母的知识文化水平,父母道德水平在德育过程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这是德育和智育的主要差别之一,也即为何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可能培养出心肠歹毒的罪犯,而善良的农妇母亲却培养出怀瑾握瑜的道德楷模。尽管这位农妇母亲在语言上不会妙语连珠,技巧上不能循循善诱,她甚至做不到言必有中,但是她用拙朴的、“肤浅的”方言,用她自己真真切切的、春风化雨的言传身教,让孩子明了:什么是善恶,怎样断是非。她就这样为孩子的心灵涤尘,唤醒了孩子内心的良知。
第二是儿童成长和家庭德育之客观规律。孩子的成长过程存有许多共同的阶段性特征,也即经历全人类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阶段。但共性之中有个性、特性,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发育过程的快缓程度和各阶段的表现特征都不尽相同。在适当的时机提供合适的德育,是德育中至关重要的规律。太超前的、跳跃性的德育,太滞后的、保守的德育,或泛泛而谈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德育,都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譬如,有家长为了所谓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他们提前学习后一阶段的知识,以拔得头筹、抢占先机。殊不知,此举违背了德育的规律,无异于揠苗助长、沙上建塔。长期这样下去,势必导致儿童学习动机丧失、学习兴趣湮灭,良好的品德及积极的心理品质也得不到应有的培养和发展。德育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有其固有的、本原的内在规律,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理解并遵循这些客观规律,结合每个儿童的特点和个性,制定合理的德育计划,是家庭德育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四、目前家庭德育面临的几类困境
困境一:威权型家庭德育。采用威权型德育模式的家庭,或多或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威权型德育中,父母习惯在孩子面前摆“架子”,仿佛他们的言行一贯正确,他们的威严不容挑衅或质疑,孩子只能无条件服从其命令。父母即使有爱要表达,也通常采用不易被孩子感知的方式。他们将对孩子的爱包裹于“威严”的外衣下面,孩子很难穿透这一层外衣去体验本质的父母之爱的温暖。于此种模式,父母一般较多伪装自己,在孩子面前摆出“高姿态”。长期以来,孩子会产生对于父母的畏惧和隔阂,亲子之间本应有的亲切感黯然消沉。这种教育方式无疑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伤害,也在其内心深处种下等级观念的种子。如此,孩子长大以后,一是无法与父母较为亲近:在他们想亲近父母时会觉得不适——往日父母“威权”形态仍历历在目;二是他们对自己的子女也会不由自主地摆出一点“架子”,即便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样不妥,但他们除了这个模式未曾接触过其它模式,且这个模式在他们身心已根深蒂固,他们有些无法抗拒;三是他们在领导面前会表现出“奴性”。由于长期以来对于父母威权的适应和妥协,很难想象,他们在面临领导类似的威权时会有反抗,有批判、创造性的思考。
困境二:控制型家庭德育。控制型家庭德育和威权型家庭德育有异同之处。在控制型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倾向于让儿童遵守既定的规律和准则,约束儿童的思维和行为,阻碍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5]。许多父母习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的身心,一旦孩子违拗其想法,就对孩子采取相应的规训措施。父母以是否“听话”作为孩子优秀与否的评价标准。譬如,许多男孩子由于长期受母亲或祖母“管教”或“控制”,言行非常“听话”,对任何“命令”都执行得很到位,他因此得到长辈们的“好评如潮”。这类孩子共同的、明显的表现特征是:说话老气横秋,7岁的儿童说话的语气、神态、习惯、内容等和30岁的中年人或60岁的老年人如出一辙;遇事唯唯诺诺,犹豫不决,因为他一如既往地只想做符合父母心意的事,竭尽全力地去成全父母的意愿。这个意愿是否正确,他不明白也不计较。长此以往,他的自由意志、果敢、创新等品性因得不到应有锻炼、培养而逐渐泯灭。一言以蔽之,他已成为其父母或祖辈的复制品,不再是他自己。譬如陈忠实先生在其经典作品《白鹿原》里,塑造出一个叫白孝文的人物,就是如上所述的活生生的形象[6]。作者刻画的这一人物性格,在当下许多家庭中司空见惯。控制型家庭德育带来的社会危害层见叠出。研究也表明:在控制型(专制型)家庭德育环境中,青少年有着较高的道德推脱水平[7]。
困境三:反面型家庭德育。若父母自身言行不端、作风不良,则会对孩子的道德品质塑形和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尤其对于学前儿童而言,若父母道德低劣、行为龌龊,孩子将会模仿(且低龄儿童的模仿能力极强),即所谓“上行下效”。有研究发现,父母一般会被视为道德行為的榜样,儿童与父母间的安全依恋体验有可能是道德同一性(道德认同)的重要来源[8]。我们常谓言传身教,很多时候,身教比言传更重要。孩子若经常看到父母酗酒、抽烟、赌博、打骂、吸毒等,他们会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把这类负面行为视为好的、善的。这对孩子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是遗祸无穷的。另外,在面对道德和经济利益的考量时,很多家长选择了后者,给孩子提供了“反面教材”。“隧道效应”形象地说明了家庭教育问题的代际传递,即孩子的问题总是折射出家长身上的问题[9]。
困境四:暴力型家庭德育。父母对孩子的暴力可分为热暴力和冷暴力,热暴力又分为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任一暴力方式对家庭德育都是有害的,都将对孩子的思想观念、政治素质、道德情操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肢体暴力也即“棍棒教育”。有些父母揣着“不打不成才”的观念,一旦他(她)认为孩子“做错了”就打孩子。此时有两种常见的错误典型:一是孩子其实没错。孩子只是出于其纯洁的天性和本能,做出了实质上很美好、泛着真诚和善意的事情,父母却要打他。因为在父母看来,孩子让自己吃亏了、“把好处让给了别人”、“没有占到便宜”等,恼羞成怒就把孩子揍一顿。二是孩子确实做错了。父母在多次口头教育引导失效后,选择使用肢体暴力,但父母在打孩子的时候,非但不挑合适的部位下手,也不顾虑到下手力度,更遑论选择合适的时机。譬如:有父母一发脾气就对着孩子的脑袋拳打脚踢;有名人回忆,小时候在睡觉时被母亲用耳光从梦中扇醒;有父母喜欢当着众人、当着孩子小伙伴的面打孩子。语言暴力又细分为两种,一是父母对孩子说一些肮脏的骂辞,用一些污秽的词句来形容孩子或孩子所行之事,二是父母虽然不用粗鄙词句,但语意同样尖酸刻薄、不堪入耳。父母言谈时肆无忌惮,全不、从不考虑孩子的心态和感受。冷暴力指的是父母长时间对孩子不予理睬,孩子主动和父母沟通,父母仍拒绝与之互动。以上暴力型家庭德育,于某些父母看来,是他们教育孩子的手段和方式。殊不知,这实则是家庭德育的重大忌讳,是对孩子身心的残害。
困境五:缺失型家庭德育。与上述几种家庭德育困境(主要表现为德育方式错误)迥然不同,缺失型家庭德育指的是家庭教育中缺失德育的重要内容和环节。这将给儿童道德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患:道德认知易欠缺,道德品质易弱化,道德行为易失范[10]。缺失型家庭德育主要分为几类情形:第一,重智育轻德育。这与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国家教育制度相关联,父母出于对孩子升学的重要性、紧迫性考虑,在家庭教育中变得“功利”:一心一意只为孩子的考试成绩考虑,与此无关的教育内容全不涉及。事实上,由这种失衡的家庭教育模式导致的对孩子天赋特长的忽视、对孩子兴趣爱好之发掘、培养和引导的缺失,皆会影响到孩子的思想道德发展。德智体美等方面当协同配合、携手共进,任何顾此失彼的教育行为都是荒谬的。第二,上文提及,长辈因陷入“溺爱误区”而将德育束之高阁、不闻不问,同为德育缺失的主要表现。第三,父母之间德育方向不一致或父母与祖辈德育观念有分歧,也会造成德育缺失。譬如,当儿童做出某些缺德举动,父母对其批评教育时,爷爷奶奶却在一旁护着他,甚至一家人常就孩子的德育问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刚刚形成的正面德育影响就会立即被负向德育影响所抵消。第四,离异、再婚家庭、单亲家庭也是缺失型家庭德育的典型。离异、再婚家庭,或因亲子之间存在隔膜与芥蒂,或因血缘亲疏的观念作祟,常使得继父、后母无法或不愿对继子女提供亲子德育。论及单亲家庭,我们先得明白一点,父母由于性别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的德育内容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来自哪一方的德育缺失都会造成整体的德育缺失,即便单亲一方不遗余力地想将它补全也无济于事。第五,留守、流动儿童或“影子爸爸”家庭的德育空缺。在留守、流动儿童家庭,儿童通常面临父母德育“双缺位”。留守儿童失教、拒教、难教,替代养育者教之无力、教之无方、教之无责等是造成新生代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困境的主要因素[11]。在“影子爸爸”家庭,父亲由于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使得他即使想多陪伴孩子,也分身乏术。第六,家庭存在的一些客观困难也会造成德育缺失。这些困难通常属于不可抗力,也即无法根据父母的主观意愿而改变。譬如,家庭的经济状况就直接影响到家庭德育的实施效果;父母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也制约着德育的输出效果。很多父母尽管渴望带给孩子优质的家庭德育,也致力于把孩子培育成道德情操高尚之人,但碍于文化修养的限制,他们无力供给精彩的德育内容,也无从驾驭高超的德育技巧。
五、搭建家庭德育立交桥,支撑起人生发展的康庄大道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家庭德育是人生成长的第一课,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基础,对人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之影响如电照风行,在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中、在社会风气和社会文明的形成发展中都具有强本铸魂的奠基作用[12]。本文将从国家、社区、学校、家庭四个层面和维度展开分析,搭建起家庭德育的立交桥,为人生发展铺设一条康庄大道。
其一,国家层面:完善制度和法律资源供给侧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与家庭德育相关的制度、政策、法律资源无疑是匮乏的,国家的绝大部分教育制度都立足于学校教育。在分析、明确家庭德育对学生身心发展之关键作用、对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文明建设进程的重要影响后,国家有关机构和部门需要加强、加大、加快相关资源供给,改善供给方式和措施。推进家庭德育相关制度资源供给侧改革,需处理好扩大有效供给与提高供给品质、清理无效供给与激发合理需求、理顺结构调整的目的与供给侧改革的手段、拓宽供给渠道与优化多元治理等基本关系。通过改善结构、制度层面的有效供给,破解教育结构失衡、供需错配的困局[13]。国家需要为家庭德育建设提供充足、合理的制度资源保障,并在宏观的制度框架下完善相关的、具体的配套措施,激发我国家庭德育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同时清除其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和路障。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家庭模式面临解构,只受家族或宗法制度、观念约束而“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家庭德育形态已不复存在,尤其在当下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网络文化广泛普及的大数据(信息)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时代,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德育势必紧跟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步伐和趋势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型。由是,国家在宏观上、外部采取实质上的举措,凸显、强调家庭德育的重要性,引導家庭做好本分和本职的德育工作,当为振裘持领之事。另外,对于经济状况陷入贫困的地区或家庭,国家有必要对其实施精准的德育扶贫。教育扶贫直指导致贫困的根源,因而作用也更为持久。推进扶贫模式转型,实施精准扶贫,迫切需要针对致贫原因构建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14]。
其二,社区层面:保障相关基础设施完备建设和公共产品充足配置。
“社区”一词的定义很多,不同研究者对该词的定义不尽相同。本文所指的“社区”是由若干聚集在一定领域里的、生活上相互关联的社会群众或组织组成的集体。譬如,就农村来说,“社区”可以是一个村、一个组等;就城市而言,“社区”可以是街道办事处下辖的自治单位,或一个小区、一个企事业单位的家属院等。社区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则是由社区居民自主选举产生的、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的基层自治组织。居民每天在社区中生活、参与社交活动,与社区中的人交往最密切。在这种密切的互动中,社区成员接受社区向其传递的意识形态,并在利用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时受到教育和启发。社区对父母的影响将被带到家庭德育之中。相比于父母在网上、文献、电视中接受的教育影响,社区的影响往往因其更真实、更贴近生活、更频繁再现而显现出对家庭德育更直接、更深刻、更持久的作用。譬如,父母可能因为邻家小孩表现优秀而效仿邻家父母的德育方式。既然社区影响对家庭德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社区视域探讨有效应对措施就刻不容缓。
与家庭德育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多式多样,总体上可分为软件和硬件两大类。于社区层面提供相关保障措施可从这两个方面切入和着力。软件方面,当从父母的、关于德育的思想态度、认知结构、方式技巧等方位着手,来提高其家庭德育水平。譬如,开展“家庭德育借力社区”活动对年轻父母进行相关培训,或在社区公告栏等地方进行广泛的德育宣传,普及家庭德育文化。硬件方面,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设施建设来提高德育质量。譬如,在社区中建设以德育为主题的“亲子乐园”,或对良好的道德行为进行激励性嘉奖。与家庭德育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配置,可由“社区居委会”等负责决策、计划、筹资、组织和执行。地方政府应对此予以大力提倡和鼓励,并积极提供资金支持。
其三,学校层面:加强家校横向联系,凝聚家校德育力量。
家庭德育并非由家庭在閉关自守中完成,它需要与学校德育携手同行、共谋发展。家庭德育和学校德育是儿童道德品质、思想观念塑形与发展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家庭和学校紧密结合、相与为一,是应有之义。加强家校联手共育,可拓宽道德教育途径,有益于培养、强化与巩固儿童的优良道德品质。家庭具备更深入、全面地洞见孩子个性的天然条件,能驾轻就熟地实现因材施教;学校则通过有效利用集体环境对于个体生命成长固有的促进作用,依托课堂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实现与家庭德育优势互补、协同配合。然而,目前我国家校合作共育处境尴尬,存在目标定位偏狭、组织运作不力和教育影响失调等诸多弊端,弱化了育人成效,其对未成年人道德健康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15]。因此,重构家校联手共育机制、打通家校合作培养渠道,为燃眉之急。家庭当做好子女的道德启蒙工作,完成从德育的被动“旁观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观念转型,充分发挥家庭德育对人的一生发展的奠基作用。学校应明确家庭对儿童德育的意义和分量,采取积极措施取得家长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敦促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联手共育过程中来。家校当构建具体可行的协作途径和制度,如家长委员会、学校开放日、家长座谈会、教师家访等,及时共享信息,搭建家庭德育与学校德育的桥梁,凝聚家校共育的力量,充分保障教育影响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可持续性,使家校德育相得益彰。
其四,家庭层面:调整对家庭德育的认知,规避错误的德育方式。
如果上述优化路径都是针对外部影响因素的话,父母自身德育素养的提高就是内在的、根本的方面。父母应立足于以下几方面来调整、改善对家庭德育的认知,规避错误的德育方式:第一,充分认识德育的内涵及其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父母理当意识到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是个体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多的是“生活的”而非“知识的”,是养成的而非说教的,优质的德育可以使生活更加美好,使人生更具意义。而只有根植于生活世界,德育才能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离开了生活,道德就成了空虚的原则[16]。因此,德育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德育的缺失也会造成生命的缺憾。第二,父母应关注孩子德、智、体、美等均衡发展、全面进步,而非只重视智育。各方面素质本就相互促进,任何偏废都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充分发挥其它方面教育因素对德育的协同、促进作用,无论对于德育还是其它教育之效果保障都至关重要。第三,引导孩子自主思考、自主行动,而非控制孩子、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身心。对教育尤其是家庭德育而言,“教是为了不教”,“不教”不仅是作为“教”的结果,而且是内在地寓于当下教的实践之中,辩证地统一在“当下之教”的过程之中。换言之,堪称优秀的家长在任何时候,欲将自己的影响加之于孩子身上之时,都应该有一种将自己的影响从孩子生命世界之中抽离出来的倾向,以此来保持孩子个体精神发展的真正的独立性,而不应该让孩子的发展成为家长威权下的强迫性实践。堪称卓越的家长,在以自身影响进入孩子世界的同时,又显现出另一种倾向,即向着孩子世界的远离,由此而让孩子成为其自我,让孩子自主自立,而不是作为家长影响的延伸[17]。
参考文献
[1] 苏振芳.道德教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
[2] 周先进.家庭德育环境的主要特征及优化思路研究[J].理论界,2007(12):171-173.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4.
[4] 李燕,肖博文.父母的人格、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J].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206-211.
[5] 王挺,肖三蓉,徐光兴.人格特质、家庭环境对中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1(3):664-669.
[6] 陈忠实.白鹿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7] 刘国雄,陆婷.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及其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J].中国特殊教育,2013(4):40-42.
[8] 曾晓强.国外道德认同研究进展[J].心理研究,2011(4):20-25.
[9] 李积鹏,韩仁生.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及家庭德育策略[J].现代教育科学,2017(08):103-109.
[10] 王露璐,李明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6):41-44.
[11] 段乔雨.新生代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困境及其突围[J].现代教育科学,2017(12):24-29.
[12] 翟博.树立新时代的家庭教育价值观[J].教育研究,2016,37(03):92-98.
[13] 周海涛,朱玉成.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几个关系[J].教育研究,2016,37(12):30-34.
[14] 孟照海.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J].教育研究,2016(11):47-53.
[15] 冯永刚.儿童道德教育中家校合作偏失及其匡正[J].中国教育学刊,2011(09):83-86.
[16] 李大健.生活化:高校人本性德育的真谛[J].教育研究,2008(09):76-79+92.
[17] 刘铁芳,颜桂花.教师:活在师生关系之中[J].大学教育科学,2015(03):76-81.